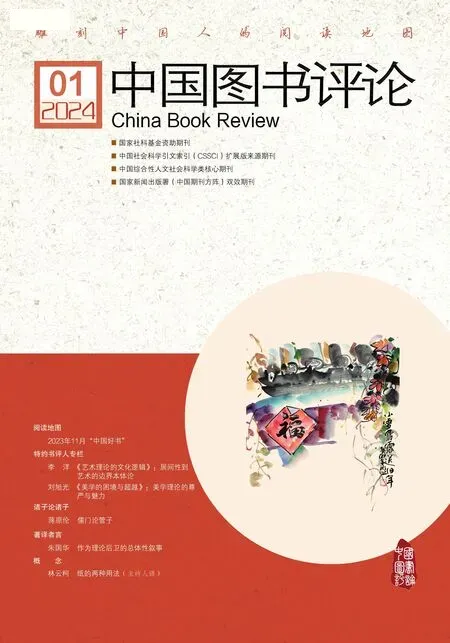从 “文学讲稿” 到 “诗学专论”
——读 《读与被读》
□凌建侯
【导 读】 刘文飞新著《读与被读: 世界文学名著十一讲》 是一本外国文学通识课讲稿, 与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同属一类, 不只会对听课者产生语文方面的积极影响, 还会在学生们心中播下“文学用美的形式唤起我们心底的善” 的种子。 批评的激情与理论的“冰冷” 能否兼备? 本文重点分析该书中隐含的“作家文论” 元素, 指出整个讲稿具有一个潜在的贯通性理论命题—— “人身上的悖论”, 如果把《读与被读》 的副标题换成“世界文学经典人物形象的悖论”, 它就会成为有关人物塑造的诗学专论。 本文作者切盼外国文学研究者用作家笔触丰满理论身躯, 这类作家文论早该成为“理论化” “理论主义” 之后现代文论的另一种样态, 也切盼俄国文学研究者在诠释经典的过程中, 有意识地用作家文论引导年轻学者重视理论思维, 以此为中国文艺理论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刘文飞教授又出了一本新书。这次不是译著和专著, 而是一种新的文体。 他把给首都师范大学本科生上外国文学通识课的讲稿辑为《读与被读: 世界文学名著十一讲》,因此这本书既是文集, 又有教材的功效。 可从篇目及内容看, 比论文集浅显易懂, 又没有一般教科书的“八股气”。 生动活泼、 金句迭出的文风恰像他发表在《人民文学》 上的散文《纳博科夫与蝴蝶》, 但似是有意为之, 读者明显感觉到从“文学性” 往学术性收紧的痕迹。 说它是文学批评, 激情却内敛至极, 像极了洛特曼讨论普希金与法国文化关系的学术随笔: 平和的语气, 沉稳的节奏, 信手拈来的比较, 触类旁通的知识, 还有对细微处的着意等, 都是它们的共性。 当然, 苏联学者的随笔偏重考据, 缺乏素质教育的博雅宗旨。 称此书为作品赏析也颇为不当, 因为少了一份灵光乍现的即兴感触, 多了一种重读经典后的深思熟虑。 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如书名副标题所示将它界定为讲稿, 但讲稿种类繁多, 即便是名师讲课稿,也会因为学科、 专业与主讲人个性的不同, 在语体或文体上千差万别。
只要读过作家的关于文学的讲稿, 我们就会惊喜地发现《读与被读》 和它们同属一类。 比较而言,它更接近学者型作家的讲稿, 表达审美感悟, 客观缜密的思维压倒自我沉浸式的恣意发挥, 从这个意义上说, 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是其范例。 不过, 与 《俄罗斯文学讲稿》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喜和对高尔基的抨击不同, 刘教授选用的十种作品与一个作家, 从荷马、 但丁、莎士比亚、 塞万提斯、 歌德、 雨果、托尔斯泰到乔伊斯、 川端康成、 纳博科夫的代表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历经重重考验, 是世界文学史上经典中的经典, 加上他本人待人温和、 圆润, 没有沙俄贵族刻在骨子里的那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阐释的又非中国文学经典, 拥有持第三方立场的便利, 因此字里行间隐藏溢美之情就不足为奇了。 刘书为它们各配一个主题, 避开了寻常文学史的面面俱到, 还强化了经典作品之特色的“标签化”, 如荷马史诗的悲悯情感, 神圣与喜剧的矛盾结合,哈姆雷特的双重性格, 堂吉诃德的“笑”, 梅菲斯特的两次约定, 作为建筑的巴黎圣母院,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细节, 现代派小说开山之作中的意识流, 《雪国》 的死亡隐喻, 粉色、 黄色、 深色、 灰色、 金色集于一身的《洛丽塔》, 涉及文学的情感与美育, 还有宗教、 哲学、 建筑、 死亡等主题, 以及心理、 诙谐、 细节、 雅俗等诗学问题。 文飞先生犹如现实主义漫画家, 给每一部经典作了一幅画, 突出它们或公认的或他心目中特有的鲜明特征。 课堂里的数百学生多年后定会遗忘许多东西, 却很可能还记得漫画上的凸显部分, 如“无情英雄若有情” “但丁的矛盾修饰法”“双重人格的影响” “《魔侠传》 的笑” “人身上的浮士德” “石头的交响乐” “落地的一粒麦子” “卡列宁的大耳朵” “乔伊斯的狂傲” “死是美的极致” “性的色彩” 等。 同学们记得更牢的, 也许会是讲课人与纳博科夫一样, 下足了新批评意义上的细读功夫。 这种阅读方法在“二战” 后曾风靡西欧与北美高校。
20 世纪40 年代末至50 年代, 纳博科夫执教于康奈尔大学, 为本科生开设文学通识课时, 采用的就是细读法。 他的讲课影响了许多选课生的职业生涯。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 她在一次访谈中回忆道:
我对写作的关注, 归功于曾经的两位老师, 不是在法学院, 而是在康奈尔大学本科时的老师。 一个教欧洲文学。 他的名字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他热爱语言的声音,教我选择正确的单词并以正确的词序表达的重要性。 他改变了我的读书方式、 写作方式。 他对我有巨大的影响力……直到今天, 我还能回想纳博科夫说的一些话。 《荒凉山庄》 是我们在他的课上读过的其中一本书。 在第一堂课上, 他大声地朗读了这本书的开头几页, 描述的是大法官法庭的位置及其浓浓的说服氛围。[1]
文学课对选课者的帮助之大的确超乎想象。 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 里讲解西欧7 位名家的7 种名著, 第二部作品就是查尔斯·狄更斯的《荒凉山庄》, 可见金斯伯格的记忆并未出错。 老师用文本细读激发同学们的听课热情, 令他们终身受益。 中外古人早已认识到文学的通识性。 所谓的“三科” (trivium, 文法、 修辞、 逻辑) 与“四学” (quadrivium, 算术、 几何、 天文、 音乐),被统称为“七艺”, 是欧洲古代学校的7 门课程, 现已演变为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重要内容, 涉及语言、 文学、 艺术、 历史、 哲学、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 以培养宽广的知识视野与良好的表达(写作) 能力为核心目标。 中国的“四书” “五经” “六艺” 是古代培养士人的科目, 学生要学会读书与作文, 还要学会礼、 乐、 射、 御、 书、 数六种技能, “学而优则仕”, 谁学得好就选谁当领导。 西方的三科与中国的读写相当于现代语文教育, 核心对象正是世界文化的宝库——文学经典。 金斯伯格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 现任大法官只有九位,去世一位才递补一位。 能和纳博科夫扯上师生关系, 这样的人在旁人眼中必定是实力派人物, 尽管1958年《洛丽塔》 在美国出版前纳博科夫还在为生计到处奔波, 康奈尔大学的任教也出于谋生之需。 当然,大师在新大陆成名之前在旧大陆已经是大师了。 他的讲稿从一个侧面说明, 大师亲授文学通识课的重要意义。 《读与被读》 会产生什么效应? 现在谈论这个问题为时尚早,因为听课者还未毕业。 但不难想见,数百学生中许多人都会受大师课堂(master-class) 的启发甚至激励。 这种影响有时候是立竿见影的, 有时候是潜移默化的, 有时候是平静悠远的, 有时候是突然触发的。 爆发力与持久力究竟有多大, 除了经典本身是否贴合听者的气质和喜好外,授课者如何释读经典, 甚至他的个人魅力, 都会发挥关键作用。
作家的文学讲稿, 如果只限于产生语文方面的积极影响, 如果仅以传授知识为宗旨, 如果单纯教授写作技巧, 那么作用无疑会受到很大束缚。 《读与被读》 读来让人欣喜, 在于作者一讲接着一讲不断地向同学们强化如何发现文学的“美”, 或者说文学经典在审美上的伟大, 还在于把文学的情感教育融入对“美” 的发现中, 因为“文学用美的形式唤起我们心底的善”[2]。关于文学的美育功能和情感教育功能自古就有很多论述, 所不同者只在材料选用上, 多数论者使用一个民族的甚至一个时代的作品, 或某个区域的或某种语言的作品, 《读与被读》 则解读了从古至今11 位外国经典作家。 鉴于刘教授的俄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学术背景, 他的这种选择, 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世界文学通识教育在19 世纪中期的沙俄高校积极推广、 在20 世纪的苏联蓬勃发展的影响, 也和20—21 世纪之交世界文学研究在北美高校的小规模复兴不无关系。
讲解世界文学经典, 其实赋予了讲者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对文学进行理论思考的机会。 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批评, 无论是中国文学批评还是外国文学批评, 都不缺新颖锐利的观点, 缺的是成体系的学说。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中国学派提倡多年, 始终未见起色, 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一整套理论学说。 作为外国文学的一个分支, 俄国文学的中国阐释能否形成中国学派? 又怎么形成? 这是刘文飞先生率先着手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格局: 俄罗斯文学史、 俄罗斯文学批评、 俄罗斯文学理论。 但它们的发展并不平衡, 从成果数量和从业者人数考察, 文学批评一枝独秀, 文学史不敢落后,文学理论屈居末位。 与前两者相比,理论艰涩、 枯燥, 在很多人眼中甚至显得“无趣”。 批评的激情与理论的“冰冷” 能否兼备? 阅读《读与被读》, 我们发现, 作者像纳博科夫一样, 在文学讲稿中隐含“作家文论”[3]的一面。 中国人讲文论, 通常把它当作文学理论的简称。 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这门艺术的具有体系性的理论思考, 这个概念本身并非自古就有, 而是19 世纪欧洲科学化浪潮催生的现代学科分化的产物,其源头是古希腊的诗学, 即关于“诗” (现在称为文学) 的理论学说。 所以, 我们可以把作家文论看作是作家关于文学的理论思考。 其与现代文论的最重要区别在于: 一是作家用特有的生动形象的话语讨论理论问题; 二是各种理论观点相当分散, 碎片化倾向非常严重。 当然也有例外, 如俄罗斯象征派诗人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 他长期追随尼采, 倾心于关于酒神与日神关系的学说, 1912 年在罗马完成了有关“狄奥尼索斯宗教” 问题的研究,1921 年在巴库大学通过了以狄奥尼索斯为题的语文学博士论文, “1923年增补了四章的博士论文出版, 题名《狄奥尼索斯与原始酒神精神》 ”[4]。 这部专著是伊凡诺夫多年思考艺术问题的集大成者, 对弗雷登伯格的《体裁与情节诗学》、 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家在文学理论领域同样能大有可为, 尤其是学者型作家。 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 讲的虽然都是经典作家作品, 但我们到处都能体会到带有他体温的文论思想, 即便是被现代理论家发明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术语, 如结构、 游戏、 戏仿、 隐喻等, 出自他之口, 也会带上一抹温情。 《读与被读》 同样如此。 刘文飞用细读法巧妙阐述 《伊利亚特》《奥德赛》, 举例分析荷马的悲悯情怀以哪些方式流露出来。 比如, 年迈的普里阿摩斯潜入敌营, 向铁石心肠的阿基琉斯提出归还爱子遗体的请求。 不难想象, 讲课人带着何种情感向学生们朗读老人说服敌营统帅的诗行, 连坚硬如钢的心都能软化, 听者为之震撼、 为之动容、为之沉思, 完全是意料中的事。 更能引起同学们沉思的则是布罗茨基的著名公式 “美学即伦理学之母”[5], 这一讲的最主要目的正是用荷马史诗来证明这个理论观点。
荷马的悲悯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世界观, 每一位作家都是天生的人道主义者, 都是在 “杀富济贫”, 他们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解构强者, 同情弱者, 或者说书写卑贱者的崇高和崇高者的卑贱, 世界文学史中几乎没有一位作家是靠颂扬权贵、 鼓吹杀戮而成名的, 相反, 对人类苦难的感同身受, 对任何一个具体人的具体不幸的深切同情, 是每一位伟大作家展开创作的伦理前提。 荷马的悲悯更是一种美学立场,文学毕竟不同于客观冷静的历史叙事, 不以真实和合理为目的, 文学更不是军事学或经济学, 不以不择手段的胜利或利益为唯一和最终诉求, 文学只不过是一种情感教育手段, 意在发掘、 展示并培养人类的高尚感情。[5]19
没有冰冷的语气, 无须体系化的建构, 只消用自己的体温温暖所论的对象, 悲悯和人道主义也好,道德与崇高也罢, 或者更具理论色彩的表述——美学与伦理学, 它们之间的关系便温情脉脉地显现了出来。 许多作家都喜欢采用类似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文论思想, 比如, 埃科在《论文学的几项功能》 演讲中,通过分析塞万提斯、 但丁、 司汤达、托尔斯泰、 雨果、 爱伦·坡、 乔伊斯、 曼佐尼、 麦尔维尔等经典作家作品, 阐述文学的功能, 没有干巴巴的术语堆砌, 亦无冰冷晦涩的逻辑推演, 一切都像讲故事, 娓娓道来, 最终做出“教导我们认识命运、了解死亡正是文学众多主要功能中的一项”[6]这个结论。
第二讲《〈神曲〉: 神圣的戏剧》解决了一个困扰读者已久的问题:但丁宣扬基督教信仰的这部作品为何成就了他的不朽美名? 这个问题貌似与理论无关, 却透露出种种玄机。 作者通过对《神曲》 的文本细读与分析, 阐明了但丁除宗教动机之外还有政治、 知识、 爱情与艺术动机, 作品蕴含字面、 讽喻、 道德、神秘等多重意义, 尤其是在宣扬基督教信仰的绝对价值时还在弘扬人的自由意志, 以及由此引发的人身上的悖论, 如歌颂现实生活的快乐和美同时将其视为彼岸世界的准备,人具有理性却甘愿接受上帝的审判,颂扬灵魂却思考其与肉体的关系,立足世俗社会而对教会提出质问,坚信上帝是绝对真理却“坚守诗人的认知使命和情感权利, 佐证诗歌所具有的某种可以等同于上帝的臻于真善美的能力”[5]42等。 这些悖论是对“神圣的喜剧” 的最好诠释,因为神的剧本和人的剧本矛盾地合而为一, 却打破了中世纪静止、 垂直、 脱离现实生活的形象体系, 揭开了其等级世界形象崩塌的序幕。无怪乎恩格斯在1893 年为《共产党宣言》 意大利语版写的序言中把但丁视为 “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7]。刘文飞用温煦的话语说明上述悖论使但丁 “在文学中变得更为深刻”[5]42。 不妨拿巴赫金的纯理论分析做一比照:
但丁的世界十分复杂。 他的特殊艺术力量表现在其创作世界中的所有形象都充满各种倾向特别紧张的对抗。 与垂直向上的强烈愿望相抗衡的, 是形象从其中挣脱出来向现实空间和历史时间的水平方向冲刺的同样强烈的愿望, 摆脱等级规范和中世纪评价约束以考虑和决定自己命运的愿望。 由此而产生了这一均势难以置信的紧张性, 而作者的非凡艺术力量已把自己的世界带到这个均势中来了。[8]
即便李兆林先生的上述译文与俄文原著相比并无 “语义上的损失”, 却因巴赫金的理论表述本来就很艰涩难懂, 中国读者读起来也会感到“疲惫不堪”。 读者若非为了专门研究理论, 断不愿去碰这样的著作, 而更愿意去读带有论者体温的文字。 人身上的种种悖论, “正负”两极势均力敌的矛盾, 被讲课人充满情感地叙述出来, 最终证明“最好的经书可能具有文学性, 但最好的文学作品却很少是经书”[5]42。 《神曲》 用文学性悄然远离“经书” 时代而进入追求现实与历史的新时代,因此成就了自己的伟大。 用《神曲》阐发“经书和诗” “宗教和文学” 的关系, 是主讲人的最明智之举。
第三讲 《哈姆雷特和双重人》与第五讲《浮士德与梅菲斯特》 虽然在主题上各有各的特色, 但是在理论上具有内在的“互文性”。 如果说哈姆雷特是“双重人” 这一伟大形象的开端, “每一位主人公” 或多或少 “都是其作者的自画像”[5]60,那么“弥留之际的歌德不仅再次遇见了梅菲斯特, 他还再次成了浮士德”[5]98。 有内在“互文性” 的还有第四讲《〈堂吉诃德〉 与笑文学》 与第七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 但这里的“互文” 需要读者自行补足知识, 这对普通大学生来说有点难度。 塞万提斯的代表作与《巨人传》 一样, 根据巴赫金的理论, 来源于民间节日文化(民间狂欢节文化或民间笑文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 就体裁渊源而言,同样来自民间笑文化, 只是主讲人专门讲解的是“思想小说” 这个方面(巴赫金把恩格尔哈特的思想小说化为复调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英美斯拉夫学者看来, 巴赫金的专著促进了西方陀学的更新, 在心理学、 宗教学、 社会学和哲学等传统视角清单中开始加入巴赫金意义上的诗学视角, 从此陀翁研究再无法绕开巴赫金。[9]从这个角度看,只要多少了解陀学现状的人, 在读了第四讲后再读第七讲时, 自然会脑补陀翁小说的民间笑文化来源。第六讲《〈巴黎圣母院〉 与建筑》 讨论单个作品中的特定建筑主题, 却涉及多种重要理论命题, 如文学与绘画的关系, 巴黎圣母院时空背景下其同名小说的历史诗学意义, 建筑与文学的通感问题等。 不难猜想,触发刘文飞选择此题目的两个外在动因, 一是跨艺术媒介研究的盛行,二是2019 年4 月15 日巴黎圣母院大火致使其损毁严重, 法国政府向全球发起募捐, 用来修复这座因文学享誉世界的著名建筑, 与此同时,火灾客观上也使这部小说再次“火”起来。 正如主讲人所说: “一座建筑成就了一部小说, 反过来, 这部小说又拯救了这座建筑。”[5]120讲到《〈安娜·卡列尼娜〉 中的细节》 时,作者的一句话, “没有细节就没有叙事, 没有细节就没有小说”[5]171, 不但言明了细节的功能与意义, 而且其浓缩性会给听者造成振聋发聩的效果。 细节描写既是诗学问题, 也是创作论问题。 托尔斯泰的细节描写在国际学术界一直是个常谈常新的话题。 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 具有内外双重现代性, 形式上的现代性即意识流主内, 内容上的现代性即“突破政治、 社会、 艺术等方面的严格规范”[5]199的 “世界性” 则主外, 两者珠联璧合, 相得益彰, 但是也给读者 “提出挑战,它要求一种阅读的现代性或曰具有现代性的阅读”[5]200。 刘文飞没有采用时髦的主题学术语阐释川端康成的死亡主题, 却把主题学方法运用得炉火纯青, 《雪国》 中的死亡既是字面意义上的真实死亡, 也是隐喻的死亡, 这里的主题变奏包含徒劳、虚无、 缥缈和超然等, 其基础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物哀与佛教中的轮回。 与前面十讲相比, 《〈洛丽塔〉的颜色》 并非单纯的情感、 人物形象、 文学体裁、 修辞学、 主题学、文学建筑学等研究, 而是采用“蒙田散文” 的笔法, 内容随“阅读目光” 的变换呈现出色彩斑斓的多样性, 讲稿前半部分提出并分析小说与情色的关系, 后半部分用深色、灰色、 金色光谱照见未被发现的《洛丽塔》, 其中不乏诗学研究的一些重要论题, 如悬疑小说、 汽车旅馆(motel) 文学、 艺术语调等, 尽管讲稿中没有使用这些理论术语。
刘文飞的讲稿共有十一讲, 讲讲都特点鲜明。 然而, 除了《〈巴黎圣母院〉 与建筑》 《〈安娜·卡列尼娜〉 中的细节》 《〈雪国〉 的死亡主题》 之外, 其他八讲存在一个贯通性的理论命题, 这就是“人身上的悖论”, 或者人物形象的矛盾性格。在世界文学史上不乏以单一性格著称的人物, 如夏洛克、 阿尔巴贡和《死魂灵》 里的五个地主等, 但更多的人物, 性格并不单一。 从人物价值取向的角度看, 卡西莫多、 安娜、岛村的形象同样复杂、 矛盾。 如果把他们的性格也作为分析的对象,《读与被读》 的副标题“世界文学名著十一讲” 就可改为“世界文学经典人物形象的悖论”, 这部讲稿也就成了有关人物塑造的诗学专论。 19世纪后期以来, 俄国学者开启了欧洲古典诗学现代转型的帷幕, 发展至今, 诗学范畴得到了厘定。[10]作为研究文学表现手段体系的学问,诗学既可等同于文学理论, 亦可被看作是文学理论的一个部门, 主要研究文学类型与体裁、 流派与思潮、风格与方法、 形象与结构的特殊性,考察艺术整体的内部联系及其不同层面的相关性。 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人物形象, 以“性格悖论” 为线索,便可构成纵跃古今、 横跨东西的专题画廊。 当然, 这不会是一部冷冰冰的著作, 而是带有作者体温的和煦的理论读物。 用作家笔触丰满理论身躯, 这类作家文论应该成为“理论化” “理论主义”[11]之后现代文论的另一种样态。
虽然文学理论不可避免会追求“冰冷的” 科学性, 但是我们可以期待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研究者带着自己的温情系统阐发理论命题, 甚至建构理论体系, 这既能活跃“呆板的” 学术气氛, 也能给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带来意想不到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