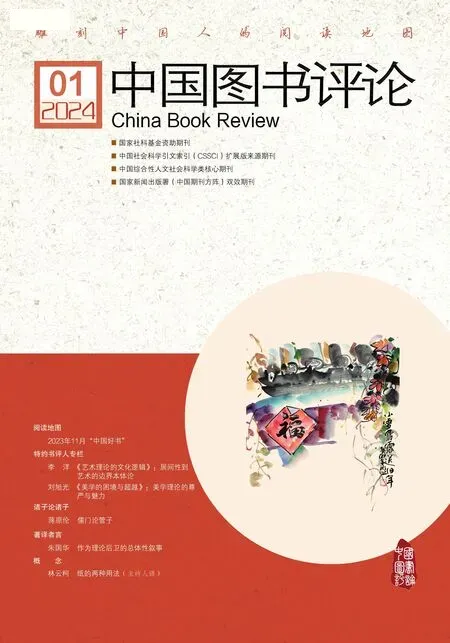“行动—影像” 与好莱坞类型电影
□周厚翼
【导 读】 德勒兹的“行动—影像” 诠释了20 世纪美国好莱坞类型电影里“情境”与“行动” 之间的二元生成机制。 “行动—影像” 理论将好莱坞电影类型转码为相关的结构性形式, 从哲学层面把握了类型电影的构成与运作规律。
“行动—影像” (L’image-action)是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 在《电影1: 运动—影像》(Cinéma1,L’Image-mouvement, 1983)一书中提出的关键概念。 通过勾勒德勒兹在《电影1: 运动—影像》 以“行动—影像” 的固有结构对好莱坞类型电影的诠释思路, 或可见出德勒兹视域中“行动” (A:action) 与“情境” (S:situation)、 “电影” 与“哲学” 的内在张力, 从哲学层面理解20 世纪美国传统好莱坞类型电影的构成形式与运作规律。
一、 定义“行动—影像”——德勒兹的问题域与锚点
在《电影1: 运动—影像》 开篇, 德勒兹即指出: “一个事物的本质从来不会在一开始就显现出来,而是在中间(Mais au Milieu), 在其发展过程中, 在当它的力量得到保证时。”[1]11这一 “中间” 在德勒兹哲学里表现为 “Becoming” 指代的“生成” (Le devenir)[2]状态, 这一状态被德勒兹用连字符“—” 体现出来。 德勒兹以“—” 连接“运动”与“影像”, 而非用“运动” 修饰影像(“运动—影像” 不是“运动的影像”), 旨在强调 “运动” 与 “影像” 间的互动关联: 并非揭示“运动” 与“影像” 二者互动的结果,而是关注二者如何互动, 如何生成。作为“运动—影像” 所存在三种变体(Variétés)[3]之一的“行动—影像” 亦是如此。 “行动—影像” 这一关键词亦置身于 “Becoming” 的问题域, 旨在揭示“行动” 与“影像”之间存在的动态联系。 参考英国经验主义(Empiricism) 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 的影像观, “行动—影像” 直接指向了“二战” 前以美国为中心的传统类型电影所呈现出的“情境” 与“行动” 之间内在的二元“生成” 结构。 “行动” 与“影像” 如何在一种动态的关系中相互“生成”? ——这是德勒兹尝试回应的核心问题。
在《电影1: 运动—影像》 中,德勒兹反讽、 揶揄地定义道: “行动—影像”, 即好莱坞式的“现实主义” (Réalisme) 电影。 或可从以下几方面对德勒兹所谓的“现实主义”电影(“行动—影像”) 的所属范畴做一个界定。 时间阶段上, 参考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 和克里斯汀·汤普森(Kristin Thompson)所著的《世界电影史》 (FilmHistory:AnIntroduction, 1994), “行动—影像” 所探讨的美国好莱坞类型电影应集中在1930 年左右好莱坞制片厂制度逐步完善, 到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Le Néo-réalisme) 和“新浪潮” (La Nouvelle Vague) 电影产生之前的这段时期[4]; 如果一定要给出确切的分期, 这一讨论主要涵盖三个阶段: 美国电影初创时期(1895—1929)、 经典好莱坞时期(1930—1945)、 经典好莱坞后期(1945—1965)。 但实际上, 德勒兹并未给 “行动—影像” 框定某个封闭的时空范畴, 或可将“一战” 与“二战” 作为德勒兹所谓的好莱坞类型电影的转折点, 但是, 它们只是一个暧昧的时间节点。 此外, 在空间意义上, “行动—影像” 的范畴也并不严格局限为美国(德勒兹也提到了大量给美国好莱坞制片体系带来影响的欧洲电影、 苏联电影、 日本电影等), 它所涵盖的是一种大写的“美国” 观念。 在电影工业意义上, “行动—影像” 主要指称的是好莱坞制造的电影, 并且集中于宣传美国中心主义的某种“主流” 院线电影, 可以理解为常识意义上的“经典好莱坞电影”。
德勒兹以“现实主义” 定义好莱坞类型片有其合理性, 因为“行动—影像” 所涉及的影片内容与美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题材大致重合;好莱坞类型片确实反映了美国的现实, 见出了好莱坞的历史观念和美国的意识形态, 这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 但是, 德勒兹本意并非如此, “现实主义” 并非他真正要去关注的内容, 而只是他的一个语词游戏。 好莱坞类型电影被德勒兹以揶揄的态度归为一个“容易界定的领域”[1]196, 因为其大众性往往也与便利性和通俗性密切相关。 “现实主义” 的构成模式在德勒兹眼中是十分简单且刻板的: “环境” (营造的幻觉) + “行为” (表现的行为) →“行动—影像” (“环境” 与“行为” 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有变式)。德勒兹断言: 美国电影的模式均无法逃离行动—影像的变式, “这也是美国电影称霸全球的秘密”[1]226。 并且, 这一“现实主义” 的揶揄是相对于“新现实主义” 提出的, 这也为他在《电影1: 运动—影像》 末章以及《电影2: 时间—影像》 (Cinéma2,L’image-temps, 1985) 的第一章里分析“新现实主义” 电影如何超越“运动—影像” 埋下了伏笔。
“行动—影像” 最重要的特征在于“结构性”, 即“行动—影像” 所指向的电影应该具有特定的“Genre”(“类型”, 亦可译为 “流派”)。[5]在电影中, “类型” 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可指代电影制作中不同领域囊括的范畴, 如历史片、 动作片、 喜剧片、 悬疑片等。 属于一种特定类型的电影或多或少呈现出某种特定风格, 正如人人皆有自身性格。 “类型” 亦可类比为电影的特定 “性格”, 这些性格由故事类型、 场景、道具、 服装、 社会环境、 视觉表征等多种元素综合而成, 而非完全被给定的先验图式。 诚如法国学者樊尚·阿米埃尔(Vincent Amiel) 和帕斯卡尔·库泰(Pascal Couté) 所著的《美国电影的形式与观念》 (FormesetObsessionsduCinémaAméricainContemporain, 2003) 导言中所述: “面对当今大量不同风格的影片公司、多样化的制作方式、 相互交叉和融合的艺术标准, 给美国电影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还是很难的。”[6]进一步, “类型” 自身的划分也是灵活的、 相对的。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对“类型” 的某种严格划分无其必要, 相反地, 这些分类和结构的剖析将引导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美国电影所揭示的美国文化和美国社会的真实图景, 以及这套成功的好莱坞电影体系的生成机制与推广形式。
二、 何种“行动—影像”?——好莱坞电影与类型机制
对“类型” 的某种约定俗成的沿用来自电影市场中种种取得显著票房成绩与观众反响的成功电影,而“类型机制” 在好莱坞的统治也是好莱坞电影“称霸全球” 的一个重要因素。 学者霍顿斯·鲍德梅克(Hortense Powdermaker) 以 “梦工厂” (Dreamworks) 形容好莱坞, 这一比喻揭示了好莱坞类型电影最为核心的本质矛盾: 它既是一种艺术类型, 又是一套工业体系。 一方面,好莱坞使得电影工业成为名副其实,可类比汽车工业的一套成熟工业,它充分利用了集中生产、 分工劳动、流水线装配等大规模生产的工业手段, 并通过“制片厂体制” 联合了制片人、 导演、 编剧、 明星、 摄影师、 电工等一众人员, 依靠 “资本运作机制” 下高度细分的制作系统和传播手段。 另一方面(这也是好莱坞最为悖谬之处), 它的流水线机制并非用于生产汽车或香皂, 而是造“梦”: 依靠影像、 人物、 情境、行动的综合, 制造一段又一段持续120 分钟左右很快变化为回忆的无形愉悦经验。
正如哥特、 文艺复兴、 巴洛克等艺术历史时期都形成了各自鲜明的风格, 好莱坞经典类型电影也拥有自己的一套叙事风格。 1910—1920 年, 美国批量化生产的类型电影已经自发或自觉地有了一套流畅、自然、 便利的叙事模型。 透过一系列明晰、 简单、 系统、 经济、 平衡的约定俗成的原则, 故事可以被毫不费力且高效率地讲述给观众。 在《美国电影美国文化》 (AmericanCinema,AmericanCulture, 1994) 一书中, 学者约翰·贝尔顿(John Belton)认为: “这种风格总的来说是无形的, 一般观众难以察觉。 它的隐蔽性, 很大程度是美国电影熟练技巧的产物, 犹如一部讲故事的机器。”[7]32一方面, 这种“隐蔽性” 体现出好莱坞电影的某种“透明性”, 通过隐匿它们的运作技巧和刻意建构的所有痕迹, 好莱坞电影坦然地鼓励我们去“看透” 和 “看清” 它们——似乎我们看到了什么, 它们就是什么。 另一方面, 这种 “隐蔽性” 所呈现的“透明性” 实际上只是一种“幻象”, 它是高度技巧和复杂运思的综合产物, 它们尽量避免用突如其来的符号、 杂多的暗示破坏流畅叙事, 从而暴露出其本身就是刻意营造的产品。 这种自好莱坞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的本质悖谬所呈现的“表里不一” 的 “双重性” 和 “左右互搏” 的“平衡性”, 深深地根植于它的类型片叙事结构之中, 时至今日都在对当代国际国内的电影工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而这种悖谬又解释了其本质的某种 “复杂性”和“暧昧性” ——它的明晰是 “希望” 被我们发现的, 而它的“暧昧”则是隐而不显的。 这也是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商业导向所决定的——毕竟“观众看得懂的电影就是好电影”, 这或许是好莱坞电影卖座的原因, 也是好莱坞电影尽可能地隐匿其内在的多义性, 使电影的核心主题尽可能明晰晓畅的原因。
“商业性” 和“艺术性” 是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双重本质。 很多好莱坞类型片导演如大卫·格里菲斯(D.W.Griffith)、 查理·卓别林(Charles Chaplin)、 约翰·福特 (John Ford)也是极具创造力和创新意识的艺术家, 他们的作品兼具商业效应和艺术价值。 如今的工业化电影和作者电影、 商业片和艺术片之间也并无一道明确的界限。 类型的划分是灵活的、 相对的, 影片的模式亦是多变的。 美国电影风格的多样化和流动性赋予其内容丰富的特征, 好莱坞电影的自身标准也在不断跟随时代的需求和叙事体系的更迭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革新。 故而, 与其说“战前好莱坞” 这一前缀对于 “电影” 而言是一个时空范畴或逻辑范畴上的界定, 不妨说“战前好莱坞”是一种开放的观念, 而这一观念在当时的历史阶段主导全球的电影体系, 并且时至今日都对国际国内的电影工业生产不断施加着复杂的影响力。
此外, 需要强调一下作为德勒兹关注对象的“类型电影” 与德勒兹提出的核心概念 “行动—影像”所规定的电影领域所存在的微妙区别。 这种区别或更偏重于情感态度和学科进路, 而不是其内容之边界的框定与分殊。 一言以蔽之, 虽然德勒兹研究“类型电影”, 但他并非在进行“类型批评”。 譬如, 德勒兹在《电影1: 运动—影像》 的 “行动—影像: 大形式” (“L’image-action: La Grande Forme”)对主要的好莱坞电影类型如 “社会—心理片”(Le Film Psycho-social) “西部片”以及“历史片” 等均有提及, 并且他以此为材料, 分门别类地进行分析, 最终证明了它们的内在本质均为“SAS” (大形式)。 虽然, 行动—影像的“S-A” 结构在德勒兹看来是一种强叙事机制, 但是, 这个结构下也潜藏一些可以呼吸、 可被打破的场域。
我们可通过德勒兹对黑泽明(Akira Kurosawa) 的“气韵—空间”(Espace-souffle) 分析窥见大形式间细碎的裂缝。 黑泽明的影像叙事结构的确存在非常纯粹的 “S →A”(由“情境” 到 “行动”) 的公式,但是, 黑泽明拓展了大形式里“S→A” 公式所能延展的范畴, 使其进入了一个较之“情境” 而言更加深邃的、 极具独特性的 “意境” 领域,这可能是日本本土叙事传统和黑泽明的个人天赋共同塑造出来的。 黑泽明的《影武者》 (TheShadowWarrior, 1980) 讲述了三雄之首武田信玄与其“影武者” 之间的“决斗”,《七武士》 (TheSevenSamurai, 1954)则讲述了农民与武士之间的 “决斗”。 在这些讲述日本战国时代战争故事的作品中, 穿透了“决斗” 的“气韵”, 这种“气韵” 在黑泽明的影像叙事中表现为一种独特的笔触,它构成了影片的“综合符号” (Synsigne) 和作者的“个人签名” (Signature Personnelle)。 黑泽明的电影里, “横轴” 与“纵轴” 的设定非常重要, 它们将影片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 一是, 对于 “情境”构成缓慢的展示; 二是, 展开人物的紧张和突然的“行动”。 譬如, 影片《七武士》 中, 拍摄角度通常是一个扁平画面, “决斗” 的气韵似乎表现为某种流动的、 无休止的“横向运动”; 与此同时, 瓢泼大雨从天而降, 又构成了断断续续的“纵向垂线”。 在“行动—影像” 所提供的封闭的、 二元的 “S-A” 结构之内,黑泽明通过制造“横向” 与“纵向”的交错运动生成了潜能的、 生机的“气韵—空间”。 通过“气韵” 的流动, 空间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情境,而是扩大成一个有呼吸、 有灵韵、有缺口的“大循环”。
总结而言, “行动—影像” 的指称对象可被大致概括为: “新现实主义” 运动(1958) 前的美国好莱坞主流类型电影。 “战前” “好莱坞”“类型” 等关键词并非一种严格的概念限定, “行动—影像” 的 “S-A”结构也并非完全僵死的范式(虽然我们致力于批判它) ——德勒兹及此前的美国类型电影研究学者亦未采用此做法; 毕竟, 若将行动—影像的指涉对象严格框定在某个“好莱坞” 的论域里或许又掉进了“行动—影像” 自设的陷阱。 如果我们到达了 “行动—影像” 理论更让人惊喜的部分, 则会发现“框定” 这一影像的边界意义不大, 因为它不断在扩展自己的边界, 并且在时间性和空间性意义上提供了极大的诠释空间。 “行动—影像” 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 它提供了一套对于美国类型电影的全新的分类方法, 这套方法可以将美国电影的内在结构和运作规律进行严格的整合与编码。
三、 “影像” 何以“行动”?——德勒兹的研究进路
正如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 将他的电影形容为“一片薄薄的蛋糕” 而非生活的一瞥, 电影并非对生活简单的截取、记录或转译, 它必须经过复杂的艺术加工和特定的环境推动。 我们在两种层面作为观众凝视一部影片的放映。 在第一层面, 我们会在智识中知晓所看到的影片是由每秒24 帧的电影胶片组成的。 正常而言, “一部90 ~120 分钟的影片由600 ~800个镜头和5 ~40 个独立片段组成”[7]38, 而这些作为组成元素的底片是在不同的布景和场面调度中进行拍摄, 进而通过镜头、 剪辑等手段组合起来的。 但是, 当我们真切置身于一部卖座影片的观影环境中,会发现电影是连贯的而不是割裂的,叙事是天衣无缝、 行云流水的延续,而非支离破碎的情节拼贴。 基于此,传统电影研究已经发展出一套较为成熟的结构分析的手段, 这种方法通常被称为“分解” (Segmentation),即将电影本身拆分成若干独立的基本叙事单元, 在从细节上剖析电影中单独的某一场, 甚至某一场中的各个部分, 进而见出电影的叙事结构与叙事技巧。 基于这两个层面,可见出传统电影类型的研究文献呈现出两条线索。 首先是“归纳法”,上溯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历史发展,具体地、 分门别类地将其安置于各自的类别中; 其次是“演绎法”, 将电影类型作为一个宏观的文化研究对象。 作为电影类型研究的传统进路, “归纳法” 以作品为首要研究对象, 从经验现象出发, 进而总结、归纳、 提炼出相关的内在运作原则和结构特性。 近年来, 第二条线索下也出现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譬如,文集 《类型定义的变化: 对电影、电视节目和媒体进行分类的文章》(TheShiftingDefinitionsofGenre:EssaysonLabelingFilms,TelevisionShows andMedia, 2008)。 该文集遵循的编辑结构则是典型的类型研究逻辑——在第一部分考察了类型的含义与历史, 在第二部分通过特定的电影考察各种类型电影的殊异, 第三部分则侧重类型感知与历史、 记忆的互证关系, 以此见出类型所体现的社会历史性。
然而, 德勒兹的方法异于传统电影研究的两条进路: 它完全不同于“归纳法”, 也比“演绎法” 更为激进。 不同于传统的电影理论家、电影史学家对于美国类型电影的剖析方式, 德勒兹无意整理、 总结和归纳浩如烟海的影像材料, 也对条分缕析地挖掘其隐匿的叙事逻辑和叙事模式不感兴趣。 他 “独断” 地将好莱坞类型电影揶揄为一个 “容易界定的” 领域。 一方面, 德勒兹并非从电影的 “发明史” 出发, 而是从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在 《创造进化论》(L’évolutionCréatrice,1907) 一书中提出的 “电影幻觉” (L’ illusion Cinématographique) 出发。 在电影真正被发明出来之前, 柏格森在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中就预料到了一种可能的电影影像, 并以其作为某种幻觉的移印抑或复制。 柏格森将“电影” (Cinématographique) 定义为一种古老的、 由虚假运动所造成的影像的幻觉, 他说: “用某个抽象的、统一的、 不可见的变化将它们串联起来……我们只能开动某种内心电影机了。”[8]由此可见, 我们好像在无意识中制造电影。 一个世纪后,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所言的“意识犹如电影” (Le Cinéma de La Conscience)[9]或许亦是此论断的某种延伸。 柏格森这一“电影” 概念, “以预言的方式预测电影的未来或本质”[1]12, 暗示着电影在其本质上就是一个由概念创造出的实体, 所以, 在德勒兹看来, 电影不仅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材料存在, 还是一种哲学本体的化身。 另一方面, 德勒兹也不遵循以往电影研究学者提出的 “类型”概念——虽然他在《电影1: 运动—影像》 中多次提及该词, 但是他仅仅将其作为“佐料”, 并不赋予其与“结构” 同等地位。 区别于“类型分析” 的某种开放性(开放性同时意味着 “隔靴搔痒”), 在德勒兹的“结构分析” 体系里, “情境” 和“行动” 两极成为商业大片的固有结构, 好莱坞式的“现实主义” 电影结构被框定在“情境” 与“行动” /“环境” 与“行为” 间的关系及其所有变式里。 他虽然从休谟切入“运动—影像”, 但并非从经验层面分析“电影幻觉” 如何产生, 这种方法在他看来过于工具化。 他选择通过批判吸收柏格森 “静态分切” (une Coupe Immobile) 和 “动态分切”(une Coupe Mobile) 理论, 勾勒出一种作为抽象机制的“元电影” (Metacinéma) 的“运动法则”。
在《电影1: 运动—影像》 的导言中, 德勒兹认为: “这项研究并不是电影史, 而是分类学 (Taxinornie)。”[1]7德勒兹对美国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分类受到诺埃·伯奇 (Noёl Burch) 的启发, 他按照“大形式”(SAS) 和“小形式” (La Petite Forme,ASA) 将 “行动—影像” 粗略分为两类, 目的则是构建他在导言里所畅想的一种全新的“影像分类学”,并通过这一分类学重新发现影像的本体。 德勒兹从法国哲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 Claude Lévi-Strauss) 《结构人类学》 (AnthropologieStructurale, 1958) 这一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 的哲学史背景进入对“行动—影像” 的概念分析, 并且试图提出一种以好莱坞电影为对象的结构主义电影观。 首先, “结构” (Structure) 区别于传统艺术史意义上的“形式” [如海因里希·沃尔夫林 (Heinrich Wölfflin) 的 “形式分析”]; 其次, “结构” 亦区别于“程式” (Formula) [如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 的 “情念/激情程式” (Pathosformel)]。 在德勒兹看来, “结构” 不是局部的规定、 规律或程式, 它也不属于艺术史范畴,它聚焦更为宏观的立场, 试图提出某种元历史的叙事模式。 与其将结构主义狭义地归类为某一理论、 某一流派, 不妨说结构主义是作为某种现代方法论存在。
不难理解为何德勒兹提出S (情境) 和A (行动) 这两个锚点作为好莱坞类型电影稳定叙事的依托——他的策略可以被理解为: “立靶子—打靶子。” 德勒兹以结构分析的方法, 将好莱坞电影类型转码为相关的结构性形式, 然后再松动并颠覆这一形式, 进而达到对整个美国好莱坞类型电影内在机制的把握和批判。 在《电影1: 运动—影像》中, “形式” (Forme) 一方面作为“结构” 的另一种说法(根据不同的情境可理解为 “模式” “形态”等); 另一方面, 又被德勒兹赋予了一种由柏拉图“理型说” 流变而来的哲学内涵。 与此同时, 探析 “行动—影像” 这一结构的建制与统治,以及厘清好莱坞类型电影“称霸全球” 的原因这两条线索在德勒兹的行文中互为表里, 相伴而行。 进一步, 德勒兹对此结构的批判, 以及瓦解此结构的尝试, 同样是从 “结构主义” + “符号学” (Semiotics) 的立场切入, 他引入美国逻辑学家、 实用主义 (Pragmatism) 创始人查尔斯·S. 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 提出的松动“第二性” 的“第三性”,进而以希区柯克的 “关系—影像”(L’image-Relation) 瓦解了 “大形式” 与“小形式” 的二元结构建制。希区柯克的 “关系—影像” 脱离了“行动—影像” 的固有结构, 它具备了“行动—影像” 的“第二性” 无法提供的意义, 进而作为 “时间—影像” 的前奏昭示了“行动—影像”所面临的这场危机之结局。
四、 结语
“行动—影像” 理论所呈现的某种“二元性” 原则不仅可以作为分析美国好莱坞类型电影的总体方法论, 整个美国社会的二元意识在文化表现和行为习惯中也体现为某种结构化的内在构造及运行特征。 某种长期的断裂曾持续存在: 类型批判缺少理论的谱系, 而结构主义则缺少具体、 现实的, 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材料。 不同于传统的电影理论批评家们以“类型” 为切口层层剖析, 以求解决此问题的答案,德勒兹从一开始就试图将好莱坞类型电影“编码” 为二维的固定结构,进一步地厘清 “行动—影像” 的内在机制, 在结构层面找到扭转这一症结的关键锚点。 无论是好莱坞电影内在运行机制这一研究对象, 还是德勒兹这一异于其他学者的研究方法, 都对解决学界此前遭遇的电影史、 哲学史问题, 以及目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有积极意义——它不仅提供给我们一种观照当下电影发展的独特视角, 也指出了一条理解电影内在的哲学性变革诉求的全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