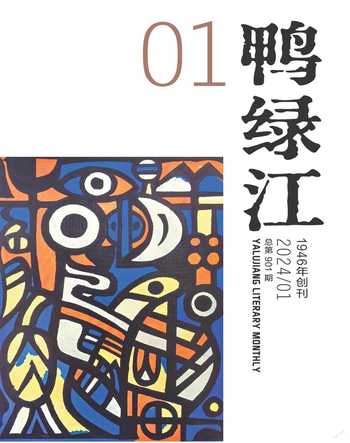失落·混沌·开放
陈锦
萬玛才旦既是“藏地新浪潮”电影的领头人,也是藏地小说优秀的代表性人物,著有汉语中短篇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梦》《嘛呢石,静静地敲》《塔洛》《撞死了一只羊》《乌金的牙齿》《故事只讲了一半》等。万玛才旦的小说大多直视生命的不圆满,用善恶交织、好坏并存的混沌人物和虚实相生、真假难辨的混沌情节裸呈世间万象。正如阳光折射下的水面,他的小说展现出光怪陆离的迷人色彩。而开放的结尾又指向故事的多义之可能。他的小说张力饱满,意蕴悠长,有着独特的美学风格和鲜明的个性特征,在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
一、失落的主题直视生命的不圆满
在万玛才旦的小说创作中,“失落”是一个常见的主题,他的不少作品都表达了这个共同的主题。主人公一直在寻找,辗转反侧,寤寐思服,但结果往往是求而不得。
《诱惑》是万玛才旦早期创作的作品。小说叙述少年嘉洋丹增受“那卷被黄绫紧裹着的”“散发出一种奇异的金灿灿的光来”的经书的诱惑,竭力想得到而始终未得。从七岁看到第一眼,到十四岁答应成为经书的主人仁增旺姆的丈夫,再到十七岁成为转世活佛,三年修行,最终圆寂,才看到经书第一页,然后缓缓飘摇而去。嘉洋丹增为看经书,付出种种努力,受尽仁增旺姆及其父的羞辱,以及师父的阻挠,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圆寂之时才看到经书的第一页。
整个小说就是一个隐喻。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就像经书对嘉洋丹增的诱惑,它强烈地牵引着一个人不顾一切地付出,但最终努力争取了一生,却只给你看那么一页,然后就“缓缓飘摇而去”。
这个追求,在《流浪歌手的梦》里则是流浪歌手次仁梦中的女孩儿。她很像《诱惑》中的经书,很美,很有诱惑力,但她只在梦中出现。为了这个梦,为了追寻梦中的这个女孩儿,流浪歌手执着地走下去,哪怕他感到自己已经疲惫不堪,无法继续。不知名的大师说:“世上的人们难道不是为了寻找那梦才来到这世上的吗?”像嘉洋丹增一样,流浪歌手也没有得到他梦中的女孩儿。当他看到梦中的女孩儿时,她已经死了。
《塔洛》是万玛才旦小说中非常成熟而深刻的短篇。塔洛被迫进城办身份证,却被理发店短发女孩儿骗光卖羊所得的全部钱财。塔洛最先是以“小辫子”这个外号为指称的,进城办身份证是他在精神上追寻“身份”的隐喻。短发女孩儿剪掉塔洛的辫子,意味着对塔洛身份认同的消解。塔洛拿到了身份证,却失去了小辫子。从此,作为他指代的小辫子没了,他为寻求外在的身份认同,最终失去了最突出的特征,就像被抽离了灵魂,再也不能顺溜地背诵《为人民服务》了。小说通过塔洛对自身身份认同的一次次建构和解构,把主题提升到超越普适意义的身份认同问题,追寻而不得,反而失去更重要的东西,比如内在特质,比如生命,比如灵魂。
追寻而不得或错过,还表现在《我想有个小弟弟》《寻找阿卡图巴》《寻找智美更登》《陌生人》等作品中。小学生丹增想要有一个小弟弟上下学时跟在他屁股后面跑而不得,“我”去寻找阿卡图巴却错过,导演江央寻找演智美更登的演员而不得(包括故事中的故事,老板和蒙面女孩儿追求爱情而不得),陌生人想找第二十一个卓玛而不得等。
万玛才旦的小说始终离不开失落。“命运”荒诞与无常,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爱而不得、求而不来,不完美的结局似乎是生命的常态。万玛才旦在接受徐晓东采访的时候说,世上的事,多半是以“不圆满”为结局的吧。①(一语成谶,故事写到一半,万玛突遭意外,又何尝得“圆满”二字?)不圆满是人生的隐喻。万玛才旦的小说是指向人生的大书,他直视生命的不圆满。虽然他的作品多以短篇形成出现,但众多的短篇却也制造出众声喧哗的复调效果。
二、混沌的人物和情节裸呈世间万象
万玛才旦的小说,人物的善与恶、好与坏并不分明,情节的真与假、实与虚也难辨。但正是因为这种虚实相生、真假难辨,如阳光折射下的水面,他的小说才展现出光怪陆离的迷人色彩。
《站着打瞌睡的女孩》叙述“我”替参加高考的乡书记女儿当“枪手”发生的故事。作者没有批判乡书记以权谋私,也不觉得成为乡书记女婿的秘书卑鄙无耻,更没有对乡书记的女儿有所不满。乡书记从胖到瘦,后来生病去世了。秘书后来成了乡长,娶了乡书记的女儿但没有得到她的爱情,最后离婚了。“我”最终和乡书记的女儿结婚了,但好景也不长,后来她也死了。只有乡书记秘书和她生的女儿叫“我”爸爸,还遗传她站着打瞌睡的习惯。故事中的人物不是非黑即白,不是简单的坏人和好人。“我”写的作文《一件小事》是编的,却感动同学、感动乡书记女儿。整个故事是虚构的,却又那么真实。
好的小说往往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这个世界是多面的,并非简单的二分,非白即黑,这不是现实,或者说,这不真实。万玛才旦说:“我觉得‘混沌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也是对这个世界的准确呈现。”②他又说:“很多时候,我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构,它们的界限在哪里。我分不清。”③由于他出生于藏地,小时候听闻许多在我们汉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他曾经接受采访时说:“一个牧民,没有上过学,不识字,有天去山上放羊,几天几夜没回家。家人到处找,发现他在山上某个地方昏睡。叫醒之后,他回想起来,就是睡了一觉,梦里看到了《格萨尔王传》的画面,就像看电影那样。醒来之后他就会说唱《格萨尔王传》了。这是科学没办法解释的,大家相信他们说唱《格萨尔王传》的能力是神授的。”④
藏人的思维和藏地的人事似乎与汉人的习惯不一样。这使得万玛才旦的小说更加迷人。
再如《普布》中的普布,打死了袭击他和驴的狼,但之前他也把仅有的一疙瘩糌粑分一半给饥饿的狼吃。后来他还打死了曾收留他、又要用掺了老鼠药的青稞酒毒死他的寡妇玉珍,却说:“你是这辈子对我最好的人。”玉珍的女儿卓嘎后来并没有抛弃普布,还叫他阿爸。她知道阿妈在青稞酒里放了毒药,她也知道阿妈是被普布杀死的,但她仍然善待普布。故事中的人物不是十足的恶人,也不是没有一丝缺点的大善人。他们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真实不虚。
小说《岗》写有相同名字和长相相似的两个通体透明的女“岗”和男“岗”,大学毕业后他们放弃了留在城市的机会回到家乡执教。他们期望通过自己异样的躯体来帮助乡亲、解决困难,但现实的权和利却没有顾及两个“岗”的感受,最终两个“岗”的希望全然破灭了,于是他们就从人间匿迹,回归大自然的怀抱。《岗》一方面通过“梦境”和“异类”等手法对现实进行了魔幻化处理,一方面又把它置于牧区民族教育事业、变化中的民族文化和金钱对人性的腐蚀等诸多现实问题上。像“雪一样的一种圣洁的理想追求”的两个“岗”从满怀希望到不懈努力再到梦想破灭,犹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马孔多小镇发生的一切。
万玛才旦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小活佛嘉洋丹增、流浪歌手次仁,还是普布、塔洛、岗等,他们有的强烈追求自己想要的,有的顺从命运的安排。万玛才旦没有美化、片面化人物,也没有装饰情节,而是冷静地呈现这世界本来的混沌甚至魔幻的万象,让读者去体会、去感受、去品评、去取舍。万玛才旦说:“这个世界对我而言很重要,较之过于理性与坚硬的现实,它呈现出某种混沌、松软与诗意。”在呈现的混沌中展现松软和诗意,让小说蒙上了混沌的美感,这就是万玛才旦小说所达到的艺术境界。
三、开放的结局指向多义之可能
万玛才旦的小说较多反映藏地的传统,以及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碰撞的困境。但他并不是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亮明自己的立场,而是尽可能地展现,让读者去体会,因而他的小说的故事结局大多是开放式的。
比如《塔洛》中的塔洛,他最终命运如何,被理发店短发女孩儿骗光了所有的财产之后是继续放羊还是做什么,作品没有交代。其实小说家不必给出明确的答案,他没有责任和义务必须在作品中交代结果。
还有《氣球》。达杰的妻子卓嘎最终有没有拿掉肚子里的孩子,故事没有交代。故事结局,达杰从街上买来的两个真氢气球,一个爆掉了,一个从两个孩子手中脱落,飘向了天上,“越飞越高,越飘越小,最后消失不见了”。气球的消失意味着什么?这个有意味的结局,指向了多义之可能。
《水果硬糖》也是。“我”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多杰加读书一直很好,每年都是三好学生,人家都说他是天才。他以全省第三名的成绩考上大学,毕业后到拉萨的医院里工作,一直做到副院长,还娶了好姑娘央金。小儿子多杰太,从小像个傻子,到四岁才会说话,但他却被证实为卓洛仓活佛转世。刚开始大儿子多杰加用现代科学的眼光看传统宗教的代表多杰太,眼里充满了怀疑。后来母亲生重病了,两个儿子守在她身边。多杰加似乎认同了多杰太的活佛身份。故事在儿子儿媳品尝阿妈买来的水果硬糖——当阿妈还是少女时,卓洛仓活佛塞到她手里的那种糖的味道中结束。水果硬糖到底什么味道?酸酸、苦苦、淡淡而又甜甜的味道。各人品尝不一样,但都是人生的味道。
开放式的结局,既不强加观点也不提供确定性,不轻易做出价值判断。万玛才旦没有将人物的命运彻底地决定下来,读者可以结合自身经历和认知进行自由解读、想象和思考,让读者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而不仅是被告知故事的结果。这让读者拥有更多的主观性,与作品共同创造出一个具有多种可能性和意义的世界。这些开放式的结局,也使作品更富有生命力,更引人入胜。
《故事只讲了一半》这个小说也就干脆以此为题。“我”去纳隆村找扎巴老人采录之前没有采录的最后一个故事,阴差阳错,最后关头,老人去世了,“我”还是没有采录完最后一个故事。万玛才旦在接受《解放日报》读书周刊记者的采访时说,他知道“里面没有讲完的故事,源于一个藏族的民间故事”,他“可以把它讲述完整。但小说不是故事会”,他“认为用这样‘只讲一半的方法,效果也许会比把故事讲述完整更好,带给读者的东西会更多。这是一种未完成性。”把剩下的部分留给读者去创作,去生发,去延续。这也更高明。
万玛才旦作为精通汉藏两种语言的作家,又兼具翻译家、小说家、电影导演和编剧等多重身份,他的小说创作有丰富的藏地素材,又多了一重汉族的视角。既可以藏人的眼光从内关照藏地的信仰和传统,又可从汉族的目光从外凝视,呈现传统的价值和信仰在现代外来文明的渗透之下变化、挣扎的状态。他竭力摆脱单纯从外关照的隔膜,深切展示藏地和藏人的生存困境和在此之中展现出来的人性。他说:“以前有一个提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我个人更喜欢‘越是人性的,越是世界的。”⑤小说只有深入写出人性的丰富和多面,这样的小说才是对世界的多一份挖掘,这也就是万玛才旦被西藏文联主席扎西达娃称赞“创造了藏民族的电影和小说双子座的高峰”的原因。
注释:
①②徐晓东、万玛才旦:《万玛才旦关于小说创作的访谈》,《撞死了一只羊》,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 221、202页。
③万玛才旦:《故事只讲了一半》,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版,卷首语。
④⑤顾学文、刘芳旭:《万玛才旦:讲了一半的故事,更有深意》,《解放日报》2022年11月1日。
——来处已然消失 归途无所觑见
——以万玛才旦的《塔洛》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