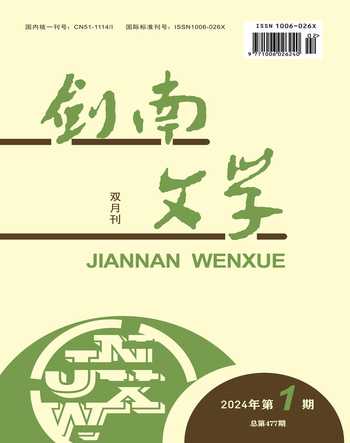最后要求
那个老农很瘦,背微驼,肩着一个旧布兜,脸上的皱褶似乎受到了什么挤压,叠到了一块。他已在招待所大门外徘徊了许久,几次想进来又收回了腿脚。
我想他可能就是我在等待的那个人,便慢慢走近他,还不住地故意干咳。门卫见了我马上立正,行了个不太规范的军礼。
这次矿难不幸发生后,矿务局的这个招待所便成了临时接待死难者亲属的场所。难属来到后分别安顿好,由专人负责。善后督导组要求我们对难属要好生招待,特别是就赔偿事宜妥为协商,尽量让对方满意。于是,作为工会主席的我,被指定接待来自偏远山区的一个徐姓难属。不料,几天过去了,一拨拨难属拿到应得的抚慰金和赔偿款后陆续离去,唯有这徐姓的难属迟迟未见露面。在这景况下,我也焦急。
与老农一攀谈,果然就是他。我自报了姓名、职务,他便慌忙掏出身份证和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信给我看。这证明信保存得极好,大红印章叠印出另一个红圈圈儿,印泥似乎还没有干透。虽然他说的方言我听着有点吃力,可还是明白话中意思。核对情况后,我瞅瞅他的身后,问:“徐大叔,就您自个来的?”
“就我一个,多了会给政府添麻烦。”
此时,工作人员小王过来了,光看我。我有点恼怒:“看我干啥,好好招呼客人!”
在门卫别样的目光中,我俩将这最后一位客人领进招待所。小王打开备好的房间,退一步请他先进。客人往里瞅瞅,又看看我,也后退了一步。
“这是啥地方?”
“给您准备的房间。”
“不可不可,住这地方我睡不着。没有旁的睡屋了?”
“这是专为您安排的,想让您好好歇息歇息。”
到餐廳后,这徐大叔的眼光又不够用了,东看看西瞧瞧,眼皮子乱跳。四个盘子上来,有鸡有肉,香气腾升。他却不落座,惶惶四顾。
“还有人吗?”
“没有其他人,就咱仨。”
“吃不了,吃不了,剩下又丢,可惜。”
“吃吧,吃吧,不会浪费的。”
“哎,有大蒜和咸菜么?”
“难道这菜不合您口味?”
“没有大蒜我下不去饭……”
他这一说,我突然想起乡下的父母:他们来到我家也说住不惯,吃饭时少不了大蒜,还要咸菜。这一想,父母的身影就与眼前这位大叔重合了。
餐后,天色已晚,我让小王明天带新衣服和鞋子给大叔换上,然后陪他在院子里转转。
矿区的夜景璀璨亮眼,灯光串珠与星河相连,群声渺起似幻境梵音。老徐看着听着兴奋不已,眼睛里映射着光芒,好像全然忘记了此行的目的。借此机会,我与他唠起家常。一听说我当过兵,他一惊,连声说:“我相信你,相信你……”
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奇怪的是,在第二天商议赔偿事宜时,他眼睛光往外边看,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只说:“按国家规定办,咱不能让政府作难。”
赔偿不到一个小时就协商妥了。签字时,他的泪珠滴落下来,洇湿了自己的名字。
此刻,我心里紧得难受,向他反复申明:“大叔,您老还有啥要求尽管提出来,我向上反映,保您老满意。”
“满意满意,太可心满意了。这钱够盖三间新房的啦,小妮子上学不用犯愁了……没别的事我得赶紧回家,地里的庄稼可不能误。”
“您老轻易不出来,趁这机会我陪您走走转转,看看风景。”
“庄稼地就是好风景,我离不开。”他擦干净眼睛,笑。
次日徐大叔离开时,矿里派车,由小王送他去火车站。他又换上了来时的衣服,只是洗得很干净。临上车时,我一直将他送到大门口。在即将分别的那一刻,我猛地抓住他的臂膀,最后一次问他还有啥要求。
“没啥,没啥……”说着,他挣脱了我的手,往餐厅方向瞟瞟,眼里游出一丝亮。
“大叔,您说,您说呀!”我急得将意思点明了,像是恳求。“还要多少?”
“要的不多,够路上吃的就可——你们饭堂的馒头真好,还有那新蒜。”
我向小王使了个眼色,小王一抬脚飞奔而去。不多时,一包馒头,还有大蒜咸菜,呼噜噜全部塞入他布兜。
看着那满当当的布兜,我知道那里面除了吃的,还有他舍不得穿的新衣和鞋子。
束紧了布兜,他突然向我们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这两天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一转身,躬腰进了车。
我急忙还礼,扭过脸去咳嗽不止,鼻涕眼泪就跟着下来了。
泪光中,车影渐渐远去。望着那车影,我行礼的那只手久久不能放下。一看,门卫也和我做着同样的动作。
自那以后,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位徐大叔。不过,我也养成了好吃大蒜的习惯,并且将父母接来和我同住。
司玉笙,男,1956年生,在新疆长大,当过农场知青、小学教师,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个人专著九部。河南省小小说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