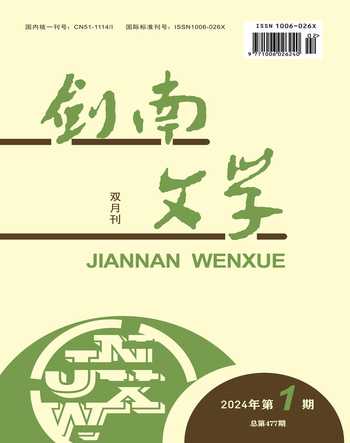老枣落叶
一到秋天,老枣树的叶就刷刷地随风落,风不吹也落,树枝上还有干红的枣,鸟啄食,翅膀一振,黄叶纷纷落下。
老枣树是落根在五奶家的院内的,粗壮的枝和杆直指蓝天。
老枣树的枝叶不受约束,张狂地伸出去,有一半落在了二柱叔家的院子里。
秋天老枣树落叶,许许多多的叶就落在了二柱叔家的院子里了。
这是一个大早晨,五奶一扫帚一扫帚地扫着院子里的树叶,叶随扫帚走,五奶就小声嘀咕:又是一年了。
二柱叔也在扫落叶,扫得心里烦,枣叶碎小,藏进沟沟缝缝里,实在是不好扫,二柱叔就埋怨:唉,长的不是地方。
五奶抬头望枣树,晨光绕在枣树的枝头,环环绕绕的织出一片锦绣,树头还有一些红红的枣子欲掉还休般坚守,黄叶剩下不少,尽管稀疏,要落尽恐怕还要些时间。
二柱叔仰头对着太阳打了个喷嚏,老枣树在二柱叔强烈的喷嚏震动下,又落下黄叶,二柱叔摇了摇头:扫不尽呢。有鸟飞来,二柱叔认识这鸟,是灰喜鹊,春天在老枣树上搭过巢的。
老枣树梢上的红枣是留给鸟们过冬的,大冬天鸟要吃食,总要给鸟们留些吃的东西。过去割田里的晚稻,村里老人会指指戳戳,要割稻人茬子留深点,田边地角丢下些还青着的穗子,给鸟们留点口粮。村子里的果树,主要是柿和枣不摘尽了,留些给鸟,给大雪封门时鸟们吃。
五奶家的老枣树能结得很,春天一树星星状的花,夏天、秋天一树的枣,把树枝“沉”得弯下腰。
一些年里,老枣树是五奶家的盐罐子,青枣红枣卖点钱,称盐打油,给五奶家不小的帮助。五奶的丈夫五爷在世时常念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托上辈的福。老枣树是五爷的爷爷栽下的,这还不是享祖上的福?
二柱叔家也没少沾老枣树的光。夏天里老枣树筛下一院的阴凉,端把凳子就能享受上美美的凉气,枣子青了,拿根竹竿就能打下,甜了孩子们一张好吃的嘴。枣子红了,还会从枝头落下。自然成熟的枣真甜。
老枣是五奶家的先辈栽下的,根落在五奶家的院子里,自然是五奶家的,可老枣的一半枝丫又撑在二叔家院子的空中,归属权就变得暧昧了。也正因为如此,二柱叔家里的人打枣、拾枣,几十年了也少有争吵。
落叶归根,根很大,老枣树落在五奶的院子里,可谁知根盘向何方?叶落进二柱叔的院子也正常。
近几年,老枣树静寞了。过去枣子挂了枝,一村的孩子围着转,一不小心低处的枣子还没成熟就被打尽了,好在树大,半高和高处的枣子仍是累累挂着。有那么一天,村里的人向城里涌,年轻人去工作,孩子们去上学,村子里人越来越少,老枣树上结的枣也安稳了。
五奶起先高兴,眼看着一树枣花开,眼见着一树青枣绿,眼看着一树枣儿红,眼见着一树鸟儿争食枣。可时间一久就高兴不起来了,一树枣子不见人来看、人来打,五奶的耳朵都闲得没处放了。
到了秋天,风刮过,红红的枣子落地,五奶用扫帚扫着归类,可也就放在一边。
二柱叔何尝不是,常常望一地落枣生闷气:人去城里,何时回?树上枣子红得澎湃,真是一树枣子望它红,但红也就红了。
五奶隔着院子喊二柱叔:二柱呀,枣子红透了,喊孩子们回来打枣哦。
二柱在院子这边,拣了两颗熟透的枣捂在手心里,回话说:谁说不是呢?孩子们忙,喊不回哦,过去枣子精贵,现在不算啥了。
五奶仰着头看枣子,枣子红彤彤的,泛着好看的色调,枣红色,正色。五奶嘆气:唉,一树好枣。
老枣树上的枣,多多的留在了枝头,鸟们高兴,一阵阵飞来,又一阵阵飞走,叽叽喳喳地叫着、喊着。
二柱叔惜护枣子,用棍子轰鸟,可怎能赶得走?
二柱叔爱干净,拿着扫帚守在院子里,一有落叶,二柱叔就去扫,可咋也扫不尽,风欲止,而叶不尽。
五奶扫落叶,可扫着扫着停了下来,五奶拿起了手机,拍了枣树上的红枣,拍了落地的枣叶,还悄悄拍了二柱叔扫落叶的视频。
五奶新潮,拍的照片和视频全部传到了微信群中。
微信神奇,一夜间大发酵。
第二天,村子火热起来,一行行人扛着长枪短炮来了,直奔老枣树,来了就找二柱叔。
老枣树和两个院子成了网红打卡点,说枣树是长在舌尖上的乡愁,落叶美,落叶归根,人人都要找根。
来人对着老枣树的落叶拍,让二柱叔摆出扫落叶的姿势,却不让将落叶扫走,落叶就在五奶和二柱树的院子落了一层又一层。
五奶悄悄问二柱叔:落叶比红枣金贵?
二柱叔反问五奶:落地的叶比树上红枣好看?
鸟在老枣树上飞过,尖尖地叫了几声,叶又落下一羽羽,枣又滴落下好几颗。
张建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出版散文集《向阳草暖》等。曾获安徽省社科奖(文学类)、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