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然宇宙观的深层特质:以唐君毅的论说为中心
王国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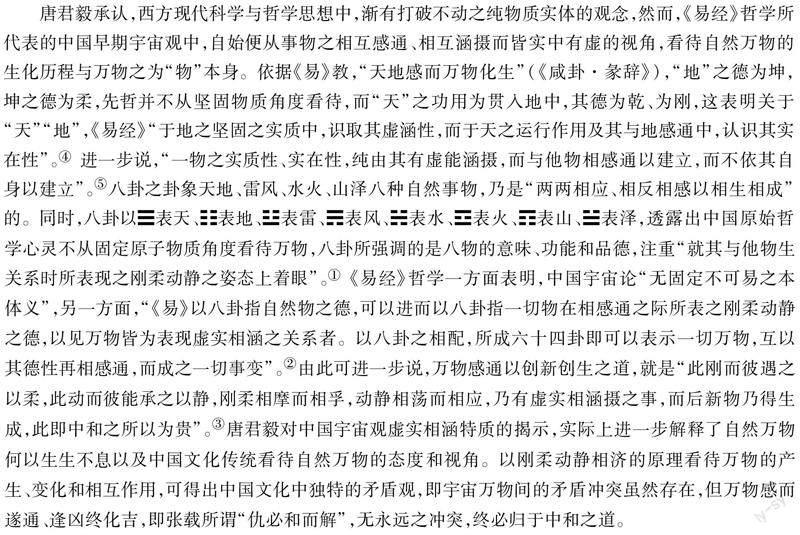
关键词 自然宇宙观 内在自然律 位序时空观 道德存有 唐君毅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4)01-0102-09
自然宇宙观是关于自然万物及其与人类关系的基本观念,往往构成某种文明形态的世界观基础。中华文明的独特形态首先体现在自然宇宙观上。深刻把握中国自然宇宙观的深层特质,对理解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及中国人对自然的智慧无疑十分重要。一般谈到宇宙论,往往侧重对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构成论两大话题的讨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宗教的宇宙论、哲学的宇宙论和科学的宇宙论三大类型。①本文所讨论的自然宇宙观主要是哲学层面的宇宙观,而探究自然宇宙观的深层特质,也并不局限于对宇宙生成论或构成论的讨论,而是重在对中国自然宇宙观的整体文化特征进行分析和把握。西方汉学家通常用“关联性宇宙论”概括中华文明宇宙论的特色。国内学界对古代宇宙观的考察虽有多学科的多维视野,但主要聚焦于对《周易》和儒道哲学等具体经典文本的探究之中。从宏观层面对中国自然宇宙观之特质的揭示,则往往集中于宇宙生成论、构成论和“天人合一”论所凸显的人文宇宙观。当代学者中,陈来将中国自然宇宙观整体特征概括为“关联宇宙”“一气充塞”“阴阳互补”“变化生生”“自然天理”和“天人合一”诸方面,对中华文明宇宙观的有机整体主义特质的揭示颇为清晰。②王中江结合出土道家文献对中国自然宇宙观的基本形态和整体面貌作了深入分析和描述,认为中国自然宇宙观诞生于早期道家思想。道家宇宙生成论既描述了宇宙的原初状态,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宇宙生成模式。① 安乐哲有系列论著探究中国宇宙论特质,提出中国哲学的“焦点—场域式解读方式”,认为中国古代宇宙论“有其自身的因果与逻辑”。②
当前推进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既需要跨学科、系统的、整体的方法论探索,以及整合出土文献新材料,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消化吸收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就笔者所见,现代新儒家巨擘唐君毅对中国自然宇宙观的讨论丰富而深刻。唐君毅早在1937年就曾发表《中国哲学中自然宇宙观之特质》一文,从中西印相比较的角度,就中国自然宇宙观提出12个方面的特质,即“宇宙以虚含实观”“宇宙无二无际观”“万象以时间为本质观”“时间螺旋进展观”“时间空间不二观”“时间空间物质不离观”“物质能力同性观”“生命物质无间观”“心灵生命共质观”“心灵周遍万物观”“自然即含价值观”和“人与宇宙合一观”,并特别解释“自然宇宙观”不完全等同于“宇宙论”,因后者广义上可包括纯粹本体论问题。③ 而在此之前的1935年,唐君毅为解释他所提出的中国文化根本精神,即“将部分与全体交融互摄”精神,已将中国宇宙观特质作了7个方面的概括。④ 不过,在1951年写成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自序中,唐君毅自言对其20世纪30年代的相关论述深感不满,⑤并在该书中辟专章讨论“中国先哲之自然宇宙观”,重新集中讨论中国自然宇宙观的特质,颇有深度,并在后面各章展开讨论人生观和艺术观视角下中国自然观特色。在稍早于此书的1946年,唐君毅针对《易经》经文所蕴含的宇宙观亦曾提出10个方面的特质,认为“《易经》中实含一以宇宙为大和之境的宇宙观”。⑥ 而在60年代写成的《哲学概论》巨著中,唐君毅在“生生之天道论”和“宇宙之对偶性与二元论”等论题之下,围绕气化观念和阴阳观念,对中国宇宙观亦作了进一步申说。⑦ 本文拟以唐君毅的相关论说为讨论中心,对中国自然宇宙观之深层特质加以阐发,借以推进对中国宇宙观和中华文明特质的进一步理解。
一、生生之理是万物的内在律则,非超越的必然律
从对比的角度看,与西方自然宇宙观强调超越具体感觉世界的共相,注重把握普遍关系,相信自然万物是由超越的、客观的普遍必然律所支配的思维不同,中国自然宇宙观不将自然律视作外在于事物者,而是内在于自然万物者。万物的秩序和律则,并非由神从自然万物之外赋予或自上而下的安置者,而是可“由万物之运行变化或发挥作用而见”的“物之性”。⑧ 唐君毅认为,在中国自然宇宙观中,超越的涵盖万物的“共相”是后起的,非“第一义之理”,而当“以一特殊事物本身所显示条理秩序为第一义之理”。⑨万物存在的根本之理是“生生不息之理”,这是任何事物所以能生起的内在根据,就其为万物所共有而言,可以称之为“万物之道”或“天之道”,也可称为生物、成物的“乾坤之理”或“仁之理”。唐君毅进一步指出,生生不息之理虽然使万物生生成为可能且必然,“却非使万物之所生起为何形式本身为必然”。即,由于事物的生起依于变化中的相互交感,因此,物如何表现生之理,将生起何种事象,都会随感通情况而变化。“一物之性之本身,即包含一随所感而变化之性”。由此,唐君毅总结说,中国思想中的“物之性”不是西方式的必然律原则,而是自由原则、化生原则,是“随境有一创造的生起而表现自由”①之性,表现于与他物感通而化生之际。
强调自然律内在而非超越,遵循自由化生原则而非必然原则,强调万物相感通的生生之理,而非西方“以物之本质为力”之说,是中国自然宇宙观的第一个特质。推究中西自然宇宙观差异之根源,怀特海认为,古希腊支配万物的“命运”观念,罗马法之刚性宰制一切的“法律”观念,以及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观念,是近代西方产生将自然律则看作绝对必然而又外在于事物本身之观念的思想根源。而唐君毅认为,中国自然宇宙观上述特质可由“对自然界生物之发育,物与物之相感之直接经验以证实。亦为中国宗教精神以天高听卑,帝无常处,儒家以仁道仁心观宇宙,及道家以逍遥齐物之眼光观宇宙之精神”② 所涵攝。与西方机械论宇宙观不同,中国的自然宇宙观是“生生”宇宙观,这从《易经》强调“乾坤相感”和“无固定不可易之本体”的宇宙论观念中即可窥见。③ 西方透过其理性分析精神而提出的原子论和原质论,均是“舍显求隐”,无视直接经验事象之连续性的表现。曾亲炙唐君毅教泽的安乐哲也认为,理解万物及其关系要从其“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富有创造性的、相互依赖的因果性”去理解,“中国古代宇宙论有其自身的因果与逻辑”,而不是休谟式的“外在因果律”。④
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自然宇宙观将宇宙看作生生不息、变化不已的过程,变化的根本内容是“生生”。相关论说非常丰富,如:“《易》之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天地之大德曰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这些论述都表明,中国先哲将宇宙看作一个本身变化不已,且以创新生成为内容的运动总体。在20世纪30年代的论述中,唐君毅便将“生生不已观”列为中国自然宇宙观的特质之一,并指出中国思想家从一开始便“以宇宙乃永远生生不已者”,“中国人素不好论世界之始终,论宇宙开辟者尚有,论世界末日者乃竟无人”。⑤ 同时,唐君毅认为,“生命物质无间观”也是中国自然宇宙观的重要特质。不同于西方将生命和物质二分的思想传统,中国自然观“只见生命不见物质,物质即是生命流行表现之境”。⑥与西方“物质”概念最相近者,就是自然界流行之“气”,但中国先哲认为气中含有生命,无论是《老子》的“冲气”、《庄子》的虚而待物之“气”,还是《礼记》中的“神气”“精气”,抑或汉儒的“生气”,都隐含生机之意。中国人看“天地”,也从不视为纯物质之天地,而是生生不息、生机流行之源。变化之流就是以气的连续统一性为载体的生命之流。
西方汉学家牟复礼曾提出中华文明缺少创世神话,并将之作为中国宇宙观的一个特色看待。⑦ 陈来认为,中国缺少创世神话乃中国人的生成论思维所导致。中国宇宙观具有显著的生成论特征。他说:“天地万物是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生成就是becoming。所以,不是being而是becoming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⑧《周易》作为最根本的中国自然宇宙观之经典清晰表明,生成是自己的生成,阴阳的相互作用乃是生成的基本机制,自生自化的生成论才是中国自然宇宙观之生成论的基本特色。《易传》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是也。文明源头处没有创世神话表明,中国自然宇宙观不重视外在力量,而强调自生自化的内在动因。安乐哲也认为,与偏好借助因果范畴解释世界变化的西方传统不同,中国先哲主张自然的生成不需要外在原则加以解释,“一切事物可以产生任何事物,故而任何特定事物既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原因,也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后果。这种因果论及其逻辑,与西方哲学的因果论和逻辑存在明显区别”。① 李约瑟认为中国自然宇宙观模式“没有主宰却和谐有序”。实际上,中国宇宙观并非没有“主宰”观念,只不过从殷周“帝”“天”宗教文化观念演进至宋明时期的“天理”,中国宇宙观始终强调主宰是内在的,而非外在超越的。“主宰”只是借用之辞,生生之理就是万物自己主宰自己和自身运行之理之道,亦即万物所以能生起的内在根据。
二、万物皆以虚涵实,无纯物质性的实体观念
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倾向于视自然万物为真实固定的实体,也不同于印度哲人将当前世界视为梵天的幻化和虚妄不实,唐君毅认为,中国哲学视万物皆以虚涵实,宇宙是“虚而不妄、实而不固者”,即“实非实质而含虚、虚非虚幻而含实”。② 事物之所以皆可与其他事物相感通而化生不已,乃因为事物的本性能涵摄其他事物,这可以看作“实中有虚”。《尚书·洪范》解释五行曰:“金曰从革,木曰曲直,火曰炎上,水曰润下,土爰稼穑。”这是将五种自然事物从相互感通时所见之“功用”上看待。《易经》八卦,则从“健、顺、陷、丽、止、悦、入、动”的德性和功用角度诠解自然事物“天、地、水、火、山、泽、风、雷”。中国宇宙论中,没有不可破坏、永恒不变,且潜伏于感觉世界之下的物质性实体观念,而是从万物相感通、相涵摄、相生成的功用角度理解万物及其生生互联的。
与“虚”“实”相应的另一对概念是“有”“无”。中国哲学认为,自然万物有中含无,无中含有,有无相含。从宇宙现象发生角度说,“有”乃来自“无”,“无”能化为“有”。“无”何以能化出“有”?因为“无”中本含“有”而非虚无。同时“无”化为、化出“有”之“有”中,乃“不含实质意”之“有”。相关论述如“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万物出乎无有。”(《庄子·庚桑楚》)“虚者,万物之始也。”(《管子·心术》)“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张载《正蒙》)
唐君毅指出,正因为中国自然宇宙观将宇宙理解为虚而实、无而有的,“所以中国哲学上用以描述宇宙本质的名词如理、气、易、阴阳之类,均一方不含实质意,故理则曰‘浩浩不穷,气则曰‘流行不息,‘易者变化无方,‘阴阳者升降不常,一方又不含空幻意,故理则曰‘万古不息,气则曰‘充塞宇宙,易则曰‘弥纶天地,‘阴阳无始无终”。③唐君毅此论可谓精彩!理解中国先哲的万物观需要从虚实相涵的两方面加以把握,这也是把握中国哲学核心观念之特性所需注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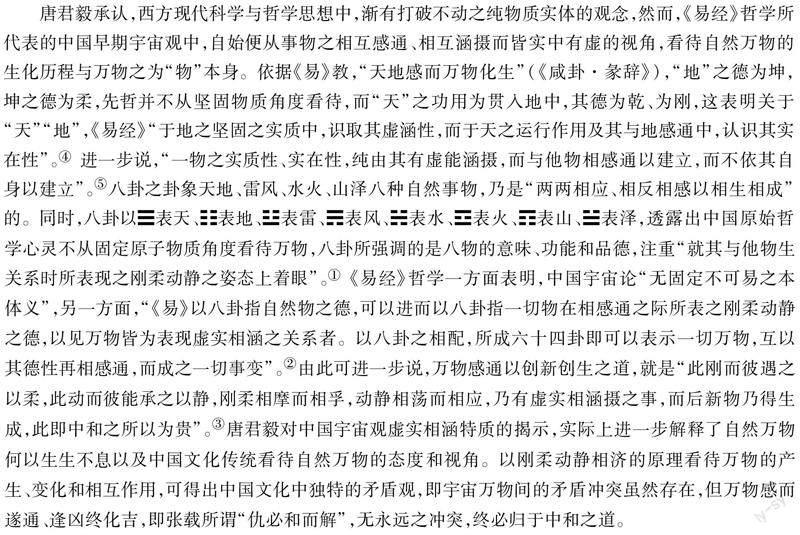
中国哲学视万物为气化之流行,也是“以虚涵实”宇宙观和万物观的内容和体现。严复曾在《名学浅说》中指出,中国人思想中惯用“气”指称世间万象,是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分析观念和清晰概念的表现。唐君毅却评论说这也“正可见中国人视一切物为一意味、动态、功用、过程”,④也是中国人“即用显体”“即体即用”思维的体现。针对严复的观点,在《哲学概论》中唐君毅分析道,“气”可以看作“一物之能自己超化其形象,以成其他形象之能”,“此气可连之于初具某形象之物,而称之为某物之气”。然而一物总是在不断变化其形象,所以“具某一形象之物之本身”,便只不过是一气之化或气化历程。正因为万物乃由气化而成形者,所以自然万物之“性”,就是“指其能超化一形象,以成他形象,或生他形象之性”。“万物之性”在于万物能由化而生,而不断更易其形象之“几”上,宋儒称之为气化中之“理”。自然万物之“性”“不在此形之中,亦不在此形之外,而如位于此形与形之相续之间,以化此成彼者”,“故所谓物之性,实只由物之呈其所能或作用而见。而凡物之呈其所能与作用处,无不有化于物之旧形,而有成于物之新形”。⑤ 看待自然宇宙要从万物生而化、化而生的大化流行处着眼,万物的形象具有动态性、连续性,也具有整体性和关联性,阴阳相继不已,显隐相承不断。这种有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万物观,强调从万物之关系处、流变处,亦即感通性和摄受性上看待万物之本性,而无原子论和原质论式的纯物质实体观念,是中国自然宇宙观视万物“虚以含实”和“虛实相涵”观念的重要体现。陈来认为,注重关系而不重视实体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与将宇宙万物还原为原初最小实体单位而注重实体状态的西方自然宇宙观不同,注重关系的中国哲学“把事物理解为动态的关系,而每一具体的存在都被规定为处在不可分离的关系之中,每一个存在都以与其发生关系的他者为根据”。⑥ 感通是万物互联的状态和生成机制,而理解世界的感通就需要理解万物的虚实相涵。法国汉学家朱利安在其《唐君毅之中西自然宇宙观》一文中亦指出,唐君毅所论自然宇宙观之特质,“最重要的是可由此引出‘自然物之实中皆有虚之观念”。⑦
三、独特的位序时空观,物质与时空统一不离
正因为自然物皆虚实相涵,甚至可以说一物之所以为“物”,就在其具有摄受性与感通性。因此,中国自然宇宙观表现在时空观方面,便认为时间、空间与物质从根本上是不相离的。这与在现代新物理学之前,西方实体性物质观念将时空与物质各自独立看待有根本不同。传统西方实体性物质观念认为,物之外有虚无的空间,物质运动经历时间,物之外尚有无限空间和时间,从而有无限延展的时空观念。而中国自然宇宙观如上文所述,从不将一物看作只限于占据一定时空的固定物,具有独特的位序时空观。在唐君毅早年所总结的中国自然宇宙观特质中,特别列有“万象以时间为本质观”“时间螺旋进展观”“时间空间不二观”“时间空间物质不离观”四个方面。① 唐君毅认为,在究极的意义上,时间是事物的本质,时间与天地万物根本不可分。《周易》所谓“与时偕行”“与时消息”“天地革而四时成”“变通莫大乎四时”等论说,均“表示天地万物与时同生同灭同升同降,顺贯而行”。② 同时,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提出时空不可分离之前,中国先哲始终强调时间与空间不二,秦汉以降常以四时配四方,而且中国哲学常用时间的观念说明空间,用空间的观念说明时间,如《易经·泰卦》“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和《易传·系辞》“往来不穷之谓通”“变则通,通则久”中,“往来”“变”“久”是时间状态,而“天地际”“通”是空间状态,可以很好地说明时空不二观。
独特的位序时空观是中国自然宇宙观的鲜明特质。基于《周易》卦爻之“时”变“位”亦变,“位”变即“时”变的“时位说”的启示,唐君毅认为,“位”即代指空间,“时”也可以称为“序”,位序变则事物所感通的其他事物和事物本身也相应变化,事物与位序(时空)不相离。所谓自然万物的空间,就是“万物赖以相与感通的场所”;所谓事物间的时间,就是“万物之相承而感通之际会”。所以,没有空洞的时空,时空就是“宇宙生生之几之所运,皆乾坤之大生广生之德所覆载而充满”。③ 不应有将万物仅看作有限形体占据一定时空,而其外仍有无限时空的观念。唐君毅以日和草木举例说:“日之所在之空间,非只在彼天某一部,乃遍在于日光之所照也。草木之生,非只生于其生之时。其生乃生于使草木生之过去宇宙之其他生化历程之上,而复生于此草木之生所开启之未来宇宙之生化历程之中。物之作用之所在、功能之所在,即物之所在。”④既然时空与物质相即不离,物体之外空无所有的无限时空观念便无意义。
“往古来今曰宙,上下四方曰宇”。位序时空观念之下,中国文化重“自当下位时以说宇宙”,认为“当下为今古四方上下之所交会”,也可以称为今古上下四方的“极限”或“中和之地”。自当下中和之地看,宇宙乃是万物充满的生化历程,人与万物亦始终在相互感通之中。所谓时间和空间的无限,可从万物相与感通无尽而生化不穷的角度看,“当感通之际,即物皆超出其原先之位序,超出原先之有限时间空间,而见无‘限”。上文所举日和草木之例便是唐君毅所理解的在感通中见证无限。当下是过去和未来的交会之际和四方上下的中和之所,“凡物之感通,皆见一时位之物,与他时位之物之交会,而见一中和。故中国先哲不言无限而言中和。此中和之所在,盖即无限之所在也”。⑤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也。
正因为万物与其所处时空之位序不相离,又由于中国哲学一气充塞和阴阳循环的观念,万物及其所在时空便被视为往者恒来,“恒若周旋以折回”。相关论述如:“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周易·泰卦·象》)“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老子》第十六章)。“消息盈虚,终则有始。”(《庄子·秋水》)中国文化中,宇宙不是直线平展的,也不是层叠式的,而是轮流周转和回绕式的。基于对“列星随旋,日月递癤,四时代御”(《荀子·天论》)的把握,中国先哲认为天地中和之气常在,生生之几不息,可从万物往来不穷中得证时空之无限。中国文化中,对天地开辟的本源问题的兴趣,基本上止于太初元气概念,道家学派虽表现出较多兴趣,但亦不更加深究详求其具体历程。中国历史上,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和三统递换说,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说,邵雍的元会运世历史观等,均是以人当下所居时位为中心,观天地万物的循环往复和宇宙之无限性。诚然,西方平展无限的天体观念、时空观念和进化观念促使西方天文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进步并贡献于人类文明,然而,中国独特的位序时空观也构成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宇宙观基础。此外,结合战国出土文献《恒先》《凡物流形》等道家文献,现代学者指出,以战国道家为代表的早期宇宙观中,“道”“太一”等“常被描述为根源性和恒常性的时空统一体,一个蕴含着无限潜能和生机、浑朴宁静、无始无终(时间)的太虚(空间)。这个时空统一体自然而然地兴作生成大宇宙时空,分化繁衍出万事万物。而在宇宙万物生成之后,它继续成为宇宙周而复始运转的枢轴,万物生生不息再生成的不尽源头,以及人类回归本根本命的永恒家园”。① 道家从生成论角度对大宇宙时空的生成及万物化生回归本根特征的揭示,可以看作中国独特位序时空观的生成论论证。
四、人与自然感通有情,价值内在于宇宙万物
中国自然宇宙观的另一重要特质是天人合德,视自然万物本身含有美善价值。唐君毅认为,这是中国自然宇宙观的最大特征和中西思想最大不同處。中国哲学视自然宇宙为生机流行发育的境界,生命与物质无间,物质就是生命流行的表现,所以中国人对自然万类素不喜作客观冷静的科学分析,不是强调价值中立,而是强调人与自然感通有情,以道德的精神和艺术审美的眼光观自然之善美。这即是哲学上的“道德存有”问题,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对此掘发最为用力,作为牟宗三挚友,唐君毅亦有自己的论说,且将之作为中国自然宇宙观的重要特质,阐发得最为全面而圆融。
唐君毅认为,依中国的道德精神看,自然世界表现价值不可否认。与牟宗三的观点一致,他认为“人性之仁,即天道之仁,而天道之仁,即表现于自然”。② 人性之仁乃是绝对无私,不仅不私其财物、气力等,更不私其德。因此,人不仅肯定自身有仁心仁德,也必然外推至他人与万物,“望其能仁而视若有仁”,肯定万物皆有类于人之仁德。人的仁心表现在人与万物感通而成己成物,而化育流行的万物也在相与感通之中。人有仁义礼智之德,万物亦莫不有元亨利贞之德。万物虽不能自觉其有德,但既然万物化育时可显示出感通、生生、成就之理,与“人之出于仁义礼智之心之行事,显相同之理”,那么,视天地万物同享元亨利贞之德“将为情之所不能已”。③这里从人之仁心和道德价值感推出价值内在于万物的论述,建基于唐君毅以“道德自我”为核心概念的哲学体系。他还说,万物求生存而不断创新发育,也显露出万物具有内在之仁。自然界的矛盾和斗争服从于生命体之求统一与和谐,阴杀服从于阳生,万物生生不息本身就证明“天道之必以生道为本、仁道为本”,亦即可证明“自然界并非不表现德性与价值”。④他认为,西方自然主义的缺陷正在其不言价值与德性。中国文化中,则根据人不私仁与德的道德精神,能够将仁德客观化于自然宇宙。
正因为中国哲学视宇宙处处充满价值表现美,故对宇宙之美与德的赞叹,在历代经典著述中随处可见。如:“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系辞》)“上善若水。”(《老子·第八章》)“诚者天之道也。”(《中庸》)“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礼记·乐记》)儒家对自然万物有一种充满敬意的心境。人不是万物的主宰,也不是宇宙生命进化的顶点,更不把万物看作神为人而创造,而只将人看作万物之灵。人心有虚灵明觉,可与万物感通而有情。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乃是互为宾主的关系,相遇以礼,相待以仁。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是情上的感通。人由自然得其养,故对自然抱有感恩之心而非征服之心。⑤ 唐君毅指出,西方近代认识论中的自然,是智性认知活动的产物,而人对自然首先应是情感上的“统体觉摄”与感通,并奉之以禮的关系,智性认知活动应是第二位的。
价值内在于自然万物的宇宙观,使人注重寄托其情于天地万物,并注重在日常生活中顺应自然。早期文献《周礼·夏小正》和《礼记·月令》等皆详细记述了自然节气、物候之变化与人在行为上应如何配合,“使人求其行为事业中之精神意义、文化意义,与自然节气之意义,交相融摄”,①并认为一年节气的运行可与音律配合,而有审美的价值,天体、时序的运行,乃是宇宙在演奏无声之乐。同时,中国的历书兼顾日月之运行,对昼之日、夜之月,同样地加以尊重,这比阳历的不重视夜月,更为爱戴自然的光明。中国的传统节日多以阴历为据,清明至郊外扫墓以不忘其亲,端午到水边纪念屈原以表达爱国忠君之意,七巧节望天星以培养天长地久的爱情意识,中秋节赏月以祈望团圆美满,重阳节登山以表达避灾敬老之意,过年守岁以静待万象更新,均是对“重要的自然物,一一表示亲情,而同时于其中培养表现吾人之爱祖宗、爱国家,与悠久的儿女之情,与慧福之合一,心境之扩大,及成始成终之意识者”。②由中国节日文化可见,中国文化注重将人之精神文化活动与自然宇宙时节的运行“相应而并展”。
价值内在于自然万物的自然宇宙观,表现在中国艺术审美上,便是“中国人恒能直接于自然中识其美善,而见物之德,若与人德相孚应”。③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和“暮春咏归”的言行已经点出自然兼有美善的意味。中国人在观自然之大美的同时,也将人心之德性寓于其中,可以看作人不私其德而奉献给自然的大礼。于是,“君子观乎天,则于其运转不穷,见自强不息之德焉;观乎地,而于其广大无疆,见博厚载物之德焉;见泽而思水之润泽万物之德;见火而思其光明普照之德”。④ 尤其是水之德,更是被诸子百家赞颂不已,孔子见其川流不息之德,老子见其柔谦善下之德,庄子见其虚明如镜之德,孟子见其德性流行之德,荀子见其明察须眉和平中准之德,韩非子见其水平公正之德,不胜枚举。以上为无生物之德,至于有生物,更是显见。如动物中马有武德,犬有忠德,牛有负重之德,鸡以五德闻名,以至以麟凤龙龟为“四灵”,如麒麟为仁兽,凤凰为圣禽之说。哪怕西方人认为狡诈的狐狸,中国文学中也常将之化作多情美人。植物中,有所谓“岁寒三友”“植物四君子”之说。松、竹、梅、菊均无争强斗胜之姿态,不以力显,与物无争。中国人看待天地万物,乐观其“连而不相及,动而不相害”(《礼记·礼运》),注重自然万物的“生机”“生意”“生趣”和“生德”,不像西方那样单纯赞颂自然力。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此心仁德的流行。⑤
人以道德之心和眼光看待天地万物,于是天地万物成为道德性的存在对象和本身即含有美善价值者,这就是所谓“道德存有”问题。杨泽波近著认为,儒学谱系中有一主一辅两条线索,与道德践行主线并行且互动的辅线,即是道德存有的线索。这一线索先秦已经开其端,于宋明儒学中真正展开,而将问题挑明讲透的则是“十力学派”,熊十力及其弟子牟宗三认为,“道德之心不是死物,有很强的创生性,不仅可以创生道德践行,也可以创生道德存有,赋予宇宙万物以道德的价值和意义,使其成为道德的存在”。⑥ 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道德之心在完成道德存有的创造后,即包括天在内的万物成为道德存有对象后,“受之前天论传统的影响,人非常‘谦虚,又会不自觉反身来一个‘道德投射,将自己的功劳推给天”,“经过这种投射后的天摇身一变,喧宾夺主,不再是道德存有的对象,反而变身成了主角,不仅成了人的善性的形上来源,而且成了宇宙万物‘原本就有道德色彩的终极原因”,⑦ 并由此引申出一种天人合一感。杨泽波对“道德存有”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指出了“价值内在于自然万物”这一中国自然宇宙观特质的思想实质,可视为对熊十力及唐牟诸先生相关思想的批判性推进。
五、结语
中国自然宇宙观深刻地体现着中华文明形态的特质、思维方式和性格走向。在肯认人与自然宇宙深刻贯通的“天人合一”观念之下,中国自然宇宙观认为,自生自化的生生之理是宇宙万物的内在律则,该律则是自由原则、化生创生原则而非外在必然原则。看待自然万物也不取物质性实体观念,而是将万物看作虚实相涵的关系性存在,由此强调在连续、动态、关联的视角下理解世界,而不取静止、孤立、实体的自我中心的哲学观念。正因为中国哲学将万物看作具有摄受性与相互感通的存在,所以自始便具有物质与时空不相离的观念,形成了独特的位序时空观与以当下为中心的“中和”观念,宇宙不是直线平展的,而是轮流周转和回绕式的,此时此地乃是上下四方、往古来今的中心、中和之场域。又由于中国哲学视自然宇宙为生机流行而无限发育的,物质即生命流行的表现,从而进一步强调“万物一体之仁”,人与自然万物感通有情,价值内在于宇宙万物,建构出中国哲学独有的“道德存有”论。
唐君毅基于中西印相比较的视角,以《周易》哲学和儒家哲学为主要思想资源,①对中国自然宇宙观总体特质的揭示十分深刻,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自然宇宙观的理解。在关于宇宙“从混沌到有序”问题的认识上,中国自然宇宙观取整体的、有机的、动态的观点,而非西方式的“原子论”和“机械论”的立场。自然与人的关系也非主客二分,而是互为主客、相待以礼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可以说,中国这种“非决定论”的自然宇宙观与西方近代科学的机械决定论式的自然宇宙观格格不入。然而,西方近代实验科学的成功及其与技术结合后的巨大成就,造成了西方自然宇宙观“天然的”正确的主流地位和认知误区。与此相应,中国自然宇宙观沦为“前现代”而“非科学”的初民朴素思想,甚至被认为无真理性可言的错误宇宙论。不过,现代系统论尤其是“耗散结构理论”,以及现代物理学“量子场论”的创立,与中国自然宇宙观强调“整体性”“感通性”“摄受性”“规则秩序的内在性”和“生生不息的动态性”相呼应、相支持,②可以说中国古典自然宇宙观获得了现代科学的支持而具有“科学合理性”。
客观地说,中国古典自然宇宙观的现代衰落,主要是无法有效解释西方经典科学之成功所致。究其根源,作为西方科学之根基的机械决定论的自然宇宙观虽远非对自然宇宙的整体真理性把握,但不可否认有其适用和有效的范围与场域;而中国自然宇宙观虽具有其深刻性和真理性,但若仅将自然宇宙描述为一个整体的、直接的和谐状态,便无意中忽视了“宇宙中还有‘封闭系统(与外界只有能量而无物质交换的系统)和‘孤立系统(与外界没有能量和物质交换的系统)的存在”,③ 从而无法避免“拉普拉斯决定论”和“拉普拉斯妖怪”的攻击。因此,若要重建中国自然宇宙观,重新认识中国自然宇宙观的深层特质和其真理性是重要而关键的第一步,同时,还必须正视西方“机械决定论”和宇宙观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唯有将中国自然宇宙观与西方经典科学观和宇宙观看作相互合作而非根本排斥的关系,主动涵摄机械论自然宇宙观于自身之中,中华文明形态的自然宇宙观才能获得现代性和有效性。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