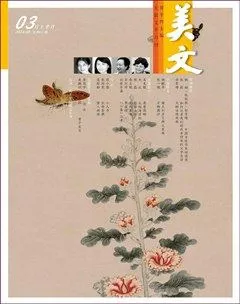少雨的土地
张华 上官文露
上官文露 文学博士,作家,首届梁晓声青年文学奖获得者。曾任北京电视台等媒体记者、主持人。2015年开始创办文学及音乐类互联网电台“上官文露读书会”“阳光书签”“博文夜读”“那些歌儿”等节目,全网收听量逾30亿次。诗歌作品曾入选《2020中国年度优秀诗歌选》,微电影剧作曾获金鸡百花奖和北京国际微电影奖等。
一
本文标题取自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玛丽·奥斯汀的《少雨的土地》。在人类社会,文学一直以“文学即人学”作为自己的旗帜,以占据一席之地。然而书写沙漠的自然文学似乎最不关心人,玛丽·奥斯汀的《少雨的土地》“始终把自然环境置于那些关于人的故事之上”。程虹老师在《美国自然文学三十讲》中这样评价《少雨的土地》的超越性:“奥斯汀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不是单纯的自然,也不是复杂的人类,而是一个为了同样需求而使自己适应于沙漠生存环境的,由动物、植物和人共同组成的不可分离的社区。我们可以说,通过这个社区,我们能够看到整个世界,甚至未来世界的缩影。”“请你失去自我。”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一个人都很少能从文学读本中读到这样的话,但程虹老师却在《美国自然文学三十讲》中将这在当今时代显得如此悖逆人生旨趣的话语分享给了我们,它来自于美国女作家玛丽·奥斯汀,在此时此刻,显得如此恰到好处地出现。
几世纪以来,我们所作的表达,几乎都是在声嘶力竭地为被时间尘封的作家而招魂,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黑塞、卡夫卡,这些对人类自我的迷失而忧心忡忡的智人,他们曾不遗余力地揭示人类自我的迷失,并尝试探寻出路。而于20世纪下半叶美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自然文学,却给出了另一种方向,它强调对于自我的淡化。现今,人们被一种矛盾所围困,一方面,人在人群中的自我还稍嫌孱弱,另一方面,人在自然面前的自我却越发膨胀。自然文学符合一切人们对于用世间最灵动优美的文字描述自然的想象,代表作家梭罗曾经凭借一本《瓦尔登湖》使之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旅行圣地,但在这样的文学流派中,后来却有一支作家队伍剑走偏锋地进入了最为严酷、苛刻的环境之中,那片曾被人类视为生命的禁区,与死亡联系最为密切的生态景观之一:沙漠。
“如果可能,你会选择定居在沙漠吗?” 假如对一个久居城市绿化带中的人问出这个问题,他一定会认为你有些疯狂。的确,沙漠和所有自然景观一样可以作为审美景观存在,可以容人寄托情愫 ,但不同的是,唯有沙漠是最不能容人置身其中的。水被视为生命的源泉,而一个少水之地注定了与人类利益的冲突,一种根源上的敌对。沙漠,毕竟比不上瓦尔登湖的环境令人神往。在自然文学作家中,爱默生与梭罗有终生以散步为职业的浪漫命名,一生流连于相对温和的自然环境中,而美国女作家玛丽·奥斯汀却去往沙漠小镇住了12年,创造了在当时的美国还无人问津的沙漠美学。唐纳德·沃斯特在其《帝国之河》中这样评价玛丽·奥斯汀:“终其一生,她都极度渴望抱住一处私人空间,免于与他人的逼仄纠缠,她发现沙漠于她再适合不过。她敬畏那里的植物,它们趋向于孤独生长,为彼此留出足够的空间。”
玛丽·奥斯汀的沙漠美学出现以前,在美国西部,人类与沙漠的对立更加极端。19世纪40-60年代,大约有30万人陷于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之中,他们不得不穿越极度干旱的地区,有人一夜暴富,也有无数人命丧于此。这是人与沙漠最近距离的交互,一位淘金者几乎死于热井之中,在他70岁的时候仍能想起沙漠之行的每一个恐怖细节。
此后,90年代科学家对沙漠的介入为自然文学作家开辟了道路,使他们能够带着科学理性和艺术感性两种目光走入沙漠。这种深入沙漠的眼光和体验,使得人们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人们最初将自然视作“被实验和被开发的土地”,后来过渡到将自然视作“被崇尚和被珍惜的土地”。
二
那么沙漠究竟有何原因應当被珍惜?这个问题人们当然会发问,但从自然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着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人类的这种傲慢,唐纳德·沃斯在《帝国之河》中也曾特别清晰地揭示过:“他们坚持认为,自然缺乏任何一贯性、秩序或者效率。当河流抵达大海,或者在干旱的沙漠空气中蒸发,他们称之为‘浪费水流,他们断言人类必须尝试主宰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强行为这些自然的元素做出更好的安排。” 那么究竟什么才应当是最好的安排?沙漠是否应该被消灭,沙漠中植被覆盖是否越多越好?在沙漠治理问题上,我国也曾走入过想当然的误区之中,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国的三北防护林、北部几大沙区治理,在植造林地的时候,都往往追求多多益善。这种方式在二十多年后终于出现了弊端:树木大面积死亡,沙区地下水位严重下降。这样的现象使得人们对于治沙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最终发现,以往的治沙行为以高覆盖度的植被追求极致的治沙效果,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生态用水难以支撑这种高密度的植被覆盖。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森林培育学家尹伟伦曾说:“在干旱、半干旱地区覆盖的植被,是低覆盖度疏林或稀疏灌丛,这是自然现象。大自然造就了沙漠沙地,治沙的理论和实践,也要向大自然学习。”
沙漠几乎是治疗人的狂妄和傲慢最好的药物,这是人不得不在用多少为人惊叹的智慧也无法扭转的自然规律面前,低下他高昂的头颅的时刻。在自然面前,人类一向以符合人类利益为最高准则。然而,如果不去考虑人的存在,沙漠作为独立的存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该如何理解它?它有着自己运行的逻辑,有着适宜它本身环境的生物,在这个视角中,人饱胀的自我终于得以稍稍被抽离,使得人们有思考自然本身喘息之机。人类剔除傲慢,真正愿意理解和尊重自然本身。在这种视角之下,当我们否定沙漠时,我们绝不仅仅是在为人类否定掉威胁和恐怖的事物,同时也否定了一种可贵的超越性的视角。美国史学家、作家华莱士·斯特格纳曾提出一种名为“超越绿意”的理念:你要超越绿意。你要放弃那种只与花园和草地相联的美丽,你要适应无人的视野,你要理解地质年代。当我们变得只会欣赏容易取悦自己的美丽时,就将无法看到事物的整体性。如果我们只能欣赏绿植与鲜花,而不能欣赏沙漠的存在,就无法理解大自然鬼斧神工下的完整而平衡的生态之美,它“从不知去钟爱某物”,它为角蟾和响尾蛇所花的心思与它为美丽的五彩蝴蝶所花的心思别无二致,它为沙漠和鲜花丛生的山谷所花的心思也一般无二。
三
在沙漠是否应当被珍惜这个问题之中,最不需要解释的部分,就是沙漠能够作为风景、作为审美对象被欣赏这一点了。纪德在他的名篇《沙漠》中写道:“不毛之地;冷酷无情之地;热烈赤诚之地;先知神往之地——啊!苦难的沙漠、辉煌的沙漠,我曾狂热地爱过你。沙漠审美的尽头,是一种足够复杂且矛盾的意象理解。”
中国也有沙漠美学,最早出现于诗经时期,在唐代则有蔚然成风的边塞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脍炙人口。公元737年,王维赴往西河,望着今天的腾格里沙漠写下壮阔的诗句,这是中国沙漠美学的一角,也是边塞诗沙漠意象的全盛时期。
当代中国也有很多为人熟知的关于沙漠的叙事,如徐克导演的《新龙门客栈》等。沙漠作为一种典型的情境帮助编剧完成塑造人物性格、行动逻辑等戏剧任务。沙漠是人们口中的“无情无义之地”,令金镶玉养出了一身的市侩狠辣。金镶玉情执于已有钟情之人的周淮安,周淮安的一句“我不像你有勇气面对这片沙漠”,也让观众明白,他注定无法欣赏金镶玉沙漠一般的豪直性情。而沙漠作为柔和的事物以浪漫的气息示人,则要得益于女作家三毛笔下的撒哈拉沙漠与她的爱情传说。在大多数时候,沙漠是作为人的点缀出现的,我们用爱情和人性去将之赋予意义,人们对于沙漠的接纳,也基本上是以一种玩赏的态度。
梭罗不会想到他虽成就了瓦尔登湖的美名,却也可能为瓦尔登湖招致了毁灭之灾。游客涌入瓦尔登湖,一边享受着自然之美,一边用尿液进犯那绿色的透明的湖水,瓦尔登湖已不复梭罗笔下的景致,几乎成为人类的小便池。然而,人类将自己当作游客和大自然的座上宾,将自然之美放在手中把玩,这种态度正是自然文学所反对的。自然根本不是为了人而存在的,它不为人而美,当然也没有供养人的义务。玛丽·奥斯汀在《少雨的土地》中写道:“在所有它的栖居者中,它对人是最不上心的。”也正是在像沙漠这种最拒人千里之外、最残忍的自然面前,我们才知道美是自然的本质,与人类世界的善和道德无关,它不是由人赋予的,人类的欣赏,也只是他们自身的一厢情愿。
在这种自然文学中,人类将重新取得对于自然的视觉角度,那也许是平视,甚至仰视,而不是俯身向下,以临幸的姿态对待自然。
(责任编辑: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