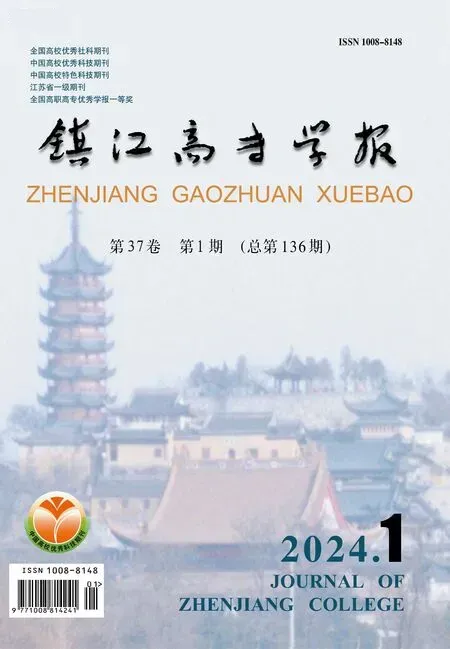关联、异同、比照、影响
——赛珍珠与鲁迅的中国小说观比较
朱希祥,王从仁
(1.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上海 200062;2.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5)
在赛珍珠研究中,鲁迅与赛珍珠的关系是颇受学者关注的问题,主要涉及3个方面内容: 1) 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即鲁迅给友人的信函中对赛珍珠作过的3次简短评价。对这些评价,许多学者都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论,点出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多侧面的意义等。2) 通过对鲁迅与赛珍珠相关作品和人物的分析,肯定鲁迅与赛珍珠在关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写作观念方面的相似与相异。3) 对鲁迅与赛珍珠关于中国古典小说文学观异同的分析。这方面的论文极少,且系统性分析有所欠缺。
由此可见,我们较多关注了当年鲁迅对赛珍珠的评论与评价,也注意到了赛珍珠与鲁迅一样,采用中国农村和农民的题材进行小说创作的实践和取得的成就。但我们对赛珍珠与鲁迅的中国小说的评述言语与理论的关系,及其两者对后世的影响,还未有较为系统与深入的研究。
笔者以赛珍珠1938年在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中国小说》、鲁迅1923年编成与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据1924年讲学记录稿于1925年整理出版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为主要个案(1)赛珍珠.大地三部曲[M].王逢振,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进行影响比较与平行比较相结合的研究,以厘清他们有关中国小说史及中国古代小说经典作品的评说。因这些评说,对其后的中国乃至世界的中国小说评价线索、主旨、范畴、内容等,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尤其是鲁迅的评论,基本是中国小说作品评论及小说史撰写的圭臬。赛珍珠的演说也因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力及作品的受欢迎度,而具有世界性的重大意义。笔者主要就两者对中国文学史编写与文学作品的评论所产生的影响,延伸性地作一番简析。
据多方资料揭示和概括,赛珍珠对鲁迅非常敬重与感佩,对鲁迅的小说创作与评论也是非常熟悉,并在自己的创作与演说中参考与借鉴了一些鲁迅的观点和论说。例如,就在鲁迅以不无轻蔑的语气评价赛珍珠之后的第3天,赛珍珠就向一位名叫章伯雨的来访青年问起鲁迅的情况,对鲁迅的学问、创作深表敬佩,对鲁迅的处境表示由衷的关切和同情。1934年赛珍珠主编《亚洲》杂志之后,又请斯诺撰写《鲁迅——白话大师》,发表于该杂志的1935年第1期。1936年9月号上,该刊又登载了斯诺翻译的鲁迅小说《药》和散文《风筝》,这大概是在鲁迅生前发表的最后作品英文版。尽管鲁迅若在世,很可能对此仍不以为然,赛珍珠却在授奖仪式上讲演《中国小说》时,引用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许多资料,她表示将来要写一部中国小说史,用小说体裁写成关于中国艺术的历史。1954年,正当中国和苏联的文艺界指责赛珍珠的言论是“猫头鹰式诅咒”时,赛珍珠却高度评价鲁迅,“周树人——笔名鲁迅——也许是第一个清醒者。他意识到虽然自己的灵感可能来自于西方文学,但只有把自己新产生的激情用于写自己的民族,才能摆脱模仿”[1]195。1972年,也即赛珍珠辞世前一年,赛珍珠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指出“后来有许多优秀的中国作家写有关农民题材的作品,鲁迅就是其中非常有名的一位”[2]139。
赛珍珠有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学习的经历,也有兼具中美思维的宽广视野与丰富的创作经验,故而在借鉴与承接鲁迅成果的基础上,又延伸与拓展了相关的中国小说评论理念,进而形成了独到的思路、见解与观念。
1 赛珍珠与鲁迅中国小说观的关联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在其1920年至1926年于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基础上整理而成,思辨色彩颇浓,理论性较强,以文言文撰写,文字典雅精炼、言简意赅。赛珍珠的《中国小说》是赛珍珠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讲稿,逻辑性、连贯性不是很突出,口语化讲述、枚举式分析,篇幅不长,但通俗易懂、重点突出,风格与鲁迅关于中国小说研究的讲演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较为相似。
两位都是实践性的作家,不仅精通小说创作,还深刻了解中国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有着学习与借鉴的影响关系,故在两者陈述、评论和评价中国古典小说的语言材料中,会不时呈现些许相似与相同又有所差异的观念与语句。
中国小说出自民间,被当时文人所轻视,这是鲁迅与赛珍珠谈及中国小说起源时相同的观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与第二篇、《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一讲里,反复引用与阐释了《汉书·艺文志》中的话语,即“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鲁迅引孔子的话“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后,作了进一步发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他强调的是中国“小说”概念起源于“小道”,认为小说出自民间,当时文人颇为轻视小说。赛珍珠则用口语化的语言表达了这个意思:“……因为人民创造了小说,而活着的人们做些什么并不会引起那些认为是艺术的文人们的兴趣。”[3]957她还借题发挥,用一个民间笑话和自己的描绘,嘲笑了文人干硬酸丑的形象,然后得出结论,即“文人不认为小说是文学,这是中国小说的幸运,也是小说家的幸运”[3]958。
鲁迅虽具极深沉的锐气,却似乎未曾对中国小说与文人的关系说过如此尖刻的话语。鲁迅曾言:“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却刚健,清新。”[4]35这样的语言来表达民间文学与文人的关系,似乎更平和与切合实际。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没有就此再做延伸、发挥与拓展,而是在《门外文谈》《花边文学·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等文章和一些书信中表达过相似观点。赛珍珠却不停歇,仍继续此话题。她又引用中国的姚鼐著作和《四库全书》作例子,再次强调中国小说原本与文人无关系且有着自身特有的背景和环境(“土地就是普通人民”“阳光就是民众的赞同”“小说在中国是普通人的奇特产品”等)[3]958-959。这些都可看作是赛珍珠对鲁迅文艺思想的承接与延续、拓展,由此引发与深化的是对中国小说特点、风格、作用与功能的概括与归纳。
赛珍珠与鲁迅相似的看法是,中国小说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众人。鲁迅认为“‘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造也”[5]7。赛珍珠不仅承接了这一理念,而且还结合作品将此理念阐述得更为具体。她曾言:“中国小说不像西方那样受一些伟大作家左右。在中国,小说本身一向比作者重要,……《水浒传》的现代版本虽然把施耐庵的名字作为作者,但它并不是由一个人写的。……《三国》形成的历史表明了它在总体结构和无确定作者方面和《水浒》完全一样”[3]970。赛珍珠的这些说法虽不够严密,但充分表明了她的民间视野与民俗立场,也即她在演讲中曾反复强调的,“(中国小说)用白话写成,……以流畅通俗、清晰易懂的风格,……默默地通过在茶馆、乡村和城市贫贱的街道上,由一个未受教育的普通人对平民讲故事的方式开始出现”[3]960-962。这可看作是鲁迅相关民间观念的通俗释解与延续拓展。
赛珍珠直接引用鲁迅的意思评析中国小说的地方并不多,好像只有一处,即在论及《儒林外史》的情节结构方面的艺术特色时。赛珍珠认为“这部书虽然很长,但没有中心人物,每一个人物都通过事物的线索与另一个人物相连,人物和事件一起发展变化,就像著名的现代中国作家鲁迅所说的那样:它们像缝在一起的一块闪闪发光的锦缎”[3]973。鲁迅原话是这么说的:“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5]190由此可见赛珍珠对鲁迅思想的借鉴与承接。
也正因如此,我们在阅读与欣赏鲁迅的小说《祝福》《阿Q正传》和赛珍珠的小说《母亲》《大地》等作品时,会被其中的中国旧时乡村和农民形象(如祥林嫂、阿兰、王龙、阿Q的朴实、勤劳又麻木、愚钝的特点)所感染,进而引发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思考、对作者高超精湛的艺术创作手法与中国“史诗精神”描述的鉴赏。
2 赛珍珠与鲁迅关于中国小说观的异同
就家庭背景、社会经历与生活历练、性格特征、文艺理念、审美趣味等方面而言,赛珍珠与鲁迅有着极大的差异,故而在有关中国小说的评论与评价乃至有关文艺的观念等方面,他们有着许多不同点并各自显示独特个性。但因评论对象基本都是中国古代小说经典,所以,两者观点仍是同中有异或异中见同,还能不时显现承接与延续的痕迹。
在中国小说观阐述方面,赛珍珠与鲁迅使用的体裁不同,鲁迅用史论方式,赛珍珠用演讲形式。因而鲁迅既有对中国小说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寻觅与揭示,更有对小说文体和各个时代小说特征的概括、归纳与评析;赛珍珠则侧重对中国小说整体特色的揭示、叙述与阐释,也间接而简要地概括有关文学和小说发展历史的一些她认为的要点。
鲁迅称其《中国小说史略》是“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5]1,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则是要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5]268。我们从他《中国小说史略》的各篇标题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各讲标题可看出这种“粗略”的概括与历史变迁的“线索”。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除前4篇和第7篇标题比较客观地显示相关内容,如研究综述、神话与传说、汉代小说、世说新语等,其余各篇都将各个时期小说的特征显示在标题上,如六朝之鬼神志怪、唐之传奇、宋之志怪及传奇、宋之话本、宋之拟话本、元明传来之讲史、明之神魔、明之人情、明之拟宋市人、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清之讽刺、清之人情、清之以小说见才学、清之狭邪、清之侠义及公案、清末之谴责等。《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相关表现方式有所变化,除“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唐之传奇”“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三讲外,其余的两讲“明小说之两大主潮”和“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都是在正文层次的标题上显示其主题和主旨。如“明小说之两大主潮”即指“神怪之争”与“世情”,“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强调了“四派”即“拟古”“讽刺”“人情”和“侠义”,重点突出,让人一目了然。
赛珍珠的叙述与描写相结合的《中国小说》显得更口语化,热情洋溢地用讲故事、抒豪情的方式讲述中国小说的特色及其与外国作品的相似与差异。例如,她说到“中国小说是自由的。……它没有受到文人艺术那种冰霜寒风侵袭”时,引用了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话与诗,随后又以抒情加比拟与议论的语言作了小结,认为中国人的“故事的天才之水随意奔流,任凭天然的岩石阻拦、林木劝阻;而且,只有普通的人才来饮用,从中得到休息与乐趣”[3]959。
说到中国小说用白话写作的理由时,赛珍珠采用了叙事的方式来表达,“在一个有两百人的村子里,也许只有一个人会读。逢年过节或者干完活以后的晚上,他就向人们大声朗读某个故事。中国小说的兴起就是以这种简单的形式开始的”[3]961。而讲到中国小说是“从这种变成故事并充满几千年生活的民俗精神中发展起来的”时,她又引用爱尔兰作家乔治·拉塞尔的诗化语言来表达,“……那种精神就是以其民间传说式的想像认为什么事都有可能。它创造出金的船、银的桅杆、海边的白色城市、金钱的奖赏、美丽的仙境;而当那种广泛的民俗精神转向政治时,它随时都会相信出现的一切”[3]965。在演讲的最后,赛珍珠又重申了中国小说的民间性与大众化的特点。她表达了她的观点,即中国小说作者就是“在村里说书的人,他要用他的故事把人们吸引到那里”,这之后,赛珍珠又用了一段极其口语化和小说化的语句作了全文的总结:
文人经过时他无需抬高他的嗓子。但若一群上山求神朝圣的穷人路过时,他一定要使劲把他的鼓敲响。他必须对他们大声说:“喂,我也讲神的故事!”对农夫,他一定要讲他们的土地;对老头儿,他一定要讲到和平;对老太太,他必须讲到她们的孩子;而对年轻的男男女女,他一定要讲他们之间的关系。只要这些平民高兴听他讲,他就会感到满意。至少我在中国学到的就是如此[3]976。
阅读过中国经典小说和欣赏过赛珍珠多部小说的读者,恐怕都会呼应赛珍珠这番近乎振聋发聩的声响并认同她那句诚挚真切的表白。
当然,赛珍珠在《中国小说》和其他著作中,关于中国小说及其创作、关于文艺批评作品不同于国外小说的艺术特色与审美特征的概括与归纳、评价与赞赏还是占据了更多篇幅。而这些既显示了赛珍珠的独到见解与个性理念,也可看出她与鲁迅有关中国小说观的异同。
除上面已提及的内容外,赛珍珠还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与探讨的中国小说观念。例如佛教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中国小说的人物高于一切、汉朝是黄金时代而唐朝是白银时代、小说情节常常是不完整的、创造的本能是一种巨大的额外的生命力、小说家不完美但他们是人,等等。这里的一些观念如赛珍珠所说是她的独创,“我这样讲是我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们当中并没有人这样说过”。这里的“他们”,赛珍珠认为就是那些歧视中国小说家的“自称艺术大师的人”[3]974。
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对这些内容一一加以评论,只是就与鲁迅较为相同的话题作一个简要评析。那就是佛教对中国小说的影响。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开头有这么一段话: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见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5]29。
鲁迅这里论及的是佛教对中国志怪小说形成的影响。志怪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形式之一,以记叙神异鬼怪故事为主体内容,“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鲁迅陈述得比较客观,没有对其特征与价值作更多主观评价。赛珍珠也特意讲过中国小说用“白话”写作的“例外的情况”,即受佛教影响的情况:
有些文人从印度来到中国,作为礼物他们带来一种新的宗教——佛教。……他们到中国以后,发现文学已经远远脱离人民,在历史上所谓六朝时期的形式主义的影响下濒临死亡。文学家甚至不关心他们要说的内容,而一味追求文章和诗歌中的文字对仗,而且他们对所有不符合他们这种规则的写作都不屑一顾。佛教翻译家来到这种封闭的文学气氛当中,他们带来了极其可贵的自由精神。他们当中有些是印度人,但有些是中国人。他们直说他们的目的决不会符合那些文学家的文体概念,而是要向普通人讲明白他们要传授的东西。他们把宗教教义变成普通的语言,变成小说用的那种语言,而且因为人们喜欢故事,他们还把讲故事用作传教的手段。著名的佛教著作《梵书》的前言写道:“传布神的话时,要说得简明易懂。”这话可以看作是中国小说家的唯一文学信条,实际上,对中国小说家来说,神即是人,人即是神[3]960。
赛珍珠的这一段有意插入的话语,讲的也是佛教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与鲁迅的那段话比较,可以看出主观色彩的浓郁和主旨思想的鲜明,赛珍珠强调了中国小说语言方面通俗易懂、题材方面神人一体与融合的特色。
鲁迅与赛珍珠的这些对宗教、神灵崇信的观念,我们在他们的《故乡》《风波》《祥林嫂》和《大地》《龙子》等作品里都可以形象、生动地感悟到。
3 赛珍珠与鲁迅中国小说评论的比照
无论是讲小说还是写小说史,具体的作品评论、评析与评价是不可或缺的。鲁迅与赛珍珠谈及以上内容时,自然也紧紧地扣住了中国小说的具体作品特别是几部经典的小说。两人不约而同地论及一些相同的作品,但观念与见解仍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鲁迅与赛珍珠的演讲涉及的中国小说非常多,特别是鲁迅的两部著作,谈及的作品不胜枚举,笔者在这里以赛珍珠演说提及并加以评论的中国经典小说为主(按演说提及的顺序排列),用表格的方式,与鲁迅所谈作一简要的比照(见表1,上文已提及的不载),以便要点不烦和清晰明了(所谈内容有时不限1部作品)。

表1 鲁迅与赛珍珠对中国古代经典小说评论要点
从以上摘要性的对照语言,可基本看出赛珍珠与鲁迅对同一中国小说作品评论的相似与差异。总体看来,鲁迅从作家兼学者的角度评判较多,字字珠玑,深邃精到;赛珍珠从作家的创作和普通读者甚而是平民的视角阅读、欣赏与评论更多,行云流水,详略得当。对《水浒》与《红楼梦》,两人都较为详尽全面地批评,对其余作品都各具个性特色:有的三言五语,有的铺陈展开;有的只讲史实,没有结论,有的只讲感受,一言定音……。因内容丰繁,此处不再展开具体内容。但这些可贵的资料,可留无数文章让后人续写。
4 鲁迅与赛珍珠中国小说观的学术影响
鲁迅与赛珍珠的中国小说观(主要是以下几点),对当时的学界,尤其是对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4.1 关于小说起源于民间
“小说”的概念来自“街谈巷议”,当然,这个“小说”概念还不是指文学作品,只是指“小道”,即现在说的小道新闻。这一追溯,是鲁迅依据史书记载加以自己的辨析从学术层面确立的,对此,赛珍珠深表赞同。在“中国小说源于说书”的问题上,赛珍珠更与鲁迅异曲同工,共同推进了这一观念的深入探讨,并给时人后贤以深刻影响。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引用了大量资料,不仅揭示了唐代《一枝花话》的说话形式,还提出宋代的“说话”分为小说、讲史、说经、合生四家,其中小说、讲史最为重要,进而确立了“话本”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无独有偶,赛珍珠也专门研究过讲史与小说的关系。1931年赛珍珠在《星期六文学评论》发表《中国早期小说》,第二年此文被修订为《中国早期小说源流》。赛珍珠在此文中说:“中国的著作中很早就开始包含故事素材。除开说书人和巡回演出的艺人,多少世纪以来,也一直有写下来的故事。……到了宋代,故事的篇幅大大增加,部分原因也许在于使用了印刷。据说,因为天下太平,无事可做,皇帝宋仁宗就命令大臣们给他讲以前的故事。故事越来越长,一天讲不完,第二天接着讲,最后,就有了后来的长篇小说的篇幅,然而,这些故事除了开始分章分回以外,实际上只是长篇故事而非长篇小说。”[7]尽管宋仁宗命令大臣们讲故事的说法不太靠谱,也许是赛珍珠的误读,但中国小说尤其是讲史源于说书的见解,是明白无误的。
这不仅是鲁迅和赛珍珠的观念,还是一个时代的潮流,不少文学史家纷纷将目光从传统诗文转向小说戏曲,其中最早也最为突出的是1932年出版的郑振铎《插图本文学史》。其子郑尔康在《爝火不息——〈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重印后记》中说:“在这部书里他最早把历来不为文人雅士们所重视的弹词、宝卷、小说、戏曲等不能登上文学殿堂的所谓‘俗文学’,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了进去,以他独到的见解为‘俗文学’正了名,为‘俗文学’争得了文学殿堂中的应有席位,堪称为‘前无古人’之壮举。”[8]183尽管郑尔康称其父“前无古人”,但从时间上而言,郑振铎重视民间文学受鲁迅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与赛珍珠至少是不谋而合,只是在体裁范围方面,郑振铎有更大的拓展。
4.2 关于小说读者在民间
赛珍珠认为,在中国是“人民创造了小说”[3]957,小说因其非正统性而缺乏了主流的关注,作品也常常容易流失,但因此也少受了诸多的批评、干扰与限制。于是,赛珍珠将民众比作供小说“随意成长的土地”,而“民众的赞同”于小说发展而言,是“最充沛的阳光的抚育”[3]958。
如果说梳理中国小说的源头与流变,是一项带有学术探讨性质的事,那么,把握小说的阅读对象,即确认小说为谁而写,涉及小说创作对象的本质特征,赛珍珠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中国小说主要是为了让平民高兴而写的”[3]960。
这一观念,除了出于理性思考外,更多的是赛珍珠从生活中获知的。她回忆孩提时在镇江,“我们也听周游四方的说书人讲故事。他们在乡村道边走边敲小锣,到了晚上,就在乡村中打谷场说书。一些江湖戏班也常到村里来,在大庙前找个地方唱戏。这些艺人的演出,使我很早就熟悉了中国历史,以及历史上的英雄豪杰”[1]26-27。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三侠五义》等武侠小说“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也”[5]250,又引《〈三侠五义〉及〈永庆升平〉序》所云,认为此等书“善人必获福报,恶人总有祸临,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终逢吉庇,报应分明,昭彰不爽,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5]250-251。同时鲁迅也阐述了小说读者在民间、小说的兴盛在民间的理念。
于是,《中国文学史》在被编写时,出现了对民间文学的重视,这也影响到小说创作。以“山药蛋文学”著称的作家赵树理在《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中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其后一直坚持下来。”[9]56他进一步认为,只有“实地参加在大众的生活里,体验了大众的心情与体态,用大众的语言”,才能创作出真正属于大众的文学。
当然这些作家的理想追求有区别,鲁迅关注“国民劣根性”,赛珍珠具有基督精神、宗教情怀,而赵树理更多地是秉承文艺为大众、为革命事业服务的信念,但三者颇有共通处是可以感知的。
4.3 关于小说与文人的关系
如上所云,赛珍珠说“文人不认为小说是文学,这是中国小说的幸运,也是小说家的幸运”[3]958。这是赛珍珠的率性之说,其实“文人不认为小说是文学”的证据很明显也很普遍。自从有了中国书籍“经史子集”的四库分类法,历代“四库”,包括清代的《四库全书》均不收白话小说,“集”部是文集之意,是传统意义的文学作品汇集,可是只收诗文而排斥小说戏曲。中国古代的小说大多为说书人口耳相传的结果,相当于集体创作。即便有署名作者,也采用化名,真实的作者多不可考。可是赛珍珠毕竟是外国人,也并非是严格意义的汉学家,她不会引经据典,只是凭感觉来叙述。
相比之下,鲁迅不仅凭借史料,以及自己的考证来说明问题,而且他的结论也尖锐、老辣。他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却刚健,清新。”[4]35这个说法扩大了论述的范围,从小说扩展到整个文学,还涉及外国文学,暗含鲁迅历来提倡的“拿来主义”。鲁迅对“不识字的作家”的褒扬,堪称空前,影响巨大。
中国小说乃至中国文学的非文人化倾向,影响相当大。在文学史的撰写方面,一度出现了民间文学引领文人创作的说法,认为《诗经》引领了先秦的文学,《汉乐府》引领了汉魏诗歌,以此类推,不一而足。这个颇有些极端的结论,具体表现在北京大学1955级学生编写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这部用了35天写出的75万字的文学史,显然是大跃进的结果,但论其滥觞,确实与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论断有一定关联。
其后的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的编写,经常与时俱进、应时而变,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仍是重要的参考文献,其中的一些论断也基本被承接。赛珍珠的一些有关中国小说的理念,因与鲁迅相关理念有密切关联,所以虽没有资料说明对后世文学研究与创作的直接影响,但其中的一些通俗而精辟的论说,也“英雄所见略同”般地被无形地引用与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