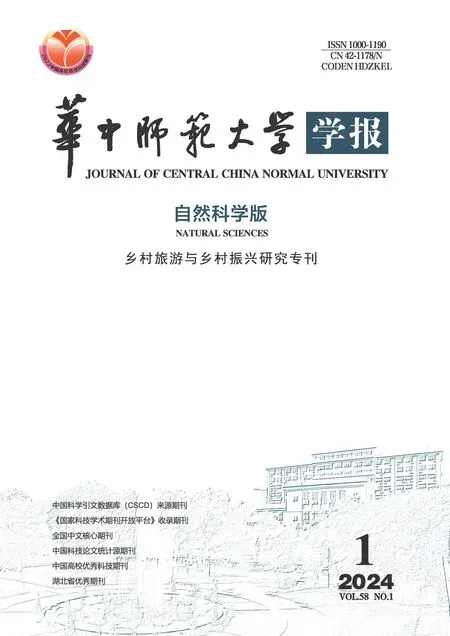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关系及影响因素研究
王兆峰,刘路锋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长沙 410081)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是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上的普遍富裕[1].共同富裕是一个内涵丰富、层次多元的范畴,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其发展性、共享性与可持续性.实现居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然而当今我国社会仍然面临着城乡差距、区域贫富差距等问题.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定通过并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求自觉主动缩小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旅游业作为当今的朝阳产业和幸福产业,对地区经济的拉动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凭借着原汁原味的山川景色和风土人情,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休闲消费[2].因此,厘清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关系,对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共同富裕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国外研究中,虽然直接探讨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关系方面的文献较少,但在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农村收入等与居民共同富裕具有一定关联主题的研究积累了大量成果.这些研究主要探讨了旅游影响理论中旅游乘数、倍增效应对社会经济、环境产生的作用.Ghali[3]与Mathieson[4]认为旅游发展能够有效增强经济的倍增优势;Hwang[5]认为旅游政策可以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Schuber[6]认为旅游发展依赖地区经济等;Samimi[7]认为区域经济与旅游发展存在相互作用.国内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多与经济改革[8]、农业经济[9]、中国政治[10]等领域相结合.研究方法由早期对概念阐述[11]、理论分析[12]等的定性研究逐渐转向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13]、建立评价指标体系[14]等方法的定量研究.国内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聚焦以下方面: 1) 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如李鹏基于产业质量视角,分析了旅游对共同富裕的提高路径[15];郭为通过回归分析,定量验证了旅游可以促进中低收入家庭提高收入[16].2) 共同富裕视域下旅游发展的路径研究[17-19].3) 双向关系.直接探讨居民共同富裕的研究不多,当前学界主要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讨旅游发展与其相近的主题,如乡村扶贫[20]、乡村振兴[21]、美丽中国建设[22]、农村可持续生计[23]等耦合协调研究.因此,当前文献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亟须完善的空间:1) 共同富裕与其他学科领域结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与旅游学科结合较少,仍需进一步深化研究.2) 共同富裕与旅游学科关系多为定性研究,鲜有通过时空耦合协调关系角度进行定量研究.3) 以往研究多聚焦两者单向作用,较少关注两者协调关系的影响因素,探讨关键驱动因素时空效应变化的文献更为鲜见.
鉴于此,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作为案例地,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及GTWR(geographically and temporally weighted regression)模型,定量分析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之间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动态演变,并揭示其耦合协调关系的影响因素,对长江经济带实现居民共同富裕和旅游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1 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机理
居民共同富裕主要涵盖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区域统筹与城乡统一等,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和功能的目标系统;而旅游发展是必须遵守经济、社会、生态等基础,以实现地方、区域、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动态系统[24-25].人地关系理论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是区域关联要素综合分析的重要理论基础.在区域系统中,可以将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分别看作系统的重要构成要素.实现居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实质上是创造和释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过程,这为旅游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环境基础;依附于环境的旅游业,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生态友好的重大使命,旅游发展不断培育的新产品、新业态满足人民的多元化休闲、康养、文化等需求,丰富精神生活,从而助力实现居民共同富裕.可见,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间实质蕴含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作用关系,并且,结合耦合协调理论以及参考郭为[16]、徐紫嫣[26]和张东徽[27]等学者研究来看,两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有序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耦合协调系统(如图1).
居民共同富裕是旅游发展水平的环境基础.1) 居民共同富裕有助于刺激旅游消费.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改善,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为人们产生旅游活动提供了充足的收入和充裕的时间,刺激旅游发展水平进入新的阶段[28].2) 居民共同富裕有助于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居民共同富裕有助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共享发展成果,不断提高偏远农村公共服务水平.3) 居民共同富裕有助于扩展旅游市场的服务能力和空间范围.居民共同富裕的实现会使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极大的提高,原有的旅游消费的形式和空间则难以满足居民产生的新兴旅游需求,因此市场需求将会反过来促进旅游发展进行升级迭代[22].4) 居民共同富裕能为旅游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实现居民共同富裕,不仅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而且也将提升人文素养.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认可与欢迎态度,将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并转化为旅游业发展的软实力.
旅游发展水平是实现居民共同富裕的动力引擎.1) 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是“富裕”,经济增长是实现“富裕”的必由之路.旅游业通过刺激消费、增加投资、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等途径带动地区经济发展[20].2) 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加快区域协调.旅游发展加强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治理的协调联动,推动沿线地区通过旅游业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加强了省际交界地区的合作交流与均衡发展[29].3) 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通过旅游吸引城市居民前往农村进行旅游消费,发挥旅游的乘数效应,刺激乡村经济的蓬勃发展,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30].4) 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丰富精神生活.旅游活动不仅可以放松身心,缓解精神压力,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也可以利用旅游发展创造的经济价值,实现对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和传承,从而保障区域文化的繁荣发展[31].
2 研究设计
2.1 区域概况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个省级区域,面积约205.23万km2,占全国的21.4%,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自然资源丰富,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地貌复杂多样,多高山大河;人文资源灿烂,吴越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民族风情等蕴含其中.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势头强劲,率先实现了“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其余城市与此仍有不小差距;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城市群之间出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因此需要在经济腾飞的基础上,处理好地区贫富差距的问题.与此同时长江经济带也是我国旅游发展较为活跃的地区,截止到2020年,全区域景区数量为5 510家,接待人数49.4亿人次,旅游收入为62 240.63亿元,依旧保持这良好的发展势头.因此廓清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不仅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对旅游高质量发展更是大有裨益.
2.2 指标体系构建
2.2.1 共同富裕 在结合新时代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现实需求[32]与相关理论[33]的基础上,根据体系构建的基础、目的、原则、依据、标准等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参考谭燕芝等[14]、陈丽君等[34]与胡西武[35]等的研究成果,从发展水平、共享差距、可持续3个维度选取25个指标构建居民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发展水平是衡量全体人民是否取得实质性进程的显著标志,是满足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和高品质生活的重要选择.设置发展水平维度旨在揭示共同富裕的城乡发展的实质性进程.共享差距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核心内容,是化解新发展阶段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路径.设置共享差距维度旨在反映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凸出问题.可持续性维度主要强调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是一个渐进式、先富帮后富的过程,需要持续发展的经济、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支撑.设置可持续性维度旨在表明科技、文娱、生态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具体指标数据见表1.
2.2.2 旅游发展水平 参考陈志军[36]和李佳[20]等学者的研究,从旅游经济、接待水平、基础设施3个维度选取10个指标构建旅游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旅游经济选取的指标为各地人均旅游消费、旅游活力及旅游密度,直观反映地区旅游价值;接待水平选取的指标为地区旅行社水平、游览场所水平、住宿业接待水平与餐饮接待水平,直观反映地区旅游服务的充裕度;基础设施指标选取交通密度、客运总量与污染治理,直观反映地区旅游交通的便捷度和环境质量.具体指标见表1.
2.3 研究方法
2.3.1 熵值法 本文采用熵值法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熵值法是用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的数学方法.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也越强.其优点在于排除了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广泛应用于各领域研究中[37].
2.3.2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指的是系统与系统间通过相互作用、彼此影响而促使系统实现协调发展的过程.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本文构建了居民共同富裕和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模型,参考相关文献,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的权重分别设为0.5[38].公式为:

表1 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和旅游发展水平指标表Tab.1 Index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of resident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1)
T=αU+βE,
(2)
(3)
式中,C为耦合度,U和E分别是共同富裕系统和旅游发展系统.D为耦合协调度,耦合协调度值域为[0,1].参考相关文献,协调等级的划如表2所示[36].

表2 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耦合协调等级划分Tab.2 Coordination classification of residents’ common prosper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2.3.3 GTWR模型 地理时空加权回归(GTWR)模型将时间维度与空间异质性相结合,可以更好地处理时空非平稳性,基本公式为[39]:
(4)
式中,(ui,vi,ti)是第i样本点时空坐标;ui、vi、ti分别表示第i样本点的经度、纬度和时间;bo(ui,vi,ti)表示第i样本点的回归常数,即模型中的常数项;Xit为第k自变量在第i点的值;ai为残差;bk(ui,vi,ti)为第i样本点的第k回归参数,其估计方法如下:
(5)

(6)
其中,带宽的选择影响时空权重的确立,本文采用AICc法则.
2.4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与代表性,本文所选取的数据均来源于2011—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其中缺失数据利用插值法计算得出.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分析
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如图2).说明在经济体制转型升级、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协调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矛盾的时代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在发展能力、共享能力、可持续能力方面虽有改善,但变化幅度偏小.分地区看,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呈现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阶梯下降特征.具体来看,下游地区的居民共同富裕程度远高于中上游地区,分别为1.79%、1.52%,且年均增幅2.04%.该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繁荣,其主要依靠中小企业的民营经济带动,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发展典范,在块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特点的区域经济,形成优势互补,良性竞争的区域关系,从而缩小了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尤其是浙江省在2021年被国务院列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印证了江、浙、沪地区居民共同富裕在全国具有示范作用.中游区域虽有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经济增长极,但是省域内居民共同富裕发展不均衡,存在明显“断层”现象.上游地区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上,受限于地理位置、产业基础等因素,使得发展多依赖于省会城市,往往表现省会强劲,其余市县发展疲软的状况.

图2 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水平Fig.2 Timing diagram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resid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由图3可知,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总体旅游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并在2019年达到最高值,之后出现回落.这主要是因为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凭借着全国战略地位最高、区域经济活力最活跃、经济发展水平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旅游产业规模发展进入快车道,在经济提质提效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然而2020年受疫情的影响,导致旅游活动在前半年一度停止,后半年虽有短暂发展,仍难以扭转疫情带来的冲击.具体来看,下游地区始终位居领先地位,由2011年最低值0.315到2019年最高值0.405,年均增幅3.17%,而在2020年骤降至0.34,降幅高达16.05%.中上游地区交替领先,水平相差较小.2011—2017年及2020年中游地区水平高于上游地区,2018—2019年上游地区领先中游地区,因此,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三大区域呈现“下游领先,中上游水平胶着”的空间格局.下游地区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区域,是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主要是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强劲的经济实力、广阔的市场环境为旅游发展塑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在此基础上利用自身旅游资源禀赋以及较强的服务接待能力,为游客提供了高质量的旅游体验,从而奠定了龙头地位.然而,旅游具有脆弱性,在此次疫情冲击下,对下游地区造成的影响尤为显著.中上游地区旅游发展水平发展受制于经济基础、市场环境等因素,虽与下游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但在基础设施和接待水平上得到了发展.

图3 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水平指数Fig.3 Timing chart of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3.2 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特征
3.2.1 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耦合协调的时序演变 基于耦合协调公式计算得到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同时根据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所处的耦合协调阶段进行分级,依此揭示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表3).
从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耦合协调度整体表现为波动上升趋势,其耦合协调水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11—2016年处于轻度失调阶段,2017—2019年处于勉强协调阶段,2020年处于轻度协调阶段.表明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联系逐渐加强,耦合协调水平不断得到优化,趋于向好发展;2020年,遭受到疫情冲击,出现下降状况.从省域层面看,江浙沪三省市耦合协调水平位居前列,且远高于其他省市.研究期内,江苏、浙江在2019年皆达到濒临协调阶段,而上海更是进入初级协调阶段.上游地区的重庆和贵州两省市研究期内耦合协调峰值均突破0.4,尤其是贵州,从2011年的0.28上升至2019年的0.42,年均增幅达1.6%,增幅位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之首.原因可能是近年来采取的淘汰落后产能、改善粗放型发展模式、大力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加强旅游资源的开发营销以及西部大开发政策在经济、科技、金融等方面的对口帮扶等措施,使得重庆和贵州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表现为波动上升趋势,但耦合协调水平偏低,这些省市需要抓住长江经济带发展新机遇,不断提高居民共同富裕度和旅游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以免造成两者失调.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各省市在疫情影响下,2020年均呈现不同程度的降低.

表3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演变表Tab.3 Coordinated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among residents in all provinces and cit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3.3.2 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耦合协调的空间演变 2011—2020年的研究时期中,由于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受到影响,故2019年为研究期内峰值,为更好探究研究期的耦合协调空间变化情况,故采用自然断点法,选取2011年、2019年、2020年进行空间变化的展现(如图4).2011年,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由下游到上游表现为“高-较低-较高-低”的发展格局.其中上海、江苏和浙江勉强协调和轻度失调,湖北、湖南、重庆和四川轻度失调,安徽、江西、贵州和云南中度失调.2019年是研究时期的峰值,空间分布呈“东高西低”格局.各省市耦合协调均表现为稳步提升,上海达到初级协调,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江苏、浙江、重庆、贵州达到濒临失调,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及云南则为轻度失调.2020年上海有所下降,但依然处于勉强协调;江苏与浙江处于濒临失调,其余省市皆为轻度失调.这说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推动着旅游发展产业的繁荣,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各省市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表现出“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增强了长江经济带的旅游发展水平;旅游发展水平也在推动了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活跃了市场资源、促进了资金流通,为居民旅游服务的同时也促进了资金流入社会进行再分配,提高了共同富裕度.2020年耦合协调度降低,主要是由于疫情管控,对旅游业造成了巨大影响,使得旅游发展水平大幅度下降,与居民共同富裕差距拉大.
3.4 影响因素分析
3.4.1 变量选择 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是一个综合发展系统,包含经济、社会、环境等综合因素.参考赵传松[40]、陈梦根[41]等学者的研究,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选取8个指标作为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的影响指标,其中经济方面包括人均GDP(元)、旅游收入占据总GDP之比(%)、人口密度(万人·km-2);社会方面包括受教育人数占比(%)、养老保险人数占比(%)、科技费用占GDP之比(%);环境方面为污染治理费用占GDP之比(%).
3.4.2 数据的处理和评价 考虑到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量纲差异,故采用标准化对数据进行量纲处理.此外为了消除伪回归现象,对解释变量数据采用显著性和共线性检验,得出各影响因素结果,见表4所示.
由表4,最终选取人均GDP(元)、旅游收入占比(%)、污染治理费用占GDP之比(%)、人口密度(万人·km-2)4个指标作为GTWR的解释变量.并将解释变量进行GTWR测度,拟合效果良好,见表5.

图4 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图Fig.4 Spatial map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of resid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表4 最小二乘法各参数一览表
3.4.3 影响因子时序分析 运用时空地理加权模型,对不同时间内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进而绘制各系数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如图5所示),以观测时间演变趋势.
人口密度对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的影响由负向逐渐转为正向,且后五年离散程度增大.我国丰富的劳动人口,使我国经济受益于“人口红利”,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样背负着人口膨胀对社会经济压力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人口密度过高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也影响我国教育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给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而对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耦合协调产生抑制作用.随着产业结构优化、“两山”战略及精准扶贫等战略的实施,使得我国经济逐渐转型升级,人力资源对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趋向正向促进作用.
污染治理投入对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的影响作用正向和负向皆有,但是分布范围在-0.1~0.1之间,影响作用较小,离散程度趋于集中.这可能是我国虽在生态环境治理上逐渐重视,但是更多是表现在推动转变企业发展方式,提高技术效率,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不同省份的环境质量存在差异,污染治理投入的不足则会抑制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性.
旅游收入占比对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作用为正向,研究期内影响系数大致围绕0.4~0.6左右,保持着较高的影响力,呈“V”型变化趋势,由分散到集中再分散.旅游收入的发展是促进地区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就业率、增加居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因此区域内旅游收入占比高,经济更为活跃,居民共同富裕和旅游发展水平表现更高水平.
人均GDP对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最大,且呈现正向作用,但表现出下降趋势,前六年影响系数逐渐下降且离散程度趋于集中,而后四年则继续下降但离散程度逐渐变大.人均国民经济收入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只有在满足基本生理(食物和衣服)和安全(工作保障)的基础上,才会激发更为高级的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而对旅游而言,人们收入不仅决定着是否外出旅游,也决定着旅游类型、旅游时间、旅游地点等,进而影响旅游规模、层次等.人均GDP影响系数的降低则意味着近些年受到国际经济下行压力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对居民共同富裕和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协调产生较强影响.

图5 GTWR影响因素回归系数时序图Fig.5 Time sequence diagram of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GTWR
3.4.3 影响因子空间分析 利用ArcGIS 10.4,计算GTWR回归系数,取其各年份均值进行可视化表达,从而对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耦合协调各因素进行空间分析,由此得到图6.
人口密度回归系数中仅有四川和重庆为负向作用,这可能是两地人口密度过高,而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经济增长难以承接人口增长的压力;其余地区呈正向作用,其中云南和贵州系数较高,可能是由于近些年经济增长快,而两地人口基数相对其他省市较少,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成本投入到经济中.
环境污染治理回归系数大致为“上游>中游>下游”,这说明下游地区人口稠密、工业发达,“三废”排放多,而政府环境治理费用投入相对较低,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环境健康问题;而上游地区地域面积广大,而经济开发力度较小,相对于下游地区,环境承载力更强.
从旅游收入占比回归系数来看,产业结构系数为正向作用,其高值集中于下游地区的苏、浙、沪、皖,而在中游地区湘、渝两省市系数最低.产业结构对下游地区经济提供动力支持,优化经济结构,保障经济稳定性;同时地区经济存在“溢出效应”,安徽受益明显.而中西部产业结构在省市内经济占比不足,对当地居民收入增长和旅游发展起的作用有限.
人均GDP回归系数大致为“上游>下游>中游”,这说明下游地区人均GDP回归系数相对与中下游地区带来的耦合协调的影响更为显著;并且上游地区随着经济发展,旅游资源得到了开发,两者均得到了跨越式发展.

图6 GTWR模型回归系数空间分布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for the GTWR models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共同富裕的社会背景下,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评价体系,通过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定量分析了研究区域的居民共同富裕和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采用GTWR模型揭示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 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综合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中下游地区水平较为接近,而在2020年均出现下降,居民共同富裕综合水平整体呈逐年向好趋势;空间分布上,下游地区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皆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
2) 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呈逐渐上升趋势,2019年达到峰值,处于勉强协调阶段,重庆和贵州两地耦合协调水平上升较快,2020年下降到勉强协调;空间分布上,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格局,上海达到勉强协调,江苏和浙江则是濒临协调,其余省市为轻度失调.
3) 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影响大小依次是人均GDP>旅游收入占比>人口密度>环境治理投入.人均GDP与旅游收入占比表现正向作用,而人均GDP的影响逐渐降低,旅游收入占比呈“V”型发展态势;人口密度与环境治理投入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空间异质性,逐渐由负向转为正向作用.
4.2 建议
根据居民共同富裕和旅游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为更好促进两者耦合协调水平的优化提高,故提出以下建议对策.
1) 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的实现重在跨区域协同合作.推动政府与市场合作互补,发挥江、浙、沪地区的经济引领作用,使人口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资源由西部地区流向中东部地区,使资源优势转化为资金优势,同时进一步推动资金由东部发达省份向西部落后省份进行财政转移支付,采用“先富带后富、区域共同富”的协调发展模式带动区域实现共同富裕.
2) 长江经济带需要积极落实国际黄金旅游带建设,贯彻旅游发展理念,倡导区域内外旅游联动开发,加强旅游资源创新性开发,不断完善旅游政策,持续优化旅游设施,提高旅游宣传力度,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实现旅游高质量发展.同时,继续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为受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严重冲击的旅游企业采取相应的财政和政策扶持,减轻旅游企业负担;加强信息的共建共享,及时更新相关信息,确保旅游安全.
3) 长江经济带的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出现的地区差异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政府扶持、财力支持和跨区域合作,发挥下游地区经济的溢出效应,以长三角为龙头,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坚持对点帮扶西部省份.通过旅游发展,带动当地居民就业,扩大收入来源,提高收入水平,进一步缩小西部省份居民的贫富差距.
4.3 展望
居民共同富裕是促进旅游发展的前提与保障,而发展旅游是实现居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分析,有效地研究了长江经济带存在的贫富差距、旅游发展不均衡以及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但研究也存在局限性.1) 居民共同富裕是一个复杂多样的体系,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增加其他相关指标使评价体系更为完善.2) 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得到的结论,对于其他地区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问题是否准确还需讨论,未来可选择不同地区、不同时段、不同数据来源,进一步验证区域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的协调关系.3) 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的影响机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些因素难以进行量化研究,比如低收入群体增收效果、收入分配方式合理化进程、居民精神健康状态等等,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细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