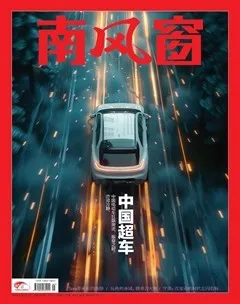美国效仿中国之后
人们普遍认为,美中关系紧张是两国之间巨大差异的不可避免结果—美国拥有一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中国政府则牢牢把握着经济的船舵。其实,许多美中冲突都源自两国日益增长的共同之处。尤其是,美国的相对衰落使其不安全感日益增加,促使其采取各类新经济和国家安全政策。随着美国效仿那些对中国颇有助益的战略,双边关系中的矛盾也成倍增加。
中国的惊人经济增长最终为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好处,因为它为其他国家的企业和投资者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場。此外,中国的绿色产业政策拉低了太阳能和风能的价格,为全球低碳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国家自然也会对中国的干预主义和重商主义做法有所抱怨,但只要发达经济体的政策是由消费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逻辑驱动,这些影响就不会给对华关系造成巨大压力。
相反,许多知识界和政策精英认为,西方和中国的经济操作是互补和相互支撑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和莫里茨·舒拉利克创造了“中美国”一词,来描述这种表面上的共生关系:中国补贴其工业,而西方则乐于消费中国提供的廉价商品。由于这种观念在西方盛行,失利的工人和社区得不到什么帮助或同情;他们被告知,要重新接受培训并搬到就业机会更多的地方去。
但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好工作的消失、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重要战略产业对外依赖性的增加所带来的问题,已变得不容忽视。美国政策制定者开始更加关注经济的生产方面,而新战略所围绕的产业政策,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那些并无太大区别:新技术和先进制造活动得到补贴,可再生技术和清洁工业也不例外;本地供应商和国产零部件受到鼓励,而外国生产商则无法获得同样的优惠。
根据“小院高墙”理论,美国试图限制外国获得那些被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倘若这些政策能使美国社会更加繁荣、团结和安全,那么世界其他国家也将从中受益—正如中国的产业政策通过扩大本国市场和降低可再生能源价格使其贸易伙伴受益一样。因此,这些新政策和新优先事项并不意味着美中冲突必须加深,但它们确实需要一套新的规则来管理两国关系。
良好的第一步是双方都卸下面具,承认各自做法的相似性:中国在敞开的窗户上装上了纱窗,而美国则在小院四周围上了高高的篱笆。
第二个重要步骤是,提高政策目标的透明度并加强沟通。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中,许多针对国家经济福祉以及国内社会和环境优先事项的政策,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作用。贸易伙伴们需要在各国采取产业政策来解决重要市场失灵问题时,给予宽容和理解,并将此类措施与那些明显以邻为壑的措施(也就是这些措施在本国产生利益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区分开来。
第三,必须确保那些限制性国家安全政策是目标明确的。美国将其出口管制定义为针对 “一小部分”引发“直接”国家安全关切的先进技术的“精心定制”措施。这些自我标榜的限制措施无可厚非,但对半导体的实际政策是否符合这一描述,以及其他措施可能是什么样子,还存在疑问。此外,美国经常会用过于宽泛的术语来定义其国家安全。
美国将继续把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安全放在首位,而中国也不会放弃其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合作难以成为当今中美关系的主流,但如果两国都认识到自身政策既不会有太大差异,也不一定会给对方造成伤害,那么合作可能会变得容易一些。
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国际经济学会主席,著有《贸易直言:对健全世界经济的思考》。本文已获Project Syndicate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