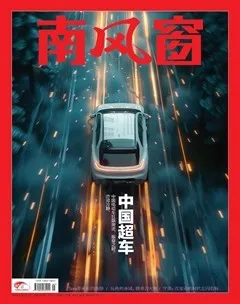中国新能源车海外狂飙,隐忧几何?
谭伊妮

哈萨克斯坦小伙阿卡斯首次萌生买辆比亚迪的想法,是在2022年下半年。
那时,他的朋友花20多万元人民币找人从中国买了辆比亚迪汉,车型外观设计很酷,还有五花八门又便利的智能化配置,一下子戳中了他的心,于是阿卡斯也到中国买了一辆比亚迪。在此之前,他对中国的汽车品牌几乎一无所知,身边人多爱买丰田、起亚、现代等日韩系燃油车。
提车回国后,阿卡斯发现,他每次出门总有人问车在哪买的。原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及其他中亚四国不少人对中国的电动汽车都很感兴趣,只是苦于没有官方销售渠道。
阿卡斯意识到,机会来了,于是,他开始在中亚和中国来回跑,干起了倒卖中国电动汽车的活,头一个月就卖出20多台,赚回了一辆比亚迪汉的钱。这样的造富故事并非个例,有人甚至在干了一年后卖出4000多台车,赚到几套房的钱。
近年来,由于智能化程度高、性价比高等优势,中国的电动汽车越来越受到海外群众的欢迎,出口量持续走高,酝酿出大量的市场机遇。
不过,“二手车”出口仅是隐秘一角,中亚、俄罗斯也并非中国电动汽车出口的主市场,主机厂在海外铺设渠道售卖新车的情形,或许更能直观体现中国电动汽车在海外的受欢迎程度。
比如,在中国电动汽车出口目的地排名前三的泰国,比亚迪就曾在2022年上市一款纯电汽车,预定首日就在展厅外迎来排队长龙,甚至由于购车人数太多得“叫号购车”。
正是在这些海外群众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整体汽车出口量屡创新高,在2023年取代日本摘下世界第一汽车出口大国的桂冠。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20.3万辆,同比增长77.6%,大大超过57.9%的汽车整车出口增速。
如此成绩,不能不令人振奋,尤其在上世纪我国汽车工业落后、市场由外企合资品牌割据的情况下,仅仅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电动汽车就逐渐走到世界前沿,这一华丽转身实属不易。但值得警惕的是,尽管我国电动汽车形势大好,出海路上依旧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售后难、地缘政治和文化差异等;是昙花一现还是产业长青,要看后续打拼的成效。
升维与降维
如何用一句话概括我国电动汽车出海的现状?
EqualOcean创始合伙人黄渊普的回答是,去年成绩很好,但不要过于乐观,属于“农村包围城市”。
单从数据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增速喜人,几乎是“跳跃式”蹿升。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3年,我國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分别为31万、67.9万和120.3万辆。
但放到全球大背景来看,尤其是散落到各个国家,中国电动汽车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和可见度依旧较低。黄渊普去年到德日美等20多个国家调研,发现在街上极少碰到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德国、日本、美国的车依然占据绝对优势。
这是因为我国的电动汽车出口量,算上了外资品牌在我国制造、并对外出口的车型,比如特斯拉。2022年中国出口的纯电动汽车总量约为94.5万辆,其中特斯拉产品占比接近32%。而在2023年,特斯拉的具体比重虽未公布,但也不低。
与此同时,宝马、大众、雷诺、奔驰在中国的工厂,都在对外出口电动汽车。而日美等车企除去本国生产和制造的汽车,还在全球各地建厂本地销售,多数不算是“出口”。
此外,我国电动车出海主力市场依旧在东南亚、非洲和拉美等部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像欧日美这样的发达地区声量较小。从全球来看,尽管在2023年我国出口的120.3万辆电动汽车中,欧洲市场占到38%,贡献不俗,但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虽然2023年中国新能源车出海势头很猛,但有一定的偶然性。
从2021年就开始做电动车出海的王海深有感触,他最开始做的是中东、中亚和东南亚等地区,后来才慢慢将业务拓展到非洲、欧洲、北美洲等地区,一方面是因为运输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政策和免税问题。
他表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从中国出口汽车到亚非拉等地区,属于降维打击,当地人民接受程度相对会更高一点,而到美国和欧洲等地区,属于升维,由于地缘政治、文化差异、品牌认可等因素,前期开拓市场的难度相对更大。
至于欧洲,也是在近几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才逐渐有了一点声量。法国伊诺韦夫咨询公司统计的数据显示,2023年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新车销量中,中国品牌占比达8%,高于2022年的6%和2021年的4%。
在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看来,虽然2023年中国新能源车出海势头很猛,但有一定的偶然性,尤其是在欧洲,前两年受疫情和全球芯片短缺因素影响,欧洲车企的产能普遍没有恢复,导致欧洲缺车,给了中国电动汽车可乘之机。随着欧洲局势的稳定、反补贴调查的进行,以及欧洲车企产能的恢复,欧洲车必定会发起反攻。
这一担忧并非无的放矢。王海去年在欧洲调研时发现,大多数欧洲人对于中国电动汽车的品牌熟悉度和信任度并不高,更愿意购买有一定知名度的汽车品牌,比如被上汽收购的名爵,甚至有的中国电动车企担心欧洲的消费者因其中国背景而犹豫,会在售卖产品时隐去该信息。
但品牌一事确实急不来。黄渊普告诉南风窗,相比其他品类(如无人机、运动相机),汽车领域出世界级品牌还要更难些,即便中国新能源汽车再强,且假定不受地缘政治影响,也很难想象会有很多“60后”“70后”的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去开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得等时代变化和代际更替。
“目前国产品牌称得上是世界品牌的还没有,比亚迪很有希望,长城、吉利、‘蔚小理等也都是候选,但品牌之路,基本单位是十年,需要数个十年才行。”黄渊普说。
竭泽而渔
出海的中国电动汽车,售后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无论是以二手车名义出海还是主机厂自主出海,由于出海时间尚短,在单个国家的量不大,售后困扰着每个电动车企。

提起售后问题,做了两年多“倒爷”的林吉很是头痛,去年他从中国倒卖了30多台电动车到俄罗斯,结果投诉率较高,多是车机账号注册故障等网络和传感器等硬件损坏的售后问题。问题出现后,由于俄罗斯没有汽车品牌的直营店和维修人员,基本很难得到解决。
去年6月,有位俄罗斯客户从林吉这买了车,结果不到半年,传感器和车机系统就出现故障,一直没得到解决,于是天天到俄罗斯主流媒体的评论区谩骂该品牌。林吉说:“所以后来找我买车,我都要事先声明:默认无售后。”
此外,电动车在低温天气下容易出现电池衰减,从而导致车子无法前行,而俄罗斯疆土面积大,人烟稀少,且充电桩设施不够完善,遇到这种情况时只能把车抛下,很难马上解决。
电动车维修非常依赖自动化的专用工具和软件,对于场地要求较高,对维修专业度的要求也更高。
黄渊普指出,燃油车和电动车完全是两个体系,电动车发展到今天,在全世界还不够普及,相应人才很少,在国内出现故障,维修尚且有一定困难,更何况是在国外。
根据车百智库、中汽智检、中国汽研联合发布的研报《智能电动汽车后市场新机遇与新挑战》,电动车维修非常依赖自动化的专用工具和软件,对于场地要求较高,对维修专业度的要求也更高,如新能源汽车维修可能涉及高压部件以及电池的开包检测等深度作业。
售后也是王海在倒卖时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了避免这一问题,他的选择是尽量跟有一定电动维修能力的经销商合作,以及到量稍微多一点的国家卖。
王海觉得,卖车和售后有点类似于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问题,卖车没有售后会阻拦很大一部分客群,而有售后的前提,是这个地区的汽车总量达到一定程度,有人愿意钻研,有利可图。
“没有售后去卖车其实很危险,好比竭泽而渔,”王海说,“毕竟买了车维修无门的顾客不会推荐该品牌给其他人。”
售后这回事,轻则投诉,重则涉及外交问题。据虎嗅报道,有相关从业人员透露,去年曾有国产电动汽车品牌向埃及销售了一批轿车,但没有提供技术支持,导致交付后车机上各类服务都不能用,结果当地车商和车主通过埃及驻华大使馆向我国主管部门进行投诉。
据王海所知,有小部分同行和车企曾为了避免该情况,特地打一枪换一炮,卖完一个地方就跑到另一个地方卖,但这并非长久之计,甚至可能致使一个产业“折戟”。20多年前中国摩托车在东南亚因不重视售后导致出海失败,就是一个例子。
本地化,始于人才
品牌、售后问题之外,提到中国电动车出海,可能更为人所知的困难,依旧是地缘政治和文化差异,比如欧盟反补贴调查。
在崔东树看来,要想克服这一挑战,在海外建厂是中国电动车企的必然选择,也就是从整车出海过渡到供应链出海。
在传统燃油车时代,随着日韩欧美等汽车崛起的还有它们的零部件公司,但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开始异军突起,比如电池领域就有宁德时代和比亚迪,而海外相关的零部件企业很少。通过在海外建厂,将车企利益和当地企业利益捆绑,创造就业和税收,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当地政府的反感。
黄渊普认为,仅仅建厂而不做本土化,也很难适应当地市场变化,占据一席之地;中国企业出海当前普遍遇到的最大瓶颈,就是全球化人才缺失和全球化组织能力弱。
这里又不得不提到前车之鉴,我国的摩托车出海。2000年前后,我国摩托车进军东南亚市场,曾迅速超越日本,一度市占率达到80%,但很快,不到三年,市场份额就被日本迅速夺回,现如今我国摩托车在当地的市场份额已经不到1%。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永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因为当时摩托车只是在当地建厂,没有跟当地产生合作,本土化是要尽量跟当地政府、企业合资,在资本层面达成合作,变成本地的公司。
除了资本方面的本地化,还得做到产品本地化。以欧洲为例,黄渊普表示,要想真正吸引欧洲顾客,得造出欧洲人喜欢的车,而不是中国人喜欢的车。像欧洲人其实大部分对于隐私比较看重,对于花哨的智能化设施接受度也没有国内那么高。
产品的本地化,并不是换个零部件或者软件那么简單,而是要考虑市场需求、消费群体,明确改进方向。这些都需要大量深谙当地市场和技术的人才。
产品的本地化,并不是换个零部件或者软件那么简单,而是要考虑市场需求、消费群体,明确改进方向。这些都需要大量深谙当地市场和技术的人才。
黄渊普告诉南风窗,人才和品牌一样需要时间去培养,不过中国本身有大量人才,可以鼓励他们走出去到亚非拉等地区。
除了以上人才,黄渊普还强调我们国家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很缺乏懂当地政治生态和形势的人才。由于我国是一个效率比较高的国家,我国不少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想当然”,在与当地政府、企业打交道时容易做无用功,客观上难以让企业在海外安全稳定地落地生产。
“不止产品和技术的本地化,整个企业做事情的方式也得融入当地,实现本地化。”黄渊普说。
在一起,继续狂飙
无论是从出口数据还是电动车全球市场来看,我国已经占尽先机。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数据显示,2023年1月至6月中国在全世界新能源乘用车销量中的份额为60%,产销量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
而从全球趋势来看,根据欧美各国碳达峰、碳中和的长期规划,燃油车禁售是必然趋势,我国新能源汽车换道超车的机会也是巨大的。不过这依旧需要时间,汽车出口跃居第一只是第一步,要想像日本那样拥有汽车品牌的全球影响力,我们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于电动车是新一代技术革命,本质上来说是电子产品,需要电、网络和软件驱动,对于环境的要求很高,中国的汽车崛起之路也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车赶超美国车不同,在基础设施上,需要做大量建设。比如充电桩的铺设,尤其是在俄罗斯、北美等部分国家人烟稀少的地方,对于续航里程要求更高。
另一方面,团结协作也是中国电动车企出海应该考量的因素。此前,参照日本汽车的丰田模式,出海并不是单独一家企业出海,而是财团、后勤、金融和供应链企业一起支撑着出海,可以起到很好的协同作用。尤其是零部件链条长的汽车产业,当中国电动车企协同时,想必能在海外发挥出更大的效应。
目前我国电动车拥有一定的先行优势,但若想把这一优势转换为产业的发展优势,还需要戒骄戒躁,多方协同努力。
(文中王海、林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