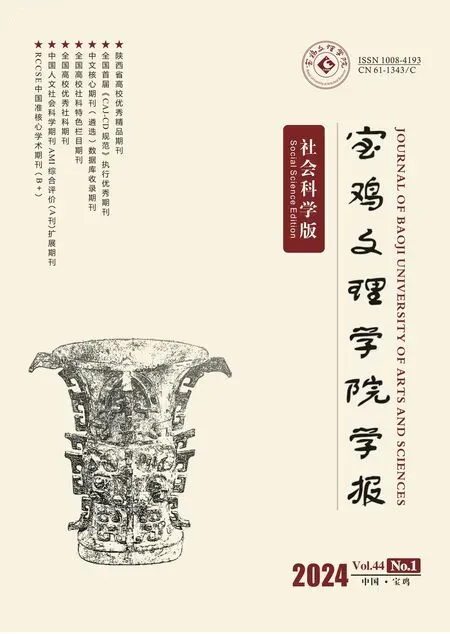明清兽灾言说与生态保护意识
王 立
(大连大学 语言文学研究所,辽宁 大连 116622)
野兽作为动物世界的大部分成员,在古代社会,既是人类的近邻,又是人类危险的对手和捕食者。明清时期,人类与野兽的关系虽然还在基本持续既往的状态,也有一些新的变化,从民俗叙事中可以约略体察。
一、明清兽灾的猖獗与自然生态环境恶化
明清时期,战乱频繁与人口无序增长,许多地区的山林被砍伐、垦殖,侵犯了一些猛兽的旧有领地,加剧了兽灾的爆发。首先,野狼、老虎等猛兽从山林中跑到人类活动的区域里,猖狂袭击人类。野兽反常的行为模式,折射出居民的生存危机。清初董含《三冈识略》卷二《狼入境》:“凤阳颍上县,群狼入境食人,行旅皆结队而过。”《申江杂识》的载录者很有感慨:
云间素无虎……九月初,忽有虎从西来。初十日,伏东郊外华阳桥灌莽中。有顾氏子,年十七,早行被啖。复潜迹至天马山一带,居人多有见者,俱闭户不敢出。总戎遣兵四出搜之,虎往来倏忽,偶一遇,逡巡却避,经月不获。诧为神虎。乃于普照寺建道场,命黄冠咒阴兵驱之,后竟逸去。余作新乐府以记其事……嘉靖初年,一虎自北从官路来,入市西空房中蹲坐。市有少年勇力五人,持刀枪攻之。虎跃起,五人皆伤,二人死,虎亦不食。[1](P181-182)
人兽相斗,互有所伤。战乱饥荒带来一些特定地区人口锐减,也促发了以虎为中心的兽灾猖獗,以至于某些地区人口为避虎而流亡异乡:“襄、蜀之人,十九血于虎口,其幸而免者,率皆聚于荆、鄂之间。”[2]可以说,如此避灾所带来的一系列民俗心理、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的变化,不可忽视。兽群乘着人间乱世、灾荒致人口锐减,迅速繁殖,在春季食物短缺时,偶或出山吓跑居民,一度占领了县城,驱赶那里的原驻民不得不奔走异乡。董含还称:“蜀保、顺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以千计,相率至郭。居人逃避,被噬者甚众。县治、学宫,俱为虎窟,数百里无人迹,南充县尤甚。”[1](P27)
其次,对付兽群泛滥的挑战,明清多地“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兴起了杀兽自救运动。民家叙事者对捕获猛兽器械发明和捕兽高超技术,进行着意的标举。如明人总结捕猎经验:
帅府茶会,言及杀虎云:虎骨之异,虽咫尺浅草能伏身不露,及其虓然作声,则巍然大矣。杀虎法,当用三只枪。虎扑人,性劲,必及中枪即杀者上格,退次之,左右枪既接,可杀也。又闻野豕雄甚,牙一触马腹即溃。其尤老者,恒身渍松脂,眠以砂石,为自卫之计,枪不能入也。中官海寿,射生有名,无不应弦而倒。一日,得老豕,矢着辄火迸,数矢不入。一老胡教之,云令数卒随之,作呵喝声,豕必昂首听,颔下着矢,彼必倒地,尾后更着矢,斯仆矣。已而果如其言。[3](P278)
在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人们若不讲究对付猛兽的方法,可能受到更多更大的伤害,于是不少捕兽发明也相继出现。据赵翼《檐曝杂记》,他以外来“他者”眼光介绍山西岢岚州捕虎能人多,以其地多虎:
故居民能以一人杀一虎。其法用枪一枝,高与眉齐,谓之齐眉枪。遇虎则嬲之,使发怒,辄腾起来扑。扑将及,则以枪柄拄于地,而人鞠躬一蹲,虎扑来正中枪尖毙矣。或徒手猝遇虎,则当其扑来,辄以首撞其喉,使不得噬,而两手抱虎腰,同滚于地,虎力尽亦毙。
他任官镇安时当地多虎患,有的虎甚至兼有肉翅,“盖千年神物”,重金召募能杀虎者,多方不可得;只得一普通的虎,还是靠设下机关以肉为饵钩获[4](P46-47)。处于人虎对立的时代,清代人显然是以土地——万物主人自居,千方百计猎虎杀虎。而实际上,此举为的只是人类自身一时的安全,并没把虎作为生物链上的一个环节,没想到虎的减少会使得食草动物数量骤增,加剧破坏当地的植被,最终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
多数情况下,毋庸讳言,那些带有新闻性的野兽食人传言,立场基本上是站在人类中心的,似乎人类是野兽疯狂扩展侵略的受害者,控诉中把野兽完全推到灾害施加者的被告席上。光绪二十七年(1901)云南镇康城坝山野间虎食人,先后达四五十人:
绅首马玉堂命猎户张地弩,以药箭射之,杀一虎,而余虎隐遁。……光绪三十年甲辰,镇康坝湾桥下首有虎与蟒蛇互斗于山坡,数日后,蟒蛇为虎所败,食其首尾,余其身,长四五丈,大如厦柱。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三月,猛黑有夷人上山打猎,到一岩房下,忽来一熊将伊咬死……六月下旬,大雾露地方忽有一虎,将山上黄牛咬杀二只,十月初四日半夜后,有虎入德党寨将杨小张家所蓄之骡擒去一匹,至寨外食之,次日,人过其处,见馀骡腿一只。”①
明代诗歌对兽灾的控诉,明知事出有因,基本上仍是进行“一面理”的单维推因:
山中猛虎食不饱,群集欲餐狐兔少。号风吼日无奈何,不避人烟来渡河。万家城郭河边器,一虎横行入城里。夜餐犬豕昼食人,只图饱腹不顾身……一人被噬万人畏,数月城中无稳睡。繁华市井转凄凉,阴云惨淡空断肠。一薪一米贵如玉,忍见儿啼并女哭。[5](P3)
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古人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把猛兽视同仇敌,恐惧而痛恨,更要思考为何猛兽要离开它们旧有的活动区域而进攻人类的疆土。
二、家畜救护人类及官吏德行影响动物
面临野外猛兽袭击,人与家畜之间的亲密依存关系,得到了实在的验证,而生死存亡的利害关系呈现,强化了人类与驯养动物彼此的凝聚力。
其一,人们往往依靠有一定抵御能力的大型家畜护卫,并集合群体力量向猛兽斗争。这些“爱畜”,最有特色的是牛,牛斗虎故事也特别具有动物伦理特色。说詹氏子牧牸(母牛)正躺在牛背上,邻儿一旁玩耍,有虎从草丛中冲出:
直前搏牸。二儿痴,不识为虎,掷瓦砾,嗾而逐之,虎顾牸不肯去。二儿徙倚观稍前,乃缘登木。牧子念其家贫,惟恃此以耕,不胜愤,径归取斧,将以杀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母视其来也,遽问,而告其故。顾东作方殷,家无男子,乃集里妇数人,譟而从。既至,二儿观酣,嬉笑自若,牸以角拒,虎爪啮无完革矣。牧子视牸且困,挥斧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牸来。时木影漏日,刃环舞翕霍有光,虎益自缩,作势奋迅,欲以攫取,牸少憩力甦,乃前斗。虎舍牧子与之相持,牧子气定更进,虎又舍牸。牸与牧迭抗虎,如此者弥半日……虎遂弃而去,牸牧竟全。[6](P371)
故事特别突出儿童天真无知,虎似对其不急于攻击:“二儿不知畏,不被搏噬。”余愭《书义牛事》也载牧儿方七八岁:“虎至,牛力护之。众农集,趋杀虎。”牛能如此,既可御虎,又能护儿,不能仅以动物来歧视它,事实上已具有懂人情、明事理,至少道义上与人是站在一个阶位上了。这当然不排除载录者的选择与偏好,明清伦理文化氛围,营构出人心目中的理想家畜形象。有时出于自卫,竟还有猛牛斗杀虎奇闻,说陕西汉中的猛虎,猎户、官兵均无奈,“善搏虎某者”也死于虎口,当群牛遇虎皆退缩时:“惟一牛独前,与虎熟视者久之,忽奋力一角,正穿虎喉,虎立毙。报之县官,遂将此虎赏畜牛之家,并以银五十两奖之,一县称快。”[7](P384-385)奖额不可谓不大,关键是表明官府的重视态度,需要在鼓励垦殖山林时轰动性的褒扬效应,试图消减“野外作业”中虎患的阻遏。
其二,面临野兽威胁,多数情况下作为和平居民的人们,仍依靠地方官德行、能力弭灾驱灾。明代陈耀文《天中记》卷三十四搜集传扬此故事类型,如引宋代《九国志》载谢杰为高州刺史,境内多虎,夜入郭中为暴扰民,杰就沐浴谒城隍庙祷告:“愚民何辜而虎暴之?盖刺史无德化。愿虎只食刺史,无伤愚民。”因屏左右独宿殿庭中。三鼓时闻庙东南隅忽有物咆哮如雷,迟明见数虎悉毙。这是典型的“清官廉吏所在地灾害不起”的书写模式,将灾害与地方官员个人的伦理品格结合,倡扬爱民恤民[8]。不过,更多的还是积极动员百姓自救,而官府予以政策性鼓励。清初地方官汤斌(1627-1687)先后在陕、江西、苏、京四地作官,一直将消除虎灾为民除害,成为一项重要政绩:
照得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本道暨各州县刑之颇僻狱之放纷。苛政之害,甚于猛虎,以致恶兽咸召而来,吞噬残黎,攫啮牲畜。各官既不能希踪古循良吏,增修德政,使虎类知感而渡河,自应责彼兽,人驱虎害。乃近见各属有民间擒得虎豹,强徼其皮献之官府,是百姓冒死而得者,止供官府馈送之资,何所利而为乎?为此,是仰州县官吏即传谕有虎地方人等知悉。如有猎户善于搏虎者,听其捕逐擒获。一切皮肉任彼变卖,不得强行索取。更当洗濯其心,捐除苛政,勿蹈乳虎之诮。[9](P415)
消除虎灾,地方官员依靠的是“借虎灭虎”方式,用猎获者有权处理猎物的“物质刺激”,来充分调动当地民众捕虎杀虎的积极性。他及时地洞察到下层官吏不去组织救灾,而是乘机“发虎灾财”,勒索猎户献虎皮的弊端。他深知,如听任继续侵吞猎户的战利品,会降低猎户们冒险捕虎除害的热情。如此规定,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既可减少地方财政开支,还能起到全民救灾的功效。
虎灾盛行,“小兽伏虎”则属“借兽治兽”,蝗灾亦然,被解释为盛世所感,更因地方官德行而有意助人。据说灵寿山区有虎害,程邑侯为文虔祷山祠,忽睹异兽,文身锐角:
古称酋耳能食虎,果见搏虎如搏羊。恣噉血肉须臾尽,委骨林麓皑如霜。自兹虎患为衰止,山氓仍得安农桑。前此春寒土出蝻,入夏生羽成飞蝗。竟有细蜂来蔽野,群飞啮蝗蝗尽僵。出境之蝗渡河虎,大书异绩史册光。中牟传美或无二,侯与先后相颉颃。邑民感此互传述,士传其语作颂章。观风使者采入告,用备药什升明堂。[10](P527)
不过,那些战乱地广人稀之地,生产力落后,敛财之风难遏,百姓依旧笼罩在虎灾盛行的阴影之中。以至于汤斌还要重申此令:
照得虔南兵燹之后,人民凋丧殆尽,荆榛塞路,虎豹昼游,吞噬残黎,攫啮牲畜。本道暨府县各官不能如古循良吏,增修德政,使虎类知感而渡河,自应责令乡民驱除虎害。乃近见各属有民间擒得虎豹,强徼其皮献之官府。是百姓冒死而得者,止供官府馈送之资,何所利而为之乎?合行申饬!为此,仰府县官吏即便大张告示,晓谕乡民人等,如有猎户善于搏虎者,听其捕逐擒获。……仍破格赏赉,以示鼓劝。各官更当洗濯其心,慎重刑狱,毋使人谓苛政之害甚于猛虎也。仍将行过缘由,回报查考,毋违。②
两次三番颁布如此法令,说明地方官吏不顾民众在虎灾肆虐下的死活,而执意搜刮虎皮;对猎虎获利自得之法也是一再拖延颁布,拒不执行。可见,任凭兽灾横行,还要“大发灾难财”的贪官污吏是何等猖狂:
山南白昼猛虎来,柴门竟日常不开。村东少妇血渍草,村西老翁骨成堆。官府明文下猎徒,村舍奔走相号呼。入门不顾索鸡酒,由来苛政猛于菟。亦毋张尔弓,亦毋亡尔镞。明朝群起颂相公,虎畏相公渡河北。[11](P248)
与对付害虫——蝗灾的方式类似,似乎,如同虎这样的猛兽,也有神灵暗中驱使,而当地官吏的德行、或关爱子民的诚心,则会感动神灵驱使灾星转移。在无助无奈之际,这种迷信的幻想实在也是无法之法,情有可原。
其三,在边荒地区,也不排除人们往往是是直接求助于当地的神灵。清初时东北地区地广人稀,生态环境呈现出多虎而人们无力抵御,为免除当地兽灾的最大危害——虎患,多以伐木采参等野外活动为生的人们,就建立虎庙求助神灵保佑。但虎患却并不为之减少。《出关诗》中收有方式济《虎庙行》:

方式济(1677-1717),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康熙五十年(1711)因《南山集》案被株连,举家流放卜魁(齐齐哈尔),作为关内文化中心地区来的汉族文人,荒蛮北地的猛虎成为他最不适应的方面之一。无疑,深在地借虎灾横行的现状,诗人感慨愤懑找到了一个喷发口。
其四,是如同发生灾害要问责地方官员一样,有的还要甚至将治理兽灾无效,来“问责”当地神祗。据说左文襄(左宗棠)驻军甘肃时,见其地多狼,食人畜,遂命部下出队围猎,而终日不获一狼。某军官献计曰:“闻狼之为物,冥冥中有神管辖,故非人力所能驱除。”文襄听罢大怒,命手下抬来当地城隍神,褫夺其冠冕袍笏,责四十军棍,用木枷于营门外。[13](P4789)以祷神、责神来治理当地兽灾,当来源于阴阳两界官员“同治一方”的互动配合观念。如明后期带有写实性的公案小说,就昭示出某些地方官员祈神——陈祖拜城隍语曰:
汝为朝廷守土,我为朝廷守官。人害人惟予除之,物害人惟神除之。人害弗除,则为废官;物害弗除,则为废祀。凡物之为害,莫过于虎豹、蛇蝎、蛟龙、豺狼……[14](P77)
说明在古代的生态环境和冷兵器时代,野兽对于人类安全的巨大威胁,兽灾同样会危及对当地神灵的供奉。
三、野兽精怪食人的人事兆应与灾害预兆
在古代中国,正史的的文化建构作用是巨大而不可低估的。由于史书之中《五行志》将野兽妖异与人世变故联系对应的神秘思维定势,明清人往往还是把无法抵御的精怪,同野兽联系起来。在清代一些叙事作品中,有的还借助于前代民间野兽精怪食人传闻,强调“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陈忱的水浒续书描写老僧真空给闻焕章讲述灾异之事:
有龙挂在军器作坊,兵士取来作脯吃了,大雨七日,京城水高十馀丈。禁中出了黑眚,其形丈馀,毒气喷开,腥血四洒。又有黑汉蹲踞,像犬一般,点灯时候就抢小儿吃。狐狸坐在御榻上。……种种怪异,不可殚述。总之“国之将亡,必有妖孽”。眼见得天下大乱了。这是老僧饶舌,先生须要谨言。[15](P121)
这显然还是基于人兽对立、兽灾预示人世的思维路径。小说这段情节非向壁虚构,而来自明代正德七年(1512)的“黑眚”传闻:“形兼赤黑,大者如犬,小者如猫,若风行有声,夜出伤人,有至死者。初自河间、顺德,渐及京师,人夜持刁斗相警,达旦不敢寝,逾月始息。”此前的成化十二年(1476)七月:“京师西城,有物夜出伤人,其色黑,踪迹之不可得。上乃于……”[16](P270)而宋代佚名《大宋宣和遗事》载宣和三年五月金使来,六月黄河决口,恩州有黑眚出:“洛阳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儿食之,至二秋乃息。二月,童贯进太师,谭稹加节度。”似乎这一具有野兽般外形的精怪,是一种征兆,预示着人间要有相应的别的灾难发生。国外学者更多地注意到民众恐慌心理上,实当为灾害心理的濡化所致。
较多载录野兽侵犯居民的是地方志。根据不同地区的野兽物种的分布,可以看出,如果不是生态环境恶化,野兽固有的生活领域遭到破坏,是不会有如此之频繁的野兽与人争夺资源事件的:
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秋九月,杭州属县诸山聚虎成群,白日入民家伤人,道路无独行者,死者不可胜记,且不可猎,余杭尤甚。”
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秋,(广东东来)狼虎成群,白昼噬人,成郭之外,行人几断。”
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八月:“常德熊入城,伤六人。”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皖南)虎成群食人,自后十年中计伤千余人。猎人张网焚山捕之,不获。”(洪亮吉:嘉庆《泾县志》卷二七。)
清高宗乾隆十三年(1748)冬,山东胶州:“狼食人,白昼入城。”[17](P485-490,493)
野兽出现了与往日积习异常的行为,对人类造成了严重威胁。以当时毫无防备的和平居民看来,真是需要认真对待,因此,记载或咏叹如何捕捉、击毙、抵御猛兽,成为富含人本意味的民俗文学题材,如诗咏:
市儿青裙头布帽,争言缚虎沙潭侧。地平实异溪谷险,公然攫人到昏黑。此物岂因气数至,居人恒愁爪牙逼。劲弧疾弩谁命中,纷纷贪天谓己力……[18]
王培荀也写蜀地建昌多虎。雅安令募人以毒驽射死五虎,艾生、习生也打虎,感叹“我乡百年无此物”,杨世焘作《打虎行》:
踞牙钩爪斑斓虎,扑地一吼人皆惊。聚众追随远相逐,虎行缓缓故不速。直上前冈始负嵎,吞身缩爪睅其目。到此相看不敢前,虚呼空喝祇徒然。勇哉艾生无客气,习生亦豪为之贰……[19](P462)
全不思虎的领地受侵,生态恶化中人类的责任。有的则将别的自然灾害同兽灾通盘考虑,如地震,有些动物就预感到了,它们袭击人类其实就是地震前兆之一。康熙《上元县志》卷十三称明成化十七年(1481):“江苏二月,地震,猛虎进城杀人。”光绪《渭南县志》卷十一也载清光绪五年(1879)陕西“多鼠食牛,噬婴儿,啮瓮破。五月十三日寅刻,地震。”说明在对兽灾恐惧的观察之中,有时还能关注了其与其他灾害的联系。
四、兽灾作为生态环境变化的显象
首先,对于猛兽带来的威胁,明清时代人们进行了带有神幻意味的思考。如所谓义虎仁虎情虎故事,仁狼情熊的传说甚夥,就是一个重要方面。像义虎能惩恶救善:荆溪二人发小,长大一贫一富。贫子略知书,妻美艳。富子就设谋,邀其夫妇进山去应聘管家,途中富子让贫子妻守舟,与贫子先行,引行险恶溪林中斫之“陨绝”,认为已死,哭下山告诉艳者其夫君被虎啮,与妇同往检觅,宛转引行险恶处时,忽有虎出将富子咬死。妇返舟与夫相逢,悲喜交加。作者感慨:
视贼始谋时,何义哉!已乃以巧败,受不义之诛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妇不遇虎,得理于人。而报贼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尽虎,以义表焉可也。[20]
如此具有是非善恶观念的猛虎,岂非现实社会中人将自己的伦理观念投射所致?由此看来,明清两代小说中带有仙幻性质的诸多“虎妻”(如《虎荟》《萤窗异草》)、“熊妻”(如《埋忧集》《道听途说》)等故事,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人们对于兽灾受虐的心理补偿。事实上,有关人兽和谐的实录性文本虽然不多,但上述希望自然界猛兽也能具有人的情怀、理想,干预凡俗的善恶恩仇,也当被视为恶人必得“遭克”期许的艺术化体现。[21]
其次,兽灾出现,有时还被认为是灾害的预兆。作为民俗记忆,1932年太原瘟疫前就传闻,近日狼入村中,后村西逐出一狼大如驴,无毛:“人多势众,狼畏,登山而去。已故里人多以为不祥,虑疾人之不利,恐多丧亡耳。”存续前清观念的这位作者,还并不止于客观情状的描述,进一步伦理推因:“瘟疫之行,人之不善所致也。人情风俗之不善有以致之也。人须为善,以驱逐瘟气耳。”[22]实际上狼灾乃为旱荒之果,又被作为疫灾先兆。
最后,地方官员应对兽灾的侵袭,还体现在对于勇斗猛兽、协力抗暴的百姓,予以及时表彰资助,减免徭役等方面。如李符清《海门文钞》载,乾隆己丑(1769)广西合浦人虎搏斗,吴氏兄弟仲、叔、季三人持农具斗虎自卫,虎伤而曳尾遁,众抬季归:“后数日,邑侯汪公龙冈过其地,召视创,且询人虎相搏状,感其笃兄弟义,给资疗之,复免其徭役焉。”[23](P167)在有些在大力开发垦殖的地区,人兽冲突就更加激烈。[24]的确启发人们需要“综合治理”的思考。
野兽表现狂躁异常,往往并非猛兽的一些小型动物,也令人难于应付。这也在兽灾与其他灾害联系的民俗言说中屡见。清代后期的同治、光绪年间,社会屡遭兵燹,自然灾难频发,尤以雨雹灾和旱灾为主要形式。不过兵燹后自然界的生态失衡,又会令人感到恐惧困惑。据说,同治七年(1868)西北某一地区出现的怪异现象:“鼠皆硕大如猫,白昼游散不畏人,且反食猫。粟粮已久无存,不知何以如斯之大,且多狼,成群二三十不等,向堡寨有人处肆行,经多人抢矛追逐,殊不奔避,辄向大众中,择人而噬。……其肥腯迥异平时。”[25]又如蜘蛛、蝙蝠等母题,这些“灾害”激发、丰富了民国武侠小说中人兽关系描写的审美想象。③
其实,在冷兵器为主的时代,人们与猛兽的抗争,往往也是代价沉重的。满族官员记载了冷兵器对付猛虎的训练方法:
定制,选各营中将校精锐者,演习虎枪之伎,凡巡狩日相导引。上大猎时,其部长率伎勇者十人,入深林密箐中觅虎踪迹。凡猛兽出,其部长排枪以伺,虎跃至,猛健先以枪刺其胸仆之,谓之递头枪,然后群枪林至。其头枪者赏赉优渥,故人思效命焉。纯皇帝定制,凡杀虎时为虎毙及被创者,照军营殉难受伤例赐恤焉。[26](P394)
蒲松龄对无辜受害者对猛兽的反暴复仇,有着极高的热情和激赏态度。他评杀狼报父仇的乡民于江:“农家者流,乃有此英物耶?义烈发于血诚,非直勇也,智亦异焉。”[27](P550)对于大蟒口中救兄的胡家弟,则赞扬:“噫!农人中,乃有悌弟如此者哉!或言:蟒不为害,乃德义所感。信然。”[27](P72)人们与猛兽斗争,不仅需要勇猛,也离不开智慧,像《聊斋志异》写对付狡黠狼的篇章即然。而清初徐昆也写山右多狼,性最狠而狡黠善伺人,某荒村狼夜推碾发声,引妇出门拖走。说某役乘马夜行路过辛庄:
见路旁有若人趺坐者,呵之,乃两狼背负,见人奔逐,马惊逸,尽力而驰,两狼固不舍也。黎明,望见郡城门未启,乃就路旁空灶跃而上,左手牵马为护,右手以鞭格之,急呼店主人醒,启户,狼始去。未几,闾邻左有豕疾声而渐远,两人裸逐不能及。盖狼度不能得人,负豕而去也。后余至山左亦多狼,人或夜行,必挈伴持械,老弱或为所噬,宁海无猎者,遣兵役捕之,凶焰少熄,亦不能尽绝。[28](P120)
而对杀熊报父仇的童元发,俞樾则突出了该青年的正义行为有山神托梦报讯,揄扬孝子缘此善行惠及乡里:“粤寇之难,近村多被焚掠,而童孝子一村独无恙。”[29](P123)明清史乘《孝义传》《列女传》载这类事几乎全站在人类中心的立场上,多所采集和彰显赞扬,而地方官员也寄予深切的同情和尊重。如斗虎救亲的漳浦人蓝忠,事后里中父老请旌表:“忠泣辞甚力,佥曰:‘无伤孝子心也。’乃已。”[30](P2488)并不完全听凭常规和借助舆论为自己的政绩造声势,归根结底还决定于孝子自身的愿望和意志,说明在抗击受灾过程中,地方官员相关举措还是相当人性化的。一定程度上这也称得上“民本”思想、乡间舆情对官员决策的制约。
兽灾母题的生态美学意义在于,人的生存状态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在特定动物的活动(正常的与异常的)中表现出来,人们在与动物的生存对抗中互有输赢,但具有启示性:人类不能仅仅从自身为世界主人的立场出发,而不去思考动物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尤其是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否同人类自身行为有关。国外学者即指出,应该把野生动物活动看成是人类入侵和破坏自然环境的晴雨表[31]。兽灾的出现,以往常常把野兽群发说成是野兽对人类的侵袭,对于和平居民的威胁骚扰,其实,这是片面和不公平的。如果从当今生态文化与生态伦理角度来全面审视,可以了解,这不能单单来指责野兽,其实,正是人类对于彼时彼地生态幻境开发的过程中,打破原有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的野兽生存状态恶化;或导致原本不应有的灾害发生时,那些野兽被迫走出固有的生活圈,进入到了人类聚居地寻求食物所致。在华夏灾害、御灾与生态学融合的文学书写之中,这可以看作是人与动物关系的一个令人警醒的方面。
注释
① 《云南·镇康县志初稿》卷二十四《轶事》。
② 范志亭等辑校:《汤斌集(上册)》第一编《汤子遗书》卷八《戢虎暴以除民害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虎渡河”事,典出《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载刘昆任江陵令,“虎皆负子渡河”。《宋书》卷四十一本传载宋均任九江太守,“虎相与东游度江”。
③ 可参阅王立《蝙蝠谱系:还珠楼主小说与明清恶物灾难母题》,载于《华夏文化论坛》(总第二十八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刘卫英《还珠楼主蜘蛛母题的道德化书写》,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