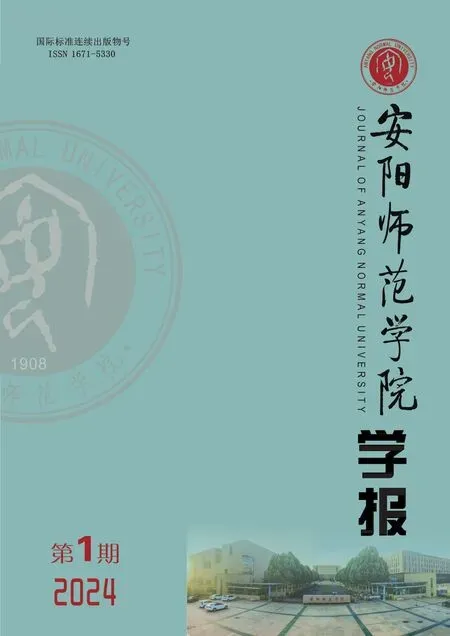符号修辞中的共情伦理
——以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像山一样思考》为例
贾丹丹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自然文学作为一种绿色写作,主要描写的是人类与自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里所说的“绿色”,在早期作品中表现为对“自然”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物质性描写,而在后期作品中则主要表现为对“生态”的符号性描写。恰如生态符号学家卡莱维·库尔(Kalevi Kull)指出的,“生物修辞学是把生命体系统作为修辞手段的一种评论、一种研究。这就意味着,生命体系统可以类比解释为话语,而不是语言。如果生命体是表达或意向的实体,那么修辞也是。因为生命体系统有需要,他们就不可能只是表达,而是相应地影响着有机体之间的整个交流。”[1](P697)自然文本作为人类交流的符号形式之一,它注重突出“人”与“自然”这二者作为生态符号所产生的认识论价值,以及由此产生了共情伦理。
美国有名的生态批评家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H. Slovic)曾从修辞角度,论证美国自然文学放置于亚里士多德的“劝导”修辞语境之中的状况,认为自然写作的认识论维度与人类的政治维度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张力:前者旨在说明“宇宙本质和人类(或者人类自身)与自然世界关系的理解;后者指的是“努力劝导听众去接受对自然环境的一套新态度,潜在地把这些启蒙态度转化为相对而言非破坏性的行为。”[2](P115)彭佳也提出“自然修辞”的说法,认为它主要指“在对自然进行表现或再现的符号或文本中,运用修辞方法对自然界中的对象实现的转义或逻辑呈现。”[3](P7)“修辞”对于自然文学来说,不是因为“非虚构”就受到了限制,而是由于“非虚构”让更多修辞方式被内置于文本形式中了。
因此,本文以生态符号学为理论基础,分析奥尔多·利奥波德《像山一样思考》中狼的“眼睛”和“叫声”作为生态符号所蕴含的生态认知问题,以及动物模塑的符号过程中隐在的生态伦理价值。
一、“眼睛”中的认识差
《像山一样思考》这篇散文源自利奥波德一次跟朋友出去打猎的经历,他们当时开枪打伤了一只母狼,而就在这只母狼快要死去的时候,利奥波德从狼的眼睛里悟到了一种意义,从此,他决定再也不打猎了。在这篇散文中,利奥波德这样描写到:
我们及时赶到老狼身边,看到那凶猛的绿色火焰在她眼里消失,我然后意识到,自此后才知道,对于我来说有一些新的东西,在那双眼睛里有一些只有她和那座山才知道的东西。我那时还年轻,容易一触即发。我想,因为更少的狼意味着更多的鹿,没有狼便是猎人的天堂。但是,当看到绿色火焰熄灭后,我感到狼和山都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4](P130)
在这一段引文中,“眼睛”变成了一种符号,它对作者产生的一种模塑作用主要来自一种“归约式的类比”,即“人”的眼睛可以从“狼”的眼睛里接受到一定量的信息,相当于此刻的“眼睛”作为一个再现物,对两个不同种属的生命体之间的信息传递做了一次生物翻译,即狼的“动物语言”顺利过度为“人类的语言”,原本只是用以识别的感觉器官现在变成了可以用来相互模塑的介体。那么,这里是否存在了一个“认识差”的问题呢?
根据爱沙尼亚生物符号学家乌克斯库尔的观点,每一个生命体都被赋予了一种感知器官,可以感知信息并构建自己的“环境界”(umwelt),但是,自然界中的所有客体即使拥有所有可能性的感知特征,也不可能成为独立于主体之外拥有存在的事物,它只能作为认知主体的产品。“只有当它们被所有感知所覆盖,才能变成我们面前的‘物’,而这些感知也是所有感觉能给予它们的。”[5](P107)“此生命体”的感知器官对于“彼生命体”的感知器官来说是不一样的,因此,“彼”与“此”之间的相互模塑也必然首先要克服它们之间的认识差,才能构成一个共性环境界。
从共情论视角看,共情的词根是“情”,指的是我们作为“我”在与他者的交往过程中,以一种共享“情”的方式达到一种共识,恰如荷兰行为生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认为的,它是“一种直接的、非推断性的了解他者心灵的方式。”[6](P62)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作为西方情感主义伦理学的代表人物也曾指出,在人的认知中有一种“自然的仁慈”,它可以通过人的“同情”来实现。美国当代有名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家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后来肯定了休谟的同情论其实就是较早的共情思想,认为由于这种同情的作用,人会对自己的亲人或者身边的人阐释一种偏爱。但是,休谟所采用的词是“同情”,从最原初的意义看,这个词指的是,我们对某个人的关怀,主要表现为依赖于个体身上的共情培养。
构建共性环境界需要一个共情伦理的生成,那就需要克服其中不同生命体之间的认识差。例如,在《像山一样思考》这篇散文中,作者其实在一开始就设定了生命体环境界构建中的认识差问题,而且这个“认识差”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文章中的“我们”是人类的代表,我们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决定这个自然界的存在模式;在“狼”与“鹿”之间,我们倾向于认为,如果减少了“狼”的存在数量,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鹿”。因此,我们对“人-狼-鹿-草-山”这样的一个环境界进行了粗暴介入,控制了自然的存在模式,“狼”作为其中的一环被强硬去掉了,于是“人-鹿-草-山”这个非常规的认识模式就先天性地失衡了。在散文的最后,作者自己也承认,“太多的安全似乎长远看来产生的只有危险。”[4](P133)
从认识逻辑看,在关于狼的眼睛的描写中,作者所采用的词汇,如“狼”“绿色火焰”,是我们既定的认知图示所建构出来的意义,然而对于“山”来说,“灭鹿者”“生态”才是真正的认知结果。两种不同的阐释都源自不同的认识逻辑和符号体系的构建,我们可以从符号形态的对比中进一步审视其中的行为动机及其伦理预设(见表1)。

表1 狼的符号形态认知对比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狼”是一个生态符号,它服务于整个生物域。而“人”无法成为一个生态符号,就在于人类仍然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征服者,而不是生物界的一员。这里,作者把“鹿”“牧场主”“政治家”“我们”共同列为一个认识序列,同视为这个自然界的生态符号之一,都有责任重新反思自己的“安全”意识,我们也应该去荒野之中重新寻找启示。由此可以发现,母狼的“眼睛”起到了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神的力量,作者在审视狼的“眼睛”的过程中,一种神秘的布道行为也同时完成了。这个过程的完成需要借助于作者的生物修辞,即“狼”所在的世界是没有被文化编码过的,是单纯的生物性生命过程;人的文化构建过程同样需要跨越不同的生物界限,同样依赖于一种感官认识意义上的生物过程来完成。因此,人就与其他动物在生物性层面处于同一个位置,“我”与“狼”在“眼睛”的对视过程中实现了符号的信息交流,而且这个过程超越了我们原有的认识方式,即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问题。
在这个生物域内“狼-鹿-草-山”是一个食物链,这其中的自然语言作为符号体系即荒野中的动物话语,存在于“狼与山”之间,同样也存在于狼与其他的动物之间。我们惟有认识到其中的认识差问题,我们才能理解“狼”作为符号的意义。对于“狼”的自然本性存在而言,作家对自然的描写仍然是先验的当下,而不是即刻性当下。作家借助自然的非连续性,尽情细致刻画自然的本然存在,同时又借助其广延性,让它作为自然符号存在与整个自然界乃至人的存在联系起来,扩大了它的存在意义。
二、“叫声”中的功能圈
“功能圈”(the functional circle)是乌克斯库尔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用来描述人与自然关系的,它也可以看作是生态符号学中关于人与自然之间意义模式的最为原初性的定义。根据乌克斯库尔的观点,环境界的构建至少需要两个不同的生命体相互产生关联,它们之间的关联是一种“对位性”(contrapuntal)的关系,所有生命体都起源于这种对位关系,生命体与自己所处的环境之间是一种有意义的关联,它存在于生命体自身的对立结构之中,也被保存于它的主体世界之中。当所有生命体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整个自然界。
《像山一样思考》一开始就借用狼的“叫声”来告知读者生态功能圈的存在,作者这样描写到:“对鹿来说,它是所有肉体形成方式的提醒;对松林来说,它是雪地上的半夜混战和流血的预言;对于郊狼来说,是就要来临的拾遗的允诺;对牧场主来说,是银行里赤字的威胁;对猎人来说,是狼牙抵制弹丸的挑战。”[4](P129)在散文的最后,作者再次用“狼”的叫声来唤起读者的反思。那么,我们应该从这个叫声中获得什么认知呢?
从生态符号域的角度看,作者列出了“狼-鹿”“狼-松林”“狼-牧场主”“狼-猎人”等几组关系项。作者用一系列的排比,列出了这个生物域内的生态关系,这个生态关系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必然引起生态危机,恰如作者所写的,“鹿”太多会因为食物不够而死去,山坡上的“草”会因为鹿过多变得光秃秃的,而山也会因为“草”减少了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等等。
这篇散文中,狼的“叫声”作为一种客体是不可叙述的,只能描写;即使是描写,也必然是前语言符号,恰如贝特森说的,任何事物的存在只能是以“物”的形式,如名字、属性、关系进入语境[7](P60),因此,这里狼的“叫声”作为动物符号,在文中的模塑所产生的是现象学在场,即一种“在场、现在”的经历,它唤起的感觉类似于原初性的自然经历。只有“高山”可以听懂“狼”的叫声,这个意象的描写实质上正是把这个“叫声”作为一种模塑作用,我们人类也应该像“山”那样去客观地听,去感知这里存在的一种生态关系。这也是作者在《沙乡年鉴》中关于土地伦理的整体认识论在“狼”身上的体现。因此,正如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land ethics)所认为的,我们人类应该扩大人类的共同体的边界即“大地”,把土壤、水、植物、动物包括进来[4](P204)。
很显然,利奥波德的伦理思想强调了“共情”的重要性,各种生命体之间应该构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西方情感主义伦理学代表人物马丁·霍夫曼的《共情与道德发展》(Empathy and Moral Development)一书中有类似表述。霍夫曼认为“共情道德应该在关怀和最具公正原则的引导下,在文化中提升亲社会行为,进而减少攻击性(aggression)。”[8](P22)根据霍夫曼的观点,道德的源头可从共情中去探索,共情本身就是一种“亲社会动机”,具有引发助人行为、抑制攻击性行为等亲社会功能。正义和关怀的道德原则也是通过共情这种情感起作用的。
同样,在我国现代儒学代表人物王阳明的“万物一体”的伦理思想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观点。“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9](P968)可以看出,王阳明这里突出的“情”也属于共情,是一种“环境美德伦理”,如黄勇认为的,“他的伦理学所关注的对象超出人类而涵盖天地万物。”[10](P162)
简言之,《象山一样思考》这篇散文所关注的问题,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环境问题或者生态问题,而更多的是人类构建环境界中的伦理问题,即我们应该如何来改变认知主体的思维模式,重新认识当前的人与自然之间功能圈的存在形态。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解决当前的自然问题。这篇生态散文尽管篇幅短小,但是却通过把“狼”设定为一种特定的生态符号,以其“叫声”来揭示它在整个生物域中的位置,进而把这些生态关系一一梳理出来,从反相位揭示了当前生态危机中的功能圈问题。
三、动物模塑的符号过程
自然文学中对动物的描写包含了物质性的过程和意义关系,它的被经验过程是由内到外,但是,这个诗学空间不是外在的、精神性的,而是内在的、具身性的,因而总是一种充满意义的变体的物质。《像山一样思考》通过把自然秩序还原为人类的伦理和审美,同时也把人类的秩序还原为自然,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模塑中揭示了生态位构建中的符号过程。
(一)从自然描写到伦理模塑
生物学意义上的模塑发生于动植物界,主要表现为各种生命体对自然环境的积极适应过程;对于人类来说,生命体之间的相互模塑主要依赖于我们的生理学能力、身体感知和多感官知觉。人们利用他们的环境界结构、感知感觉和神经系统,以及一些相对应的行为能力,来模塑周围的世界。
这篇散文中的自然现象不是“物”,而是“符号”,因为利奥波德笔下的“狼”“鹿”“山”,并不在散文中,不在图画中,而是在被看和被转换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对于作家来说,他也不是为了“看”或者“画”,而是为了变成这座山,具备它的精神特质,感受这种生态位的存在意义,进而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与大地的关系,“它让我们正确地认识我们的生活,把它作为一个生活在生物圈的具身问题,把物质性和意义融合在同一个共性基础系统内。”[11](P119)德国生物诗学方面有名的安德里斯·韦伯(Andreas Weber)博士把这种写作方法称之为“诗学性的客观性”(poetic objectivity)[11](P118),也就是说,自然文学作家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科学实践来讲述大自然中如山川河流的内在心理活动,但是却让整个写作过程变成了第二人称的关联。因为作家追求一种全方位的客观性,但是,自然界中许多现象可以感知,却无法命名。看到一座高山进而赋诗一首或者创作一篇散文,但这不是“山”,而是通过共享所产生的一种山的变体。
(二)符号伦理的生成
从文学创作论来看,这篇散文中的“山”“狼”作为自然符号是重要的阐释向度:第一,当作为符号指向生态时,必然就带有“人”的因素,那么关于符号的描写就是一种介入性的描写,这时候的符号“是其所非”,那它显然就是象征;第二,当只作为符号时,不涉及我们认为的生态批评时,符号“是其所是”,那它指向的是其自身则必然是符号。动物符号自身所呈现出的二维向度,也是它可以被语境化的重要因子。恰如西比奥克所说,模型既可以是象似性的,“依靠有效的相似”,也可以是象征性的,“依靠一种推加的、约定俗成的、习惯的临近性。”[12](P143)在这篇散文中,作者为读者展示了一种现象学的在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象似性描写唤起了我们对自然的最原初的经历。
从认识逻辑看,自然文学中的文本语言、文本主题和文本所描写的事物,三者并不处于同一个层次,这是基于我们对文本的结构化认识,把三者凝聚为一个单元体,这就为文本内的符号关系阐释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即符号原本并不描述实在,只是以其展示世界的方式来质问世界的本质,但认识逻辑的混乱却导致了阐释层次的混乱。或者说,作者把不同的逻辑层次融合在一起,惟有以模塑来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关系加以审视,才能更好地发现这里的认识逻辑。
换言之,这篇散文对于作者来说,在符号意义上是为了客观再现理想生态位的意义,但是在写作模式上却选择了把情感和意义视为科学性的观察的重要入口,因为规约性的、科学性的方法来研究或者理解自然,根本无法表述清楚自然的本质,更无法洞察人与自然这二者之间的生态关系走向。因此这篇散文所展示出来的把符号伦理作为一种表意实践方式,构成了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实在论,它的优点在于,实在论中所有构成概念的要素都是可以发现的,是客观的,而认识论中的构成要素是主观的。这是一种原始的认识论,是充满生态想象的艺术认识论。
四、结语
对于几乎所有的自然文学研究来说,如何把握自然文本中的自然描写,突破现有的生态批评窘境,避免一种直观式的阅读反应,都需要从理论上反思生态批评的方法论问题。毕竟如果我们只是就文本内的单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故事去谈,读者可能对此毫无兴趣,而且文本内的自然描写也远没有与笛卡尔的身体-心灵二分法分离开来,我们都只把自然文学中的“自然”看作是纯粹的物质的,而不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符号过程中被模塑出来的。因此,本文通过分析文本中的生物修辞,尝试为自然文本中的客观描写寻找一个可信的、可行的意义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