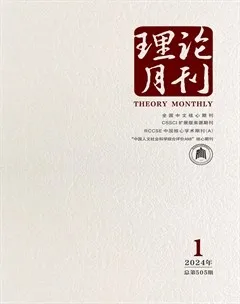中国东部农村的空间功能与制度安排

[摘 要] 东部农村处于城市经济辐射范围之内,实际上内在于城市体系,发挥着城市生产生活空间配套、建设用地指标储备、绿地空间涵养和市民休闲旅游四重功能,是城市运转不可缺少的部分。服务城市发展并从中分享收益是地方政府对东部农村的总体制度安排。东部农村农民依托地方市场在家门口灵活就业,大量农田流转给龙头公司或外地农民规模经营,农业生产呈现出依附政府补贴、服务城市中产的特征。为缓解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紧张,政府常常以环境治理、违建治理为工具推动农村分散的工业作坊向园区集聚,将腾退的建设用地指标用于重大项目,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空间。东部农村与中西部普通农村的市场区位及空间功能差异,决定了治理资源拥有量和面对问题的情形不同,这为中国政策制定、地方政策创新扩散提供了分类基础。
[关键词] 东部农村;空间差异;工业集聚;风貌管控;城乡一体化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1.013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4)01-0123-08
既往学术研究和政策设计通常将农村视为有着相同需求的村庄,诞生于发达地区农村的经验经常被推广至全国其他地区。从经济形态看,中国起码有两种类型的村庄,一类是以上海、广州东部农村为代表的东部农村,一类是以中西部农业生产为主的普通农村。东部农村的突出特征是在城市或都市圈经济辐射范围内、在未来30年有望实现城市化。为叙述方便,本文以东部超大型城市东部农村为表述对象。东部农村和普通农村作为中国农村的两个基本类型,其不同的区位空间功能决定了不同的政策需求。
一、东部农村的空间功能
上海、广州、北京等超大型城市的农村,尽管在空间形态上仍保有农村样态,但其实际功能却已不同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普通农村[1]。东部农村是城市体系内在的一部分,发挥着城市生产生活空间配套、建设用地指标储备、绿地空间涵养和市民休闲旅游四重功能。
(一)城市生产生活空间配套功能
中心城区土地空间稀缺导致城市功能向周边区域外溢。随着中心城区向外拓展,城郊农村从农业生产空间向工业生产空间、再向工商服务业空间演变,反映出中心城区对郊区农村空间功能的支配角色[2]。
郊区农村是城市产业配套和各类所需物资周转的重要区域。随着市中心土地租金上涨,大量服务于城市产业和居民生活的行业在城乡接合部农村集聚。从中心城区转移出来的小工业、服务业及仓储物流运输业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这带来东部农村突出的人口倒挂问题,即外来人口远远超过本地人口。上海农村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比例通常在5∶1以上,有的地方高达10∶1。当地农民或者二房东为了獲取更多租金,将房屋隔成10平方米左右的隔间来满足只要一席之地过夜的打工者,农村租赁住房产权分散化诱致外来人口治理困境[3]。
职住分离一直是超大型城市难以化解的难题。城郊农村作为住房租金或住房价格洼地,成为新市民群体或无房群体的青睐之所。城郊出现了中产阶层小区与农民还建房小区交错、间杂农民工居住的违建棚屋的建筑景观,这一马赛克式的阶层空间分布,展现了互不相容的多元利益诉求和基层治理困境[4]。目前,不少大城市为了缩短市民通勤时间,扩大城市经济辐射范围,开始投入大量资金修建城际铁路、跨河/江桥梁和地铁,大大增强了郊区农村与中心城区的互动频率,推进了产城深度融合。然而,职工在工作距离近之外还有追求良好教育资源的愿望,这类职住分离现象只能通过教育资源均衡分布来解决。
城郊农村提供的居住生活、中低端产业配套空间,成为城市各行各业所需的人力、物资和物流服务资源的蓄水池。一定意义上,离开城郊农村空间,城市的工商业和生产生活系统是无法维持的。
(二)建设用地指标储备功能
当前中国城市扩张的主要形式是将城郊农村变为城市。在中央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指标和城市开发强度的政策约束下,城市扩张不单是有无土地空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城市建设用地指标。2014年,上海城乡建设用地占比已明显高于伦敦、巴黎和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公共绿地规模占比仅为发达国家城市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建设用地的GDP产出仅为巴黎的三分之一、东京的九分之一。上海市政府在2014年明确提出,市规划建设用地的终极规模为3226平方公里,这意味着2020年以后,上海市将实现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 零增长。事实上,上海市希望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建设用地总规模的“负增长”[5]。为此,上海市在建设用地方面提出“总量锁定、增量递减、存量优化、流量增效、质量提高”的“五量调控”基本策略。
从2014年的国土规划方案看,上海在2014—2020年的7年里只有156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增量空间,但在实际运行层面,上海城市建设用地的年均净增量在50平方公里左右。上海市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策略有二:一是更新城市既有工商业和住宅用地;二是压缩农村建设用地空间。从农村获取建设用地指标的方式主要有征地拆迁、集中居住、违建拆除和建设用地减量化等政策。上海市政府在2014年制定国土空间规划之后,迅速启动“五违四必”工作,以违建治理为抓手,大力推进各街镇建设用地减量化。农村地区的违规工业用地、低效零散的工业用地以及农村集体和农民违建的仓库、出租房皆在被整治之列。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主要被用于城市商业住宅项目和像特斯拉新能源汽车这样的国家级重点项目。浦东新区某村在2015年初到2017年底三年间拆除违建面积40万平方米,其中村集体违建厂房面积占80%,村民私人违建面积占比20%。
(三)生态绿地空间涵养功能
生态绿地空间占比是衡量一个城市宜居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绝大多城市政府在国土空间规划中都会优先保障城市生态绿化空间,除了在市区建设众多口袋公园外,还要在郊区构建生态保护区。上海的长兴岛、崇明岛以及奉贤、南汇、青浦等郊区承担着全市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任务,农村大量的山水林草空间被纳入生态保护区范围。
生态宜居的理念更是被植入超大型城市的新城和开发区建设中。广州市的中新知识城将50%的国土面积划为生态绿化区,预计到2035年,该区人均公园和开敞空间面积大于18平方米,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不低于85%,森林覆盖率大于42.6%。
上海市五个新城的规划建设也致力于构建显著优于中心城区的生态格局。五个新城的规划建设方案明确提出,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和南汇五个郊区要立足各自的水绿山林资源,借鉴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的建设经验,顺沿各级河湖网络完善环廊森林体系,发挥水绿生态空间的叠加效应,创造宜居、宜业、宜乐、宜游环境。五个新城的生态格局及郊野公园项目如表1所示[6](p54-55)。
上海五个新城是上海农村农业所在的主要片区。五个新城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纾解中心城区功能,将优势产能和优秀人才留在上海。从新城空间布局看,除了规划建设新兴产业园区和商业住宅外,新城尤其强调其生态宜居的空间特性,传统的农村空间在未来将就地转变成郊野公园、生态走廊、观光农业等生态空间。
(四)市民休闲旅游消费区
相较中心城区密集的建筑和人口样态,低密度的农村空间使人感到身心愉悦。在市民厌倦大城市的快节奏生活时,农村的自然风光、文化风俗节事、特色餐饮、农耕畜牧等体验项目,成为城市中产阶层暂时逃离城市的避风港。发展满足市民需求的文旅服务,成为城郊农村的一项主要工作。
与西方社会类似,对自然生态和真实农村生活的消费需求,是资本进入农村旅游领域并推动大城市周边农村景观转型的驱动因素。上海崇明岛依托上海庞大的消费市场,充分发挥其海滨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独栋别墅式的农家乐,其高质量的农旅产品曾经红火一时。如今,该地将地方农产品、手工艺品放入农村购物中心,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他们对开放绿地、周末度假和农村休闲的渴望,推动了农村民宿经济和配套服务的商品化。2022年7月,笔者在广州黄埔区调研发现,某度假村一个房屋的消费标准是一万元/天,而且档期已经排到一个月之后。疫情期间,在跨省旅游和出国旅游受到影响的情形下,城市周边农村旅游获得更多机会。尽管有的民宿、农家乐在疫情期间遭遇重创,但市民就近旅游消费的结构性需求并未变化,面向城市人群的特色农产品和特色服务仍有较大市场。2023年2月,笔者到上海嘉定区毛桥村调查发现,当地的民宿旅游、餐饮、采摘项目在节假日供不应求,顾客主要是城区的中产阶层家庭。
在信息化时代,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研发部门和新业态不再依赖市中心的区位优势,将研发基地和办公场所迁移至农村地区。不少城郊鄉镇也积极发展公共交通,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打造人才公寓,吸引创业青年和白领青年到农村居住,为城郊农村发展带来活力。
综上,东部农村已然内置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因此,它们与普通农村在农民农业、产业形态及风貌管控上具有显著差异。
二、东部农村的农民与农业
20世纪末,我国中西部农村出现的“三农”问题在超大型城市郊区农村几乎不存在,这主要得益于此类地区农村较早开启工业化,农民从非农就业中获得较高收入,地方政府基于地方工业发展获得税收,农业农村较早进入现代化进程。
(一)农民就地城市化
多数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乡镇企业,到2000年前后基本上销声匿迹。然而,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农村凭借区位优势,将商品贸易从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使得乡镇工业得以延续。珠三角以“三来一补”外向型经济为依托,快速推动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长三角地区的浙江则以民营经济为主,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中小型工业企业集聚农村,实现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而苏州、上海则从集体经济转向以地方政府主导的大型工业园区建设,农民转变为工厂管理人员或小商品经营者。
长三角、珠三角城市超强的经济辐射能力给当地农民带来丰富的就业机会。广州、上海、苏州农村的农民几乎不从事农业生产,绝大多数年轻人凭借学历进入政府、企业部门工作,学历较低的年轻农民则从事小商品贸易、车间管理、网约车、中介服务、咨询服务、农家乐服务等,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可以做保安、保洁、楼栋管理员或街镇聘用的环保志愿者。以上工作的辛苦程度较低,对纪律和时间的要求较低,自由度较高,工资水准中等。当然,务工收入只是当地村民收入的一部分,相当多村民还有房租收入、失地保险、退休金和集体经济分红收入。
郊区农村的绝大多数农民较早在中心城区购买了商品房,他们将暂时不住的农房或商品房出租,获得财产性收益。按照2022年的市场行情,上海市杨浦区的房屋租金水平为每平方米每月100元到150元,浦东新区农村的租金水平为每平方米每月50—90元。浦东新区的村民将一套150平方米的房屋出租,每月最低可得6000元租金。而在集体经济收入动辄上千万元的村庄,农民的社保、医保、教育支出基本上由集体经济支付,农民家庭每年还可以从中分得福利品和分红,例如张家港市永联村、佛山市子南村等。东部农村农民依托市场优势,将先天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在家门口实现充分就业,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在全国人才竞争的大城市中从容生活。
(二)补贴型农业生产模式
与中西部农民惜地如金的土地观念不同,东部大城市郊区农民基本上不种地,甚至在某些地方还出现连片抛荒现象。原因在于农民种地不挣钱,年景不好还可能赔钱。一个60—70岁的农民到市区打工,一天能挣200元左右,而一亩地的纯收入每年只有1000元左右。
既然绝大多数城郊农民不再从事农业,为何超大型城市政府仍然重视农业农村工作呢?这源于地方政府所担负的“米袋子”“菜篮子”以及基本农田保护的政治任务。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政府每年都要向农村投入大量资源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对农业生产全过程进行补贴。以浦东新区为例,农户获得租金为2150元/亩/年,其中1000元为政府补贴①,1150元为租户支付的最低租金。耕者一亩地可获得1300斤稻谷,2022年的稻谷市场价格为1.3元/斤,即耕者每亩稻谷可获得1690元的收入。扣除租金之后,农户只获得540元,这些收益无法覆盖人力、种子、农药、肥料、用水及机械收种的开支。事实上,上海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政府财政补贴来推动。
上海市政府除了向承包户(上海本地农户)补贴规模经营奖励金外,还要对种植户(耕者)进行高额的农业生产补贴。2022年,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出台的《浦东新区绿色农业生产补贴专项有关实施细则》显示,该区农业生产者可以享受种植业条线、蔬菜条线、农机条线、畜牧条线、渔业条线、种业条线、农产品质量监管条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基本农田保护补贴九类补贴。以种植业条线补贴为例:(1)水稻种植直接补贴430元/亩(市补260元/亩、区补170元/亩);(2)水稻病虫害防治物化补贴区补120元/亩(其中绿色食品认证水稻每亩增加不超过30元);(3)杂交稻良种物化补贴区补80元/亩(数量2公斤/亩)、常规稻良种物化补贴区补40元/亩(数量4公斤/亩),补贴良种须为本区水稻主导品种;(4)水稻机械化种植补贴区补50元/亩,包括机械化育插秧、机械化直播、无人机飞播等;(5)家庭农场水稻种植面积达到80亩以上的,或水稻种植面积占经营面积50%以上的,区级财政对水稻种植增加平均每亩270元现金考核奖励补贴(镇级家庭农场每亩150元的现金考核补贴)。综上,农户种植水稻每亩地可获得790元到950元的种植补贴。
种植条线还有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补贴:(1)冬绿肥种植补贴300元/亩(市补75元/亩、区补225元/亩);(2)冬季深耕晒垡补贴200元/亩(市补50元/亩、区补150元/亩);(3)有机肥使用、绿色防控技术应用等水稻绿色生产技术应用,施用商品有机肥每亩不少于500公斤,根据水稻种植面积补贴120元/亩(市补15元/亩、区补105元/亩);(4)秸秆机械化还田补贴50元/亩(市、区各补25元/亩),秸秆综合利用补贴300元/吨(市补240元/吨、区补60元/吨);(5)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与集中处置补贴3.15万元/吨(市补0.6万元/吨、区补2.55万元/吨)。这一部分的农业补贴只能覆盖成本,农户无法从中获得剩余。
事实上,上海市部分乡镇在2000年左右就通过“土地换社保”的形式将绝大部分农地承包经营权收归村集体所有,村集体通过区政府平台向有资质的承包户或企业发包土地。上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中大大提升了农田水利设施等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了农业机械化、专业化水准,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的调控力度。上海市实行农地休耕政策,耕者如果在一块田地连续种植两季作物,则不能获得相应财政补贴。在上海农村种地的农民多数来自安徽、河南、四川,他们通常耕种100亩以上的土地,每年工作6个月时间。粗略估算,耕者可以从每亩土地获得500—800元的净收益。
(三)都市农业
在城市发展战略推动下,东部农村的产业空间与生态空间被重构,都市农业成为其新功能之一[7]。超大型城市依靠科技与人才优势,在郊区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基地,将农村农业空间变为农技创新、技术示范、教育观摩、高端产品供应的空间。例如,浦东新区张江镇2021年投资900万元在环东村现代农业基地引入自动化蔬菜生产区,建立自动化新型叶菜盆栽系统,实现蔬菜工厂化生产、设备全自动流水线作业栽培模式,从播种、育苗到生产以及最终产品都实现专业化的管理。同时,该镇还加快推进环东村农业苑蔬菜示范创新基地,以张江蔬菜栽培新技术为载体,投资500万元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农业生产基地,展示“小而特”农业的示范效应。由于毗邻张江科学城,张江镇的农业生产示范基地还成为科学城工作人员的“后花园”,发挥都市农业的空间功能。而上海南汇新城的农民则利用轮耕时间,种植小西瓜、小番茄、8424西瓜等高附加值、高价格的“私人订制”型农产品。
超大型城市的农民因城市经济的溢出效应而能就地或就近就业,未出现中西部农村常见的留守儿童问题;超大型城市的农业因城市强大的财政实力支撑,而较早实现规模化、机械化和现代化。在此背景下,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农村治理、农业发展和农民福利,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农村而言具有“未来村”的示范引领价值。
三、东部农村的工业整合
上海郊区农村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从农业向工业转型,2000年以后随着乡镇企业转制,农村成为中小型私营企业主的生产空间。在30余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当地农民获得就近就业机会,农村集体获得土地厂房租金收入,农民凭借参与工业化的技术、资本和经验积累进城买房、就业。2010年前后,上海郊区农村成为中低端工业和外来人口集聚的空间,面临着生态环境治理和外来人口治理两方面的困境。
(一)农村工业企业进园区
2014年起,上海市政府为了实现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和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的双重目标,开展了一轮又一轮的农村违建和生态环境整治工作。上海郊区曾经遍布小作坊、仓库、加工门店的村庄逐渐变回20世纪80年代的田园生态模样。曾经在农村的大中型工业通常迁入政府新建的大型工业园区,而小型企业和家庭作坊考虑到成本要素,要么外迁、要么关闭,农村工业向园区集中的趋势明显。
“五违四必”是上海市“十三五”期间的重要工作之一。“五違四必”是指“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这五种情况,必须做到“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建筑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必须取缔”。“五违四必”是上海市向存量建设用地要空间的重要策略。在锦标赛体制下,各街镇努力实现“新增违建零增长、在建违建快速拆、存量违建大量拆”的目标。例如,浦东新区张江镇2016年共消除新增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11151.6平方米,消除存量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107.45万平方米,完成当年任务目标的424.8%。据报道,2015年7月至2017年3月底,上海市连续三轮“五违四必”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共拆除违法建筑8531.84万平方米,消除违法用地14286.4亩,整治污染源2440处,关闭查处无证违法经营企业11633家。
政府推动农村违建治理的中心目标是农村建设用地减量化,缓解大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压力,为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战略空间。在“五违四必”整治中,多家企业关停、迁移,仅张江镇某村就有140多家企业或关停或迁址,该村2019年的集体土地和房屋租金为935万元,较2016年减少80%,该村被拆除的集体违法建筑和违法用地面积为32万平方米。
在中西部省市仍在寻求工业化契机的当下,东部省市大力推进本地农村去工业化,要求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展现出东西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需求。东部农村的去工业化并非去产能化,而是地方政府规划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步骤,正如上海郊区农村建设用地减量化出来的用地指标被用于建设支援特斯拉汽车工厂用地一样,广州、杭州等超大型城市将分散的农村建设用地集中起来用于建设高新科技产业园区,满足了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提升了城市发展的全球竞争力。
(二)农村人居环境景观化
农村人居环境的高档化、绅士化、景观化成为后工业时代的重要标志。在农村工业整合的同时,地方政府往往启动美丽农村、美丽庭院等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投入大量资金改造农村公共环境和居民庭院景观。
浙江省近年来提出“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四边三化”等政策,大力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整治。这些政策与上海市的“五违四必”“拆建管美”有着相同的目标,即拆除违法建筑、消除违规用地、腾出建设用地指标、建设美丽农村。与上海不同的是,浙江農村工业化是以农民企业家为主体的家庭式工业化,农民将庭院、宅基地和自留地改扩建为工厂的现象较为普遍。农村拆违工作需要与家庭小私营企业主打交道,工作难度相对较大。据报道,杭州大慈岩镇通过强势推进“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四边三化”等工作,统筹推进全域环境整治,已拆除“一户多宅”、土地违法、乱搭乱建共计8万余平方米,优化了村镇建设用地,美化了人居环境[8]。
在上海,近郊农村的公共空间建设日益与城区一致,政府在村庄路口建造花坛、栽植绿化、设置路灯,在河道水流两岸设置护栏,将村庄生活用水和自然河流纳入污水处理系统。粗略统计,浦东新区某村2017年至2020年四年间,在美化点位、道路建设、村容风貌、公共建设方面的投入资金是1.2亿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市、区公共项目。而上海嘉定区某村的村庄平移工程,在基础设施投资上保守估计花费4亿多元。这些村庄是规划保留村庄,也是地方政府重点建设的美丽乡村和乡村振兴示范点,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发达地区村庄的发展模式。
上海、广州等超大型城市凭借强大的财政实力,能够在从农村汲取建设用地指标的过程中给予农民较多的实物补偿或货币补偿,亦能投入大笔资金改善生态环境,因此,这些地区农村的去工业化并未带来农村的衰败,反而成为农村生态化转型的契机。
四、东部城市郊区农村的风貌管控
“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适用于任何一个超大型城市的城乡空间概况。无论是上海,还是广州、北京,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存在,远郊农村的破旧风貌与国际大都市地位似乎并不匹配。然而,如果将郊区农村视为超大型城市的一部分,就可以理解超大型城市政府对农村风貌管控的政策逻辑。
(一)东部农村的宅基地政策
宅基地审批和农房翻建管理政策是决定农村风貌优劣的关键因素。上海市国土部门对农村风貌管控一贯严格,农户翻修房子必须报国土部门审批,农户获批的宅基地面积也有明确规定——人均30平方米,户均不超过90平方米。如果子女成家,可视为一个新户申请宅基地。农户新建或翻修房屋之前,需要四邻签字确认地界,奠基和封顶时必须请国土部门管理员和村干部到场签字。如果农户建房超过规定高度(上海南汇区规定不超过13米),必须拆除超高部分,否则这个住宅无法取得房屋使用权证,也无法办理户口迁入迁出业务。地方政府对违建的严格管控,为后期的违建治理积累了制度势能,例如浦东新区某村在“五违四必”期间顺利拆除农户8万平方米的违建房屋。国土部门严格的宅基地管控政策,导致上海嘉定区、奉贤区、松江区的绝大多数原始农村农房是1990年之前建造的,农村风貌老旧;浦东新区农房翻新的政策延续到2000年左右,农村风貌整体良好。
相较之下,广州郊区农村的农房布局构造更为复杂,违建情形较多,违建治理效果较差。这一方面与地方政府的违建管理政策混乱有关,一方面与违建管理部门的工作能力有关。近年来,广州市的旧村改造政策公开承认了某个时间节点之前的违建房屋合法(例如,广州市黄埔区为2009年12月31日),潜在鼓励了其他违建者。调查发现,无论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征地拆迁,还是企业主导的旧村改造项目,对农户的违建房屋都予以最大范围的承认。这显著加大了征地拆迁或旧村改造的难度和成本。
(二)东部农村的征地拆迁补偿
珠三角地区的征地拆迁补偿标准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该地区采取“按户补偿或按建筑面积补偿”的方案。以广州市黄埔区当前的政策为例,如果按户补偿,一户补偿240平方米,18岁以上的成年人无论是否成家都算作一户;如果按照建筑面积补偿,则按照单层建筑面积的4倍予以补偿,当地户均宅基地面积通常在100平方米以上。
上海征地拆迁补偿同样采取“人头多数人头,砖头多数砖头”的模式,如果按人头补偿的话,人均补偿30—40平方米(农村户口为40平方米,城镇户口为30平方米,公务员不予以补偿);如果按房屋原始面积补偿,则补偿合法建筑面积单层的2.5倍。因此,与上海市传统农村整体上有序的风貌不同,珠三角农村呈现出新旧不同、高低不一、握手楼常见的马赛克式农村风貌。
广州和上海农村空间风貌治理效果的差异植根于地方土地制度实践。广州在20世纪90年代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产业,许多农村农地就地转化为工厂和集体宿舍,农户可以自建多层房屋出租获利。1998年土地管理法出台后,明确规定城市工业和商业用地必须经过国家征收程序。但在1998年之前,珠三角地区已经形成大批历史性违建房屋。基于外来企业和外来人口的空间租赁需求,珠三角农民能够轻易从土地、房屋上获得可见的货币利益,因此形成了强烈的土地共有观念。当地农民在征地拆迁中的预期收益高、讨价要价能力强,加大了城市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本,贺雪峰将该地区的土地制度称为“先发劣势”[9]。
上海的国土空间规划建设延续了严格管控的政策逻辑。农民不具有违规建设、利用土地的历史合法性。加之,上海市政府基于长期的土地征收和开发经验,在征地拆迁中坚持了相对统一、长期稳定的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和公开透明可追溯的工作流程,降低了农民在征地拆迁中的机会主义心理预期。
在超大型城市的空间规划中,绝大多数村庄在未来30年是不保留村庄,东部农村的破旧风貌成为城市发展中的过渡性景观。农村风貌管控政策具有两方面效果,一方面避免农村资源浪费,一方面降低未来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征地拆迁的难度和成本。那些未能在过去和现在有效控制农村新建、违建房屋的超大型城市,则要在未来支付巨额政治经济成本。
五、结语
东部农村虽然在体制上是农村,但在功能上已成为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一方面分担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一方面分享了城市发展的收益,是城乡一体化的具体空间呈现。
东部农村的核心特征是处于城市经济带的輻射范围之内,自然地分担了城市功能,分享了城市经济外溢的利好,是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典型地区。东部农村农民与市民之间基本上不存在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异性政策权利,其主要差异是更为普遍的消费能力差异。相较市民,农民拥有农村集体身份赋予的独特权利——宅基地使用权利、农地承包权、集体土地收益分红权等村社权利。在东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通过征地拆迁获得较多的房屋和货币补偿,就地实现有就业支撑的城市化。
在当前阶段,超大型城市政府对农业和农民仍实行优惠政策,但绝大多数本地农民已离开农业和农村,相应的政策精准度有待提升。同样,超大型城市郊区农村的治理资源和治理任务与中西部农村有着明显差异,该地区的社会治理分为以外来人口为中心的外部治理和以福利分配为中心的内部治理,社会治理创新经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郊区农村与普通农村的区位及空间功能差异,决定了其面对的问题不同,这为中国政策制定、地方政策创新扩散提供了分类基础。
需说明的是,东部农村作为一种类型,并不完全以地理边界为准。东部地区也有个别不在城市经济带辐射范围之内的村庄,例如省市交界处的边缘村庄;中西部地区也有在城市经济带辐射范围内的村庄,例如省会城市、二线城市的少数近郊农村。如上农村在各地区都属于少数,可以按照属性划到相应类型中去,并不影响东部农村与中西部普通农村的类型划分及政策研究。
参考文献:
[1]贺雪峰.东西中国:中国区域差异的经济视角[J].开放时代,2023(2).
[2]杨忍.广州市城郊典型农村空间分化过程及机制[J].地理学报,2019(8).
[3]魏程琳,钟晓华.空间再组织:城乡接合部闲置农房产权整合与社会有效治理——上海农房再利用案例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22(4).
[4]熊易寒,曹一然.空间再分配:城乡接合部治理的政治学意义[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
[5]上海2020年后实现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零增长”[EB/OL].(2014-04-25)[2023-05-11].http://www.gov.cn/xinwen/2014-04/25/content_2666424.htm.
[6]上海市新城规划建设推进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十四五”上海新城规划建设导则》[EB/OL].(2021-03-01)[2023-05-11].https://www.shanghai.gov.cn/cmsres/23/23b5a00e39c14deaa1b8b854ec15ccee/276edb9ce6476a09580e2168d0cc7790.
[7]陈潇玮,王竹.城郊乡村产业与空间一体化形态模式研究——以杭州华联村为例[J].建筑与文化,2016(12).
[8]建德大慈岩镇:以土地综合整治助力全域风貌提升[EB/OL].(2022-12-29)[2023-05-11].http://zjrb.zjol.com.cn/html/2022-12/29/content_3615428.htm.
[9]贺雪峰.发达地区土地利用上的先行劣势[J].农村工作通讯,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