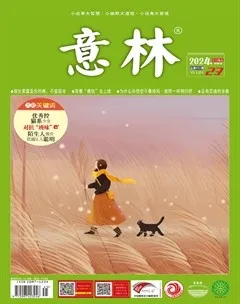如果杜甫有手机
这几天正在追一部谍战剧,扣人心弦,我欲罢不能。所以我刚才上台前只想睡觉,因为昨夜很放纵,追剧追到凌晨两三点。这部剧的背景是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充满紧张的悬念,种种阴差阳错,种种千钧一发;但是,看着看着,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漫长、精密的故事,之所以能够牵着我一路跑下来,有一个根本条件——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几乎每一处悬念、每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人物手里有一部手机,问题就不存在了,不必紧张了,平安无事,月白风清。敌人在门外设下了罗网,必须马上通知屋里的同志。我在街上狂奔,寻找一个公用电话亭,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里边的姑娘正在和闺密讨论电影和口红,简直活活急死人。这个时候如果掏出手机,问题就没有了。所以我这一夜一夜看的是什么,是由于不连接,由于弱连接,由于连接的故障,造成的一个个否定性情境。在这个情境里,人面临着庞大的偶然性。偶然性是什么?偶然性是意外,是你的“意想”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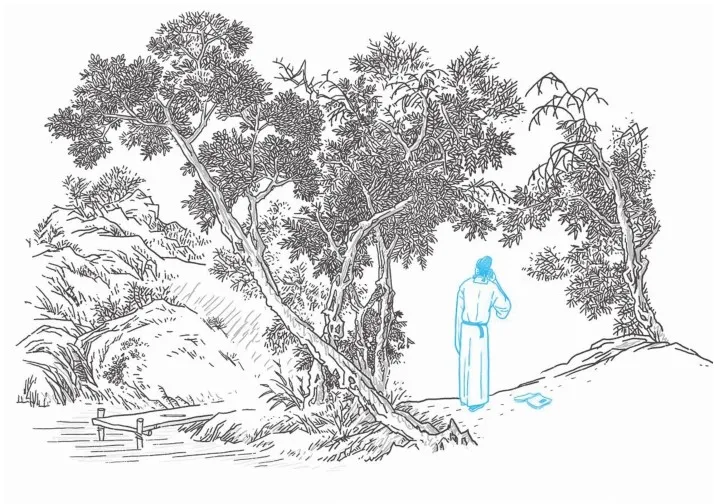
假设这个世界上早有手机,那么昨天晚上那部电视剧就没有了,很多剧很多小说都不会有。我们还会失去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杜甫的很多诗。杜甫的诗留存下来一千四百多首,如果他有手机的话,起码有五分之一是不必写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写的都是空间和时间上的阻隔、间断,这种阻隔、间断、不连接使杜甫成为一位追忆、遥望、惦念和感叹的诗人。王国维谈“隔”与“不隔”,讲的是心与景、词与情之间,好的诗人要望尽天涯路,捅破窗户纸,由隔抵达不隔,不隔方为高格。但如果没有对“隔”的深刻感受,又何来“不隔”?对杜甫来说,“隔”就是一个精神空间,一个抒情场域,他的追忆和遥望,使不可及的人、事、物返回和构成他的世界。
我们都知道杜甫和李白关系很好,杜甫在漫长岁月里写了很多首诗想念李白、怀念李白、歌唱李白。我想,如果他有手机,如果他和李白随时都可以通电话、刷微信,那么,这些诗就不必写了,而且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感情很可能维持不了那么长时间。天天话来话去,紧密连接,他们的个性如此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也很不相同,又生逢天崩地裂、意见纷纭的大时代,不知道哪一天一言不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所以幸亏不连接,不仅人间有好诗,而且人间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