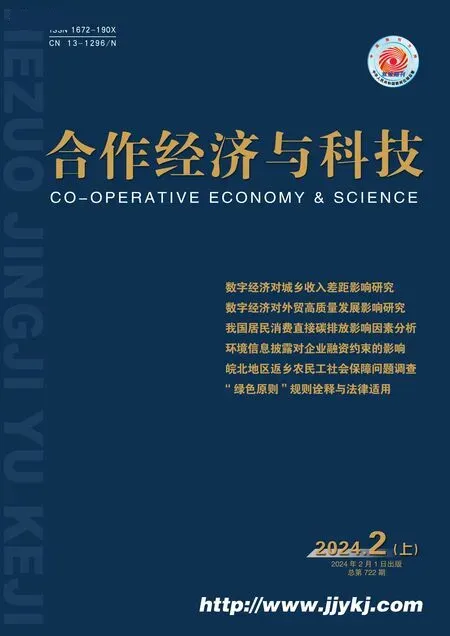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通道空间发展研究
□文/毋 宁
(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西藏·拉萨)
[提要] 喜马拉雅地区自古以来所形成的贸易通道不仅仅是传统的边民贸易通道,未来更是我国加强南亚周边交流互信、实现跨喜马拉雅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通道。本文从自然空间、空间实践和空间重构三个方面对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通道空间发展进行研究。
引言
喜马拉雅地区位于亚洲中部,地处青藏高原南麓,是世界海拔最高、地理位置最重要的山脉。目前,喜马拉雅地区已经形成了“一横多纵”的空间分布格局,并且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中国与南亚周边国家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地区。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贸易通道的建设成为各国推进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促进国家间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西藏喜马拉雅地区是我国南亚开放大通道的重要交汇点,在南亚开放大通道建设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空间生产理论是由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首次提出。他认为“空间”不仅是一个社会互动的物质载体,更是社会的产物,并构建了“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三层空间生产框架。空间实践指实体感知的物质空间的“空间性的生产”,对应于发生在实际空间中的物质性实践活动行为及其结果,是指人们通过一系列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对自然空间进行开发利用,被社会化了的人造空间;空间的表征则是由社会成员所构想的概念化的抽象空间,是一种精神空间;表征的空间则指向空间的表征的对立,是一种物理空间,是一种自然的、先天客观存在的空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空间生产是空间本身的生产,是指人类通过空间实践对原有的自然空间进行社会性的改造,使其空间产品符合自身发展的利益。
本文在空间生产理论的框架下,研究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通道空间发展。喜马拉雅地区的贸易通道将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活动空间,成为南亚国家间经贸合作、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的重要载体,对于实现南亚开放大通道建设、构建现代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近三年大都是在“南亚开放大通道”和“一带一路”背景下对西藏的边境贸易口岸、中尼边境贸易发展等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进行相关研究。在重要性方面,刘秧(2019)、孙喜勤等(2020)分析了在我国“一带一路”和“南亚大开放”战略下喜马拉雅地区的重要性。其中,刘秧(2019)分析了喜马拉雅地区吉隆河谷通道所具备的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认为喜马拉雅地区将成为连接我国青藏高原地区与南亚次大陆文化的中心。在测度方面,冶莉等(2022)就从“南亚开放大通道”背景出发,运用评价指标体系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近年来中尼口岸贸易可持续发展水平和跨境交通可能性。在发展路径上,张春燕等(2018)分析了跨喜马拉雅地区的中尼贸易关系前景。徐黎丽等(2020)从西藏边境口岸展开分析,对西藏边境口岸建设和中国与南亚通道的建设路径进行研究,提出要将重要的边民互市升级为口岸,最终通过边境口岸将中巴、中南、孟中印缅三大走廊连接起来。国外学者现阶段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自然地质环境、地质构造和地缘政治较多,在早期阶段主要针对尼泊尔、印度等几个国家的贸易路线进行了相关研究。Manzardo A E 早在20 世纪70 年代就对喜马拉雅地区南北两部分贸易进行了研究,并以南部塔卡利羊毛贸易为例,分析了早期南部地区特别是尼泊尔国家在喜马拉雅地区展开跨喜马拉雅贸易合作所受到的生态限制。
目前,有关喜马拉雅地区的研究相当多都是针对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地质构造等进行研究,国内外学者较多的是针对中尼贸易或者早期印度尼泊尔边境贸易路线史进行研究,而当下结合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南亚开放大通道”建设等当下政策分析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通道空间发展的相关文献还有待丰富和扩展。
二、空间生产原点:喜马拉雅地区空间现状
喜马拉雅地区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山区和丘陵地带,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和自然空间。其北部包括我国西藏自治区大部分地区和克什米尔的达拉克地区,南部包括尼泊尔、不丹两国、西孟加拉邦北部、锡金邦和喜马偕尔邦。喜马拉雅山脉不仅是各大河流的发源地,也是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天然国界和重要的贸易通道,在梵语中意味“雪域”,藏语中的意思为“雪的故乡”。
从自然空间来看,喜马拉雅地区背靠喜马拉雅山脉而得名。喜马拉雅山脉全长2,400km,贯穿中国西藏,以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地理位置特殊,历来都是各国焦点所在。喜马拉雅地区自然空间特征复杂,不仅有着高山、山谷和冰川,还有着各种复杂的河流峡谷、侵蚀地形。其中,喜马拉雅地区南部降水丰富,植被类型多样,适合种植业,盛产大米、小麦等农作物;北部地区则因西南季风等受到山脉阻挡,降水较少,充斥着河谷地带,地势宽阔平坦,植被稀疏,适合发展畜牧业。
在喜马拉雅地区独特的自然空间下,也形成了该地区独特的社会文化空间。在社会文化方面,喜马拉雅地区一直以来是一个相对孤立的空间,与外界接触比较少,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几个世纪以来,该地区的民众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语言,不受任何人的干扰,彼此之间依靠贸易“以物易物”来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粮食作物或者毛皮、食盐等。印度教、佛教和部落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和信仰。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通道不仅是贸易路线,也是印度教、佛教等进行朝圣的路线,这些为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通道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作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分界线,喜马拉雅地区不同文化相互重叠,民族和宗教信仰纷杂,各种语言宗教文化交汇,虽然种族差异很大,但在喜马拉雅地区却发展出了一种共同生活、和平互动的生活景象,同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并在服饰、装饰品、修道院、神社和节日日历中体现出来。
三、空间生产转型: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通道历史演变过程
(一)古代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通道空间形成及演变。吐蕃时期,吐蕃就与唐朝、南部天竺、西方的尼婆罗及北方的突厥等四个政权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吐蕃地方政权还专门设有“商官”,以专司其对内和对外贸易。从此之后,西藏地区与四邻民族的商贸往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到了宋元时期,贸易兴盛,西藏地区更是形成了许多的贸易集市用来交换茶叶、羊绒和白银等,进行边境贸易。元朝时,中央政府开始以法律的、规范的方式对西藏进行全面施政,西藏社会也趋于稳定,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公元17 世纪以后,西藏与周边地区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密切,特别是与尼泊尔之间,有着聂拉木和吉隆两处重要的贸易通道,并在喜马拉雅地区开设了贸易商品集市。而尼泊尔人也经常通过喜马拉雅地区的贸易通道进入到中国西藏与当地商人开展粮食、羊毛等贸易交换。到18 世纪中末期,廓尔喀侵略军入侵西藏,清朝乾隆皇帝在派兵打败廓尔喀侵略军后,制定了详细的章程律法来明确西藏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贸易往来准则。
(二)近现代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通道空间发展。19 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西藏地区逐步步入半殖民地社会。1888 年及1903 年英帝国主义者先后两次举兵入侵我国西藏地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并开放亚东等地为商埠,在此享有治外法权。为方便对中国进行入侵,更是在喜马拉雅地区开辟了诸多贸易通道和商埠,从此在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展开了长期的经济掠夺。
新中国成立后,西藏获得和平解放。为了改善西藏当时落后的经济面貌,满足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1956 年中尼签订《中尼协定》、中印先后签署两个《协定》,恢复了喜马拉雅地区的贸易通道,重新开放了西藏边境地区的贸易市场和通商口岸。但是由于1962 年后中印边境冲突导致中印两国边境贸易市场和通商口岸关闭,中印之间传统的贸易路线也逐渐衰落,随后在喜马拉雅地区,中国与尼泊尔之间的贸易成为主要的贸易往来。1991 年12 月13 日,中国和印度在新德里签署了一份关于恢复边境贸易的备忘录,1992 年7 月1 日签署了一项关于边境贸易入境和出境程序的议定书,1993 年9 月7 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第二项议定书,扩大了跨什布奇拉山口的边境贸易,将印度喜马偕尔邦地区金瑙尔县的南加和西藏自治区札达县的久巴开放为边境贸易市场。
随着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趋势,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要以合作共赢代替对抗零和。2001 年我国加入WTO,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更加密切,环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不断涌现,以“合作共赢”为目标的区域经济合作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倡议和重视。
四、空间生产结果: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通道空间重构
由于在各个历史阶段空间实践的结果,导致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通道历经萌芽、发展、衰落、恢复等阶段后,形成了目前“一横多纵”的空间分布格局。截至目前,我国西藏自治区边境线上面向喜马拉雅地区和南亚共有对外通道312 条,其中常年性通道44 条,季节性通道268 条。对外通道分布在中尼边境184条,中印边境85 条,中不边境18 条,中锡边境8 条,中缅边境5 条,克什米尔地区边境12 条。有28 个国家口岸和开放的边贸市场,18 个分布在中尼边境,7 个在中不边境,1 个在中印边境,1 个在克什米尔地区边境,其中有樟木、普兰、吉隆、日屋、亚东5 个国家口岸。
五、研究结论及发展建议
(一)研究结论。喜马拉雅地区具有不可多得的地缘优势,发展众多的边境口岸和对外贸易通道,可以为我国发展边境贸易、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南亚开放大通道”建设提供有利的基础条件。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结合相关文献,从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通道的空间基础、空间实践和空间重构结果三个方面分析了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通道的空间历史演变过程,基于上述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从空间生产基础来看,在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通道的形成过程中,空间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叠加关系,而是经过历史的复杂的空间实践所形成的现有的空间重构结果。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通道的形成受到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社会人文等多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设才形成了历史上传统的边民贸易通道。(2)在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对贸易通道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环喜马拉雅地区经济带”“南亚开放大通道”建设等政策不仅仅关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更是涉及诸多国家的切身利益。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通道未来将不仅仅是贸易通道,更是沟通“中心-边缘”以及南北文化的桥梁和纽带,对于构建中国与南亚周边国家新型关系,实现以合作共赢代替对抗零和,推动“南亚开放大通道”建设等提供了重要的现实路径。
(二)发展建议。(1)完善我国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喜马拉雅地区的交通设施发展滞后,使得该地区在对外开放中面临着诸多阻碍。因此,发挥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通道发展潜力,必须要加快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国家间区域间合作的开展,推进中尼跨喜马拉雅铁路建设等项目实施。(2)发挥贸易通道“桥头堡”的地位和作用。喜马拉雅地区作为中国和南亚周边国家沟通的经济政治前沿,应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通道为基础,不断巩固和扩大其“桥头堡”地位,从贸易合作逐步扩展到经济合作、政治合作。以合作促发展,不仅有利于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通道的构建,也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3)充分利用区域发展差距,形成贸易带动经济发展格局。从区域发展战略角度看,要在“一带一路”倡议、南亚开发大通道建设等国家战略引导下进一步促进中国-南亚贸易通道健康持续地发展,构建中国-喜马拉雅地区-南亚互联互通通道,引导南亚各国积极参与建立环喜马拉雅经济带,这将对于恢复和促进喜马拉雅地区贸易交流和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可以加深中国同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交流和对外开放程度,有效推进跨喜马拉雅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区域合作,构建中国与南亚周边国家和地区沟通的桥梁和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