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前夜的四重临界:《来自近未来的子弹》创作谈
任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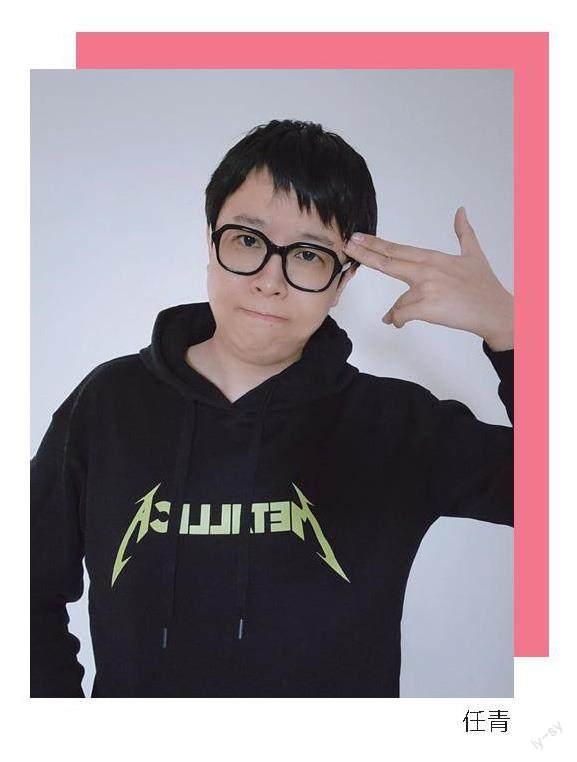
《来自近未来的子弹》(以下简称《子弹》)中的故事,发生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那是一个魔幻的年代。在那个时候,我读了大学,交到了朋友,体验了爱情,感受了被裹挟着随波逐流的人生,疯狂过,欢喜过,狂怒过,忧愁过,也冷静过,所以我对那个年代,是有深厚感情的。这种感情谈不上是“热爱”,更像是一种思念和乡愁。时间奔涌,总会洗刷掉什么,我自己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很多中国人的一部分,已经随时间、随风雨、随疯狂生长的网络、随盛会、随经济奇迹、随野蛮的角落、随漫无尽头的幻念,永远留在了那个时代中。
而如果结合科幻的概念,你甚至可以把那段时期叫作“智能时代的前夜”。以最早的智能手机为例,第一代苹果手机 iPhone 是2007年推出的,小说里提到的诺基亞 E50手机使用塞班系统,也在同年推出,而首款安卓系统手机则在2008年上市。这些手机只是新技术的初步应用,仅供人们尝鲜,智能手机市场真正迎来爆发要到四五年之后了。
在智能手机普及之前,我们当然也会使用个人电脑,但人和智能设备的结合尚未如此深入,技术依然是被神化和膜拜的对象,人类还不曾体验到“置身其中”“如影随形”的感觉。智能手机普及之后,实现了人的主体性的再次外延,我们俨然拥有了新的器官、新的四肢,甚至有更为“赛博”的头脑。
《子弹》中的故事,便发生在人的定义得到扩展的前夜,此时近未来的技术焦虑刚刚成形,旧时代的科技崇拜尚未离场,于是,在文本与现实生活的交界处,我们得到了一个如行过死荫之地般半明半暗的故事。
此即技术的临界感。
另一方面,《子弹》的故事发生在两个很有象征意义的场所,一个是即将破产重组的旧工厂,隔壁则是将要升级为本科院校的农学院。工厂代表着消逝的过去,学院意味着不确定的未来,这两个庞大的实体都难以把控自身的命运。可想而知,它们之中的诸多小人物也必将深陷在命运的流沙之中。可以说,《子弹》里的所有角色都处在人生的交错点,不管是否主动,是否“有本事”,是否热爱生活,他们都面临时代变化带来的新选择、新困境,甚至开始怀疑自身存在的意义。比如智兽医,他深知得到实现预言的能力多么重要,却也感受到这种笃定的宿命感多么可怕。再如陈校长,作为一个刑满出狱的贪污犯,他从事保安工作,在生活中诚惶诚恐,对人客客气气,却始终暗自怀有改变余生命运的热情,这种热情的目的未必是获得什么成就,更像迟暮之年的垂死挣扎,用研究不知所踪的神秘事物,去挽回自己整个人生的意义。
《子弹》中,最具象征意义的角色大概是梁建伍,他作为保卫科科长,在对工厂与学校的存续风波、连续死亡事件的探索中首当其冲,原本找不到任何途径证明自己的他,终于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当主角”的机会。他也是整个故事里行为最主动的人,但步步紧逼到最后,面临的却是巨大的虚无。梁建伍的迷茫和幻想、人格和处境,可以称得上是整篇小说的精神写照。“抓住不切实际的救命稻草”——临界中的人,在临界的时代做些疯狂的事情,形成了大时代中渺小生命的群像。
此即人物的临界感。
有了技术和人物,在小说这种载体中,需要更深一步表达的,便是彼此之间的关系。科幻故事里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科技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在《子弹》中,我着重描写了一种自组织的机器集群,已经存在和迭代了千余年之久。千年来,它对人的影响愈演愈烈,人对它的反抗也没有停止过,不过这种反抗实属无力,绝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最终在生死时刻找回人性的,竟然是残疾人智慧美。她虽然没有太多“智慧”,但残疾为她带来了人性中的纯美。在面对独立于人世之外、俨然成为神祇的技术怪物时,她用直接果断、专属于孩子的行为拯救了儿时玩伴,成为唯一不懂科技,却能够“驾驭”科技的人。而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小说努力营造山雨欲来的微妙感,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所有人的关系都是“临时性”的,临时的搭档、临时的朋友、临时的师徒。这些不稳定的、没有安全感的关系让他们更容易受到技术的影响。最终,在角色面临诸多选择时,科技的超然力量成为观察者,人类似乎是玻璃箱里的蚂蚁,即便撕咬掉一切同类,也永远不能脱困。正是在这样的无力之境,故事最终行进到了血与救赎的终点,而救赎,最终也成为虚假的事物。
此即关系的临界感。
最后我要谈的,是情感与情绪。特殊关系中的人物,情感也会处在特殊状态。《子弹》中很多人都被边缘的情绪裹挟着,他们虽然做出不可思议的选择,但并非出自突发的激情,而是在技术、环境、关系的作用下一步步滑向了深渊。他们的爱不是爱,已经在自我阉割中异化;疯不是疯,被不可名状的机器操控,深陷在未来的恐惧之中。那颗来自近未来的子弹,虽然只有一发,却最终击中了每一个人。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自己日常的很多情绪,实际也行走在理性的边缘,小说似乎能照出我们每个人的影子。现在举起你手里的智能设备,看看网络中铺天盖地的新闻、消息、图片、段子、受控的自媒体,它们在拼命尖叫着,争先恐后要对我们施加影响,让我们变成人云亦云的乌合之众。你感受到恐惧了吗?
此即情绪的临界感。
从四种临界感出发,我构建了这样一个故事,它是对逝去岁月的挽歌,是关于近未来因果倒置的文本艺术,也是一次对“或然现实主义”的探索和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