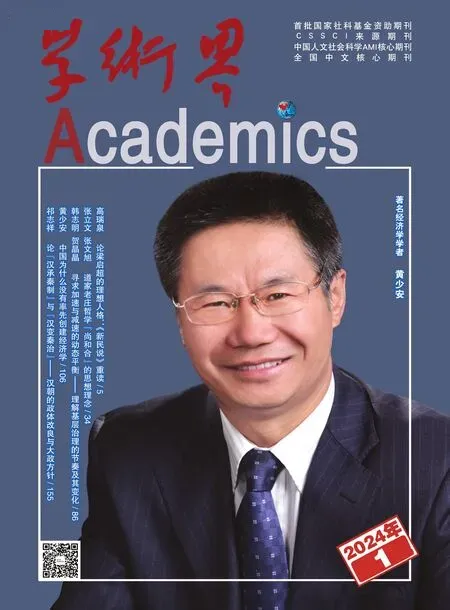科举时文与经学话语:江永《乡党文择雅》新解〔*〕
陈居渊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 安徽 合肥 230601)
江永(1681—1762)字慎修,又字慎斋,清代康乾期间江南徽州地区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他在传统经学、宋明理学、古代音韵学和中西算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特别是所著《周礼疑义举要》《礼书纲目》《律吕阐微》《乡党图考》等经学著作,代表了当时“三礼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其中《乡党图考》对古代典籍中制度名物“考核最为精密”。〔1〕因此,学术界都视其为研究古代礼仪制度的必备经典。事实上,在江永编撰《乡党图考》前曾经编撰《乡党文择雅》(以下简称《择雅》)一书,以时文的形式,集中讨论了古代的各种礼仪的传习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深受当时学人的赞誉,认为“此集有功于经学者大矣”。〔2〕《乡党图考》则是在《择雅》的基础上“核其同异”“绘图明之”,进行了细化考证,两书相辅相成,可分可合。长期以来,《乡党图考》的研究成果较为密集,而《择雅》作为古代科举从业者的应试之文,常常被误认为是糟粕,学术含量有限,备受冷遇,导致《择雅》所蕴含的学术价值被漠视,至今未见有学者的专题讨论,从而也影响了对江永学术全面客观的评估。对此,本文尝试从经学的角度作一些新的解读,旨在抛砖引玉。
一、《择雅》其书
《乡党》是《论语》二十篇中的第十篇,全篇由二十七章组成,〔3〕主要记录了孔子生前讲述朝中、朝外以及乡间不同场合待人接物的礼仪,为我们展现了古代社会包括言语、傧相、朝会、服饰、祭祀、会饮、馈赠等礼仪活动,是研究中国古代礼仪制度除《仪礼》《周礼》《礼记》之外的重要文献,彰显了孔子与儒家对礼仪的现实关怀与传递礼仪实践的经学场景。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对于《乡党》的解读,历代学者的理解也因时代的不同而产生异议,汉唐诸家的注疏已有异同,宋元学者更多的是阐发其义理而轻视注疏,故有“议礼之家纷如聚讼”一说。自从明清时期《四书》成为科举考试必读书目之后,《论语·乡党》所蕴含的制度名物,渐渐淡出学者的视野,从而成为科举从业者争相“揣摩弋获之书”“代圣贤立言”,解读粗率谬误,即所谓“独《乡党》传文绝少其传者,又未必果可传,非独圣人气象难摹,亦缘其间多制度名物,关涉《礼经》,经术不溟,举笔便成疏谬”,〔4〕从南宋经元明至清,历代著名学者对古代礼制的相关解释也频频出现谬误。江永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观察:
这里所说的《集注》,是指朱熹撰写的《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论语集注》,该书被学界视为南宋以后对《论语》最为权威的解释。《注疏》是指北宋学者邢昺的《论语注疏》,该书被历代官方认可为解释《论语》的标杆性著作。《蒙引》是指明代学者蔡清的《易经蒙引》,以阐发朱熹《周易本义》而著称。顾麟士即顾梦麟,顾炎武的族兄,著有《论语约说》。饶双峰即南宋著名理学家饶鲁,著有《语孟纪闻》。吴草庐即元代学者吴澄,著有《礼记纂言》。《聘礼》《玉藻》《谭工》《丧大记》等皆为《礼记》一书中的篇名,孔氏指孔颖达,曾经编撰了《礼记正义》;贾氏指贾公彦,曾经编撰了《仪礼注疏》,两人都是唐代著名的经学家。钱鹤滩即明代状元钱福,以诗文敏捷著称。而“命圭”“用圭”、“绀”分别指《乡党》的第五章和第六章,“趋进”为第三章,“升车”为第二十六章,“裼裘”“袭裘”为第六章,这些都可视为对经典中有关古代礼仪习俗和礼制的解读,具有很高的经学价值。正是出于弥补应试者的经学短板而提供应试范文的愿望,江永以七十一岁的高龄,于乾隆十六年编撰了《择雅》一书,他在该书的自序中描述了他对当时经学状况与时文写作的担忧和期待:
从来经学之难,《礼经》尤甚,不独有明以来多卤莽灭裂,即汉唐注疏诸家已多斑驳,至宋元诸儒谈理盛而研经疏。朱子以海阔天高、茧丝牛毛之心力至晚年修礼书,而制度名物之学始精。况其几者乎,又况降至时文家一生精力肯用之《礼经》乎?宜乎《乡党》传文不少,概见也。余素不敢言时文,岁辛未,年已过七十,与汪泰瞻兄弟讲业于纳城之锄经处,泰瞻向留意《乡党》,欲多以《乡党》题文为课艺。……以太史公择言尤雅之意名为《择雅集》。……此集不唯《乡党》文之开山,亦经学之指南。〔6〕
《礼经》即《仪礼》,儒家《六经》之一,为上古贵族礼仪的汇编,涉及冠、婚、丧、祭、朝、聘、飨、射等各个方面,汉唐以来的经学家都试图从中探索远古的史影。然而宋代以后,对《仪礼》的解读逐渐走向理学化,取代了传统的经注模式,虽然有朱熹等人的呼吁,但是元明时期注定成为绝响。江永则认为《择雅》不仅首开《乡党》时文之先,而且具有经学指南的现实关怀。值得指出的是,书名虽然取为“择雅”,但并不是指时文的文章之雅,而是指时文的经学之雅。如江永《乡党》第四章“过位色勃如也”时文,评云:“典雅深醇,拔之以励经学。”赵丹《乡党》第五章“享礼”时文,江永评云:“禀经酌雅,自异俗嚣。”徐士林《乡党》第五章“私觌”时文,江永评云:“原本不尽与《礼经》合,加删润亦可达雅构。”又如赵泉《乡党》第十四章“乡人傩”时文,江永评云:“取经籍之菁华,而去其糟粕,若直写《月令》《周官》,同小胥之抄矣。原评谓足当雅字之目,信然。”再如江永《乡党》第二十五章“有盛馔”时文,评云:“用经籍处,风雅绝伦。”江永在编撰《择雅》自拟的凡例中,进一步彰显了《择雅》这种经学之雅的品格,现摘录如下:
一、《乡党》文向无专选,是集独创题文,欲充备题,适得三百有奇。
二、《乡党》多制度名物,文须典核无纰缪为贵。明文可采者无几,概从姑舍。
三、其疏题举典之皆切确,又无他文可易者,乃登之。
四、填砌痴肥,空滑甜俗,及制度疏舛、解义未的者,不入选。
五、考经籍,自是平时工夫,时文用经,自有剪裁点化。
六、《乡党》制度解说,多沿误处。凡此,皆详为考订,不敢曲徇。
上述撰写《择雅》的六点凡例,与当时以考据为导向的经学研究正可谓异曲同工,所以《择雅》甫出,便赢得学术界的一片掌声,被誉为可与历史上的郑玄等经学大师相比肩,即所谓“读其文,经籍贯穿,考据精核,一字不苟,且时文疏谬处,辨讹定解,胸有卓识,可挽颓波,诸制度题,皆堪羽经翼传,质诸康成、贾、孔而无疑”。〔7〕当时名儒姚鼐也赞其书的经学价值:“江慎修先生以诸生说《论语·乡党》篇,尤多于古制不明,乃作《乡党图考》,又录前人《乡党》题文,颇辨论其是非,其有题而文无足录者,乃自撰之,合三百余篇。《乡党图考》昔已梓行,乾隆五十一年,朱石君侍郎典试江南,以‘过位’章命题,士有达于江氏说者,乃裒录焉。独其《乡党》文存于里中,郁而未发。今其里吴君石湖乃雕板以传,用科举之体,达经学之原,士必有因是而兴者,余窃乐而望焉。”〔8〕由此可见,从“经学指南”到“经学之原”这一经学意义上的置换,可以说,《择雅》是江永假借时文的文体而编撰的经学专题论文集。
《择雅》系江永弟子汪世望的手写抄本,分正编、补编两部分,各一卷,正编卷首载有程廷和的序、江永自序和该书的“发凡”,补编后附有汪世望的跋文一篇,详述他抄录《择雅》一书的缘由,现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右《乡党》题,总三百五十篇,吾师慎斋先生所精选评论,并为补选者也。先生之学,事事探讨本源,虽律历算数之幽,河洛图书之妙,音韵翻切之微,山川地理之赜,皆待考精思,各有心得,有撰著,自幼便研诸经,三礼之学尤深。诸家同异、是非之言,皆有剖析辩论。尝编《礼书纲目》九十卷,礼部特行文采取。辛酉崴,程栗也大史强之入都,时方纂修三礼,诸公邃经学者折节下问,先便自书数十纸,力辩后人解经之误,今其碎纸盈筐,录之可数卷也。戊辰岁,世望幸及先生之门而问业。今岁辛未,先生年已七十有一,世望禀家君命,再请至锄经处,朝夕受教,益心慕先生理学,欲多以《乡党》题为课艺,先生逢课,率以《乡党》命题。《乡党》文从无专选,强先生为之,先生既诺,时方酷暑,挥汗成雨,评之,改之,仍日拈题两三首,三月余而集成,世望疲于抄录校对,而先生不以为劳也。先生素谈于声华,不欲以时文鸣,为学徒拟课之作,不下二千篇,皆不留稿。今于是集二百数十首,世望不欲私为枕秘,将付坊梓公诸世。盖先生之学,以经为本,时文其枝叶耳。今其文具在,观此自知其为本深末茂,不待世望喋喋。既略知先生素履于编目,后稍道其一二以为跋云。受业汪世望谨识。
现存《择雅》正编收录江永自作《乡党》时文216篇,补编收录当时著名学者130余人的《乡党》时文138篇,其中便有大名鼎鼎如任启运、褚寅亮、杭世骏、何焯等清代著名经学家的作品。正、补二编共计时文354篇,分别见于《乡党》的二十七章之中。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列表如下,以清眉目:

表1
从上表所列《择雅》所选《乡党》各章所作篇数而言,其中第3章的“君召使摈”、第4章的“入公门”、第6章的“君子不以绀饰”和第8章“食不厌精”等时文,远远超出了《乡党》其他的各个章节,这也是正编与补编共同的特征,而《择雅》所选的这些时文,恰恰提供的正是古代典籍中待人接物、日常行为举止的礼仪与饮食礼仪的经学话语。
二、《择雅》的经学话语
《择雅》收录的时文,与以往为科举考试的时文相比较,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它不受官方所严格规定时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的模式限制,写法不拘一格,用词高古,突出作者经学话语的特色,即所谓“选近今文,浓淡奇平,不拘一律,唯择其尤雅且生新者为鹄”,〔9〕“时文亦不必拘一律”,〔10〕从而呈现出考据精深、羽翼注疏、考辨纠谬等经学话语的特征。
(一)考据精深
考据精深,是《择雅》经学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考据,指研究历史、语言等的一种方法。通过考核事实和归纳例证,提供可信材料,从而作出结论。《择雅》正编录有江永《乡党》第六章“君子不以绀饰”时文19篇,补编为11篇,反复考证了古代的服饰礼仪。其中江永的“缁衣羔裘”三句最具代表性:
诸侯以天子之冠弁服视朝,其衣类玄端,其色缁则其裘以羔,而臣亦视之,所谓羔羊退食者也。大夫又服朝服以祭,夫子以当临祭也,则亦羔。夫朝宜裼也,祭宜袭也,皆必有衣也。虽羔裘而饰豹褎,其色同者犹裼缁,既犹是羔也。则缁衣以裼之。
以天子之皮弁服视朔,其衣如素积,其色素则其裘以麑,而臣亦如之,所谓麑裘而韠者也。诸侯又以皮弁服受聘享,夫子如当出聘也,则亦麑。夫视朔宜裼也,执圭宜袭也,皆必有衣。惟麛裘而青豻,其色杂者宜裼绞,若犹是麑也,则素衣以裼之。
若夫狐裘,有白、有青、有黄、衣狐白而裼锦衣者,诸侯也,夫子不敢也;衣狐青而裼元绡衣者,冕服裘也,夫子不必备也。惟若狐裘黄黄者,用之腊先祖五祀,以其上服用黄衣、黄冠故也。如其与蜡宾乎,皮弁素服以祭,犹是素衣麑裘,若既蜡而息,岂可违乎黄冠草服之义,而别有他色以裼狐黄哉?
该时文出自《论语·乡党》第六章:“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意思是用紫羔制的皮衣,古时象征诸侯、卿、大夫地位不同颜色的朝服。刘宝楠《论语正义》引郑玄注云:“‘缁衣羔裘,诸侯视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经传凡言羔裘,皆谓黑裘,若今称紫羔矣。”朱熹《论语集注》:“缁,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黄。衣以裼裘,欲其相称。”可见,朱熹的解释比较简略,而江永此文则在郑注的基础上作了一番考证,内容翔实,语言生动,深入浅出,说理缜密,平正通达,无丝毫晦涩之感,读之流畅自然,别开生面,体现了以考据为时文的特色,所以该文被评为“似此考据详晰,方于各经语相通”。〔11〕在江永看来,撰写时文犹如研究经学,而经学中的典章制度往往需要考证,然后才能准确揭示其中所具有的真实含义。他在该篇时文的自记中说:“三裘三衣,时文家既不明裼袭之制,又不详考所用之事,且忘裼衣外有朝祭上服,此上服又有天子诸侯之差及君臣同异之辨,辄向颜色黑白上穿凿解义,臆说流传,未有能辨正者,经义于是荒矣。”〔12〕无独有偶,当时精于《仪礼》之学的任启运也作有“黄衣狐裘”时文,但是该文因疏略考据而未入《择雅》补编中。江永在《乡党》补编吴岳的“黄衣狐裘”时文后评云:“《注》云裼主于有文饰之事,然则燕居之狐裘,外但股深衣,不以黄衣为裼矣。任钓台当暑两节文,发黄衣句云:‘息民如是,燕居之股亦如是。’既侵狐狢句,又不思然居无裼裘之义,故其文不入选,恐相沿误,附识于此。”〔13〕可见《择雅》衡文标准不以文名高下,仍以考据为首位,所以清人梁章钜说:“名文之不讲考据类如是,不必徒震其名也。”〔14〕这也真实地映现了当时学者对时文的基本认识。江永又有“趋进”时文:
圣人之相礼,有趋进之时焉。盖相礼者必进,进则当趋,非夫子岂易言中度耶?日者君有召命,以摈事重委吾子。若曰门外传辞,子承摈也,则循序以立,庙中相礼,子上相也,则当事以趋。〔15〕
此文出自《论语·乡党》第三章:“趋进,翼如也。”意思是快步向前时,好像鸟儿舒展开了翅膀。朱熹《论语集注》云:“疾趋而进,张拱端好,如鸟舒翼。”考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言端好。”邢昺《论语注疏》:“趋进翼如也者,谓疾趋而进,张拱端好,如鸟之张翼也。”显然,朱熹是根据邢昺《论语注疏》而作出的解释。当时时文名家如王步青、方朴山、任启运等人对此都没有合理的言说,甚至牵强附会。而江永对“趋进”的解释,则与他在《群经补疏》的疏解“趋进”如出一辙。为了证明自己所理解的不诬,同时他在《乡党图考》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证:
趋进,翼如也。注疏皆不言在何时,以《仪礼》考之,庙中相礼时也。庙中相礼,上摈之事卿为之,夫子大夫也,而相礼摄相也。夹谷之会,孔子摄相,此亦重其知礼而使摄,故特记君召使摈,此趋进及宾退复命曰宾不顾,皆上摈相礼之事,一记其容,一记其辞也。凡发足向前为进,俗解不知趋进之义,谓入门时摈者趋入有事。君迎宾入门,与宾雁行,摈、介皆随后雁行,及庙上相先入,此时安得有趋?趋则在君前矣。且经传未有以入门为进门者,故必详言之以正其谬。
事实上,这些考证文字,同样来自江永的“趋进”时文内容(文长不俱录)。如果我们再追溯其渊源,那么江永则是以《仪礼·公食大夫礼》的“摈者进”三字来诠释“趋进”之义的。如在《择雅》补编中亦收录了徽州学者汪梧凤的同名时文,文义一如江文,文末评云:“考之《聘礼》,趋进为中庭相礼之时,非入门时也。入门时摈介随主宾后,入庙门,每门止一相,安得有趋?且发足进前为进,经传从未有以入门为进门者,今经生家谁能见及。”〔16〕江永评云:“俗解沿误,紫阳书院已据经订正,在湘在书院,固预闻其研经,亦自有心得,不从靠讲说也。”〔17〕又如浙江钱塘学者周绍洙的同名时文,也以《仪礼·公食大夫礼》解释“宾退”之义,江永评云:“经畲久荒,《仪礼》绝少寓目,注疏尤等弁髦。此经复命原由,《聘礼》注疏历历,有明数百年来,未经提出,知其详者,仅见斯文。志古之士,不肯汩没时俗,经学有复明之机,稍为删润,以成完璧。”〔18〕可以说,江永是从经学的角度来撰写时文,同时还从经学的角度来点评时文的优劣,甚至寄希望于时文来承担经学复兴的角色。
(二)羽翼注疏
羽翼注疏,是《择雅》经学话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所谓注疏,是指汉代至唐代期间,学者阅读儒家经典和古文献时所作的解释。这些解释往往有传、笺、章句、义疏、正义等名称,内容关乎经典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以注疏为时文,则大致包括注人、注物和注事等方面,包括释义(名)、增补、延伸、旁证、辨误、评点、凡例、综述、述论、参考等形式。注疏不仅起着释疑、补缺、续无、证有、广见、参错、明体、识要等作用,而且成为时文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择雅》补编录有吴县学者何焯“乡人傩”一节时文:
明乎傩之礼者,其敬又行于乡矣。夫乡人但相与傩耳。其礼则惟夫子明之,所以阼阶之上,必朝服以致敬哉。且昔者周礼在鲁,犹有先王之风,孔子闲居,莫非盛德之至,岂惟必谨于大饮,而亦不忽于大傩也。无傩何自起哉?古之制礼者,知一寒一暑,过则为灾,有鬼有物,凭而生疠,故毕春达秋,以时磔攘其害气,岁且更始。俾民呵禁其不祥,固必命之有司,亦得用乡人也。独自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饮之为乐,犹有若狂者矣。况若方相所帅,百隶所殴,傩之相沿,得毋近戏也。〔19〕
此文出自《论语·乡党》第十四章:“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意思是乡里人举行迎神驱疫仪式时,孔子穿着朝服站在东边的台阶上。朱熹《论语集注》:“傩,所以逐疫,《周礼》方相氏掌之。阼阶,东阶也。傩虽古礼而近于戏,亦必朝服而临之者。”何文则从历史渊源的角度详加讨论,并且以《仪礼·郊特性》孔注“恐惊先祖”结合邢疏“此明孔子存室神之礼”解释。何焯在该篇时文的自记中说:“《郊特牲》篇云:‘乡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则注中后一说,亦礼家相传之义,故兼用之。”江永评云“抒义正大,可翼经疏”。这显然是采用了古人注疏对此作出的解释。值得指出的是,戴震亦有“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时文,其一节云:
诚敬接于乡人,即一傩而见礼仪之尽焉。夫夫子以诚敬与乡人接,讵傩也而或忽诸?立于阼阶,正其礼也;必朝服,谨其仪也。且礼之行于乡,皆王道所乐与乡之人共之也。由是相习而成俗于乡,正圣人与乡之人将之者也。故事属典礼之微,久矣为众之所忽,而圣人当之,俨然德盛礼恭之至著焉。何言之?圣诚而已矣。以圣人而与乡人接,傩亦其一端也。凡出于先王之制,则礼虽细亦巨。而率百隶而时傩,掌于方相氏,故不得谓黄金四目,执戈扬盾之象,徒以狂夫为之而遂置之不足数。〔20〕
不难发现,戴震是从经学注疏的角度来解释“乡人傩”的,近似何焯的解释,所以被评云:“直写胸中所见,竟似汉人经疏,若论制艺体裁,原应如此。惜难为帖括者道也。”
此外,《择雅》补编录有江苏无锡学者蔡德晋“执圭”时文:
聘莫重于圭,可以观圣人之执之和。夫聘之用圭,礼之至重者也。夫子执之,宁不足以观礼哉?且先王以六瑞等邦国,以六挚等群臣,故人臣惟挚挚观国圭,则君执圭礼也,乃臣为其君聘问,必有执以通信,则以人臣执器,圣人尢竟竟焉。
此文出自《乡党》第五章:“执圭,鞠躬如也。”意思是孔子出使别的诸侯国,拿着圭(礼器)表示恭敬谨慎的样子。朱熹《集注》:“圭,诸侯命圭。聘问邻国,则使大夫执以通信。”考《周礼·大宗伯》:“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榖圭,男执蒲璧。”江永评云:“包咸注言执君之圭,邢昺疏遂引桓、躬等圭。《集注》言命圭,亦承其误。朱子晚年修礼书,引瑑圭、贾疏入《聘礼》,则亦知此圭非命圭,但《集注》未用追改耳。先儒有失检处,赖后人弥缝,何时人犹呶呶于桓、躬不置耶?此文出,可补正注疏,不惟淹贯《聘礼》,余沥可沾丐后人已也。”〔21〕
再如,《补编》录有姚张深“享礼有容色”二节时文:
于执圭后观圣人,敬者转而和矣。盖享礼私觌,所以达情也。和亦有渐深焉。可徒以敬观圣人哉?考之《聘礼》方执圭时,宾与群皆袭其后乃裼焉。质文异尚也。夫尚质则以敬为先,尚文则以和为贵,而和之中,又有不尽同者,非圣人能忠中礼乎?
此文同样出自《乡党》第五章:“享礼有容色。”意思是献礼物的时候,态度要诚恳和友好。朱熹《集注》:“享,献也。即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实,有容色,和也。《仪礼》曰:发气满容。”这显然是根据郑玄与孔颖达的解释,江永评云:“根据《礼经》,非甜俗一派可拟。”《补编》录有彭启豊同名时文二节,江永评云:“根据三礼,自出镕裁,故与钞胥迥异。”又录有赵丹同名时文,江永评云:“禀经酌雅,自异俗嚣。”这些时文不仅圆润了传统的经学注释,而且将《论语》从《四书》体系中剥离出来,重新置于传统经学系统中。
(三)考辨纠谬
甄别时文运用典制名物的正确与否,从而进行考辨纠谬,是江永《择雅》又一个重要的经学话语。江永认为:“学必穷经为根柢,如朝聘礼仪,原有三礼甚详,时文家稍涉猎皮毛,犹不免疏谬,况未经寓目者乎?”〔22〕如《补编》录有江苏苏州学者汪份“入公门”一章时文,其首节云:
尝考鲁有三门,曰路门,曰雉门,而其最外者曰库门,其制拟于天子之皋门者也。凡库门与雉门、路门皆可曰公门,而此志夫子入朝之始,则所谓说公门者盖库门也。夫此门也,不惟远于治朝之堂,抑且及外朝之位。
此文出自《乡党》第四章:“入公门,鞠躬如也。”孔子走进朝廷的大门,显得谨慎而恭敬的样子。朱熹《论语集注》对“公门”没有解释,仅说:“公门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汪文中所谓的“路门”,指古代宫室最里层的正门。《周礼·考工记·匠人》:“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郑玄注:“路门者,大寝之门。”贾公彦疏:“路门以近路寝,故特小为之。”所谓“雉门”,指古代诸侯之宫门,一说天子之宫门。《礼记·明堂位》:“雉门,天子应门。”孙希旦《集解》引刘敞曰:“此经有五门之名,而无五门之实。以《诗》《书》《礼》《春秋》考之,天子有皋、应、毕,无库﹑雉﹑路;诸侯有库、雉、路,无皋、应、毕。天子三门,诸侯三门,门同而名不同……《明堂位》所言,盖鲁用王礼,故门制同王门,而名不同也。”《周礼·天官·阍人》:“阍人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郑玄注引汉郑司农曰:“王有五门,外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可见,雉门泛指皇宫之门,或指代朝廷。所谓“库门”,有三种解释:一是古传天子宫室有五门,库门是其最外之门;二是为诸侯宫外三门之一;三是仓库之门。事实上,古称国君之外门为“公门”。孔颖达《论语正义》:“公门者,有雉门,有路门。皋门,天子外门;库门,诸侯外门;应门,天子中门;雉门,诸侯中门。异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考《礼记·曲礼上》:“国君下齐牛,式宗庙,大夫士下公门,式路马,乘路马,必朝服。”《春秋穀梁传》庄公元年:“秋,筑王姬之馆于外。筑,礼也;于外,非礼也。筑之为礼,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门出。”汪氏此文一出,即受到考据名家阎若璩的青睐,一时传为佳话,所谓“此文出,此说行,朝位堂制度皆纷紊,举世靡然从之,鲜不纰缪者”。〔23〕对此,江永“历举经传注疏,疏通证明”作了一篇近一千五百余字的评说,纠正了汪文中种种与经典原意相悖的描述,相当于一篇质量上乘的经学专题论文,后来全文被录入《乡党图考》之中。
又如《补编》录有江苏溧阳学者陈人文“宾退”一节时文,江永作了近五百五十余字的长评,强调经学对于时文的重要性。如文中所云“经传未有以入门为进门者”“《聘礼》郑注甚明”“《聘礼》注疏甚明,讲章、时文家皆不考”“经学之荒久矣”等等。这些时文都经过江永的改写才录入《补编》中,梁章钜说“此文今入《乡党文选》,已经慎修先生删改大半矣”,〔24〕是有历史根据的。
三、《择雅》的学术生态
江永《择雅》所彰显的上述三个经学话语特征,源自清代康乾时期特定的学术生态。
首先,自康乾以来的基本国策,由崇尚程朱理学逐渐回归汉唐经学。学者的经学信仰发生了变化,尊经复古、穷经读书成为读书人的优先选项,时文的撰写也因此走出专尊《四书》与迷信朱熹《四章句集注》的传统,不少学者从经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时文的经学渊源,认为时文就是经学。如康熙时被誉为“清真雅正”时文典范的苏州状元韩菼说:“予尝论科举文字须通汉唐诸儒注疏,而折中于朱子,则士知论学而经义弗坠。”〔25〕时文名家王步青指出:“夫经以传道,制义以传经”。〔26〕学者韩梦周也指出:“制义之文,所以解经也,……盖汉唐注疏之支流余裔也。”“制义所以解经也,原本于注疏。”〔27〕彭绍升也指出:“制义者,注疏之一体,用以宣畅经旨,发挥道业而已。”〔28〕戴震说:“精心于制义一事,又不若精心于一经,其功力同也。”〔29〕阮元说:“时文即古文,古文即经解。”〔30〕事实上,视时文源于注疏、经解的见解,并非清人的创见,早在明代就有学者提出,但是未能成为学界的共识。如晚明时文名家茅坤就认为:“举业一脉,即说经也,历代圣贤所自见处,小大深浅不同,而学者即其言而疏之为文,亦当按其小大深浅之旨,而各为支流而分析之。”〔31〕由此可知,时文中阐发的经义与诠释儒家经典的注疏是一致的,是经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都是为了准确地诠释经典。
其次,《择雅》的编撰,正值清代乾隆时期,经学研究强调“实事求是”,形成了“博瞻贯通”“无征不信”的考据学风。这种学风偏重于经典的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等研究,治学方法是详细占有材料,注重证据,再由归纳例证中得出结论。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赞道:“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术界势力……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所构成。”〔32〕考据学成为当时学者经学研究与进入仕途最为倾心的选项。如乾隆十年(1745)11月颁谕,责成九卿、督抚举潜心经学的纯朴淹通之土。又曾经召见吴鼎、梁锡屿面谕云:“汝等以经学保举,朕所以用汝等去教人。大学士、九卿公保汝等,是汝等绩学所致,不是他途幸进。”著名汉学家惠栋也以“博通经史,学有渊源”,为两江总督黄廷桂、陕甘总督尹继善列名荐牍。戴震首以布衣入翰林,一时上自名公巨儒,下逮博士学究,无不以考订经籍为己任。经学成为衡量能否进入仕途的主要评判标准。昭链说:“今日自朱石君讲论古学,时文中试者,多填硕经典为贵,文体为之一变。”〔33〕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江南乡试,即以《乡党》“过位”二节为试题,阮元取用了江永“过位”时文中的考据成果,得中乡试第八名举人。诚如钱大昕所说,“江南乡试,以《乡党》篇命题,士子主先生(江永)说皆得中式,由是海内益重其学”。〔34〕嘉庆陕西周至学者路德说:“时艺之遵朱注,功令也,而《乡党》文则不然,《乡党》一篇,大而朝庙宫廷,细而饮食衣服,无一事不资考据,而朱注阙如,非朱注之疏也。汉唐笺传注疏,多考证制度名物,宋儒则专言义理,发圣学之根本。若制度名物,则传注具在,学者可自考之,又何尝谓不必考据哉?考据不确,则题解不明,虽名手无从下笔。近日海内能文之士拈《乡党》题多宗他说,衡文者未尝以功令绳之,势不得不然也。”〔35〕所谓“题多宗他说”,即时文已不再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为唯一选择,所谓“势不得不然”,即指当时以经学为时文已是学界的共识。由此可见,《择雅》不仅仅是一种科举之体的象征,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探索经学之原的经学话语。
四、结 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择雅》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首先,《择雅》所录时文,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时文选本,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经学著作,更不是专门诠释经典的读本,与宋元明以来的经学注疏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然而就其中的具体内容而言,则是通过时文的体用排偶、反复铺陈、正反论说等长于说理的特点移用于解释与阐明经典,在继承传统经学遗产的过程中,不仅更多的是发展了一种成为真正圣人代言人角色的自我感觉,而且为研究传统经学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同时也延续了时文自身的学术生命,即所谓的“说经之家广为训诂,即有卓越之见,世恒束阁不观,莫若就人人共业之文,发挥搜剔,使圣贤未泯之蕴,儒先未启之局,如岭云山月,探之不穷,岂不于经传为有功,世道人心为有益,而制义将自兹不废”。〔36〕将经学话语融入时文写作,既是对时代学术思潮的积极回应,又为我们当下把握与诠释经典提供了指导价值和借鉴途径。
其次,《择雅》所录时文,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以文献为依据的注经、解经与释经而获取意义的经典诠释传统,事实上已具有融和汉学与宋学的诉求。清人翁方纲说:“愚尝谓往日言时文者,不甚留意于注疏,恒伤固陋,而近日稍知看注疏者,又高谈汉学,喜驳宋儒,此学者之大患也。”〔37〕路德说:“汉学宋学悉为体讲,不事偏倚攻诋、标榜坿托,讲论文艺以经训传注为宗,力挽剽窃空疏之习,备见传刻各文批评论着,谓自有制艺以来,无其精审。”〔38〕这表明时文不再受限于宋明理学的羁绊,预示儒家重视知识的传统再次复活。换言之,时文不仅反作用于经学,而且也是对经学的反哺,可谓源流同贯,孳乳相生。诚如清人冉觐祖所说,“高明之人,多厌时艺为无用而欲废之者。余谓今之人无不读经书者,率以为时艺之资耳,不为时艺则不读经书矣。是知时艺为经书之饩羊也,顾可废哉?”〔39〕从而为我们今天的经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非主流的经学文本题材。
最后,《择雅》所录时文的作者,往往具有时文名家兼经学大师的双重身份,他们虽然身侧“举业”之林,但是心游“举业”之外,致力于儒家经典的研究,所以他们所撰写的时文,也融入了对经学的现代思考与理解,从而衍生出一种有别于传注疏笺为主体的传统经学研究模式,但是其表现出来的经学信仰和价值取向仍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其说是对宋元明以来科举时文的传承,还不如说是对传统经学的一种回应与挑战。一方面,把当下的时文与传统经学结合起来,使其不脱离传统经学,成为传统经学发展线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新的支点;另一方面,也使传统经学逐渐摆脱语言训释与义理阐发的局限,使时文由纯粹的文学作品转变为经学创作,而且淡化“代圣贤立言”的立场而成为经学专论,圆润了传统的经学注释,推动了经学的顺畅传播,拓展了新的经学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