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宏:走入现实的复杂,测量法治的真实水位
吴俊燊 欧阳诗蕾

赵宏: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德国公法、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国家学、个人信息权的公法保护等。
2023年冬天,北京的氣温罕见地降至零下十几度,干冷萧索。年末的一个上午,我给学者赵宏带了一本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的小说集,书里升腾着赤道南国的溽热鲜活。法学教授赵宏一直喜欢文学,她认为法学与文学的使命是一样的——“把光打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上。”
读完黎紫书的《流俗地》,这位法学教授时常想,到底是谁性侵了主人公银霞?
几年前,赵宏在同学、好友罗翔的建议下开始了普法专栏写作。后者是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因法学公开课成为明星学者,在他助推下,大众对刑法的兴趣也越来越大。赵宏在中国政法大学担任行政法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德国公法、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国家学、个人信息权的公法保护等。
过去近20年,赵宏一直做着宪法与行政法,尤其是德国公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德国法有着严谨缜密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架构。对她而言,学习并研究法律,一度是为了追求纯粹的智识的完美。
在当下,时间以惊人的密度呈现着现实的复杂,互联网媒介让源源不断的社会事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江歌案,高铁掌掴案,穿和服拍照为何涉嫌寻衅滋事,写色情小说到底是什么自由……在热议的背后,公众时常面对两难的局面——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习得的朴素法感、道德、正义与良善,与法律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讲解具体事件中的法律,让法律条文抵达普通人可感的生活,是赵宏如今在做的工作。对现在的她来说,法律并非“智力的游戏”,而是不断搭建并说出的共识。
2023年9月,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公开期间,赵宏多次参与讨论,始终凝视着行政法关注的核心——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这份凝视也贯穿了她在11月出版的新书《权力的边界》。
罗翔在序言中写道,“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是公法学者看待问题的基本视角。”对某些法治失序的乱象,赵宏在文章中展现了“正直的愤怒”,罗翔觉得这是西北成长经历赋予她的价值与情感的底色。而面对舆情复杂的重大热点案件时,她依然勇敢发出自己清醒的专业意见,罗翔认为,正是“这种看似孤独的意见捍卫了她所从事专业的学术尊严”。
有段时间,罗翔的状态并不好,自视已经看透学术界的“浮华不堪”,消极地拒绝一切学术写作和学术会议。是赵宏告诉他,“看得太重与看得太淡其实都是看不开的一种体现”,“愤世嫉俗很大程度上只是求而不得的自欺而已。”在这位“少有的理想主义者”的鼓励下,罗翔慢慢走出学术虚无的犬儒心态,开始认真地从事学术写作,而几乎每一篇学术文章的写作他都会首先听取赵宏的建议。
鸡蛋,还是高墙?这个由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写出的著名隐喻,也伴随着赵宏的学术研究及实践。文学家通过书写故事,让普通人的灵魂得以显影,她认为,法律人凭借严密的规范来划清公权力的界限,将其约束于法治框架内,从而“护住每个个体的尊严”。
写专栏之前,我比较沉迷于抽象的东西。德国法的概念、逻辑体系都很严整,这让我觉得有意思,因为我在追求智识完美。而写评论的过程中,我要尽可能搜集与这个普通人相关的资料,会看到自己原来在课堂谈到的很多法律,其实直接关系到具体的个人。进而发现自己之前的很多文章实际上跟现实生活没有对接。
我现在觉得,研究现实中那些没有经过裁判剪裁的案子,远比翻译德国的联邦法院判例有意思。当看到那些真实的、没有经过法院剪裁的案子时,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到,法律如何影响一个具体的人的命运,这个影响可能是你在法学院讨论那些案例时完全想象不到的。
人:比如“天一案”,你说是第一次通过写作跟他人产生真正的情感连接,这是怎么产生的?
对,“天一案”我感触很深。这个案子就是一个小姑娘写了本色情小说就获刑10年,这怎么看都与一般公众的朴素法感不符,而且背后还有很多法律问题。这在德国法领域也讨论过,如果这种色情小说是大众不能够接受的,那么还是不是艺术自由?艺术由谁认定?是大众还是少数人?当艺术自由和青少年保护之间存在冲突时,要不要以抹杀艺术自由的方式,甚至是通过让个体承受巨大的刑事代价的方式,来实现一个单一的价值?
在她身上,你完全能够看到法律对于个人命运的影响。
写专栏的时候,我看新闻的状态肯定与平时随便看不一样,平时刷一遍就过去了,大概在脑子里停留3分钟。但写专栏会看很多遍视频,来抓住细节,讲清楚案件背后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内心的震荡会停留很长时间。
写完一篇专栏,邮箱里就会有很多人来信,告诉我他们有同样的问题,比如他嫖了娼、吸了毒,他们出于信任告诉我他们的故事。我首先不会用道德审判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人,我会尝试去理解他,他所遭遇的事情可能是很多普通人都会遭遇的。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是道德完美的,所以会有这种共情。写普法专栏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它要求我把自己的论文真正地写在这片大地上。
相比于刑法,我觉得行政法跟普通大众更密切相关。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遭遇不到刑法,但每天都要和行政机关打交道。比如我作为小商小贩,我和市场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我要在小区种棵树,又要和林业部门打交道。但从法学专业上说,行政法和刑法都属于公法,都要强调防御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侵害以及国家对个人权利的积极保护。刑法要控制国家随便对个人施加刑罚的惩罚权,行政法也一样,要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探讨怎样约束国家权力,让它不至于随意膨胀。
如果国家权力没有受到约束,或者法治观念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我们每个人都会生活在危险和恐惧之中。因为你没有办法确认自己是否违法、是否犯罪。如果这个事情不能通过非常明确、稳定的法律来规定,而是进入一种不可知的过程当中的话,每个人都会面临权力不断膨胀的处境。

赵宏( 右) 与罗翔( 中)、陈碧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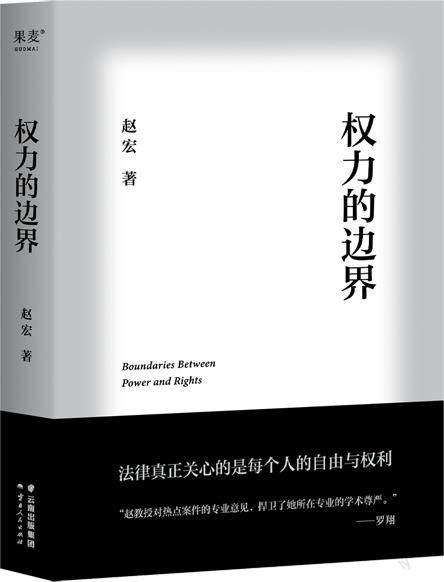
这是法学里最朴素的对国家与个人关系的概括。它很明白地表达了法治的一个基本观念。因为法治不只是约束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而且也约束国家的权力,这是法治最重要的一个面向。
所以我在生活中遇到很多与行政法有关的事情时,首先会追问,你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拿不出依据的话,那你就不能处罚。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朴素的真理,但朴素的真理仍旧需要不断地传达。我希望大家知道你是有这个自由的,而且对我們普通人来说,你较真也许这个事就解决了。
人:个体面对复杂的国家机器要怎么“较真”?
我觉得不复杂。其实是很朴素的两个层面:第一,在形式法治的层面,政府机关做的任何事情是否有法律依据?第二,在实质法治的层面,法律依据本身是否能够做出这样的解释和执行?
比如,那个拥抱梅西的少年要不要被拘留,虽然看起来这个案子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但剖析下来无非几个层面:第一,《治安管理处罚法》有没有规定?有。那么,这规定是否能够被这样解释?但从现场来看,少年是在比赛间歇冲入球场,并未干扰比赛的正常进行,更没有影响到球员踢球或是射门。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一个冲入赛场只是为拥抱偶像的少年直接施以最重的处罚,有违《行政处罚法》的过罚相当原则。公安机关可以选择警告、罚款这类更轻的处罚方式。那为什么还要对他进行拘留?无非是考虑到社会影响,也就是想要在法律上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这是要非常谨慎的。
“杀鸡儆猴”的背后有很大的逻辑问题:你怎么就认为大众没有判断能力呢?说回梅西少年这个案件,我觉得拘留这个少年没有达到真正的目的。要维持比赛秩序,就应该加派安保。
有人说,加派安保还是管不住,难道就认命了吗?对,就只能认了。因为法律是有限的,就像刑法制定得再严厉,也无法避免有人要杀人、要抢劫、要盗窃,难道要通过严刑峻法的方式杜绝吗?这种“杀鸡儆猴”的思维在法律中,其实是不承认、也不尊重每个人有独立判断能力。
法律应当允许多样化,有的人积极上进,有的人就是想躺平,从法律上来说,你也得支持别人躺平的自由,你不能说都给我爬起来,对吧?法律就是一个底线的保护,不是一个道德宣传的机制。或者说,法律就是给你提供一个最低底线,保障你各种选择的自由。
在法律上讲,个人是实现幸福的最大主体。如果我们把个人幸福的实现都寄托在国家身上,就意味着要把所有的权利都拱手相让。
而且在风险社会,每个人都要接受一定的风险。你不能要求,把这个风险降到0。当你把它降到0的时候,就意味着要求所有人配合,你的自由就会压缩到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我觉得这对普通人来说是没有办法容忍的。
这其实是我们在宪法课上跟大家讲的一个基本道理,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依存关系,国家就是手段,它不是目的,个人才是每个人的目的,而且国家的目的也是保证每个人成为独立的自己。我觉得,国家认同感的核心应该是,在这个共同体之下,我的权利、自主性能够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它肯定要符合道德,符合公众的一般期待,但反过来,你不能把法律变成道德的推行工具,法律也不能把每个人的道德都拔得很高。
例如最典型的李云迪嫖娼案,他无疑是在道德上有亏,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规定了与他的嫖娼行为相匹配的惩罚了。他又没有犯罪,接下来却还要被终身禁业。他是一个世界级的钢琴家,而且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投入了无限的时间。当通过终身禁业这种法律惩罚的方式,去推行一种在道德上要求所有人达到高标准,那后果便是,不仅对他个人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而且对公众来说,我感觉就是法律对个人要求太高,个人做不到。
每个人都不是道德完人,我们学法律的人其实最明白这个问题,人性有阴暗面是人类的常态。我有自私、虚无的一面,我也有软弱的时候,难道不能接受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人吗?把每个人都塑造成道德完人,这不是法律的目的。所以我会说,很多时候道德不能直接进入法律。
而说到江歌案的判决,这个判决当然是大快人心的,但判决中使用了大量的道德要素。把大量的道德要素引入判案,就相当于道德毫无障碍地进入法律中了,那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界限会变得模糊。道德本身是主观化的,我的道德不一定与你的道德相匹配。当道德进入法律,它就冲垮了法律本身的清晰度和可预见性,会给恣意执法带来很大空间。
同时,我认为它也会造成整个社会的虚伪,每个人都不敢流露出自己真实的一面。老师得扮演德艺双馨的老师,学生也得扮演勤奋好学的孩子。

赵宏与好友合影,从左往右依次为李红勃、赵宏、陈碧和罗翔,四人均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图/受访者提供
既然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那么如果它连最低限度的道德都达不到,肯定是有问题的。比如纳粹德国就很典型,制定的法律就是为了牺牲少数人(犹太人),抹杀少数人的生命或者限制部分人的自由,这就是连最低限度的道德都达不到。
还有一种情况,比如法律对罪犯子女的歧视。凭什么我父母是犯罪人员,我就不能考公?再比如违法记录的问题,要考虑一个人犯了多大程度的错,才要终身为此承受巨大的代价。
中国每年被治安管理处罚的人数在800万左右,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而800万人中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要被拘留的,所以在这些人当中,有多少人有违法记录呢?这个会成为终身的污点。我觉得一般人都是接受不了的。那只能是不断推进法律本身的改革。
首先尽量全面地去看事情。每个人都容易活在自己的偏见中,要多听听其他的意见。然后,每一个人都应当意识到作为一个普通权利主体,自己手中权利的珍贵和重要性,我觉得这点太重要了。
学法律不能变成知识的游戏。我觉得很多时候,学法律的人走到后面会越来越觉得自己这个专业是很有专业门槛的东西,就会变成一个智力游戏。然后,大家写出来的论文也变成看谁的概念玩得更轻巧,或者看谁的逻辑更精妙。
在这两年接触到法学院的学生,我也会感觉到他们身上的冷漠感,倒不是说对这些孩子有苛求,我非常理解,处在极大的不确定当中,每个人都想获得确定和安全感。但反过来,这也造成了很多学法律的学生对他人生活的冷漠。以前在课堂上,我发现同学们眼里有光,但最近这几年你就会发现他们更看重能不能保研,能不能获得好的分数。
这实际上丧失了一个学法律的人首先应该有的共情和责任感。其实在我看来,对于学法律,智商不重要。因为说白了,我们写东西要告诉老百姓一些常识问题,它不是高高在上的。
我觉得我们学法律的,要永远找准学科的基本定位是什么。比如说宪法或者行政法,它是与国家政治直接相关的,没有办法回避。但是反过来,这个学科本身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距离是要有的。一旦距离被消弭掉,学科就变成了政治生活的附庸。
为什么我在书里每篇文章都要探讨国家权力的边界,就是要回到这个学科最根本的问题:国家权力是有边界的,是不能随便介入个人生活的。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不会觉得我对这些事情要负责。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我会建立起一种责任感。我现在常跟学生讲,我说你们考入中国政法大学不要觉得自己特别骄傲。当你接受了好的教育,就要意识到你的责任。
我觉得不是达到个人成功就可以了,如果是这样,那学法律的目的其实并没有达到。你无非是通过学法律,成为了社会当中的强者。
但是,法律本就是要保护弱者的,而且强者也可能会有跌落的那一天。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当你越来越多地看到弱势群体和普通人的时候,那种责任感就会逐渐形成。
社会的变化、体系的调整并不会因个人的发声而改变,你要如何自处呢?持续写作、发声、“炒冷饭”,你会感到厌倦和挫败吗?
我完全承认自己的作用非常有限。当意识到自己作用有限時,就不会夸大自己的工作,但同时也不会觉得这个工作是没用的。很多人的想法可能是,我说了也没用,做这个事也没用,那就算了。但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也夸大了自己的作用。因为你似乎觉得这个国家会因为某句话而改变。
该做的事情在任何时代都要做。做完之后,结果当然不是由我决定的,但有时有些事的结果可能超出自己的想象,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我完全想不到会有那么多人关注。但当没有产生作用的时候,难道你就要躲到虚无中吗?我觉得,虚无其实是逃避或者冷漠的借口。
持续地写,我也没有觉得我就一定能改变。但是学了法律之后,这就是你的权力。知识本身是一种权力,但权力也意味着责任。比如我写专栏之后,会认识很多媒体朋友,那我相比其他老师,可能会有表达和传播上的优势。既然我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说?说也是责任。
有时候心情低落也是正常的,但低落之后,我不会说彻底躺平。我还要当老师,还要站在讲台上面对年轻人,我都躺平了,还怎么教学生,怎么教他们心怀法学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