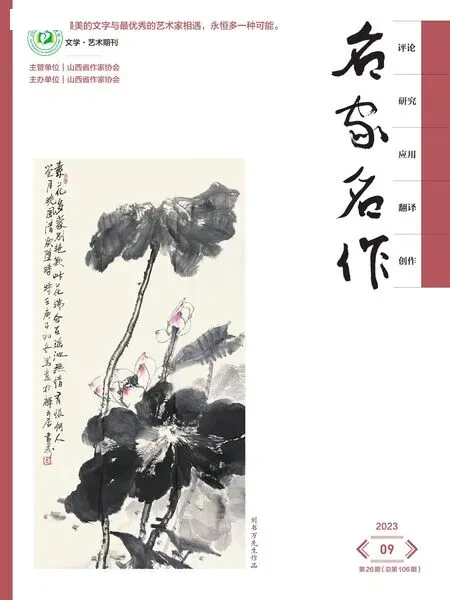从诗性空间到视觉空间:当代书法汉字异化的再认知
宋 涛
无论异化的汉字在书法现代构建中取得怎样的进步,其表达的都是一种革新的愿望,因为当代艺术在图像的冲击下,信息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而现代艺术的革新也在不断地加速。汉字异化在书法的构建中重新“定位”了汉字的建设性意义,不管是在构建中受到抵抗还是得到吸收,对于书法的建构都具有推动的意义。当异化的汉字在构建中接近一个临界值的时候,不管其异化是否有效,都会将构建带入一个方向,即使这个方向的有效性值得商榷,但依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书法作为一门传统的艺术,其内在的革新之一便是关于书法文化性格的重构。因为与文化的关系,书法在构建的过程中会遇到更大的阻力,但现代构建并不是要完全去除传统的文化性格,而是在构建中不断地调整与添加新元素,使传统艺术全方位、多角度地对接当下的构建。
一、作为“叛逆”的符号——异化汉字的“另一面”
现代构建的过程伴随着多重危机,现代主义的艺术话语虽然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但这也是现代艺术的弱点之一,其话语隐匿的破坏性很容易抹去艺术的边界,“书法主义”没有建立合法、有效的艺术话语便是其语言自身的破坏性没有得到合理的转译。传统书法除了对外在视觉特征的欣赏,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对诗词内容的审美感受,这种诗性美的欣赏方式在古典书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在现代书法的构建中,由于对视觉性的强调,这种平衡被打破,书法文字固然重要,但整体开始向视觉倾斜,在强调视觉性的时候,汉字构成特征的视觉性就会凸显,并将异化现象不断推进。如果说传统书法对诗词的欣赏构建了“思的空间”,那么现代构建便是力图建立更广阔的“视的空间”,虽然二者时刻关联,但是现代构建将书法的天平拉向了“视的空间”,充分说明书法对视觉的敏感性。威利·塞弗曾说:“19世纪是西方文化中最为视觉性的时期之一,他最关心精确观察的理念:小说家、画家、科学家都分享着一种作为观众观看到的景象,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诗人,他们是有‘洞见’的,虽然诗歌的视觉并不总是意味着观察。”[1]这说明西方艺术对视觉性的强调是多维度的,诗歌也不例外。现代书法对视觉性的强调也并不是完全否定传统范式,只是艺术家发现视觉性方面构建的多维度可能。汉字外形本身具有视觉性的特征,但是在当代,视觉性的一面显得更加突出。
人们围绕书法中汉字的异化展开了各种讨论,在不同的场景中,其实汉字的异化都相对模糊,无论图像还是符号,在不同的场景中都有不同的视觉表现,其实很难对异化做出精准的定位。德里达在讨论文字时说:“文字概念正在开始超越语言的范围,它不再表示一般语言的特殊形式、派生形式、附属形式,它不再表示表层,不再表示一种主要能指的不一致的复制品,不再表示能指的能指。”[2]这说明我们对文字的认知也体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对于汉字异化的谈论还是在表象上,主要的观点集中在是不是汉字的问题上,当我们将汉字符号转换成艺术语言符号的时候,这样的焦虑自然会减轻很多。其实书法中汉字的异化在现代构建中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艺术现代构建中,最大的特征便是多元化,这样的时代特征便要求艺术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能够吸纳当下的新元素,甚至是科技元素。而异化的含混性很难用一个精确的术语去定义。这说明异化本身是开放的,它不仅是元语言的开放,还是视觉构建的开放、认知结构的开放。异化汉字所拥有的“叛逆性”并不是要完全抛弃汉字的文化属性,而是探索一种对接当代的表现方式,从而实现书法的现代构建。
二、“重回当下”——异化汉字的再认知
书法中的汉字异化现象,其实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它将书法的中心视点从正统的书法史转译到具有边缘性质的书法作品上,让一些存在一定缺陷但有启蒙意义的书法进入创作的视野,有助于现代审美的构建。异化的汉字由于自我的解构,造成了释读上的困难,从而产生有效性的质疑。在异化汉字的构建中,其超越常态的外形在初期并没有形成有效的艺术语言,但并不能否定这样的实验性,它必须被完整地表现出来,因为异化的汉字是一种激进的变革力量。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放弃传统的评价标准,也不是绕开其合法性身份的追问,而是批判地参与构建的过程,寻求更加灵活、更加多样化的路径,寻找现代审美与语言表达的契合点,从而实现现代重构。如果现代构建意味着一种革新,那么异化的汉字便试图建立批判的话语,它所提出的问题意味着开放的制度和话语空间,具有更强的流动性与灵活性,以增强现代构建的可能。异化并不是书法现代构建的终点,相反,异化是书法现代构建的起点之一,是书法前卫的实验性探索。
在现代构建的过程中,书法还没有建立有效的理论框架来对应当下的视觉建构,因而传统的机制在对应当下新颖的视觉语言时很容易出现错位,从而质疑构建的有效性。如果汉字只是传达信息的媒介,那么看和听同样能够接收到信息,甚至在阅读的聆听过程中可忽略汉字的视觉性。当书法作为纯艺术创作进行讨论的时候,视觉特征成为书法最直接的外在因素,各种视觉的讨论都需要汉字造型的直接支撑,这也是当代书法强调视觉性的原因之一。当书法中的汉字从信息传达媒介转移到艺术表现语言上的时候,这个异化的“伪汉字”符号从信息传达的载体变为视觉传达的载体,因为当代视觉更新的速度极快,异化的汉字在形式构成上也出现了很多的变体,从墨法、笔法的改变带来的异化到线条构成的异化,书法中的汉字成为纯符号的表达。德里达认为:“解构不是拆借或者破坏,我不知道解构是否是某种东西,但如果它是某种东西,那它也是对于存在的一种思考,是对于形而上学的一种思考,因而表现为一种对存在的权威或本质的权威的讨论,而这样一种讨论或解释,不可能简单地是一种否定性的破坏。”[3]在德里达看来,这样的行为非但没有否定意味,反而具有强烈的建设意义。现代艺术在构建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将视觉从绘画中的三维视觉效应拉回到绘画本体中,让视觉重新发现色彩、线条、物质材料的美感。书法虽然不需要三维空间的认知,但汉字传达的意义能将认知带到诗性的境界,从而转入诗性的欣赏。在书法的现代构建中,异化的汉字就是将认知从诗性审美转移到汉字本身的造型上,通过线条构建新的视觉空间,发现笔、墨、线条自身的美感。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谷文达用头发代替墨汁来书写汉字还是有一定的前卫特征。
自从书法开始成为诗、词表现载体的时候,书法与诗性的美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而书法自身也成为一面镜子,用自身反射出诗、词的文学美感,从这个方面来说,书法自身的视觉美感是被降低的。对感官的强调,意味着现代书法创作对表象视觉效果的强调,这就导致形式的多样性,同时降低了对书写内容情感的依赖性。正是空间关系,而不是语义关系,将这些异化的汉字连接在一起。异化的汉字不是强化语义之间的关系,而是干扰它们,造成视觉的转向,减慢语义正常的进程,使语义在阅读中形成必然的延迟。语义本身是不可见的,需要在想象中重构,而异化汉字让这些不可见的因素更加晦涩,此时,异化汉字自身成为符号文本,从而唤醒认知的转向,在视觉空间中寻找自身的审美结构。
三、“异化之后”——身份与边界
异化汉字在书法中的身份一直是争论的话题,异化的程度很难用精确的数值来测量,当我们开始对汉字进行现代改造的时候,必定会引入更多的观念与材料,会引入艺术生态中一些非传统书法的元素,这个过程并没有压缩书法的生存空间,反而扩大了书法在当代艺术中的现实比例,同时确立了书法现代构建过程中艺术性与视觉性的优先地位。在欣赏古典书法书写的内容时,诗歌的确可以将整个欣赏过程提升,但这个过程已经不完全是书法的欣赏了。当代艺术对视觉强调,使异化汉字构造的空间更具有开放性,让观者投身于整个艺术作品,沉浸在书法作品中。这样的欣赏过程,视觉的具身性让观者沉浸在汉字符号构建的新空间中,在拓展书法的展示空间的同时,也扩大了书法的生产场域。书法现代构建的另一个倾向就是对视觉的强调,书法从创造到认知都要匹配视觉性的特征,传统范式依然有效,只是需要添加更多的内容来丰富当下书法的创作与批评机制。
艺术史家克拉克在讨论现代性时说道:“对视觉的怀疑变成了对绘画行为中牵涉的一切事物的怀疑;最后,不确定性自身变成了一种价值:我们可以说,它变成了一种美学。”[4]这种审美方式在克拉克眼里便成为现代主义审美,成为对现存视觉秩序的破坏。而在书法现代构建中,异化汉字本身就是对现存视觉秩序的破坏,这样的破坏不仅是视觉上的还是认知上的,同时也是审美方面的。去语境化可能是现代书法构建的特征之一,异化汉字隔断传统认知语境的时候,便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徐冰的“新英文书法”可能是异化汉字最重要的探索之一,在外形方面,其和传统书法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毋宁说他是遵守传统书法创作方式的,但是这些“伪汉字”创造的书法作品很难用传统的认知来解读。徐冰并没有停留于此,对于“新英文书法”,他自创了整套阅读方式,让人们有了阅读的可能。这个“去语境化”之后的“再语境化”就是书法的现代再建。而谷文达更是直接跃出了传统书法创作的边界,他用头发拧结成线,用来替代笔墨书写的线条,虽然汉字的造型依旧,但从传统的认知来看,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法。谷文达截断了传统汉字艺术的创作方式,传统认知在此遭遇到空白点,这样的失效便是现代艺术构建的方式。对于汉字所指意义来说,大众的认知基本是统一的,这是基于传统的文化认知习惯,虽然汉字能指图形的审美也有一定的规范,但不同人群的审美感受是不一样的,在能指与所指的双向认知中,书法现代构建引入的异化汉字无疑将能指的视觉性强化,这个过程并没有否定所指的含义,而是将书法引向纯粹的视觉审美。汉字所指链接到意指内容时,任何社会人都可以获得,而艺术审美是个人生存的内部经验,是对私人绵延现实的体验,这便决定了艺术创作对于视觉审美的依赖。
在书法的现代构建中,出现了“无行无列”式的创作方式,虽然没有破坏汉字,也没有破坏语序,但这样的创作方式会干扰到正常的阅读,出现认知上的延缓,在视觉上是非线性的。正是这样的方式,带来书法视觉上的奇异感。诗词创作中的无意识书写,带来了认知与创作的新范式,而这样的无意识书写运用到书法创作的时候,进一步强化了“无行无列”的形式。这样的创作方式,从形式到阅读都跟固有的认知产生冲突,进而产生视觉与认知上的双重悖论。这样的创作方式虽没有征用异化的汉字,但会延缓对语义的正确阐释,从而激发认知与知识结构的重组。即使在定义异化汉字的合法性方面有存疑,但整个的构建过程还是说明异化汉字所参与的现代构建昭示了新视觉秩序的胜利。只要构建还在推进,就会触及书法身份与边界的问题,当代艺术的开放性在书法方面依然有效,书法同样需要不断地添加新内容,在不断的试错中实现建构。
四、结语
当书法中的汉字从信息传达媒介转移到艺术表现语言的时候,为适应当代对视觉的要求,符号获得了新的重构,当汉字以异化的身份出现时,这个符号虽然很陌生,甚至无法成为标准的汉字时,在认知上是困难的,但悖论的是,在视觉方面出现了很多意外的效果。在现代书法表现中,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平衡开始发生变化,并向艺术价值倾斜的时候,说明新的认知范式正在进行实验性的探索。熊秉明先生一再强调将我们的视角从书法汉字的叙事性转移到汉字本身的欣赏上来,其中之一就是让观看的视角转移到汉字本身,去发掘汉字、笔、墨的视觉特征,回归到艺术的视觉性上。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说道:“景观不是影像的聚集,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5]这说明在影像下面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德波要讨论的。同理,汉字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符号的拼接,而且含有更深层的文化关系,正是这样的关系使符号的所指价值体现出来。在书法创作中,这样的关系虽然保持了书法的纯粹性,但是暗含了对激进的艺术解构的排斥。当代书法的实验性探索并不一定都是成功的,也会偏离正常的艺术史脉络,但不能抹杀它们的启蒙意义,因为书法建构没有可供借鉴的案例,这个试错的过程同样会推动现代构建,并为书法带来新的活力。
——评《艺术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