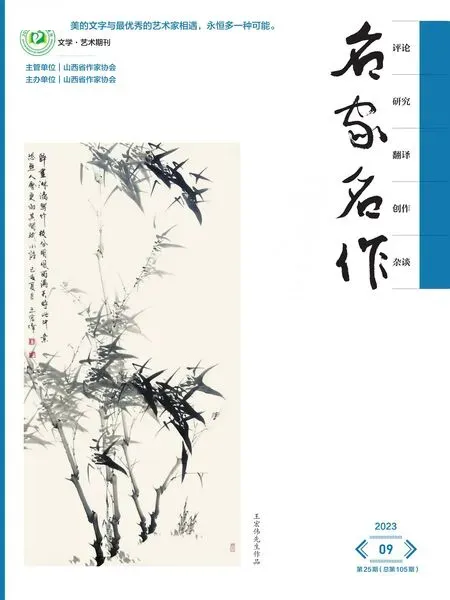清代高州府举人群体研究
梁秋婷
明清时期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就广东地区科举群体的相关研究而言,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文教发达的广州府等地,重心也更倾向于进士群体,对于举人、贡生、监生等中下等功名群体的关注则较少。清代高州府辖茂名、电白、信宜、吴川、石城五县及化州,是粤西地区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中心。明代广东共举行91 科乡试,至少录取6 968 名举人,其中高州府308 人,在广东各府中排第五。清代共举行108 科乡试,约录举人7 994 名,其中高州府共录取254 人,仅占3.18%左右。举人群体既是科举制度的获利者,也是地方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承担者。探究高州府举人群体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清代高州府科举群体研究,还有助于我们反思清代科举制度如何在边缘区域影响士人群体,进而影响区域社会。
一、高州府举人群体的生存状态
(一)时空分布
据广东地区乡试录、同年录和高州府各县县志统计,清代高州府茂名举人96 人、电白23 人、信宜35 人、吴川54 人、化州27 人、石城19 人。高州府六辖地举人数量的分布规律大体呈由府治中心向四周扩散。高州府在顺治朝、康熙朝、雍正朝平均每科中举人数不足2 人,乾隆朝以后平均每科中举人数超过2 人,除茂名县和吴川县外,其他县举人上榜情况并不理想。高州府长期处于科举录取的劣势区,大体呈现波折上升趋势,偶有相对集中的数量攀升,道光年间出现了粤西地区第一位状元。
乡试是科举制度的重要分水岭,举人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能直观反映出一地的科举水平。清代高州府举人时空分布不均,也反映出各县对举业的重视程度不一。
(二)仕进情况
本文统计的高州府254 名举人中,最终只有21 人高中进士,其中除乾隆辛未科的李应孙一人“未仕卒”外,其余20 人都成功地走上了仕途,完成了由科举到入仕的全过程。据不完全统计,除这21 名进士外,还有近百名未中进士的举人通过大选补缺、拣选、截取、大挑等形式进入官场,其中府学教授3 人,州学正3 人,教谕、训导35 人,知县38 人,官至七品知县以上18 人。即在不考虑官职大小的情况下,高州府254 名举人中共有117人踏足清朝官场。其中,登科及第者不足一成,任教职者十之二三,更多应试者奋力志学、经营半生,却老病途中,未仕而卒。
(三)经济状况
举人群体的职业情况相对复杂,收入情况也较难统计。俸禄方面,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清朝顺治、康熙年间外官俸禄“七品俸银一十二两四钱七分一厘,薪银二十三两五钱二分九厘”。高州府举人除高中进士者外,多数终老在七、八品官任上,即只按正俸计算,大部分举人的月收入水平在45 两及以下。一个知县一月正俸不足以维持一家生计,但正俸实则是官员收入最少的一部分。除正俸外,官员还有远高于俸禄的“养廉银”作为津贴,如广东省一个知县每年的养廉银为600 两至1000 两银子。此外,“在19 世纪的中国,绅士最重要的收入来自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补偿”。举人群体作为地方士绅,天然承担士绅所要求的责任和义务,也从“发挥绅士职能”中获得不菲收入。
(四)精神面貌
1.重视孝道
百善孝为先,在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中,孝行是评判一个人品格的重要指标。电白包粹乾“以母老改教职”,茂名黄玉佩“事继母以孝闻”,类似记载不胜枚举。可见重视孝道是百姓对举人的基本期许。
2.重义轻利
高州府举人包舆荆“居官廉谨,自守粗衣淡食,不妄取一钱”,“士林无不爱之其长厚”,又电白县邵咏“志守嶷然,有县令某求寿言,啖以百金,不应”。可见,随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家传统的义利观虽有所削弱,但仍作为士人重要的精神品质为人称颂。
3.狂狷厌俗
“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康雍乾盛世后过度集权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凸显,士人出现不乐仕进、隐退归田等现象。举人李东述,“生平屏迹公门,铨期届不谒选,人比辛卯”。就连状元林召棠,晚年也因不愿同流合污而隐退归乡。士人群体作为社会最敏感的成员,总是最早感受到社会的动荡不安,狂狷厌俗成为他们反抗的形式之一。
举人群体的精神面貌深刻地反映了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海晏河清时,高州府举人群体作为地方道德标榜,表现出的突出品质与历代推崇的忠义礼智信并无二般,但在清中后期却出现了多起隐逸、狂狷厌世的事例,他们的精神状态也在很大程度反映了当时官场清明与否。
(五)举业传承
乡试的高淘汰率让许多中下层士子在屡试屡败后放弃科场,但弃儒而从他业者几近于无,大多转而督促子孙后辈继续举儒为任,高州府三代之内至少产生两个及以上举人的家族有27 个。以茂名张氏家族为例,士英、士拔于乾隆十二年(1747 年)同领五经乡荐,其弟士彦又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亦举于乡,“一时有三鳯之目”,张氏兄弟在告归乡里后著书立说、教育子孙,其家族后辈多笃志好学,“士英长子梧廷岁贡,次子奋廷、孙同琳皆府庠生,同瑶邑廪生”。地方望族重视科举教育事业,形成代代业儒的良好家风传承,并通过血缘纽带、师承、同窗等密切联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中心文化圈,地方精英阶层由此深入地方话语体系。
(六)社交活动
1.游学
游学以博闻。游学问道不仅能满足士人拓宽视野、访明师友的客观需求,还是士人立身扬名、积累声望的重要途径。道光年间的电白士人邵咏就是一个典型,他“师从冯太史敏昌之门,太史称其诗文为广东后来之秀”,翁方纲于序文中赞道:“鱼山而后,舍斯人其谁与。”“自学士大夫下至负贩童稚,莫不知电白有邵芝芳其人。”
2.文会和结社
组织文会和结社比起游学来说目的性更强,成员间的联系更紧密,辐射范围也更广,社交活动的准入门槛也更高。粤东七子之一林联桂会试落第后久寓京师的情况下与“黄侍御玉衡、向官京邸与盛广文大士、谭农部敬昭、吴解元梯、黄校录培芳、张进士维屏、黄孝廉剑”七人日常咏诗为乐,后又“结诗社于都中,闲月一会,每月一会,半月一会,会辄数日乃罢”。这些文会和诗社同气连枝,共同成就了粤东七子的才名,也为落第第林联桂积累了政治资本。
3.联姻
联姻双方不仅进行资源整合,而且不可避免地成为利益相关方,共担风险。“婚姻虽缘地域之逼近而成,实因品类之相同而聚。”以粤西状元林召棠的姻亲关系为例,林召棠“以女妻汝璠”,陈汝璠是林兆棠同窗陈曾庆之子,陈曾庆是吴川县丞,家境殷实,平日乐善好施,吴川县“荒歉支科费至今赖之”。从陈汝璠的墓志铭来看,汝璠曾祖为国学生,父亲为附贡生,子孙后辈也不忘进学,陈家在当地的名望可见一斑。林氏名高,为陈氏构建更高层次的社会关系网提供了契机;陈氏财厚,对林氏来说也是扎根地方的重要助力,联姻成为士人群体间积聚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手段。
交游、访学、结社、联姻等大多不可避免地发生在同一阶层,而同一阶层的许多密切关系如同学、同窗、师徒等又是科举制度的衍生品。可见,举人群体的社交圈和社交活动都被科举制度打上深刻的烙印。
二、举人群体对地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
(一)振兴地方教育
一是重视家族文化建设。“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尤其是家族已有科第功名者,以“训子孙专务读书”为风。除了兴族学、重视子弟进学外,还包括撰写家规、家训,引导家族好学风气等措施。
二是兴建学校、义学。一方面,举人群体作为行政和教职官员,传播儒学、教化地方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提拔后进、推动地方文化繁荣是他们作为士绅的自觉担当。如电白举人黎式礼“修学宫,创书院,置田养士介捐俸为之”。又如电白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举人李斯 奇香“设义塾,教授生徒三十余载”。举人群体多以兴文教为己任,所思所行不仅促进了地区教育蓬勃发展,还引导了地方人文方向,让高州府形成世代敦儒、重视科考的风气。
三是著书立说。《左传》有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谓之不朽。”立言是文人表情达意、抒怀明志的常见途径,也是举人群体瓜分地方话语权的重要手段。高州府举人群体的著作涉及经学、文学、史学等多个领域。
(二)维护地方秩序
影响清朝高州地方治安的因素主要有匪寇、兵乱和自然灾害。随着清朝中后期社会危机的加深,高州府举人群体组织团练、招募乡勇等行为都深深打上了时代烙印。
一是组织团练。广东地区地处偏僻,历来据险为匪为寇者数见不鲜,清朝咸光年间更是让百姓不胜其扰。“咸丰末年廉州贼张阿春、李士葵犯境,廷桂谒郡守马丽文,告以举行团练法”,“道光二十二年冬知府马丽文谕各乡举行团练”,“县内陈姓匪某聚尝拜会,兵役不敢捕,(黄)东云设法擒之。又赞知府马丽文举行团练,地方以靖”,咸丰四年(1854 年),黄东云又任防剿局总局,任内兢兢业业,以靖一方。团练在清朝不仅守护了一方安宁,后来更是成为维护统治的重要力量。
二是招募乡勇。道光三十年(1850 年),拜上帝会蔓延至高州,“邑绅患之诣县请捕焉”。咸丰四年(1854年),红巾贼起义,“陈金缸既破信宜郡城,兵单勇乏”,其时,高文书院山长陈蘭彬收到密报,“飞函广东布政使伊霖告急”,“茂名举人杨廷桂商之”,救兵未至,“信宜举人李崇忠募勇攻贼”。举人群体通过向官府献策、资助、合作、招募乡勇等方式守卫地方,是保障地方治安、秩序的重要力量。
三是稳定地方物价。高州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显著,常有飓风、暴雨、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旦遭遇大灾,物价自然动荡。在饥年,举人群体联合官府通过捐款、开仓赈灾等方式维持百姓的基本生活;在巨族欺凌小户时,又积极约束,维护地方经济秩序;在官府政令与当地民众利益相冲突时,又积极建言,缓和矛盾。举人群体对地方经济的平稳运行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开展公益事业
公益事业是举人群体为地方贡献力量、回馈乡邑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咸丰年间,“匪逼境,知县王锡诰延(罗)士奇、(罗)汝彦同勷军务,履殄强寇,岁辛酉陈金缸据信宜,军务倥偬,土匪蠢动,扰太平店,逼近县治,汝彦先出资筹办军实,募劲勇,佐知县敖翊臣,破贼嗣,有流寇夜刦村庄铺户,汝彦授策兵勇,缉捕卒获贼惩办,士奇以功保奖官廉州府教授,汝彦亦得叙选训导”。小到调解纠纷、筹助婚丧,大到赈灾救济,持续的义举使举人群体在乡邑间塑造可靠、负责的形象,累积起的社会声望又进一步提高举人群体在地方事务的话语权,因而举人群体对地方事务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举人群体处理各种地方事务是“需要和习惯造成的事实”,也是举人群体获得名利的重要途径。
三、结语
通过对高州府地方社会视野下的举人群体分析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举人群体对构建地方文化形象、承担地方事务以及对掌控区域社会话语权的重要意义。他们与现行制度、政策的相互配合才使得科举制真正影响乡野,因而要充分重视人才资源对于制度的联动和弥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