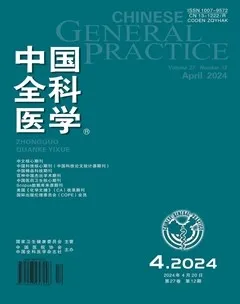医学中的全科医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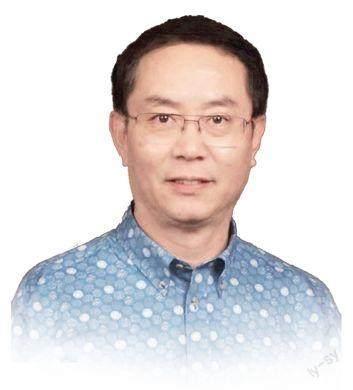
【关键词】 全科医学;初级卫生保健;生物心理社会模式;恩格尔
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有些词是张嘴就来的,但耳熟不一定能详,禁不起进一步追问。还有人热衷造新词,或换字游戏,或折腾生僻字,把美妙的中文变得面目全非。然而绝大多数“潮词靓语”如流星即逝,只有少数词经得起时间、思辨和实践的考验,这是因为它们有深刻的思想后盾,并容许评判。
我很幸运,大学一年级入学教育时,老师告诉我们这些新生,医学要进入新的时代了,这让我们非常振奋。入学后几个月的1980年,中国刚创刊的《医学与哲学》杂志刊登了乔治·恩格尔(George Engel)的文章《需要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的挑战》的摘译。该文的英文原文付梓于Science杂志上,发表时间是中国恢复高考的那一年(1977年)。在我看来,这个新医学模式所带来的思想启发和指导意义,一点也不亚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机会和幸福。大学毕业后我在社会医学教研室工作,继续沿着恩格尔的思想向前走。
乔治·恩格尔的文章没有使用任何数据,坦白说,现在读起来是非常枯燥的。然而截至我写下面这些文字的时候,其原文拥有20 000多次引用的骄傲成绩,其中文摘译版也有82次引用,这使其成为经典。恩格尔的主要成就是将一个词牢牢地、经久不衰地纳入医学文献中,并铭刻在现代医学人的脑海中,成为医学界最大的共识和话题。这个词是:生物心理社会(biopsychosocial)。
恩格爾文章的中文摘译版本,请读者移步到《医学与哲学》去赏读。下面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是2005年发表于The Lancet 的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克里斯·麦克玛纳斯教授的文章,麦克玛纳斯教授就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理解生病的综合方式》一书的评论[The Lancet,2005,365(9478):2169-2170. DOI: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05)66761-X],对恩格尔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进行了再讨论。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体会到针对恩格尔的理论从来不缺学术讨论和思辨,从而让其得以愈发丰满和发展。生物心理社会这个词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深刻的和可辩的哲学思想。把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作为认识论和学术范式的全科医学,对其进行深入理解和反思,并参与争论和推动演进,是非常必要的。
以下译文有摘译。翻译过程中得到澳大利亚 Monash 大学翻译专家秦潞山教授指点,特此致谢。
乔治·恩格尔认为,纯粹的生物医学方法“在其框架内没有给生病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因素留下空间”,尽管如今人们对这些因素在疾病中的作用似乎没有争议。
事实上,社会过程对疾病作用的认识,至少可以追溯到与恩格尔几乎同姓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恩格斯在 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描述了快速工业化的英国穷人的令人震惊的生活条件。恩格斯发问:“在这样的条件下,下层阶级怎么可能健康长寿呢?除了死亡率过高、传染病持续不断、劳动者体质逐渐恶化之外,还能指望看到什么呢?”(注意区分恩格尔和恩格斯。费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卡尔·马克思的挚友。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帮助马克思完成未竟的《资本论》等著作,并推动建立了第二国际)
确实如此,只要不是从类人猿的角度,也不必一定要站在天使一边,就能承认恩格斯和恩格尔的观点。(类人猿与天使,是一种隐喻;因为是隐喻,所以可以演绎出各种理解。比如类人猿可以是进化和发展,或者对原始事物,或者对日常的隐喻,天使或安琪儿可以是道德和正义,或者对神圣精神,或者对超越日常的隐喻。两者之间可以有生动的对比,比如“我宁愿成为一个不完美的猿猴,但能通过不断学习和成长变得更加优秀;而不愿成为一个完美的天使,开始于神圣无暇但因偷食禁果而衰落;这意味着猿猴会变得更好,而天使只会变得更糟”)
不过,生物医学的概念本身并不是个错误,其不需要被取代。正如戴维·韦瑟罗尔爵士(Sir David Weatherall)不久前在The Lancet上所说,“如果某人认为任何医学分支都不应该与生物学相关,那么他的想法是不可理喻的”。把韦瑟罗尔的说法延展开说,如果某人认为任何医学分支都不应该关注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那么他的想法同样是不可理喻的。(戴维·韦瑟罗尔爵士,1933—2018年,英国血液病专家,分子遗传学和病理学研究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牛津大学教授,基尔大学校长)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理解生病的综合方式》这本书包含很多这样的争议。这是一本激动人心的合集,由13位参加过诺华基金会研讨会的见多识广、思路清晰的作者编写,这本书让我们有幸在一场精彩的会议上成为墙上的一只苍蝇(会议室墙上的苍蝇是一种比喻,有客观第三者的含义,或指不为人知地倾听和观察)。对于那些匆忙的人,或者那些只是喜欢优雅的医学写作和思考的人来说,西蒙·韦瑟利教授(Simon Wessely)的前言以机智、幽默和华丽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概述。(西蒙·韦瑟利教授,1956年—,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精神病学和流行病学专家)
伟大的鲁道夫·魏尔啸(Rudolf Virchow)宣称“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政治只不过是大规模的医学”。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思想一直处于孵化和蓬勃发展的状态。(鲁道夫·魏尔啸,1821—1902年,德国医学家、人类学家、病理学家、生物学家,被誉为现代病理学之父,社会医学创始人)
1943年对英国来说是个转折点,约翰·莱尔 (John Ryle) 从剑桥大学转到牛津大学建立社会医学研究所,开创社会医学学科。莱尔强调心理,认为超过一半的实用医学是心理学;他也强调社会,认为慢性疾病有其社会病因。他的牛津研究所专注于英国社会医学,在英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约翰·莱尔,1889—1950年,英国医生和流行病学专家)
不过社会医学的核心存在一个冲突,托马斯·麦基翁(Thomas McKewon)和查尔斯·洛(Charles Lowe)在《社会医学导论》(1966年)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狭义的社会医学局限于流行病学和社会的医疗需求,而广义的社会医学是医学中人道主义传统的表达,把社会医学解读为符合自己愿望和利益的任何解释。这些五花八门的愿望是社会医学的现代继承者(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障碍。(托马斯·麦基翁,1912—1988年,英国流行病学和医学史专家,伯明翰大学社会医学系主任。其最有名也最具争议的观点,是18世纪以来的人口增长是由于经济条件改善,特别是更好的营养,而不是因为更好的卫生条件、公共卫生措施和改进的医疗服务。查尔斯·洛,1912—1993年,英国威尔士国立社会医学和职业医学系主任)
这些广义和狭义的观点,一直困扰着当前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不愿被归为软科学的人,通常持狭义的观点,他们以流行病学中的数学方法为核心,将自己归类成如生物医学那样的硬科学。相比之下,生物医学的人认为持广义观点的人是不可救药的“软领域“,没有明确的方法论,也没有测量或实验操作的核心技术。然而更激进的广义观点支持者则认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面临的挑战是超越其名称的模糊性、理想化的包容性,创建一个真正值得被称为模型的模型,并且具有适当的解释性和预测性。
成功的模型是很简单的,不复杂的。标新立异和包容一切的模型最终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愤世嫉俗的人重读恩格尔的论文甚至可能会争辩说,他最初的模型不是模型的模型,而仅是战斗的号角。
生物心理社会模式面临的挑战涉及还原论、二元论、机械论、方法学和因果关系。心理学和社会学现象是心灵现象,还原论的挑战是如何将心灵现象与生物医学致力的细胞、分子和遗传相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不可胜的挑战,从思想到细胞周期恶性转化的途径,只能通过数十亿个细胞中的深层生物机制和癌症基因,而心灵途径肯定是无法直接访问或控制这些机制或基因的。话虽如此,自我使用强效毒素(例如烟草烟雾)可以间接改变许多细胞过程,自我吸烟的决定可以由广告或同伴的行为决定。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每次端起一杯咖啡都涉及思想,而且仅是思想就会改变亚细胞细胞器,因为仅仅意图就会导致突触囊泡的释放,从而激活肌肉收缩,让你把杯子拿起举到嘴唇上。(还原论认为复杂的事物和现象可以通过分解成几个部分来进行描述和理解;与还原论相对的是整体论,认为系统是有机整体,而非简单的几个部分组合。二元论认为世界由相互独立的物质和意识两个本原组成,两者同等和公平地存在;哲学上的二元论则指既不偏向唯物主义也不偏向唯心主义的思想。机械论认为自然界或人体或心灵是复杂机器或工艺品,自然和人的行为可以从其组成部分和外界影响来解释)
理清因果关系是很困难的。医学是否应该只关心最直接的原因,例如造成霍乱病的霍乱弧菌肠毒素?生物医学寻找的通常是这类近端原因。医学是否还应该询问原因的原因,以及原因的原因的原因?正如约翰·斯诺(John Snow)在伦敦宽街水泵上认识到的,公共卫生和贫困是否应该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乔治·戴维·史密斯(George Davey Smith)在书中讲述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流行病学警示故事,其中的寓意是,观察性研究中遭遇的混杂因素,意味着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是随机对照试验,并且几乎不可避免地排除了心理社会作为疾病的真正原因。(约翰·斯诺,1813—1858年,英国医生,麻醉学专家,现代流行病学的创始人之一。乔治·戴维·史密斯,1959年—,英国流行病学专家,《国际流行病学杂志》前主编)
但不知何故,坚持随机对照试验为真理立场的人,会忽略混杂因素的本质。迈克尔·马莫特 (Michael Marmot) 对社会阶层及工作状况对心脏病的作用的分析,将教育视为风险因素,把“混杂因素”问题凸显出来。我还渴望在这里讨论伊恩·迪里(Ian Deary)关于儿童智力如何预测成人死亡的论述。尽管智力具有遗传影响、生物学基础、人类进化作用,及其与阶层和社会移民的关系,但在某种程度上,探究智力话题在政治上很不正确。如果死亡取决于人们对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明智选择,那么健康责任就成为说起来好听但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东西,并伴随着一系列困难的道德和伦理问题。(迈克尔·马莫特,1945年—,伦敦大学学院流行病学教授,UCL健康公平研究所主任。伊恩·迪里,1954年—,爱丁堡大学差异心理学教授)
生物心理社会模式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当然,天使们肯定会投票支持这个新模式是必需品。彼得·怀特(Peter White) 将生物心理社会模式描述为“将思想、信仰、情感、行为及社会背景,与生物过程的相互作用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了解并管理疾病和失能”。然而,他的表述仍潜伏着两个领域的感觉:针对生病的“生物性”和针对失能的“心理社会性”。(彼得·怀特,玛丽女王倫敦大学心理学教授,圣巴塞洛谬医院精神病学专家,《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理解生病的综合方式》一书的总编)
感悟——
生物心理社会模式是医学人不陌生的,全科医学、社会医学、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等对这个词更是熟悉,认为现代医学是生物医学、心理科学、社会科学的组合,那三个圆相互交叠的图形,更是对这个模式的形象表达。
很多人以为“生物心理社会”这个词是恩格尔1977年提出的,不过根据牛津英语词典考证,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51年的《高等教育杂志》(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上。可以想象,恩格尔并非是挑战科学医学(生物医学)的第一人,比如克莱曼恩(Kleinman)等1978年提出,“医生诊断和治疗疾病(身体器官和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异常),而病人拥有疾病(存在状态和社会功能减弱的变化经历)”。世界卫生组织1948年提出,健康不仅是疾病和体弱的匿迹,而是身心健康和社会幸福的完满状态。更早的希波克拉底,也提出“哪里有对医学艺术的热爱,哪里就有对人性的热爱”“理解患病的人,要比理解疾病更重要”。因此,恩格尔是对思想的继承和提炼,把这个形容词与“模式”合在一起,成为现代医学的标志性词汇之一。
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被文献反复引用,口耳相传太多;但其并非是神明,也很容易被滥用。它也受到批评,科学医学(生物医学)认为这个模式对科学依据提出质疑,因此会稀释医学的纯度。也有人认为其存在于理论层面,因此实用性被质疑。不过如麦克玛纳斯教授介绍的,对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讨论不是为了否定它,而是使其得到发展。
我国有不少学者在引进和使用生物心理社会模式时,称这是“医学模式的转变”。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生物心理社会模式旨在更完整地描述医疗保健和疾病行为,它从来没有打算取代生物医学的命题、研究和实践。生物医学是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中重要的且平等的部分,这一点很重要。相似的是,我们不应该在重视第二次卫生革命(应对慢性和非感染性疾病)的同時,否定第一次卫生革命(应对感染性疾病)的存在。当然,这些争论仍将继续,麦克玛纳斯教授对于还原论、整体论和二元论的提示,是思辨的思想基础。
恩格尔文章发表40多年,对促进医学领域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不过,将这个模式纳入日常医疗服务和健康活动的情形尚未发生。经济和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急性医疗和外科服务(即大医院服务)、科研生产力最高的生命和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经常忽视恩格尔模式的存在。当一位心内科专家向同事报告心脏病患者的抑郁问题时,会被揶揄为不务正业。有不少医学服务管理者、医疗实践者,以及社区的公众,还不知道或没有意识到生物心理和社会模式。
很多全科医生最关心的是怎样做,而不仅是怎样说,他们关注怎样让生物医学、心理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不再各画自己的圈子,不再自说自话,而是通过更多的交集,形成内在的还原与整合的平衡(和而不同)。然而,关键还是思想。大学本科是建立和拓展医学思想的阶段,而非仅是管状视野地仅聚焦在解剖结构、病灶器官、生化指标和异常细胞。医学本科教育对未来医生思想的形成,应该置于培养医疗工匠之上。
恩格尔是精神病学专家、心理分析师、内科医生、医学教授。他出生于美国,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学位。行医之初,他认为应该完全用物理学方法解释疾病过程。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研究学者时候,认识精神病专家罗马诺,一起做研究,完成从物理学派转向心理问题躯体化学派的转折。他有内科学和精神病学的双重任命,在医学培训和临床服务中结合了情感和躯体两个方面,成为心身医学的主要人物,并最终将模型理论化,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他的学识和实践背景,是他提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基础。当然他也注意到了模型落地的关键:除非那些控制资源的人有智慧地并冒险地走出完全依赖生物医学作为唯一医疗保健方法的老路,否则什么都不会改变。
读懂恩格尔文章,以及随后的各家讨论,并非所见即所得那样轻松。《Engel,Engels,and the side of the angels》这篇文章的原作者麦克玛纳斯教授,给文章赋予了丰富的语言学、人文学和哲学的意义。他获得学位的顺序是文学学士→医学学士→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医学博士。在文章题目中,Engel是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提出者,Engels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angels是道德的化身。这对只有医学背景的人来说,理解起来可能是颇具挑战的,原文中的“妙梗”也可能会因为翻译的原因而损失掉。因此翻译过程中我特地请教Monash大学的秦潞山教授,得到他的指点,特此致谢。
比如秦教授建议将题目翻译成“恩格尔,恩格斯,安琪儿的一面”,并对其中多个修辞手段进行了分析。这个题目使用了头韵,增加了令人愉悦的节奏和声音模式,使其更容易记忆和吸引人。如果angels翻译成天使,就会失去韵律感,但如果译成安琪儿,则有了悦耳的旋律。其使用了双关语,即一种涉及相似发音但不同意思的文字游戏,如Engel和Engels,创造了一种超越单纯声音相似的语言联系,增加了表达深度,尤其是考虑到恩格斯这样的人物的历史背景;使用了惯用表达,如安琪儿的一面,指的是道德上的正确立场,创造了一个隐喻的语境,唤起了道德或正义感,迎合读者的价值观;使用了转喻修辞格,安琪儿被替换为道德上正义的实体或行为,强调了善良的一面。这些修辞增强了表达的巧妙性,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鼓励思考,并可能引发微笑或对语言的欣赏。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翻译可能会损失掉一些原文的语言艺术表现和内涵意义,但有扎实功底的翻译专家会在“达意”上更有经验,非常值得我们虚心学习和请教。当全科医学是生物、心理、社会的三合一范式时,无论是研究还是实践,均需要更多的医学之外的修养和熏陶。
引用本文:杨辉.医学中的全科医学——从《柳叶刀》200年历史看现代医学中的全科医学发展(八):对恩格尔生物心理社会范式的思辨[J]. 2024,27(12):前插. DOI:10.12114/j.issn.1007-9572.2024.A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