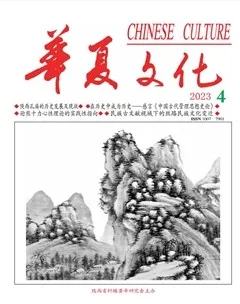《东原录》所载《丹凤门赋》考辨
□王 彬
梁周翰(929—1009年)字元褒,郑州管城人,宋初文学家、官员。梁周翰名列《宋史·文苑传》,其本传载:“乾德中,献《拟制》二十编,擢为右拾遗。会修大内,上《五凤楼赋》,人多传诵之。”《五凤楼赋》是宋代的著名赋篇,备受士林推重,南宋吕祖谦编《皇朝文鉴》时将其收入,且以之为“压卷”之作。
梁周翰曾向宋太祖进献《五凤楼赋》,这一点殆无疑义。然而北宋龚鼎臣《东原录》载:“艺祖时新丹凤门,梁周翰献《丹凤门赋》,帝问左右:‘何也?’对曰:‘周翰儒臣,在文字职,国家有所兴建,即为歌颂。’帝曰:‘人家盖一个门楼,措大家又献言语!’即掷于地。即今宣德门也。”“艺祖”即宋太祖。据此则材料记载,梁周翰献赋并没有受到宋太祖的奖赏,反而被“掷于地”,这一有趣的细节是否可信暂且不论。这里重点关注的是,梁周翰向宋太祖进献的赋篇是《丹凤门赋》。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东原录》所载《丹凤门赋》与传世之《五凤楼赋》是何关系?两者是同篇而异名,还是本就为两篇作品?
要回答此问题,应该从作品所描写的对象这个角度来考察。《丹凤门赋》描写的当然是丹凤门,《东原录》称其又名宣德门。那么,《五凤楼赋》描写的是什么建筑呢?
梁周翰《五凤楼赋》开篇曰:“伊京师之权舆也,遐哉邈乎!验河图之象,按舆地之书。宅《禹贡》豫州之域,距天文辰马之墟。”此言指出“五凤楼”的位置在北宋“京师”,即汴京,与《宋史》梁周翰本传中“会修大内”之语相合。王应麟《玉海》卷一五八记载更为详明:
建隆三年正月十五日,广皇城东北;五月,大修宫阙。乾德元年(原注:即建隆四年)五月十四日,复增修宫阙。(原注:《长编》五月乙丑,命李怀义等增修宫阙。当从《长编》月日)凡规为制度,并上指授。既成(原注:二十四日,明德门成),坐寝殿中,令洞开诸门,皆端直通豁。谓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见之。”直史馆梁周翰为 《五凤楼赋》以进。
这则史料指出《五凤楼赋》所描写的建筑实为汴京的明德门。所谓“五凤楼”实际上说的是汴京城门的形制。直到今天,“五凤楼”也一般被解释为宫城正门形制。
《玉海》指出《五凤楼赋》描写的是北宋汴京城的明德门,《东原录》声称《丹凤门赋》描写的是丹凤门或宣德门,这是不是说《五凤楼赋》与《丹凤门赋》的描写对象不同呢?事实不然。《宋会要辑稿·方域三》“东京大内”条云:
东京大内南三门,中曰宣德,梁初曰建国,后改咸安,晋初曰显德,又改明德,太平兴国三年七月改丹凤,九年七月改乾元,大中祥符八年六月改正阳,景祐元年正月改宣德,政和八年十月六日改为太极之楼,重和元年正月复今名。
宋代的东京也就是汴京,由这则记载可知,汴京皇城南正门屡经更名,太祖时为明德门,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七月后名丹凤门,后来又名宣德门。名称虽异,实即一门。反观《东原录》所载,显然存在着差误。太祖时名为明德门,不称丹凤门,所谓“艺祖时新丹凤门”乃龚鼎臣的记闻之误。《东原录》是文人笔记,撰作之时不深考究,此类差误实属常见。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丹凤门即明德门。既然“两赋”描写对象相同,都是梁周翰创作的,又都是献给宋太祖的,那就有理由相信,这所谓的“两赋”——《丹凤门赋》与《五凤楼赋》——实际就是一篇作品。这篇作品准确的名字应是《五凤楼赋》,龚鼎臣在《东原录》中记载不确。
梁周翰《五凤楼赋》所描写的明德门,也即宣德门,在宋代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美国学者伊佩霞曾指出:“宣德门是皇帝内宫与开封城民众、甚至与整个宋帝国之间的标志性分界线。皇帝利用宣德楼的象征意义,定期出现在城楼上,以示对臣民的关心。”(伊佩霞著、韩华译:《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明德门(宣德门)是北宋皇城的门面,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大宋帝国的威严。那么,梁周翰在《五凤楼赋》中是如何描写北宋皇城大门的呢?他首先被城门之上的城楼所吸引,其曰:“去地百丈,在天半空。五凤翘翼,若鹏运风。双龙蟠首,若鳌戴宫。丹楯霞绕,神光何融。朱楹虹植,晴文始烘。绣楣焜耀,雕栱玲珑。椒壁涂赭,绮窗晕红。双阙偶立,突然如峰。平见千里,深映九重。奔星坠而交触,灵景互而相逢。”在梁周翰的笔下,城楼高耸入云,辉煌壮丽,气象不凡。接下来,梁周翰描写了城门的宽敞与坚固:“门呀洞缺,若天之裂。纵举百武,横驾六辙。金铺烁人,光景明灭。舞阳之力莫得而排,叔梁之力胡可以抉。”在梁周翰看来,只要把城门一关,整座汴京城就固若金汤,即便是秦舞阳、叔梁纥这样的勇士也休想攻破。梁周翰还描写了出入皇城大门的各色行人:“冠盖葳蕤,剑佩陆离。车如流水,待漏而驰。驾肩排踵,兼蛮浑夷。万众纷错,鱼龙尊卑。咸去来之由此,竞奔凑于玉墀。亶皇风之无外,岂朝盈之有时。”这里有达官贵人,也有平民百姓,还有外国友人,他们纷纷出入皇城,显示出的是大宋开国之初开放、包容的宏伟气度。总之,梁周翰在《五凤楼赋》中以饱满的笔墨描写了汴京城门的壮丽景观,昭示了大宋的煌煌气象,所以《五凤楼赋》成为了辞赋史上的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