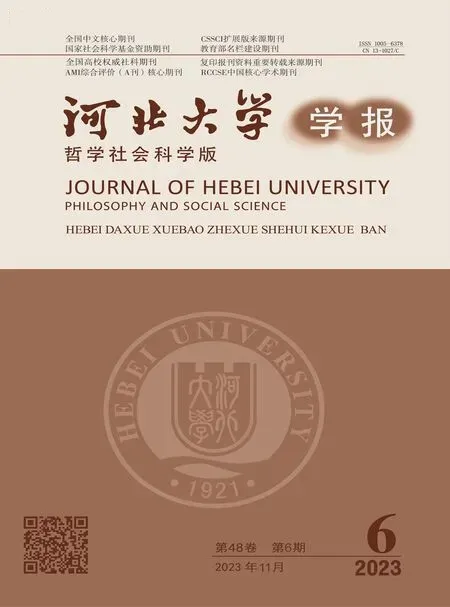驿路唐诗对边域陌生事物的书写
吴淑玲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一、引言
用“边域”而不用“边塞”,因其空间范围有别。“塞”,许慎《说文解字》释为阻隔,与“边”连用,指边防上用以阻断不同政权或国家随意往来的要塞。如《左传·文公十三年》:“十三年春,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1]291桃林塞,即陕西潼关和黄河相夹的军事要地、关口和防御工事。《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自殽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险易皆明知之”[2]2316“殽塞”即崤山,有函谷关。《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2]2694成皋、白马津、飞狐口,都是历史上的著名要塞,大行之道,即今河南沁阳境内太行山内狭长的易守难攻的通道。由以上各例可知,“塞”是具体的点或线。边塞,指带有军事防卫性质的险要地带或边邑城塞。“域”的指向范围则宽泛很多。许慎《说文解字》:“或,邦也。从囗戈,以守其一。一,地也。域,或从土。”[3]631“或”是“域”的古字,指一定范围内的疆域领土,如《诗经·玄鸟》:“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朱熹解释:“域,封境也。”[4]256《史记》中“诸侯各守其封域”“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2]246,685,都是指一定的地理空间。它没有“塞”的阻隔指向,也不是不同政权的区分线,而是指有一定管控权限的空间,涵盖范围较边塞更为广阔。
《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5]220可见“封疆之界”不是“域民”之边线,而要以“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为标准,可以打破封疆之界、冲破边塞阻隔。邹吉忠认为:“由于地缘、血缘、姻缘等现实原因和历史、文化、宗教等集体记忆的历史原因,一条人为的军事政治分界线,难以将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及其生活截然分开,特别是在和平发展时期,在国家间军事冲突和政治冲突淡化的情况下,国界不再是国家间军事与政治较量的前沿,国界两边共享资源环境和历史记忆的人民,出于共同的或相关的生活特征和文化共性,需要跨越国界的交往和互动,并逐渐形成了跨越国界的共同生活地域。在此,国界变成了跨国的边境,即共享自然资源和历史资源的人们共同或关联性的区域(本文称为‘边域’,以强调其地域性与广阔性)。”[7]11-12本文在孟子和邹吉忠“边域”概念下使用此词汇。
边域书写必然包含有边塞诗,目前学术界有关边塞诗的研究非常多,知网搜索“边塞诗”,可获得1160条资料,大部分关涉唐代边塞诗。边塞诗一定与战争、军旅相关,何新国《〈诗经〉中的边塞诗——兼谈边塞诗的起源》认为《诗经·大雅·荡之什》中的《江汉》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就已经奠定了周人的边疆观念和戍边意识①参见何新国《〈诗经〉中的边塞诗——兼谈边塞诗的起源》,《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第103-106页。该文引用《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认为边塞诗与边疆戍守、军旅生活、战争直接相关。。唐朝边塞诗的研究基本基于这一范围,虽然拓展了功业意识、苦寒生活、军级分化等,依然定位于战争、军旅、边关。任文京、闫福玲的边塞诗著作亦是此视角②参见任文京《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人民出版社2005年;闫福玲《汉唐边塞诗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而以“边域”为视角关注唐诗,尤其是关注异域风物、民族交往、民族风情等,还是近些年的事情,如王永莉专著《唐代边塞诗与西北地域文化》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西北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只是该书未涉及文学写作。论文如白登山的《诗唐·丝路·诗人——岑参的龟兹行旅与丝路创作》(《丝绸之路》2016年第7期)、吴淑玲的《驿路唐诗边域书写中的丝路风情》(《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王新宇的《探析草原风情影响下唐边塞诗中表现出的民族融合性》(《语文学刊》2022年第3期)等,但数量较少。其他关注唐代边域生活的文章多集中在竹帛考古、壁画考古、音乐流传等方面,故而本文从唐诗视角探讨边域书写,尚有较大空间。
本文以“陌生化”视角探索唐诗边域书写,借助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写作理论中的部分概念,主要指遵循内容与形式上的与众不同的原理,以陌生化常见做法即描写人们不常见的物和事,形成认知上和视觉上的新奇感为理论依据关注唐诗的边域书写,认为唐前边域书写关注面狭窄,没有对边域新奇事物的足够关注;唐前边域书写的细节描写不够充分,不足以引起世人的好奇心;唐前边域书写也缺少内心关注,情绪感染力不强,只有极少数优秀作品影响后世。而唐诗边域书写在这三个层面都独具匠心。这些诗歌以唐朝疆域辽阔、纬度变化、高低差异等导致的从中原到边域风物风情的差异为关注点,触发完全不同的观感;以异域审美心态区隔了边域与中原的界分;以同理心为向度的风物风情书写则把情谊熔铸于异域书写中。驿路唐诗对陌生事物的审美关注,拓展了唐诗的写作世界,开阔了唐人的审美视野。
二、真实视觉的陌生:铺叙描写使边域陌生事物得以真切展现
真实视觉的“陌生”,主要指亲历边域生活体验的唐代诗人对边域事物的描写。
由于唐朝国土面积空前的阔大,南北纬度、东西高度迥然不同,附着于土地上的一切,包括生物品种、植物类型、语言区域、生活习俗等,都各有特色,而那时出行主要是马步和脚步丈量,真正到过边域的诗人并不多。当时诗人走向这些从未踏上过的土地、见到从未见识过的新鲜事物,就会引发完全不同的观感,使过去在惯常环境里的固定认知受到冲击,令他们感到陌生和新奇,于是,这些新鲜事物自然而然涌入诗中,成为他们笔下扑面而来的陌生事物。
唐代诗人描写边域的陌生世界,在三个时间段比较突出,而关注点完全不同。
初唐诗人对边域世界的描写,贡献最大的当数神龙逐臣,他们因自身际遇而将笔触伸向岭南的陌生世界,大量新鲜事物涌入诗中,在南北对比的不同中展现出一个从未真正进入描写领域的世界,并在心理感觉的不适应中突出对岭南世界的陌生感。他们打开了描写岭南世界的崭新画卷。
神龙逐臣杜审言,在南贬峰州(今越南越池东南)及赦还路途上,写下了一些驿路山水诗,他从安南遇赦返回经南海时的《南海乱石山作》的景物描写,令人耳目一新:
涨海积稽天,群山高嶪地。相传称乱石,图典失其事。悬危悉可惊,大小都不类。乍将云岛极,还与星河次。上耸忽如飞,下临仍欲坠。朝暾赩丹紫,夜魄炯青翠。穹崇雾雨蓄,幽隐灵仙。万寻挂鹤巢,千丈垂猿臂。昔去景风涉,今来姑洗至。观此得咏歌,长时想精异。[8]731
诗题“南海”即今之南海西北部北部湾海域。杜审言贬谪地在峰州,诗人赦归路线很可能从越池东来,沿北部湾北上钦州,或是直接选择海路,故得以观察北部湾南海海域风景。杜审言是地地道道的中原人,北部湾海域水天相连,山石耸峙,大大小小的山石突然出现在海面上,高低不一,大小不均,没有规律,没有次第,星罗棋布,刀削斧劈,藤萝倒垂,怪态百出,是传说中的也是杜审言笔下的乱石横生之地。这些景物,今天已成旅游胜地,可在当年却是履危蹈险之路,因其景色奇异,诗人奇之,甚至想象其中多“精异”,故而罗列新鲜事物,光怪陆离,异彩纷呈,正是赦归时才拥有的异域审美之心。
同时期逐臣宋之问被贬泷州(今广东罗定),写有《早发韶州》:
炎徼行应尽,回瞻乡路遥。珠厓天外郡,铜柱海南标。日夜清明少,春冬雾雨饶。身经大火热,颜入瘴江消。触影含沙怒,逢人女草摇。露浓看菌湿,风飓觉船飘。直御魑将魅,宁论鸱与鸮。虞翻思报国,许靖愿归朝。绿树秦京道,青云洛水桥。故园长在目,魂去不须招。[8]654
韶州,今广东韶关。诗歌首句首二字便以“炎徼”称呼自己所在的韶州,认为那里是南方炎热边区。三、四句以“珠厓”“铜柱”标注自身所处极边位置。五、六两句从四时日夜的角度写此地不见朗朗晴空反而整日雾雨连绵。七、八两句从身体的感受写岭外的炎热和瘴疠。九、十两句写从未听说和见过的怪物“含沙”(传说中叫“蜮”,能含沙喷人致死的怪物)和女草(又称葳蕤草、玉竹,竹节似虫,样貌吓人)。十一、十二两句“露浓看菌湿,风飓觉船飘”小大映衬:菌小而湿,北方人难以理解;风飓船摇,更令中原旱鸭子难以忍受。十三、十四两句“直御魑将魅,宁论鸱与鸮”从整体上概括岭外除魑魅鸱鸮别无他物的特点。全诗二十句,有十四句使用铺排手法,罗列南贬路上所听所见所感的千般不熟悉、万般不适应。这种对所历环境的陌生感觉,从视觉、感觉上冲击着宋之问的心灵。
沈佺期的《度安海入龙编》则是从安南物产的视角写所见之新奇和不适:
我来交趾郡,南与贯胸连。四气分寒少,三光置日偏。尉佗曾驭国,翁仲久游泉。邑屋遗甿在,鱼盐旧产传。越人遥捧翟,汉将下看鸢。北斗崇山挂,南风涨海牵。别离频破月,容鬓骤催年。昆弟推由命,妻孥割付缘。梦来魂尚扰,愁委疾空缠。虚道崩城泪,明心不应天。[8]1052
“贯胸”指神话中的贯胸国。《山海经·海外南经》:“贯胸国在其东,其为人匈有窍。”[9]80-81交趾与贯胸连用,突出其极南之地。三、四句从诗人对气候和日照的感受写其与北方之不同。“尉佗”六句记述南粤的人文历史。接下来越人捧“翟”(以长尾山鸡尾制作的当地特产装饰品)敬献大唐王朝,唐将南下视察异域之物,颇有唐人以俯视之态管理此地的骄傲。十一、十二句则是从平原走出去的沈佺期的奇异感觉:北斗垂挂于山而非空中,涨海牵住长风使海浪悬卷。极边之地的地理感知、历史感触、物产感觉都与中原不同,让诗人确确实实体味到已经远离京都和家乡,故而结尾有“梦来魂尚扰”“虚道崩城泪”之伤。这是被贬路途上的心境,不仅没有因大唐版图辽阔而精神振奋,反因远赴遥边而伤心落泪。而待其返归时,便能以探异之心描写所见之新奇,其《从崇山向越常》写道:
朝发崇山下,暮坐越常阴。西从杉谷度,北上竹溪深。竹溪道明水,杉谷古崇岑。差池将不合,缭绕复相寻。桂叶藏金屿,藤花闭石林。天窗虚的的,云窦下沉沉。造化功偏厚,真仙迹每临。岂徒探怪异,聊欲缓归心。[8]1053
《全唐诗》诗题下按语:“九真国。崇山至越常四十里。杉谷起古崇山。竹溪从道明国来,于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欹缺。藤竹明昧,有三十峰。夹水直上千余仞,诸仙窟宅在焉。”[8]1052-1053可见诗人正是探异心理,视返归之路的崇山峻岭、竹溪曲折,林树合盖、藤桂缠绕、天深云低为人烟不见的神仙境界,称之为“造化功偏厚,真仙迹每临”。因为“探怪异”之心,他将种种中原不见之奇景,当作神仙之游的场所,以缓解自己渴望北归之情,颇有“兹游奇绝”的审美治愈之功。
神龙逐臣之所以能够对诗歌题材有这些拓展,主要是他们被迫走向了岭南,见识了岭南与中原的不同,正如尚永亮所说:“岭南山水大量进入诗歌领域则自神龙逐臣始。”“岭南天气炎热,雨水淫多,四季转换、风俗物产都与诗人们熟悉的中原相去甚远。在贬谪生活中,这些迥异于此前经验的物色既吸引了逐臣的目光,也加深了他们内心的焦虑,并成为其诗歌中反复吟咏的对象。”“把祖国东南隅诸多神秘物象、风土人情展现到世人面前,既使诗歌呈现出奇异色彩,又给后人留下了第一手的历史资料。这无论从文学角度还是从史学角度看,都是很有价值的。”[10]141-142
盛唐边域书写主要代表是边塞诗人群体。他们走向边塞多是追求功业理想,颇有盛唐精神,描写异域风光往往带着欣赏奇景的心态,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岑参。
岑参两次边塞从军,都在西域,天宝八载到十载(749—751)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天宝十三载到至德二载(754—757)任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幕府判官。岑参是湖北荆州人,从水天泽国走向绝域大漠,环境变化反差巨大,而岑参是带着“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的心态奔赴西域的,故此没有把绝域大漠的寒苦当作人生的苦难,而是从奇异审美的视角描写这里的山川草木,成就了岑参边塞诗语奇、意奇、调奇的特点。从陌生化审美视角审视岑参边塞诗中的驿路诗歌,这一特点尤其出彩。岑参很多边塞诗名作写于驿路的起点或驿路上,多为描绘边塞奇异风光之作,其中最著名的是《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全诗十八句,只有六句写到送别,余则尽是轮台奇风、异雪、奇冷。风奇,能够卷地而起、吹断白草;雪奇,八月飞雪、灿若梨花;冷亦奇,狐裘锦衾为之变薄、角弓为之失控、铠甲为之难著;景更奇,雪随化随滴至冰锥垂挂,军营红旗冻成冰板。虽是送别诗,却不写武判官思乡恋家,也不言自己思念故园,更未渲染离情别绪,而用生花妙笔渲染奇景奇寒,似乎诗人只有南人到北方后的新奇快感。再如其《火山云歌送别》写扑面而来的火山景象:
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平明乍逐胡风断,薄暮浑随塞雨回。缭绕斜吞铁关树,氛氲半掩交河戍。迢迢征路火山东,山上孤云随马去。[15]343
这是一首边塞驿亭送别诗,却尽情描写火山奇景。首两句写实,第四句以鸟不敢飞来烘托火山云高恐怖,五、六句在平明与薄暮的对比中,衬托出火山云的变化无常,七、八句用一“吞”一“掩”,夸张渲染火山云远侵近略的威力和气势。诗人送别的朋友,就要在这火山狂云的环境中踏上遥遥征途,孤人独马,寂寞前行,但诗中没有送别的伤感,只有驿路上的奇丽景色,还透出一种豪迈和爽朗的气质,见出诗人在征战生涯中磨砺出来的坚强意志。诗中的“火山云”奇异可惧的景象异常突出地刺激着阅读者的感官,令人为西域的独特自然景观赞叹不已。
岑参笔下的边塞奇景还有《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经火山》等,都是奇情异景扑面而来。辛文房评价岑参诗之好奇:“参累佐戎幕,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极征行离别之情,城障寨堡,无不经行。博览史籍,尤工缀文,属词清尚,用心良苦。诗调尤高,唐兴罕见此作。放情山水,故常怀逸念,奇造幽致,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每篇绝笔,人辄传咏。”[11]443马茂元对岑参诗以“奇”写景形成的这种陌生美评议说:“他是一位富有幻想色彩的好奇的诗人,一切新的事物对他来说,有着特殊强烈的吸引力。因而冰天雪地、火山热海的异域风光,白草黄沙、金戈铁马的战地景象,呈现在他的笔底,缤纷绮彩,光怪陆离,变幻无端,惊心动魄。有时他巧妙地运用一种细腻而柔和的南方情调,渗入于豪健朴野的北国歌唱之中,使两者融合无间。”[12]292
中唐诗人描写西域则是另类陌生美,主要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因内乱无暇西顾,吐蕃趁机侵占敦煌及其以西大片地区七十余年(776—848),敦煌几乎失去中原王朝管理下的原有社会风味,而代之以吐蕃化的生活。对这种变化的反映,最典型的代表是王建和张籍。如王建的《凉州行》:
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8]3374
在王建笔下,原本繁华的丝路重镇凉州竟然处处胡兵,曾经的万里人家不知所终,很多被掳掠的中原妇女与蕃人成家,生子说汉话。作为占领者的吐蕃人,竟然也变化其生活习惯,从不事耕种改为种禾种黍。更为奇怪的是,占领者竟然著织锦放牧(不适合放牧穿,容易撕扯坏),养蚕缲丝织成锦以做旌旗(与蕃人旗帜用料不同),城池样貌也面目全非。蕃人干不曾干的事,穿不曾穿的衣,与其样貌极不协调,是另类陌生,更是中原人眼中凉州蕃占时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凉州的悲哀。张籍《陇头行》为同类作品:
陇头路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兵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入汉家。[8]4284
陇头之路,原是丝路要道,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而今却路断人无。凉州城原本物阜人丰、和平安宁,而今却在夜间被胡人惊扰。中原戍兵死尽,陇西土地陷落,百姓被驱赶入胡,禾黍成为胡人牧场。胡人占我土地养其子孙,逼令汉人著毡裘学胡语。蕃化的凉州哪里还有唐人的痕迹! 这种对凉州古城的陌生感,正是凉州城沦陷的标志。
晚唐国力下降,唐朝内部问题纷起,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很少有人顾及经营边域,边域问题频仍的情况有时也反映在诗人的笔下,有些作品见出晚唐边域触目惊心的乱象。如诗人许棠游边,写有《夏州道中》:
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堡迥烽相见,河移浪旋生。无蝉嘶折柳,有寇似防兵。不耐饥寒迫,终谁至此行。[8]6969
夏州,古地名,西夏发源地,在靖边县红墩界镇白城子村,陕西省最北部,唐人边域经营范围,“参天可汗道”的必经之路。诗歌虽然只有八句,却有六句铺陈书写在夏州路途所见。在这条驿路上行走,看到的是一片荒凉:茫茫沙漠,连接远方城堡;远方城堡只能通过烽烟感觉到;驿路旁没有树蝉鸣叫着折柳送别之曲(荒无人烟),只有似乎是戍守兵士的流寇(无人守卫)。连续六句的描写,让温柔富贵乡的诗人感受到了“参天可汗道”令人恐惧的萧条和冷寂。
观察上述诗歌可知,驿路唐诗中这种扑面而来的边域景色,大多采用直接描写、铺叙排比的方式,从多方位多角度尽情展开,透过地理地貌、天气变化、风物风情的迥异,淋漓尽致地刻画诗人们所看到的与中原世界完全不同的景况。由于使用了大量新鲜的词汇描写之前诗作中从未或很少出现的事物,就有不熟悉,不习惯,不常见的感觉,就给读者造成了感受的难度和理解的深度,唤醒人们的注意和思考,使其诗作在陌生化视域里产生出一种奇崛的艺术效果。
三、心理视觉的陌生:以中原中心视角进行边域书写
中原中心,是先秦儒家经典文本中边域书写所突出的核心精神,是汉代大一统帝国形成后共有的人文主义倾向,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南北之间反复书写和争夺的话语权之一。先唐时期的中原中心主义的典型体现就是华夷之辨,所谓“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6]121,“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5]138,“今也南蛮舌之人”[5]239,都体现着先秦儒家经典轻视四夷的价值取向。汉代虽有司马迁主张天下一家,但在南越王尉佗心中自己仍是“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2]2698。《汉书》称汉代天下是承平之业,“匈奴称藩,百蛮宾服”[13]1143。南北朝时期,南方将中原文化带走,自视为华夏文化中心。北方则因为地理优势自认为是中原正统的承继。在中原中心的心理驱使下,四夷被视为蛮荒之地,以致中原常有以夏化夷思维。
唐朝统治者因为身体里流淌着鲜卑族的部分血液,也因为有比较开放的华夷一家思想,不再追求华夷之辨,但在中国这个儒家思想浓郁、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国度,中原、京都,依然是人们心目中的中心,是人们共同趋向的地方,就如同今人趋向北上广。唐代诗人大多有京都生活经历,京都情结是他们永远的追求。乡土,则是农业文明国度的人们永远牵挂和无法忘怀的地方。而从中原走向边域的诗人们,经历了从中心走向遥远、从繁华走向偏僻、从安适走向动荡的多层转变,这种转变既是地域的、自然的,也是身体的、心理的。对于这种变化,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绝不接受、有的人则欣然领受。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有不少诗人在稍有沉潜后,通过内地与边域的理性考量,呈现出从中原中心所审视的边域生活的异域特质。
在唐人驿路诗歌反映边域生活的作品里,比较典型的出自中原视野的主要集中在初盛唐两个时期。神龙年间走向南方边域的逐臣群体,多因被逐而心有不甘,而心念京都和家乡,因而其异域审美中颇多狞厉之美、感伤之美。盛唐走向西域的诗人大多怀有功业理想,其关注异域是以积极昂扬的心态面对雨雪风沙火山热海。但他们不是铁甲金戈而是人,也有人的思乡恋家情感,故而诗歌中也有一些中原视域下的异域审美带着新奇,带着对比,带着思乡的感伤。中晚唐因为管辖范围缩小等原因,诗歌里反映西域的作品相对较少,直到张议潮率归义军回归之后才有一些作品。由于东北部边域缺少异域风情,故我们主要关注神龙逐臣和盛唐边塞诗人的作品。
神龙逐臣被大批贬谪到南荒,岭南山水扑面进入诗人视野,而逐臣的内心中,多是将京畿和故乡作为参照物审视自己的南荒境遇,如杜审言《早发大庾岭》表现的是诗人心心念念牵系京都、故乡,在心理世界和自然世界里同时感受到了中原与遥边的不同:
晨跻大庾险,驿鞍驰复息。雾露昼未开,浩途不可测。嵥起华夷界,信为造化力。歇鞍问徒旅,乡关在西北。出门怨别家,登岭恨辞国。自惟勖忠孝,斯罪懵所得。皇明颇照洗,廷议日纷惑。兄弟远沦居,妻子成异域。羽翮伤已毁,童幼怜未识。踌蹰恋北顾,亭午晞霁色。春暖阴梅花,瘴回阳鸟翼。含沙缘涧聚,吻草依林植。适蛮悲疾首,怀巩泪沾臆。感谢鹓鹭朝,勤修魑魅职。生还倘非远,誓拟酬恩德。[8]623
此诗,《全唐诗》置于宋之问名下,显然有误,据“适蛮悲疾首,怀巩泪沾臆”透露的故乡情结,当在杜审言名下。“巩”是巩县,神龙逐臣中,怀“巩”之人恐怕只有其父在巩为官并“宰邑成名”的杜审言了! 在杜审言笔下,大庾岭成为他心理的华夷之界。在这一特殊界限上,他“登岭恨辞国”“踌蹰恋北顾”,笔下的梅花也影响了春日的温暖,鸟翼会因瘴疠缭绕损伤了翅膀,传说中含沙喷人的怪物因有水涧颇多聚集,别称吸血仔、索血草的吻草也依树林直立排行。这些当地特有的物产用中原少见的语汇描写出来,催化了杜审言的“适蛮”感觉,让他在时时北顾中与中原进行对比,突出了这里环境的狰狞感,荒野的鬼魅感。其《旅寓安南》则是从中原人的四季感知中体味到安南的“风候”之“殊”:
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催。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8]734
此诗杜审言的笔触主要放在安南风物上,但一“殊”字暴露了杜审言的立足点及其内心深处的对比心理。在杜审言的观察视野里,处处以中原作为对照,比出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安南世界:安南没有中原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该寒时不寒,不该热时已如暖夏。仲冬应是满目潇潇树叶落尽,安南却绿叶繁茂山果始熟。正月里三九天气,本该冻手冻脚,安南却鲜花漫野,胜似春天。安南雨雾弥漫永无晴日,北方下霜的季节这里竟阵阵雷声。安南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是没有春夏秋冬的世界。有人说,永远的绿色永远的花朵,不是很美吗? 但在有些人看来并不好。鲁迅先生曾说:“我本来不大喜欢下地狱,因为不但是满眼只有刀山剑树,看得太单调,苦痛也怕很难当。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 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14]374这种心理恐怕正是让杜审言想念四季分明、晴空万里的家乡的原因。杜审言笔下所描写的,是一个自己感觉到完全陌生的世界,一个让他感受到身在异域的世界,一个疏离了中心的世界。
神龙逐臣宋之问,被贬泷州(广东罗定)。罗定位于广东省西部,广西梧州南部,史称“门庭巨防,抚绥重地”“全粤要枢”。宋之问要到达贬所,也要经过大庾岭、桂江等,其《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把“洛浦风光”作为对照标准,比出了过大庾岭时所感受到的不堪忍受的陌生环境,尤其是大庾岭之外“崇山瘴疠不堪闻”的恶劣环境和“南浮涨海人何处”的迷茫心慌。其南贬路上的《经梧州》则同杜审言诗一样,从季节变换的角度写岭外的新鲜和陌生:
南国无霜霰,连年见物华。青林暗换叶,红蕊续开花。春去闻山鸟,秋来见海槎。流芳虽可悦,会自泣长沙。[8]639
诗题“经梧州”点明了写作地点和写作状态是典型的驿路诗歌诗题。“霜霰”,是北方特产,中原气候,“南国”说明所写是诗人贬谪经行之地,“无”,是宋之问在视野上的观感和心理上的比较。这种将南国与中原的比较始终在诗中流淌:南国没有冰霜雪霰,常年花开不断,林木没有落叶萧萧,树叶悄悄变换,春去鸟还在,秋凉筏泛海。一年四季,美景不变。但诗人排比这些完全不属于北方的景物,不是为了赞美,而是为了以乐景衬哀景,以抒发“流芳虽可悦,会自泣长沙”的不良心绪,意即流芳虽可悦,而我心沉重,伤比贾谊,难以被流芳感动。
如果说,初唐时期描写边域较多的神龙逐臣是以中原为中心审视异域的种种不能适应,那么,盛唐描写异域较多的边塞诗人则是把边域之异作为思乡情怀的比照或英雄主义的寄托。边塞诗人群体中,以中原视野写边域的驿路诗以岑参为多。如岑参的《宿铁关西馆》:
马汙踏成泥,朝驰几万蹄。雪中行地角,火处宿天倪。塞迥心常怯,乡遥梦亦迷。那知故园月,也到铁关西。[15]483
诗歌落笔在西域,所写途程景色“马汙踏成泥,朝驰几万蹄”展示的是西域长路漫漫、驿路泥泞、大雪铺地、关塞遥远的境况,但其关照点在中原,“地角”“天倪”都是从中原视野出发认识的西域世界。此诗不仅从中原看西域,也从西域看中原。中原乡远,梦中都可能迷路,这是西域与中原的距离。而令诗人心中稍有慰藉的是故园月色,他像一个懂事的朋友,走了千里万里,来到地角天涯看望诗人,让诗人稍解思乡之情。其《轮台即事》是到达轮台后第一个秋天所写,之前的《首秋轮台》就明确点出轮台是心中的“异域”,概括了轮台“异域阴山外”“夏尽不鸣蝉”的特点,此诗则全方位描写轮台的异域特质:
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三月无青草,千家尽白榆。蕃书文字别,胡俗语音殊。愁见流沙北,天西海一隅。[15]489
“风物异”是此诗诗眼,首联下句交代地理位置,“古单于”将视野引向种别域殊的民族。三月,中原风和景丽的季节,这里却青草不见,文字是“蕃书”,语言、风俗也与中原不同。种种与中原对比中的不同,让岑参真切感受到了自己作为中原人闯入异域,体味到被异域风调包围的滋味。其《安西馆中思长安》,时时刻刻将帝乡京邑挂在心中:
家在日出处,朝来起东风。风从帝乡来,不与家信通。绝域地欲尽,孤城天遂穷。弥年但走马,终日随飘蓬。寂寞不得意,辛勤方在公。胡尘净古塞,兵气屯边空。乡路眇天外,归期如梦中。遥凭长房术,为缩天山东。[15]252-253
“家在日出处”,一语双关,一指从安西视角感受的日出方向,一指帝王所在地。诗歌将常见的东风,当成来自帝乡的信使,认为东风应该将帝乡的温暖和情义带到辽远的绝域,但可惜的却是这里与帝乡音信难通。于是,身在大漠的异乡感涌上心头,地理、景物、生活都不再是“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时笔下的热闹纷繁激情洋溢了,而是“绝域地欲尽,孤城天遂穷。弥年但走马,终日随飘蓬”“胡尘净古塞,兵气屯边空”。从家乡或京中生活看,这都不是诗人想要的,他现在最希望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故而痛苦地感受到乡路遥远,归期如梦,只好想象使用缩地之术,将家乡拉到天山旁,以解自己的思乡之情。
大历诗人戴叔伦,史料记载没有从军经历,任文京《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中出塞和游边诗人统计表中也没有他,但他的《转应词》“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以及诗作《边城曲》似乎说明他有过游边经历。其《边城曲》曰:
人生莫作远行客,远行莫戍黄沙碛。黄沙碛下八月时,霜风裂肤百草衰。尘沙晴天迷道路,河水悠悠向东去。胡笳听彻双泪流,羁魂惨惨生边愁。原头猎火夜相向,马蹄蹴蹋层冰上。不似京华侠少年,清歌妙舞落花前。[8]3070-3071
戴叔伦诗的观察点是京都,想象的是边城远行客八月里的遭际:沙碛霜风裂肤、百草衰颓、晴天尘沙迷路、夜晚响彻胡笳、草原上猎火相望,厚冰上马蹄踏踏。而此时的京都正是暑热未尽、秋凉未尝之时,边域戍卒爬冰卧雪,京都少年却清歌妙舞、赏花观叶。在对比中,边域的艰苦令人动容。
晚唐诗人司空图,也不在任文京《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所列诗人出塞和边游表格中,但署名司空图的《河湟有感》说明司空图曾经游边。其诗曰:
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8]7261
此诗的写作背景是敦煌陷蕃七十年后。敦煌陷落,是中原人心中的痛。从中原视角看,河湟地区始终是大唐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今却被吐蕃隔断。河湟地区经历了几十年陷蕃生活,连汉人也都被同化,开始使用吐蕃语言,并且站在吐蕃的角度开始了与汉人的骂战。写至此,一种族种被灭的悲哀立升诗人心间。龚自珍在《定庵续集·古史钩沉二》中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16]22民间说:欲灭其文化,必先灭其语言。陷蕃后的河湟地区,不仅语言改变,甚至观念改变,将自己原本的母国当作仇敌,这是从中原视角观察河湟地区的诗人所不能接受的残酷现实,是中原人民心中共同的痛。
从中原视角进行异域书写,诗人们落笔的关注点主要是四个层面:一是自然地理与中原的不同,二是物产风俗与中原的不同,三是诗人在异域产生的心理落差,四是诗人们通过对家乡的思念反衬出异域的陌生。此类异域书写,诗人落笔不管是否真正写到中原,关照事物的中心点却永远在中原。由于内心深处的中原认同,其异域书写不是在文化大同观念下展开,故而异域他乡的一切都不完美,都有缺陷,所以展示的是诗人心中边域的缺陷美。它不同于今天视界下的多样化审美,会认同各个地方的美及其存在的价值,认同每一片土地上生存的人都对养育自己土地的深情。它是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原中心描写的边域缺陷美,而衬托的是家乡和京都的完美,体现的是唐代诗人对大唐王朝的深情、对家乡的深情。
四、想象视觉的陌生:以同理心为向度进行边域书写
西方心理学领域的同理心(Empathy),也被理解成为“设身处地理解”“感情移入”“神入”“共感”“共情”等,是指人通过心理换位、将心比心的方式思考问题的心理学方法,它要求思考者设身处地地对他人的情绪和情感认知进行觉知、把握与理解,在倾听他人、换位思考、自我控制等方法的影响下解决问题,是高情商的一种表现。在诗歌描写里,我们称其为“共情”。这种方法,在唐代驿路诗歌边域书写中被屡屡使用。
在唐人所写反映边域自然和生活的驿路诗歌里,很多诗人并没有到过边域,但地理常识、笔记传说、亲历者的描述,无不丰富着他们对边域的认知,而社会交往的需要,有时又需要他们在诗作里屡屡涉及边域,尤其是驿路送别诗。
驿路送别诗描写边域,往往是被送别者要走向遥边。尽管唐王朝总体是和平安宁、青春向上的,但大唐王朝的边域仍存在问题,民族冲突经常发生,依附、被迫依附、反叛、回归,各种故事在边域不断上演,故而,走向遥边的人们不管是否带着功业理想,是否贬谪发配,都是从中心走向遥远、从繁华走向偏僻、从安适走向动荡,未来的命运都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悲剧也许会随时发生。为走向遥边之人送别,是对走向遥边之人的生命的尊重,是对友情的留恋,也能够安慰和鼓励被送行者那颗躁动不安的心。正因如此,很多送别诗都有强烈的同情心、同理心,诗人们往往通过共情手法实现对所送别之人的安慰和鼓励。而在此种写作心理下的边域书写中的异域审美,就出现了诗人不在场的异域书写。
一是不在场的好奇心理开拓的异域写作空间。写作,作为一种文学手段,有在场与不在场的分别。和后来的小说创作不一样的是,小说有“七分真实,三分虚构”说,有“集合种种,合成一个”说,有“此故事纯属虚构”说,作者可以以纯客观的不在场立场进行描写。诗歌不同。诗歌无论是写作对象涉及人和物,作者都是抒情主体,其个人情感都会在诗歌中流淌,只是他所描写的对象有在场与不在场之别。在场描写是亲历者感受到的扑面而来的异域风物风情,是在场者对场域的陌生化审美体验。不在场诗人所描写的异域世界,只能通过想象描写实现,故只有设身处地方能出现边域书写。此种写法主要出现在驿路送别诗中,如杜甫并没有到过西域,他西行最远之地是秦州,但其《送人从军》写到了安西:
弱水应无地,阳关已近天。今君渡沙碛,累月断人烟。好武宁论命,封侯不计年。马寒防失道,雪没锦鞍鞯。[8]2425
弱水,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也是《山海经》记载的一条河流。《山海经》被人们当成记录神话最多的古书,其地理价值似被忽略,其实很多地理名称在现实中实有。弱水起昆仑之北,流经青海海北、甘肃张掖、内蒙古阿拉善等地,《旧唐书·高仙芝传》记载高仙芝西征小勃律时经过此河:“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胜草芥毛发。”[16]传说中弱水水势汪洋浩荡,后变成遥远险恶的代称。弱水是水,自然无地。阳关,远在天边。杜甫送人从军走向安西,设想朋友路途艰难、路程遥远,甚至认为渡越沙碛可能“累月断人烟”。但他以同理心体味着远征之人的好武求功心态,对想象的困难根本不放在眼里。只是想到安西可能非常寒冷,贴心嘱咐朋友路滑易摔、雪厚难行,小心迷路。似乎诗人已经跟随朋友到达西域,感受着那里的天寒地冻、大雪迷茫。
岑参诗被称为“好奇”,即使在他同时代,也有人有过此类评价,比如杜甫说过“岑参兄弟皆好奇”,可见岑参的好奇心很强,探索欲望旺盛。岑参在西域曾送别同僚崔侍御还京,彼时岑参并未经历过热海,但其笔下的热海能将天地间一切煮熟、融化,其《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写道:
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阴火潜烧天地炉,何事偏烘西一隅。势吞月窟侵太白,气连赤坂通单于。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见夕阳海边落。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15]321
热海,指伊塞克湖,又名大清池、咸海,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唐时属安西节度使管辖,是崔侍御回京必经之路。据今天对伊塞克湖的了解,这里气候温和干燥,冬季最冷的一月平均气温-6℃,最热的七月份平均气温15-25℃,并不太热。大约因为这里是这个纬度少见的不冻湖,而被称为热海。岑参送别崔侍御,尚未及亲历,于是根据自己在荒远之地的体验,尤其是经历吐鲁番火焰山后的经验,将热海写成了令人生恐的开水大锅:水开如煮、青草不歇、蒸砂砾石、云彩似燃、沸浪炎波、火势吞月、热侵太白、气连赤坂,都是岑参给热海赋予的想象感受,将炎热渲染到淋漓尽致、令人生畏。岑参以“侧闻”的方式进行想象描写,使唐诗世界里首次出现“热海”的异域自然景观。这样描写,其实是岑参出于同理心为朋友此行路途的担忧,是对朋友的关心。
中唐诗人张籍,有很多岭南朋友,有些诗歌不知其写于诗人岭表之游前还是岭表之游后,但写诗时一定不在岭南,如其驿路送别诗《送蛮客》《送海南客归旧岛》。《送蛮客》以追问起笔,说炎州客路途遥远,不知多久才能到达。然后颔联、颈联就写“炎州客”路行所见所遇,“江连恶溪路,山绕夜郎城。柳叶瘴云湿,桂丛蛮鸟声”,一切都是恶的,江水溪流、高山峻岭、湿气雾瘴、蛮鸟声声(因不熟悉)。《送海南客归旧岛》设想海南客所在之地当地人的生活:竹船往来、山市卖鱼、献宝赠珠、斩象祭天,似乎诗人眼见一般。但两诗均在尾部露出痕迹,前者请远行者万一返回要向自己描述海花的情状,后诗设想异域与中原迥异的生活,可见诗人以不在场身份进行描写,以心随远行到更远的同理心,幻想着远方人奇异蛮荒的生活。
二是关切同情心理下对未知世界的困难做出推测。中国有句老话教人向善,叫作急他人之所急,想他人之所想,也就是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在唐代,走向遥边,就是走向最偏僻最不发达的地方,即使不是亲历,也能想象到那里的艰难困苦,也能体味到那里的种种不适。唐代诗人很善于设身处地,大量的送别诗都是通过设想路途艰难表达同情和关切,其中有很多诗歌所写的艰难困苦完全是异域景象。如盛唐诗人刘昚虚的《海上诗送薛文学归海东》:
何处归且远,送君东悠悠。沧溟千万里,日夜一孤舟。旷望绝国所,微茫天际愁。有时近仙境,不定若梦游。或见青色古,孤山百里秋。前心方杳眇,后路劳夷犹。离别惜吾道,风波敬皇休。春浮花气远,思逐海水流。日暮骊歌后,永怀空沧洲。[8]2869-2870
海东,大体指辽东半岛以及古朝鲜,包含今之朝鲜和韩国,在安东都护府可以监护的区域。海上诗,说明薛文学归海东之路为水路。诗歌从第三句开始,就关心薛文学的海上行程:千里万里之遥,孤舟日夜行止。海天之间,前看不见所归之国,后见不到所别之地,天海苍茫,有时像仙境,有时又像梦游。往前行,前路杳渺,往回退,徘徊不定。这是刘昚虚历薛文学之所历,想薛文学之所想,忧薛文学之所忧,尽情描写了薛文学路途上的危险和内心的犹疑。它与中原陆地的不同在于,它无论如何也看不到春天的花朵,有多少思绪只能随水空流,只能寄托在空想中的“沧洲”。
又如大历时期卢纶的《逢南中使因寄岭外故人》:
见说南来处,苍梧接桂林。过秋天更暖,边海日长阴。巴路缘云出,蛮乡入洞深。信回人自老,梦到月应沉。碧水通春色,青山寄远心。炎方难久客,为尔一沾襟。[8]3155
卢纶因路遇南中使,请他顺便给岭外朋友捎去自己的关心。他通过听闻的知识描述岭南与中原之不同,不仅仅是苍梧、桂林这些向被视为遥远的地名,更有奇特的天气:秋后的天气反而更暖,海边的天空整日阴沉,高山曲路时有彩云缠绕,深山洞穴中居住着蛮人。因为路太远,收复一封书信人都会变老,哪怕梦中信到月亮也已经沉落。卢纶凭借丰富的想象,设身处地,为朋友身在遥远、久客不归而又居住荒蛮做出种种推测,但这推测的结果反令诗人忧心忡忡。
南游曾去海南涯,此去游人不易归。白日雾昏张夜烛,穷冬气暖著春衣。溪荒毒鸟随船啅,洞黑冤蛇出树飞。重入帝城何寂寞,共回迁客半轻肥。[8]8081
诗歌首联点出所写友人的不易,接下来连用四句描写友人归来路途的艰难险阻和不适应:白天因大雾弥漫需要掌灯,北方隆冬时节南边却穿着春衣,溪水荒僻毒鸟随船聒噪,山洞黝黑毒蛇绕树乱飞。冤蛇,指岭南的报冤蛇,据传闻,这种报冤蛇,如果人碰触到它,它会随人好几里地,若伤害一条,则会引来百蛇相聚围攻。这四句所写景象极为恐怖,令人毛骨悚然、浑身发冷。诗人虽未到过日南,但却能够想象得到友人驿路行程的千难万险,是为友人悲,也是为友人能冲出灾难而深感幸运,并表示愿与友人“半轻肥”,共担当。
三是基于人类思亲念友的共情表达。共情,原本是心理学的概念,是人本主义学者罗杰斯提出的,原有三个方面的含义,我们只取其一,即取其深入对方内心去体验他人的情感、思维这层意思,这是在诗歌写作中常见的手法。这种手法与前两个层面的不同在于,前两者让读者看到了具体的事物,却未必能感动对方,感动读者,而共情方式常常能感动对方,感动读者。驿路送别诗的很多优秀诗作都是使用这种方法而成为经典的。比如宋之问的《度大庾岭》: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8]641
此诗抒尽思念乡国之苦情,引发无数南贬士人的共鸣,触发读者内心深处的怜悯和同情。诗人把大庾岭的地理界线同时定位于自己的心理界限,至此才真正感受到辞国离乡的痛苦,才真正拥有徘徊犹疑、不愿南行、切盼归家的复杂心理。在这样的情绪下,诗人的“魂”和“泪”都染上了乡国色彩,冬日的“鸟”“花”等异域奇景,不仅不能引发诗人欣赏美好事物的愉悦之情,反而令诗人更加伤感。颈联写大庾岭作为地理分界线的实景,却是另一种抒情,是反面衬托,意谓:连山雨都有停止之时,江上乌云亦有演化为美丽的彩霞之时,我宋之问的归期在哪里? 尾联“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化用贾谊典故,既点出了自己谪臣的身份,又表达了自己绝不会像贾谊那样借《吊屈原赋》咒骂社会和朝廷。“不敢”二字,降低身份,尽作可怜,把谪臣内心纠结的复杂情感和企盼被君王再度征召的殷切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调动同理心和同情心,将此诗艺术推向引发读者乡国之思共鸣的高度。抛开作者自身品格不论,仅就传情达意这一角度,此诗凭借强大的共情能力建构出了贬谪文学中的经典意象[18]。
又比如王维的《渭城曲》。此诗一作《送元二使安西》,可知送别之人是出使安西都护府。诗歌写作地点在渭城客舍,送别的方式是折柳送别,虽然只有四句,也只有一句涉及安西,但这一句却语短情长,内涵丰富。西出阳关,千里万里,因为阳关就是人们心目中遥远的所在。无故人,就是要远离乡国,远离熟悉的生活圈,变成一个无朋无亲、孤独寂寞的人,这对于一个生活在“圈子”里的人而言,实在残酷。所以劝对方再喝一杯离别酒,因为这样的机会,此地一别,则千难万难,要珍惜相聚的这一时这一刻。这是多么动情的惜别之语,这是多么不愿分别的告别! 明代陆时雍《唐诗镜》:“语老情深,遂为千古绝调。”[19]541明代唐汝询《唐诗解》:“唐人饯别之诗以亿计,独《阳关》擅名,非为其真切有情乎? 凿混沌者皆下风也。”[19]541清代吴瑞荣《唐诗笺要》:“不作深语,声情沁骨。”[19]541清代刘宏煦《唐诗真趣编》:“只体贴友心,而伤别之情不言自喻。用笔曲折。刘仲肩曰:是故人亲厚话。”[19]542这些都精粹地点出了此诗因共情而达到的表情深度,也指出了此诗成为经典的重要因素。
再如张籍的《送南客》:
行路雨修修,青山尽海头。天涯人去远,岭北水空流。夜市连铜柱,巢居属象州。来时旧相识,谁向日南游。[8]4309
从共情的角度看,此诗的“天涯人去远,岭北水空流”,是通过对举的方式,传达了诗人对所送之人的依依不舍,颇有“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般的艺术效果,“水空流”,是拟人化,以水代人,表达朋友走后自己的孤独和失落。接着诗人极力描写日南非人类居住的恶劣环境:夜市直接与铜柱(马援所立极南之界)相连、居住似鸟结巢(非人类环境)。这是“恐吓”对方,但却传达的是不希望对方远行的浓情厚谊。尾联尤其煽情:你曾经熟悉的这些朋友,没有人到日南(越南中部,属林邑国)去游览。意即你若远行,将再也见不到昔日的朋友了。诗人通过危言耸听的方式,希望阻止对方远离。这是非常另类的留住朋友的心意传达,让对方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对对方无限留恋、不忍分别的情谊。
思亲念友,尤其是对于走向异域和面对走向异域的诗人,当他们使用共情手法真切地传达这种情怀时,其所抒发的恰是农耕社会的人们最在乎的浓得放不下的情怀,因而一旦唱出并发生共情的艺术效力,就最容易产生备受国人欢迎的艺术经典。
要而言之,驿路唐诗边域书写主要是通过描写以往文学书写中很少出现的陌生事物、通过感观审美放大事物效果、在尊重词源学规则下创造新词等手法,有意识地增添陌生化审美的韵味,给读者亦真亦幻的阅读体验。所使用的三种手法中,用铺叙手法进行排比铺写的方法融入的感情因素最少,但新鲜事物接踵而至,新鲜词汇纷至沓来,带给唐诗描写领域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尤其所写事物多为唐前文学中少见之物,因而成为当时边域实地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以中原中心视角进行的异域描写,展示的是唐人内心世界里对异域世界的情感认知和认同程度,对异域景物的排斥心理,体现出长期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华夏民族对中原中心的京都乡国的执着之爱;以同理心为向度的异域书写则深入到人类最敏感、最脆弱、最温情的心灵世界,让共情的伟力在异域书写中充分发挥作用,产生了无数驿路送别的经典之作,成为唐诗传播中值得骄傲的一种诗歌题材。三种类型的诗歌都描写了以往文学书写中很少出现的文学景观,不少作品通过感观审美的强化放大了中原视域对边域事物的认知感觉,在描写奇异景观中所使用的数量庞大的创新性词汇也使得驿路唐诗边域书写迥异于以往的边域书写语言,在更丰富、更细致、更多彩的描写中增添了驿路唐诗边域书写的陌生化审美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