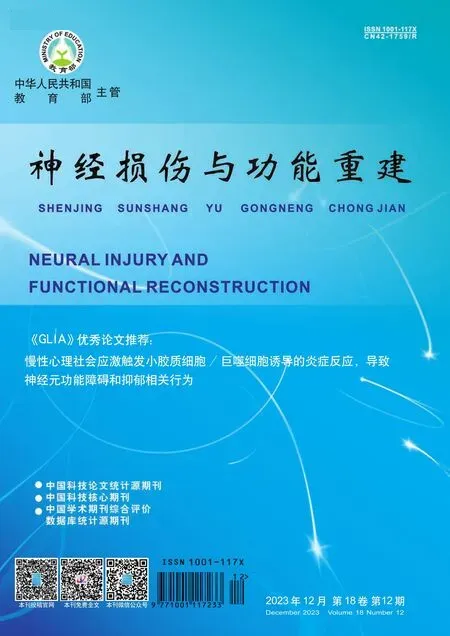Bárány协会:“颈性头晕”的观点
王钰茹(译),邢玥(译),冯宇菲(译),凌霞(译),隋汝波(审校),杨旭(审校),Barry M.Seemungal,Yuri Agrawal,Alexander Bisdorff,Adolfo Bronstein,Kathleen E.Cullen,Peter J.Goadsby,Thomas Lempert,Sudhir Kothari0,Phang Boon Lim,Måns Magnusson,Hani J.Marcus,Michael Strupp,David Susan L.Whitney
1.航天中心医院(北京大学航天临床医学院)神经内科
2.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3.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4.帝国理工学院脑科学系前庭神经病学中心
5.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学系
6.Emile Mayrisch医疗中心神经内科
7.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神经科学和耳鼻喉科-头颈外科系,
8.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9.Schlosspark-Klinik医院神经内科
10.浦那医院与研究中心
11.帝国理工学院哈默史密斯医院心内科
12.隆德大学&Skane大学医院耳鼻咽喉科和临床科学部
13.英国伦敦国立神经病学与神经外科医院神经外科
14.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神经病学系与德国眩晕和平衡障碍中心
15.匹兹堡大学健康与康复科学学院物理治疗系
1 引言
头晕和失衡与颈部病变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第一个现代假说由Barré和Lieou提出,他们认为颈椎椎体可刺激交感神经丛进而影响脑干的血流[1],之后Ryan 和Cope[2]提出颈椎病相关的颈部传入信号可能在前庭核复合体参与突触形成的调节。这些解释的一个共同的主要观点是颈部病变可以导致头晕和失衡的发生。
颈性血管性眩晕-例如在转头期间发生的极为罕见的椎动脉压迫或闭塞综合征[3]是单独的一类疾病,本文不予讨论。挥鞭损伤问题亦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其主要原因是颈部的加速度总是伴随着头部(和脑部)的加速度,因此在挥鞭损伤时颈部是否导致症状和体征的发生颇难确定;尤其是新的数据表明,前庭系统功能障碍(从迷路到大脑皮质)在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中极为常见[4],也就是说,至少在急性期,TBI 可能会干扰患者对眩晕的感知[5],这解释了急性TBI患者的症状和体征之间的不一致性[6]。描述颈部疼痛与头晕之间关系的术语很多,包括相关术语如颈性头晕或颈性眩晕;或具有病因学意义的术语如颈源性头晕或颈源性眩晕。关于颈部相关的头晕,文献中所描述的共同的特征如下[7-11]:
(1)颈部运动期间颈部僵硬和疼痛加重。
(2)颈部运动*触发短暂的失衡和(或)头晕和(或)自我运动的错觉(*研究未区分头颈部联合运动与单纯颈部运动)。
(3)颈部的直接疗法可缓解颈部疼痛、颈部僵硬和头晕。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可排除颈性头晕(见下文头晕和眩晕术语出现的章节):
(1)颈部无疼痛或不适。
(2)自发性眩晕(没有头部或颈部运动的情况下发生眩晕)或位置性眩晕(头部位置相对于重力方向发生变化时发生的眩晕)。
我们建议使用“颈性头晕”这一术语,原因如下:首先,Bárány协会用“眩晕”(vertigo)[12]定义任何原因引起的自我运动的错觉(即眩晕)。然而在既往的文献中自我运动的错觉(眩晕)这个描述在颈性头晕综合征中并非普遍存在(不常见)。相反,这些患者通常主诉至少有一种下列症状:失衡、头晕、定向障碍[13]或晕厥前症状[7],即“头晕”。虽然本文包括自我运动错觉(“眩晕”)的报道,但“头晕”的报道更为常见,因此使用“头晕”一词更为合适。换言之,多数文献描述为“头晕”,部分还有“眩晕”,因此使用“颈性眩晕”一词只符合少数文献,而“颈性头晕/眩晕”尽管描述正确,但有些冗长。由于上述原因,“颈性头晕”这一特定术语将包括少数伴有眩晕的病例,即使在名称中没有指明(注意,这种用法仍然符合Bárány 协会对眩晕和头晕的区分,正如我们对上述术语的定义)。其次,由于本病病因不明,缺乏支持关于人类此病潜在机制的确切证据,并且缺乏诊断性检查,“颈源性”一词意味着一种机制,但这个机制目前仍不清楚。因此我们建议使用“颈性”一词。
2 方法
此内容是正在制定的国际前庭疾病分类(ICVD)项目的一部分。ICVD使用结构化流程制定前庭症状和疾病的共识诊断标准。标准制定过程由Bárány 协会分类委员会审查。多学科专家自愿组成的国际团队基于现有的最佳科学证据对每个诊断分类提出初始标准。2017年3月我们撰写了颈性头晕的文献综述初稿,由小组委员会成员初评,之后收集、合并评审意见形成初步的观点共识,并于2019年11月在柏林向分类委员会提交。本文的观点在ICVD分类委员进一步讨论和细化。为了这些内容广泛适用于可能诊治该综合征的各国医务人员(耳鼻喉科医师、物理治疗师、神经生理学家、听力学家、神经内科医师、神经外科医师、心脏科医师和全科医师),经反复斟酌、仔细考虑后,提出了以下观点,以供大家参考学习。
3 流行病学
目前,尚缺乏颈性头晕相关的高质量流行病学数据,原因很简单:①缺乏诊断共识;②缺乏公认的诊断检查;③患者以不同的方式就诊于不同的专科医师。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研究[14]表明,颈部疼痛是全球第4 常见疾病(全球时点患病率为5%)。一项评估797 人的人群样本研究发现,颈部疼痛的1年患病率为68.4%[15]。而头晕(包括平衡障碍)和眩晕每年影响11%~20%的人群[16,17]。由此可见,人群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同时出现头晕和颈部疼痛症状,这二者也许关联不大。
颈性头晕的支持者指出,颈部疼痛和眩晕均由头部运动触发。然而,头部运动通常会加重几乎所有前庭疾病的症状,基于此,那些伴颈部疼痛的前庭疾病患者似乎可发生“颈部介导的头晕”—尤其是在没有彻底排除与其他前庭疾病共病时。事实上,Ryan和Cope[2]在1955年首次提出了颈性眩晕的躯体感觉假说,该假说很可能是来源于伴发颈部疼痛的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BPPV)病例的观察(尽管Robert Bárány 在1908 年提过BPPV,但直到1952年Dix和Hallpike发表后才被关注[18])。此外,无论何种病因引起前庭功能障碍,颈部疼痛几乎是公认特征,患者会因避免头部运动加重眩晕而导致颈部僵硬和疼痛[19]。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偏头痛,它是头晕(尤其是失衡[20])和眩晕的常见原因,也与颈部疼痛独立相关,在偏头痛患者中[15],颈部疼痛的1年患病率为76%。由此可见,即使不涉及颈源性问题,亦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头晕和颈部疼痛之间的关联性。
4 病理生理学
在此,我们回顾了颈性头晕的病理生理学,以提供一个合理的方案进行研究和管理。
4.1 躯体感觉传入假说
通常认为,前庭系统是多模态感觉运动系统的一部分,在该系统中,迷路产生的信号与其他感觉传入相互作用,这意味着前庭传入及其产生的症状亦可能起源于其他的非迷路终末器官或系统(如肢体和本体感觉,下文将讨论)。尽管如此,那些被证明与前庭信号密切相关的结构,并不能自动预测该结构功能紊乱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症状。例如,眼外肌受投射到前庭核[21]的肌梭密集性支配,但前庭疾病却很少在眼肌疾病、斜视手术或肉毒杆菌注射等干预治疗时发生。
颈部本体感觉信号是前庭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动物研究表明,颈部传入为前庭核复合体中的次级前庭神经元提供传入信息[22-27]。Ryan 和Cope[2]提出,这种生理联系可以解释头晕的发生,即异常的颈部关节本体感受器可以调节前庭神经元的活动,从而导致头晕和失衡发生。Brown[28]认为,异常的颈部肌肉本体感受器(包括肌肉疾病或与疼痛[10]相关的运动减少)可能产生颈性头晕,由头部运动时预期信号(感知副本)和实际信号(包括前庭和本体感觉传入)失匹配导致。事实上,灵长类动物主动头部运动时,在产生前庭-脊髓反射[29,30]的前庭核神经元以及上行丘脑后皮质前庭通路中发现了前庭传入的抑制[3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前庭传入的抑制只发生在预期信号和真实的颈部本体感觉信号反馈一致时,并且由小脑依赖机制介导[32]。
当灵长类动物的前庭传入不稳定(例如外周前庭损伤)时,颈部传入信号(包括颈部本体感受及颈部运动感知副本信号)在前庭神经元水平以反射及前庭上行通路形式对迷路来源的信号进行了部分替代[31,33-36]。因此,总体而言,前庭通路中颈部传入信号对迷路来源信号的替代,和(或)预期与真实头颈运动之间的失匹配,可能为异常的脑干前庭信号通过前庭丘脑中继通路传递到皮质区域提供了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前庭皮质处理(在动物[37]和人类[38,39]的解剖结构中,前庭皮质处理广泛分布于大脑皮质)依赖于感知和非感知机制如姿势控制[5]。因此,在皮质水平定位的前庭信号并不能表明其与感知和症状产生的必然相关性。尽管异常的脑干可塑性可能会导致人类慢性前庭症状的发生,但是,前庭高阶过程(包括感知和非感知机制)可能自下而上地主导了[38,40,41]外周前庭功能障碍的症状是否恢复。
跨物种研究发现,在上颈部肌肉或周围注射局部麻醉剂,低等哺乳动物、灵长类动物和一名健康人类受试者[44]均出现步态共济失调,然而动物出现诱发性眼震,健康受试者未出现眼震,也没有明显的旋转错觉和疼痛症状,但有倾斜、失衡和定向障碍以及位置诱发的倾斜感(持续数小时)。事实上,本研究中使用局部麻醉影响了其作为颈部头晕模型的适用性。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更现代方法如使用肉毒毒素(A 型肉毒毒素)治疗颈部肌肉肌张力障碍(通过γ运动神经元影响肌梭),却不会诱发眩晕发生[45]。
在黑暗的空间中,头部固定、躯干旋转时,颈部传入可在人体中产生微弱的颈眼反射(cervico-ocular reflex,COR)眼球震颤。研究发现40 名健康受试者与30 名存在上颈椎[46]病变患者的COR类同。外周前庭功能障碍患者COR异常更为显著[47],颈肌振动[48]或前庭康复训练[49]可增强此类患者COR,表明COR的可塑性。在前庭功能正常时COR 增强也可见于小脑疾病,然而,头部相对于躯干或躯干相对于头部旋转未能诱发头晕或眩晕症状[50],提示明显异常的COR可以不伴有头晕等症状。
一项[51]针对颈性头晕的颈部本体感觉假说的调查研究,研究人员在肌电图引导下将生理盐水注射到健康受试者的C2/3椎旁肌肉后,受试者头部偏心旋转30°的准确性下降(与基线相比),但中立位的头部定位的准确性不受影响。虽然这个研究支持颈部头晕的本体感觉模型,但有几个局限性[51],包括:①头部在空间位置的基线不对称;②缺乏头位准确程度与疼痛程度相关的报道;③疼痛消退后仍持续存在功能缺陷(弱化了疼痛与头颈体位功能受损之间的联系);④11名受试者中只有4名报告头晕和失衡,这表明头颈位置准确性受损与通常假定的颈性头晕的症状(疼痛)和体征(不平衡)之间的联系并不一致。
尽管有动物生理学和人类实验研究[44,51]支持躯体感觉假说,但对该假说进行相关实验评估时,还是需要控制重要的混杂因素。例如,实验已经证明关节运动可诱发眼震伴有相对运动错觉[52],但没有证据表明慢性上肢疼痛患者常主诉头晕(就像许多重度颈部疼痛患者没有头晕一样)。事实上,基于“躯体感觉假说”,大多数重度颈神经根病患者应该发生头晕,而且头晕应与颈部本体感觉受损程度相关。另一方面,由于前庭环路的适应可塑性,大多数本体感觉受损的颈神经根病病程常呈慢性化,可能不会引起头晕。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目前尚缺乏前瞻、盲法和对照的研究以评估重度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的头晕机制、发生率以及其病情演变、手术干预后的随访。
人类的另一个复杂性在于高级中枢对低级中枢的控制,在没有任何外周前庭激活或任何头部或身体的实际运动的情况下,不仅可以诱发眩晕错觉,而且仅凭“暗示”[41]就可以诱发眼震。事实上,人类前庭感觉和前庭反射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偶联,亦受到健康受试者的中枢适应过程[38]或脑部疾病[5]的影响。例如,健康受试者虽然对自身运动的前庭知觉阈值和前庭-眼反射(VOR)阈值在[53]量级上重叠,但知觉阈值通常大于VOR 阈值,但这种感知-反射差异在表现为“前庭失认症”(vestibular agnosia)的脑功能障碍患者中被大幅放大[5,54](前庭失认,即使强烈的外周前庭刺激也不发生眩晕)。训练中适应了前庭刺激的健康受试者(如飞行员和芭蕾舞者[38,55])可能表现出对前庭刺激的知觉敏感性降低。相反,功能性头晕(持续性姿势-知觉性头晕(PPPD)[56])患者可能对前庭感觉(包括来自预期的感觉)的敏感性更高[57,58]。颈部疼痛的45例患者,分别接受3种不同的干预措施(包括2种不同的心理训练干预、颈部振动),虽然只有振动疗法可减轻颈部疼痛,但3 种干预措施均能改善患者颈部本体觉(由盲化评估者获得)[59],说明认知对本体觉的测量结果影响非常明显。由此可见,人类的自身运动错觉、失衡、空间定向障碍、甚至是颈部本体感觉,都受到强大的自上而下的认知机制的影响。因此,所有颈性头晕的干预性研究必须双盲,并且必须是基于安慰剂或其他干预措施进行对照的治疗性研究。此外,健康受试者的中枢适应效应[38,55]和患者的脑部疾病[4,6,60](如TBI)对感知-反射的失偶联问题,提示在颈性头晕研究中需严格制定患者的纳入标准。
4.2 触发偏头痛的假说
前庭性偏头痛的共识定义[61]包括“头部运动诱发的眩晕”,如果合并颈部疼痛和僵硬,则会出现颈性头晕的临床症状。颈性头晕的核心特征是颈部疼痛,三叉神经环路传入在这些患者中普遍存在,三叉神经激活亦参与了偏头痛发生。该理论认为颈部疼痛可通过触发前庭性偏头痛这一间接通路发生头晕。反之,偏头痛可引起继发性颈部僵硬[15],再次产生颈性头晕的临床症状。此外,前庭性偏头痛急性期,95%的患者出现头晕和步态共济失调[62]。因此,偏头痛是诊断颈性头晕的一个重要混杂因素。事实上,正如Goadsby[63]所指出的,颈部疼痛可能会触发偏头痛,提示颈部病变可能参与了偏头痛的发生机制。此外,偏头痛先兆期(头痛尚未开始)即出现颈部不适[64,65],使眩晕的发生机制变得复杂。另外,很可能“……偏头痛的亚型代表了一个谱系……”[66]。因此仅排除前庭性偏头痛是不够的,谨慎的做法是排除所有偏头痛患者。虽然少数颈性头晕的干预性试验的排除标准[8]中有偏头痛,但尚不清楚在这些研究中是否采集了详细的神经系统病史以排除较轻的偏头痛表型。
由此可见,任何由三叉神经环路介导的疼痛传入都可能通过触发性偏头痛进而诱发头晕。与此一致的是,经皮电刺激诱发眶上疼痛(即非颈部疼痛),在10例偏头痛患者中有8例触发前庭眼震,对照组非偏头痛患者均未触发前庭眼震[67]。而正中神经疼痛刺激在任何受试者中都没有触发眼震(但没有记录头晕和平衡失调的症状)。支持颈源性头晕的观点认为,眶上痛患者主诉头晕的非常少见;避免触碰头皮上的痛点相对容易,而完全阻止可能引发颈部疼痛(和头晕)的转头习惯则很难。考虑到患者和临床医师的认知偏差会影响之前未考虑过的诊断的识别,因此需避免经验式的诊断(例如眶上压痛相关头晕)。
4.3 非触发偏头痛的三叉神经假说
颈部疼痛是颈性头晕的普遍特征,因此通常会累及三叉神经。虽然三叉神经刺激与偏头痛机制密切相关,但从理论上讲,三叉神经机制可能独立于偏头痛参与了颈性头晕,至少在非偏头痛患者中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颈性头痛与颈性头晕的神经生理学机制有显著重叠,尤其是躯体感觉假说[63,68]。颈源性头痛被认为是由源于颈椎局限于颅骨的牵涉性疼痛。来自三叉神经眼支和脊神经C1、C2和C3的痛觉传入汇聚到三叉颈神经核的二级神经元[69-71],导致C1-3源性疼痛可以覆盖颅骨的大部分区域。
目前尚无前瞻性对照研究评估以疼痛为主要表现的高位颈椎病变(神经根或其他部位)患者的头晕发生率,颈部疼痛治疗(手术或药物)是否减轻了头晕。一项小型研究纳入17 例颈椎间盘切除或颈椎病术后患者进行眩晕评估,没有报告有前庭症状[72]。Baron[73]回顾性病例研究纳入了147例就诊于三级“耳-神经科/头痛门诊”接受枕大神经注射和(或)附近扳机点注射患者,其中93%主诉头晕,3%主诉头痛,97%有不同程度的头晕,88%有不同程度的头痛。作者认为该枕大神经注射可治疗颈源性症状。研究发现,半数患者报告枕大神经注射后头晕改善,其改善程度略低于颈部活动范围(70%)和头痛(60%)的改善程度。本研究的主要局限性包括缺乏对照或安慰剂比较、未采用盲法评估以及注射点的选择非标准化。正如作者所承认的,最重要的局限性可能是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这意味着无法严格地对头痛进行标准分类,包括偏头痛。目前,虽然已有枕大神经注射对一系列头痛疾病有效的报道[74-76],但这些研究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如果我们认为头晕是三叉神经参与的,那么三叉神经反射可通过两种可能的机制在颈部运动时产生头晕:
(1)三叉神经-前庭反射:三叉神经作为传入神经(亦可传出)和前庭神经核有广泛的作用[22,77]。然而支持人类三叉神经-前庭反射的研究数据有限。Marano[67]研究显示,眶上骨(即三叉神经)疼痛触发的前庭机制可能支持三叉神经-前庭反射,但仅在偏头痛患者中观察到这种效应(偏头痛患者可能涉及三叉神经-前庭直接反射以外的机制)。
(2)三叉神经-心脏反射:大量文献表明,经颅刺激引起的三叉神经激活是增加迷走神经张力的有效驱动力,包括触发心脏停搏[78,79]。颈性头晕时快速转头而加重的颈部疼痛是否也会短暂影响心输出量尚不清楚,因为这需要在头部运动相关的颈部疼痛和头晕发作期间进行连续心脏监测,而据我们所知,从未有过这样的试验。然而,一项研究表明,与对照组患者相比,颈部疼痛伴头晕的患者更有可能发生体位性低血压[80]。重要的是,增强三叉神经-心脏反射的药物包括常用于慢性颈部疼痛患者的阿片类药物、治疗偏头痛药的β受体阻滞剂和钙通道拮抗剂。阿片类药物可增强三叉神经-心脏反应,也可能损害前庭-小脑功能,加剧失衡感和(或)发生失衡[81]。由此可见,在未来的确定性研究中,三叉神经-心脏反射是一个重要的潜在混杂因素,研究颈性头晕时应予以考虑。
4.4 Barré和Lieou的神经血管假说
1926 年,Barre 推测(随后由Lieou 独立提出),颈椎病对椎动脉周围交感神经丛的机械压迫可诱发椎基底动脉的收缩导致眩晕[1]。随后的动物实验不支持这一假设[82,83],因此通常认为这是一个不可信的假说[84]。
4.5 颈动脉窦综合征及相关晕厥介导的假说
另一种被提及但未达成一致的是颈动脉窦综合征假说。颈动脉窦位于颈总动脉分叉处颈内动脉起始部,是心血管系统的主要感受器。颈动脉窦综合征是由于颈动脉窦体的过度敏感,常在触诊(或按摩)时导致迷走神经介导的心脏抑制反应从而发生心动过缓和低血压。由于专家通常不熟悉其他医学专业领域,因此一些被诊断为颈性头晕的病例实际上可能是伴颈部疼痛的颈动脉窦综合征。这些患者快速转头可能会诱发颈部疼痛以及一过性心动过缓和低血压,从而导致轻度头痛和晕厥前期症状。有趣的是,晕厥专业的心脏病专科医师无法识别伴有颈部疼痛的颈动脉窦综合征,这可能是由于转诊偏倚,或者因为心脏病专科医师未询问或考虑到颈部疼痛的问题。如前所述,Morinaka[80]在对176例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发现,患有肌肉骨骼性颈痛的患者比没有颈痛的患者更容易发生直立性低血压,但年龄是一个潜在的混淆因素,因为有颈痛的患者比无颈痛的患者年龄大。一项针对健康人群的生理指标研究[85]并未显示颈部传入神经对心血管反射有显著调节。证据表明,动物的颈部传入神经对心血管反射有一定程度的调节,理论上,这种调节可能存在于一些罕见的病例中。总之,尽管理论上是可能的,但颈部疼痛可以引起心脏抑制反应的观点需要进行对照研究。
5 临床干预性研究
从试验的标准来看,许多涉及颈部手术[72,86,87]及颈部按摩[88]干预对头晕和失衡影响的研究质量都很不理想。一项关于颈性头晕治疗干预措施的系统回顾[88]表明,只有4 项研究质量符合纳入标准[8,89-91],所有研究均未提及对提供干预措施的临床医师实施盲法。事实上其他的研究质控有待提高,通常都未采用盲法、安慰剂干预或随机化。许多研究并未明确排除偏头痛或对偏头痛的遗漏进行解释,包括系统综述确认的4 项研究[92]。基于上述因素,在未来的干预性研究中排除(或控制)偏头痛作为混杂因素很重要。比如,两项干预性研究报告头痛发生率超过70%[7,91],而加重头痛/颈部疼痛和头晕的激发因素是典型的偏头痛触发因素,如压力和激素水平的波动。最后,尽管MalmstrÖm[91]在他们的一项颈性头晕的实验模型中报告了一名健康受试者的晕厥先兆,但没有研究[7-9,72,87,89,91,93-101]考虑心脏和(或)血管迷走神经介导的机制。
同一研究小组发表了两项关于颈性头晕的随机、盲法、对照干预性研究[8,9,89,98],从研究的可重复性角度来看,这是有问题的。在起初的小样本研究中[89],34例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颈部推拿干预或安慰剂(颈部激光)。虽然“偏头痛相关眩晕”被排除在外,但纳入研究的头痛患者没有详细信息,并且对进行干预措施的治疗师没有实施盲法。这项研究[89]表明,与安慰剂组相比,在第6周和第12周时,干预组10分视觉模拟量表测量的头晕和疼痛有所减轻,但使用头晕残障量表(DHI)时,两组仅在第6周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与安慰剂组相比,在任何时间段都未发现患者的平衡能力得到改善。
一项针对86 例患者的大型治疗研究,观察了接受积极治疗和安慰剂治疗后6周[8]和1年时[98]头晕和疼痛症状。研究所采用的干预措施包括:①Mulligan 维持自然体位下小关节滑动技术[102](“SNAG”,29 例);②Maitland 被动关节松动术[103](29 例),安慰剂组患者进行颈部伪激光治疗(28例)。在这项研究中,除安慰剂组颈部疼痛更严重(P=0.06)和女性相对较少(安慰剂组36%vs.干预组52%和62%)外,各组的基线特征很匹配。早期结果显示,干预组的主要结局头晕强度在即刻和12周时均有改善,而安慰剂组未观察到头晕强度的缓解。相反,在12 个月时[98],所有组的头晕强度都有显著改善,且各组之间12个月时的头晕强度没有差异,这表明,1 年时头晕强度这一主要结局,干预措施并不优于安慰剂。同时发现,所有组的次要结局疼痛在即刻和12周时降低,12个月时疼痛强度亦无组间差异。最后,干预对头晕的直接获益与头部复位的准确性或平衡能力的改善无关,似乎不支持颈性头晕与头颈部运动时受损的本体感觉和前庭输入不匹配有关这一“躯体感觉假说”。
这项唯一统计学设计较好的盲法对照研究[8,98]显示了干预的早期症状获益,但未发现对主要结局(12个月时的头晕强度)有任何影响。此外,疼痛这个次要结局和头晕的早期获益与头部复位或平衡能力的改善无关[9],这削弱了对颈性头晕的“躯体感觉假说”的支持。所有未来作为证据的干预性研究必须进行双盲和安慰剂对照。如前所述,由于人类自上而下的影响(包括预期),即使在没有任何外周前庭激活的情况下也可引起人类受试者的头晕和眼震[41]。因此仅显示一项干预措施对头晕主观特征的影响,并不能提供颈性头晕存在的证据,治疗反应不能作为任何拟用于研究的定义的一部分。
6 对未来颈性头晕临床研究的思考
支持颈性头晕诊断以及治疗的高质量研究相对较少。拟进行临床治疗和机制研究的学者,应结合与特定先验假设相关的最佳临床试验方法学(双盲、安慰剂对照治疗研究或空白对照研究)。因此,对于假说的病理生理机制,应选择主要结局(如某些临床指标)和次要结局(如实验室或机制)可量化评估的参数。我们提供了许多相关设计需注意的混杂因素及改良的方法,研究人员在设计颈性头晕研究时可以进行参考。
首先,由于颈性头晕是一种跨领域的症状学,涉及多学科专业,因此需要以多学科思维、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建议,研究团队应该是多学科的,包括(但不限于)心内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和理疗科的研究人员。
对照研究(安慰剂或空白对照)在颈性头晕研究中尤其重要。如前所述,即使在没有任何外周前庭激活[41]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影响也可引起人类受试者的头晕和眼震。在进行此类研究时,应使用相关的报告指南(如CONSORT)以确保此类研究的学术严谨性[http://www.consort-statement.org]。设计研究时,研究者应邀请统计学者参与,以确保研究具有足够的统计学意义,得出令人信服的阳性结果,并降低假阴性的风险。
鉴于对颈性头晕是否存在的疑惑,设计高特异性的研究尤为重要,这意味着不仅要有明确的纳入标准,而且要特别注意排除标准。首先,研究需纳入一组“纯”的颈性头晕患者,因此,全面排除与颈性头晕临床表现类似的前庭疾病至关重要。研究者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提高纳入对象的可信度:通过系统性评估寻找和排除BPPV 患者、任何形式的偏头痛和客观检查证实的外周或中枢性前庭功能障碍患者(例如VOR 增益降低或小脑体征)。作为经验丰富的前庭临床医师,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地先列出一些明确的排除标准,例如主诉自发性前庭症状的患者,因为在没有任何头颈部运动的情况下发生的头晕,显然是首要排除标准。
需考虑心源性诊断,并测量脉搏、血压和心电图(理想情况下可以进行动态监测)。我们强烈建议排除明显的体位性低血压(即站立时收缩压下降20 mmHg)患者[104]。如前所述,进行高质量研究设计时,注意筛查和排除由三叉神经-心脏反射或病态窦房结综合征引发的心脏传导障碍。
所有研究参与者均应仔细记录患者的用药情况,并排除服用可能影响结果的药物的患者。例如,阿片类药物、β受体阻滞剂和钙通道拮抗剂均可增强三叉神经-心脏反射(如上文所述,这是一个潜在的混杂因素)。
考虑到TBI 患者的客观和主观临床特征之间相关性较差,我们建议排除头颈部外伤患者[4-6]。对于无外伤史且神经系统检查无受损证据的患者,颈部影像学在纳入或排除标准中的作用似乎有限,系统荟萃分析表明,颈椎MR影像学与颈部疼痛之间没有相关性[105]。
一旦确定排除标准,研究者就应该考虑纳入标准。持续性的颈部疼痛和头晕且头晕因颈部运动而加重,这似乎为先决条件。之后研究者可能还需进一步确认头部固定而躯体旋转时是否也会引发这些症状,因为这种状态才是真正的颈部运动而非头部运动。基于既往提出的颈性头晕发生机制假说,研究者可能需获取颈部运动期间相关的前庭激活的客观参数(例如眼震或姿势不稳)。研究者需先定义什么是阳性结果,如5次试验中至少3 次可见的触发发作的眼震(对触发性眼震有明确定义)。一些研究者可能将颈部本体感觉异常视为纳入标准,根据他们所需的颈部本体感觉测量,可能需要开发和验证适当的评估检测手段。当然,研究者是否尝试某种颈部本体感觉的测量可能取决于他们欲验证的颈性头晕的假说,当研究涉及到颈部本体感觉受损时,进行颈部本体感觉的测量似乎必不可少。对于一些研究者而言,在激发发作期间进行连续心脏监测(以排除头晕的心源性机制)也是应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最后,研究者亦应考虑前瞻干预性研究的随访持续时间。至少1 年的随访期似乎是合理的,因为至少有一项阳性结果的干预性研究显示干预较安慰剂在早期更获益,但优于安慰剂的获益在1年时却没有差异[8,98]。
综上所述,这几方面的混杂因素使得颈性头晕的研究颇具挑战性。基于这些数据,目前我们尚不能推荐任何针对颈性头晕的特异性诊断标准,也不推荐任何的具体治疗。我们希望,对颈性头晕有兴趣的研究者,能够通过多中心、随机、盲法、对照研究设计严格的临床试验,以减少对这一个假定的临床实体(话题)认识的不确定性。
致谢
感谢复旦大学眼耳鼻喉医院王璟主任医师、湖北文理学院襄阳市中心医院常丽英主任医师、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仁医院严钢莉副主任医师、武汉市第四医院曾晓云主任医师、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李建华主任医师协助校稿!感谢宋宁、李康之、司丽红、吴月霞、马辛雁、王倩倩、汪建荣、徐源、薛思儒医师及《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杂志唐颖馨编辑协助对全文的最终修订!
备注说明:文章中的序号为英文原版中的参考文献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