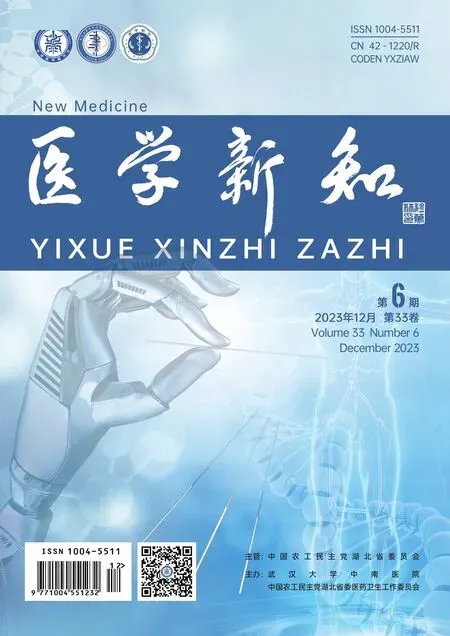母代肥胖对子代长期不良健康结局影响的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张敏杰,张敏哲,陈 锐,何启强,2
1.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武汉 430071)
2. 武汉大学深圳研究院(广东深圳 518000)
随着近年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全球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群肥胖流行率呈普遍上升趋势[1]。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自1975 年以来,全球肥胖流行率增长近三倍。截至2016 年,全球18 岁及以上成年人中超重的比例达到39%(女性为40%),肥胖的比例达到13%(女性为16%)[2]。与此同时,育龄孕妇肥胖人数也在持续增加。《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 岁以上女性的超重率为32.5%,肥胖率为14.7%,均高于2012 年的29.9%和11.7%[3]。近年来,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母亲孕期肥胖不仅与围产期及其新生儿的短期不良健康结局有关,而且还会对后代多个器官系统造成长期的健康损害[4]。为此,本文对母代肥胖引起子代长期健康损害的流行病学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制定以减少孕妇肥胖为重点的预防策略提供依据。
1 代谢相关疾病
研究显示,母代肥胖会引起子代下丘脑摄食中枢发生改变,通过下丘脑的弓状核和下丘脑旁核神经网络调节子代神经内分泌系统,引起子代食欲过盛从而导致肥胖症的发生[5]。这一过程中,瘦素起到关键作用。当母代肥胖时,新生子代体内会出现明显的瘦素激增,导致中枢性瘦素抵抗,对下丘脑摄食中枢造成永久影响,导致子代食欲过盛及肥胖[6]。另外,母代肥胖还可能导致自身脂联素水平降低以及强烈的炎症反应,最终导致子代发生血脂代谢异常、胰岛素抵抗及2 型糖尿病[7]。并且,母代肥胖会引起子代肝脏三羧酸循环、糖酵解和典型的Wnt/β-Catenin 信号调节失调,造成子代肝脏中的脂质沉积增加[8]。
1.1 肥胖症
肥胖症是一种病态状态,特征为体内脂肪过度或异常蓄积,并可导致多种慢性疾病。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女性孕期肥胖会导致后代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增加以及肥胖风险上升。Heslehurst 等进行的Meta 分析纳入了来自59个队列的79 项研究,结果显示,母亲肥胖与子代BMI 增加呈显著相关性,相比于BMI 正常组,BMI 超重和肥胖组母亲对应的后代肥胖风险分别增加了89% [OR=1.89,95%CI(1.62, 2.19)] 和264%[OR=3.64,95%CI(2.68, 4.95)],此外,母亲BMI 每增加5 kg/m2,其子代1 至14 岁期间肥胖风险增加70%[9]。曹慧等基于马鞍山出生队列研究,对2013 年10 月至2015 年4 月出生的单胎活产儿连续追踪随访至儿童4 岁,发现孕前母亲超重肥胖的儿童在4 岁时更易发生肥胖[OR=3.27,95% CI(2.15,4.98)]、腰围[OR=2.32,95%CI(1.72,3.14)]、腰高比[OR=2.29,95% CI(1.73,3.02)]超标[10]。有研究表明,母亲肥胖对子代肥胖风险产生的影响不仅限于儿童期。Hochner 在耶路撒冷开展的一项出生队列纳入了1 400 名成年人,结果发现母亲孕前高BMI 导致后代在32 岁时有更高的BMI 和腰围,母亲孕前BMI 每增加3.87 kg/m2,会导致后代BMI 平均增加1.8 kg/m2,腰围平均增加3.5 cm[11]。Dias 等分析了巴西三个出生队列(1982 年队列5 914 人;1993 年队列5 249 人;2004 年队列4 231 人)的最新随访数据,结果表明,相对于体重正常的母亲,肥胖母亲的后代在11 岁、22 岁和30 岁时BMI、腰围和脂肪质量指数更高,进一步证实了母代肥胖对子代肥胖风险的长期影响[12]。
1.2 血脂异常
脂质代谢在人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体血脂异常通常包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甘油三酯(TG)和总胆固醇(TC)等异常代谢。研究显示,母代肥胖可能会导致子代多项血脂指标异常。Bucher 等收集了98 名孕产妇血样、脐带血样以及胎盘组织并分成正常体重组(18.5 ≤BMI ≤24.9)和肥胖组(30 ≤BMI ≤45),结果显示肥胖组脐带血样中HDL-C 较正常体重组显著降低,并且肥胖母亲所生婴儿存在脂质代谢通路异常,表明肥胖母亲的新生儿可能出生时就存在脂代谢紊乱[13]。Fraser 等对英国一项前瞻性妊娠队列中6 668 对母子进行了长达9 年的随访,获得了其中3 457 名后代的完整血样检测数据,结果显示随着母亲孕前BMI 增加,子代血样中HDL-C 水平下降[14]。Gaillard 等的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对4 871 对父母和孩子进行调查,发现父母较高的BMI 与其子女在6 岁时较低HDL-C水平相关,并且母亲BMI 相关性更强[15]。
1.3 胰岛素抵抗与糖尿病
在生命早期的发育关键阶段,营养及环境因素可改变生命体表观遗传学特征,从而导致器官功能以及代谢发生终身改变。母代孕期肥胖导致胎儿在宫内处于高营养环境,可能导致后代在成年之后多种慢性疾病如2 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发病风险增加。
研究表明,随着母亲肥胖的发展,后代胰岛素抵抗严重程度会不断增加。Catalano 在一项队列研究中对53 名正常体重母亲和68 名肥胖母亲的母血和脐带血进行检测,发现肥胖母亲组的胎儿脐带血胰岛素和血糖水平高于正常体重母亲组[16]。有证据表明,肥胖母亲的后代高胰岛素抵抗可长期存在。Perng 在一项覆盖了美国波士顿地区1 708 对母亲-儿童(年龄中位数7.7 岁)的队列研究中,发现儿童胰岛素抵抗值随母亲孕前BMI增加而上升[17]。Martínez-Villanueva 将800 例肥胖患儿(平均年龄10 岁)按照父母有无肥胖进行分组分析,结果显示母亲肥胖的患儿有更高的胰岛素、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和胰岛素抵抗指数以及较低的总体胰岛素敏感指数[18]。Hochner 的研究也显示,肥胖母亲的后代在32 岁时仍然具有较高的胰岛素水平[11]。
子代2 型糖尿病风险也受母代孕期肥胖影响。Dabelea 在一项病例对照研究中分析了79 名2 型糖尿病患者和190 名非糖尿病对照者,在对后代年龄、性别和种族进行调整之后,发现母亲肥胖与子代2 型糖尿病显著相关[OR=2.8,95%CI(1.5,5.2)][19]。Eriksson 基于赫尔辛基出生队列研究对13 345 对母亲-子代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母亲低BMI 组,肥胖组母亲的后代患2 型糖尿病风险增加20%[20]。
1.4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指除酒精和其他明确因素导致以肝细胞内脂肪过度沉积为主要特征的肝脏疾病。NAFLD 是一种与肥胖相关的疾病,近年来已成为全球最流行的肝病,影响全世界约25%的人群[21]。流行病学证据表明,肥胖孕妇的子代更有可能在未来患NAFLD。在一项涉及105 对母婴的队列研究中,Modi 通过全身MR 成像和1H MR光谱评估婴儿脂肪组织分布和肝细胞内脂质含量,在调整婴儿性别、体重和出生后年龄后,母亲BMI 每增加4.2 kg/m2,婴儿肝细胞内脂质沉积增加8.6%[22]。Hagström 等纳入165 例NAFLD 患者开展病例对照研究,发现与BMI 正常的母亲相比,BMI >30 kg/m2的母亲后代患NAFLD 风险更高[OR=3.26,95%CI(1.72,6.19)],并且患重度NAFLD 的风险也显著上升[OR =3.67,95%CI(1.61,8.38)][23]。Ayonrinde 等在澳大利亚开展的队列研究发现,肥胖母亲对青少年早期NAFLD风险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母亲肥胖与女孩患NAFLD 风险上升显著相关,而在男孩中这一关联并不存在[24]。目前关于母代肥胖与子代NAFLD关联的流行病学研究较少,有待更多研究进一步探索。
2 心血管疾病
母代肥胖会导致胎盘血管异常,包括血管密度增加、血管成熟度降低和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等,而这些都会损伤子代心脏的收缩功能以及发育,导致子代之后更易出现血压异常以及心脏功能障碍甚至结构性心脏病[25]。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母亲肥胖对子代心脑血管健康具有重要影响。Jansen 对587 对母婴调查发现,肥胖母亲的新生儿出生时就具有较高的血压,并在一年内都会保持较高水平[26]。Gaillard等招募2 804 名澳大利亚孕妇并随访后代直到17 岁,分析结果显示母亲肥胖会增加后代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不良心脏代谢危险因素,母亲孕前BMI 每增加4.2 kg/m2(SD),会导致子代收缩压增加0.8 mmHg(1 mmHg=0.133 kPa),血糖上升1 mmol/L,血胰岛素上升1.1 μU/L[27]。Hochner 在耶路撒冷进行的出生队列也发现,后代在32 岁时的收缩压和舒张压与母亲孕前BMI显著正相关[11]。
此外,Razaz 基于瑞典人群队列研究显示,在1992—2016 年登记的两百万对母婴中,与BMI正常母亲后代相比,超重[HR=1.10,95%CI(0.97,1.25)]、一级肥胖[HR=1.16,95% CI(0.95,1.43)]、二级肥胖[HR=1.84,95%CI(1.36,2.49)]、三级肥胖[HR=2.51,95% CI(1.60,3.92)] 母亲的后代缺血性心脏病、心衰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随着母亲的肥胖程度增加而增加[28]。Forsén 针对3 302 名芬兰男性的研究表明,母亲孕前BMI指数越高,其后代死于冠心病的风险就越大[29]。Reynolds 在苏格兰的一项队列研究纳入了37 709名儿童,发现肥胖母亲的后代在31~64 岁由于心血管事件住院或早逝的风险更高[30]。这些研究表明母代肥胖可对子代心血管健康产生持久影响。
3 神经认知发育和精神障碍
母代肥胖会导致胎儿大脑结构和基因表达发生变化,包括第三脑室、下丘脑区域和大脑皮层的干细胞增殖和神经元成熟减少[31]、海马祖细胞分裂和神经元生成受损[32]、大脑的炎症和氧化应激增加、单胺类神经递质信号和下丘脑氧合信号失调等[31],这些都可能导致子代的不良神经发育和精神障碍。
研究表明,孕期母代肥胖与后代神经认知发育和精神障碍有关,这些障碍包括认知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脑瘫(cerebral palsy,CP)等。Dong 等对武汉健康婴儿队列中3 598 对母婴的分析显示,相较于正常体重组,超重/肥胖母亲组的孩子在2 岁时智力发展得分更低[β=-2.51,95% CI(-4.82,-0.20)][33]。Basatemur 对英国千禧队列的分析结果显示,在调整了多种社会人口学混杂因素之后,母亲孕前BMI 与孩子认知表现呈负相关,并且这种关联可能随年龄增长而变强[34]。两项基于丹麦出生队列的研究显示,母亲孕前BMI 和子代智商存在负相关,母亲孕前BMI 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子代智商(通过韦氏智力量表测量)降低0.2~0.3 分[35-36]。Rodriguez 对瑞典、丹麦和芬兰三个出生队列使用潜类别模型分析发现,包括孕前超重或肥胖的类别与后代ADHD 症状高分类别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孕期体重超重和体重增加较多的孕妇的孩子ADHD 症状风险是正常体重妇女子女的2.10 倍[95%CI(1.19,3.72)][37]。美国加州一项纳入620万新生儿的队列研究发现,在调整了母亲种族、年龄、教育程度、产前护理、保险状况和婴儿性别等因素后,母亲肥胖[RR=2.56, 95%CI(1.79,3.66)]或病态肥胖[RR=1.72,95%CI(1.25,2.35)]与CP 风险上升显著相关[38]。
4 过敏性疾病
母代肥胖导致子代过敏性疾病的机制较多,包括早期不良微生物群的建立、表观遗传因素的改变,以及在发育过程中接触炎症标志物,抑制胎儿糖皮质激素的产生而损害肺部发育等[39-40]。其中,研究显示母代肥胖通过表观遗传影响导致肠道微生物生态失调可能是导致子代过敏性疾病最重要的风险因素[41]。
过敏性疾病是一组由免疫系统异常反应引起的疾病,包括哮喘、应变性鼻炎、湿疹、荨麻疹等,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孕妇产前因素被认为是后代过敏性疾病的重要影响因素。产前和围产期包含了新生儿呼吸道和免疫系统的关键发育阶段,而母亲肥胖会影响宫内环境,导致后代过敏性疾病风险增加。Wei 等人在广州开展的出生队列研究纳入了12 845 名调查对象,结果显示超重肥胖母亲的子女在1 岁时患特应性皮炎的风险比正常体重组高20%,并且母亲孕前BMI 每增加5 kg/m2,其子女在1 岁时患喘息的风险增加13%[42]。Rosenquist 对美国北加州医疗卫生系统2005—2014 年登记的母婴对进行随访,结果显示4 岁队列儿童哮喘风险随着母亲孕前BMI 在18~30 kg/m2范围中增加而持续增加,在6 岁队列中,其哮喘风险随着母亲孕前BMI 在20~35 kg/m2内线性增加,提示母亲肥胖与子代学龄前或学龄早期时哮喘患病风险增加显著相关[43]。Ekström 对瑞典斯德哥尔摩3 294 名儿童随访到16 岁,发现母亲孕前BMI 和后代16 岁前哮喘总风险呈正相关,母亲孕前BMI 每增加5 kg/m2,其子代哮喘风险增加23%[44]。Liu 等在一项对母代BMI 影响子代哮喘发病风险的Meta 分析中纳入了22 项观察性研究,其中子代年龄在4 个月至16岁间,结果显示母亲孕期肥胖显著增加后代哮喘风险[OR=1.41,95%CI(1.26,1.59)],母亲孕前BMI 每增加1.0 kg/m2,后代哮喘风险增加3%[45]。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母亲肥胖对后代哮喘症发病的影响至少可持续到青少年期。
5 结语
目前,全球范围内育龄妇女肥胖率呈快速增加趋势,母代肥胖会对子代未来的长期健康产生多种不良影响,包括增加肥胖症、血脂异常、胰岛素抵抗与糖尿病、NAFLD、心血管疾病、神经认知发育和精神障碍以及过敏性疾病等发病风险。由于目前相关研究不能直接提供因果关联证据,因此未来应更关注后代长期、系统的结局指标,并加强对母代对子代健康影响因果关系、潜在机制和有效干预措施的研究。
为预防孕妇肥胖及对后代不良健康影响,应对适龄婚育妇女加强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干预。女性孕期应注意均衡饮食,补充容易缺乏的营养素(如叶酸、各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等),并且遵照WHO 对于孕妇的体力活动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 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身体活动,以促进母亲和后代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