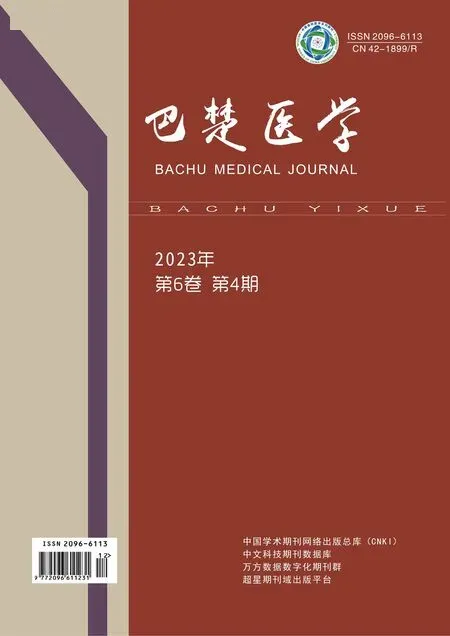DNA甲基化修饰在Graves病发病机制中的研究进展
初卫江
(莱州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山东 莱州 261400)
Gravers病(Graves' disease,GD)又称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是一种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其特点是患者免疫耐受力丧失,自身免疫细胞对甲状腺组织产生攻击,刺激机体产生促甲状腺激素受体(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receptor,TSHR)抗体,通过激活TSHR,机体产生过量的甲状腺激素[1]。GD多见于女性,患病的高峰年龄在30~60岁,60岁之后患病率显著下降[2]。在我国,GD 的发病率为15~30/10万[3]。GD 的发病机制复杂,易感因素包括环境因素、内源性因素和遗传因素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表观遗传因素在GD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4]。DNA甲基化是常见的表观遗传机制,在胞嘧啶碱基上共价加成一个甲基,随后转化为5-甲基胞嘧啶,这一过程主要由DNA 甲基转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s,DNMTs)催化完成。甲基在DNA 上的添加和去除是由特定的染色质修饰蛋白调控的,这是一个可逆的过程,并受到动态调节[5]。本文主要针对DNA 甲基化在GD 中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1 DNA甲基化与基因表达调控
异常的DNA 甲基化可导致细胞增殖失调、发育缺陷、自我更新能力受损和免疫调节异常等多种生物过程[6-7]。基因型和表型之间在某些情况下会存在差距,表型的出现并不局限于细胞内提供的遗传信息,还受到外部环境信息变化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在多细胞水平上表现出来[8]。因此,当分析原始DNA序列以获取表达信息时,必须考虑存在于原始DNA序列之外的辅助力量。DNA 甲基化被广泛认为是基因沉默的稳定调节剂,通过改变DNA 分子构型和染色体结构特性,调节遗传信息的表达[9]。DNMTs催化DNA 在特定的位置上进行甲基化修饰,调控转录区域的CpG 岛发生DNA 甲基化,某些特异性甲基化结合蛋白会与CpG 岛相结合,通过顺式作用元件序列保留CpG 岛,继而影响组蛋白修饰,影响相关基因的转录和表达,导致疾病的发生[10]。
2 DNA甲基化与GD的发病机制
2.1 DNA甲基化在GD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多种因素与GD 的DNA 甲基化改变有关,包括吸烟、碘、丙型肝炎感染、压力和内分泌失调等[11]。这些因素使DNA 甲基化水平发生变化,打破了自我耐受调节和基因表达稳态。此外,DNA 甲基化在维持T 细胞功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2]。当维持成熟T 细胞的DNA 甲基化水平和模式发生变化时,可导致T 细胞发生自身免疫。这可能是由于药物作用或者有丝分裂期间编码DNMTs的基因没有被激活,从而导致GD 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研究发现[13-14],GD 患者中有82 个高甲基化基因和103 个低甲基化基因,功能富集分析表明,高甲基化基因主要参与调控细胞生长代谢,而低甲基化基因则参与调控细胞生长、凋亡及免疫功能。
2.2 GD相关免疫因子的异常DNA甲基化
研究发现[13],与GD 相关的免疫因子存在异常DNA 甲基化,包括免疫调节因子β2 肾上腺素受体(beta2-adrenergic receptor 2,ADRB2)的高甲基化和参与淋巴细胞活性调节的β-1,3-N-乙酰葡糖胺基转移酶(beta-1,3-N-acetylglucosaminyltransferase 2,B3GNT2)基因高甲基化。ADRB2 基因是一种重要的免疫调节因子,除辅助性T(T-helper 2,Th2)细胞外,所有淋巴样细胞均表达ADRB2。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可通过刺激ADRB2-cAMP-蛋白激酶A通路,选择性抑制Th1应答和细胞免疫,使Th2向体液免疫的主导地位转变[15]。在GD 组织样本中存在Th1和Th2的混合模式,高甲基化的ADRB2基因会扰乱Th1/Th2细胞因子平衡,最终使GD 中Th1细胞的数量和Th1/Th2细胞的比例升高,在免疫反应期间吸引免疫效应物到达炎症部位,促进炎症扩展,这成为GD 发病的重要因素[16]。
B3GNT2是聚氨基乳糖的主要合成酶,在免疫系统中高表达,这对维持免疫耐受,调节免疫细胞功能及免疫细胞的激活、成熟和凋亡具有重要作用[17]。敲除小鼠B3GNT2基因后,免疫细胞中糖蛋白上的聚氨基乳糖显著减少,导致免疫细胞对刺激具有超敏和高反应性,表明聚氨基乳糖对过度免疫反应的抑制作用[18]。B3GNT2 与免疫相关的全基因组研究表明,降低B3GNT2表达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与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以及GD 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关[19-20]。
2.3 GD与DNMT基因多态性
研究表明[21-22],DNMT 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遗传危险因素,DNMT1中GG 基因型与DNA 低甲基化和GD 的难治性相关。Cai等[23]报道GD 患者DNMT3B基因中的SNP rs2424913和DNMT1基因中的SNP rs2228611 与GD 易感性相关。SNP rs2424913是DNMT3B 启动子区的一种多态性,从等位基因C到等位基因T 的过渡使体外启动子活性增加30%[24]。等位基因C 的升高表明GD 患者DNMT3B 启动子活性降低。因此,来自DNMT3B的SNP rs2424913可能与GD 风险相关。
2.4 Graves眼病与DNA甲基化
Graves眼病是GD 患者最常见的甲状腺外表现,眼眶成纤维细胞某些基因会发生高甲基化或低甲基化,涉及CpG 启动子,从而干扰转录因子募集[25]。异常的DNA 甲基化修饰可促进炎症反应,并调节参与眼眶成纤维细胞和脂肪形成的多种信号分子表达,从而导致眼眶组织纤维化和炎症浸润[4]。狭缝同源物(slit homolog-2,SLIT2)作为一种轴突导向糖蛋白,由眼眶成纤维细胞表达,甲状腺激素可提高其表达水平。SLIT2在Graves眼病中具有较低的甲基化水平,蛋白聚糖作为自身抗原通过激活CD4+T 细胞参与炎症过程,抑制纤维细胞的分化,并显著增加纤维细胞产生的炎性因子[26]。这种调节眼眶成纤维细胞炎症的作用使SLIT2 在调节Graves眼病的进展中发挥作用。
3 GD与相关分子的DNA甲基化
肿瘤坏死因子-α、干扰素、白细胞介素和细胞间黏附分子等DNA 甲基化与GD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下面逐一探讨这些分子的DNA 甲基化修饰在GD 中的作用。
3.1 肿瘤坏死因子-α的DNA甲基化
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是一种由Th1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甲状腺细胞分泌的炎性细胞因子,在启动和发展自身免疫疾病中起着重要作用[27]。研究发现[28],GD 活动期和复发期患者TNF-α水平显著升高,其多个CpG 位点甲基化水平显著降低。GD 炎症过程启动和加速的共同机制是Th1细胞因子/趋化因子轴[29]。Th1细胞产生TNF-α,刺激GD 患者甲状腺细胞和Graves眼病的眶后细胞分泌趋化因子C-X-C 配体10(chemokine C-X-C ligand 10,CXCL10)、CXCL9和CXCL11,后者结合并激活Th1细胞上的趋化因子3受体,促进TNF-α释放,从而形成正反馈回路,加速受累器官炎症细胞的募集和激活[30]。此外,在GD 中,CXCL10介导的Th1细胞募集主要在疾病的早期阶段发挥作用,活动性和复发性GD 患者血清CXCL10 水平较高,治疗后降低,表明GD 活跃期的启动和复发是由Th1淋巴细胞决定的[29]。
3.2 干扰素的DNA甲基化
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由Th1 细胞分泌,可激活细胞毒性T 细胞,并减少Th17分化,从而抑制体液免疫。研究发现[31],难治性GD 患者IFN-γ启动子区-54 CpG DNA 甲基化水平明显高于缓解期GD。这表明IFN-γ启动子DNA 甲基化与GD 严重程度和治疗反应之间存在关联,高水平的DNA 甲基化可能会抑制IFN-γ的表达,增强Th17的分化,导致难治性GD,INF-γ-54 CpG 的甲基化是GD 难治性的一个重要表观遗传因素。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该甲基化水平与甲巯咪唑剂量之间存在相关性。
此外,IFN-α功能异常也与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关,GD 是IFN-α治疗病毒性丙型肝炎的常见副作用[32]。Lafontaine等[11]报道了3 例丙肝患者,接受IFN-α治疗8个月后确诊合并GD,这提示IFN-α与GD 发病有很强的相关性。CXCL10、CXCL9 以及CXCL11等IFN-α相关的基因被报道与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关[33]。研究发现[34],Graves 眼病患者的CD4+T 细胞中IFN-α 相关基因四肽重复序列1(tetratricopeptide repeats 1,IFIT1)、干扰素调节因子7(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 7,IRF7)、粘病毒抗性1(myxovirus resistance 1,MX1)、寡腺苷酸合成酶1(oligoadenylate synthetase 1,OAS1)、泛素特异性蛋白酶18(ubiquitin-specific protease 18,USP18)及含自由基s-腺苷甲硫氨酸结构域蛋白2(radical s-adenosyl methionine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2,RSAD2)呈低甲基化水平,表明这些基因的DNA 甲基化异常可能参与GD 发病。
3.3 白细胞介素的DNA甲基化
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是调节机体免疫系统功能主要因子之一,可调节免疫细胞的活性及免疫应答。IL-6参与B 细胞分化和T 细胞增殖,并与转化生长因子β 结合,诱导Th17 细胞发挥促炎作用[35]。研究发现[36],难治性GD 患者IL-6 水平升高,IL-6启动子区-664 CpG 位点和666 CPG 位点的DNA 甲基化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和缓解期GD 患者,而外周血中Th17细胞的比例高于缓解期GD 患者。因此推测IL-6基因甲基化水平降低可促进IL-6产生及Th17分化。研究发现[31],Th17细胞的增加参与了顽固性GD 的进展,这意味着GD 治疗难度的进一步增大。
此外,白细胞介素-2 受体(interleukin-2 receptor,IL-2R)的α亚单位参与T 细胞功能的调节。T细胞表面有许多IL-2R 分子表达,IL-2R 启动子区域的表观遗传修饰会影响该基因的表达。研究发现[37],GD 患者IL-2R 基因启动子的DNA 甲基化显著降低,低甲基化可以改变CD4+和CD25+调节性T细胞上IL-2R 基因的表达,竞争性结合IL-2,通过调节性T 细胞功能,影响GD 的发生。
3.4 细胞间黏附分子-1的DNA甲基化
细胞间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ICAM-1)是一种由内皮细胞、白细胞和甲状腺滤泡细胞表达的糖蛋白[11]。ICAM-1是人类卵巢癌细胞中的表观遗传沉默基因,通过启动5-mC 氧化参与DNA 去甲基化[38]。GD 患者中,ICAM-1 在甲状腺细胞和外周血中均表达增加,ICAM-1被认为是影响GD 易感性的重要危险因素[39]。研究发现[40],GD 患者ICAM-1基因DNA 甲基化水平显著降低,ICAM-1基因低甲基化会导致参与GD 炎症过程中的多种免疫激活相关的基因过表达,从而导致对甲状腺细胞的自身免疫攻击。ICAM-1 低甲基化还与Graves患者突眼程度及促甲状腺免疫球蛋白水平呈正相关[40]。促甲状腺免疫球蛋白会特异性增加细胞表面ICAM-1基因的表达,募集淋巴细胞到甲状腺,促进自身免疫攻击。由此表明,ICAM-1 基因DNA甲基化改变在GD 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41],抗ICAM-1单克隆抗体治疗,可显著降低血清甲状腺素及促甲状腺激素抗体水平,减缓GD 小鼠的体重减轻程度,这表明ICAM-1 有望成为临床治疗GD 的靶点之一。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DNA 甲基化修饰作为一种常见的表观遗传机制,对GD 的发生发展产生影响。然而,目前表观遗传学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还有很多与GD发病或患者预后相关的DNA 甲基化异常基因暂不明确。单一基因DNA 甲基化检测是否能作为GD 的诊断标准,未来还需进一步探索。以DNA 甲基化为切入点研发治疗GD 的新药物,有望成为未来的研究新领域,对该病的治疗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