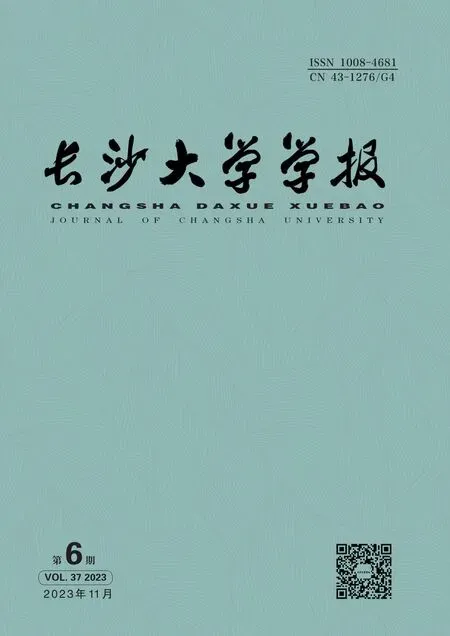阅读游戏与网络文学爱欲想象
禹建湘,张琛笑
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2
紧随中国网络文学三十年的风发泉涌,中国网络文学研究趋向全面化、特色化和深度化。对众多研究成果剥茧抽丝,便可发现大都是以中国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质性突破为根底,围绕中国网络文学新质的产生、表现和发展进行分析。其中,游戏成为新质研究的高频词和重要切入点。总体来看,现行研究以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逻辑、数字媒介表征为三大支点,建立起网络文学游戏研究体系,从审美、叙事、文学想象等方面论述网络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新形态。许苗苗认为:“游戏逻辑标志着网络小说已发展出个性风格,在强化并放大传统通俗小说某些属性的同时又呈现出自身独有的媒介特色。”[1]黎杨全指出:“游戏经验对中国网络文学的‘世界’想象、主体认知及叙述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经由游戏经验的中介,网络文学表现出了网络社会来临后一些新的文学文化特质。”[2]这些研究的落脚点始终在网络文学文本以及生产创作方,着重对当下新语境的把握,对传统文学游戏精神的内在承续虽有涉及,但未能沿着游戏的主体性和本体性的命脉进行深入挖掘。另外,关涉网络文学与游戏关系的既有研究,较少将读者纳入游戏的系统范畴,划开游戏者行为与游戏之界线,没有厘清网络文学整体游戏逻辑,更没有觅得网络文学游戏性的真正意指所在。
从艺术游戏研究到游戏文化研究,西方游戏内涵开拓出以康德、席勒为代表的主体性路径和以加达默尔为代表的本体存在性路径。以德里达、福柯、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游戏说虽打着反叛旗号,但仍是在剔除逻各斯、理性、真理的框架内沿此二路径,以解构、颠覆的姿态极度高扬游戏本质内涵中的主体性和本体性,强调后现代个体自由和生存处境。网络文学中的游戏影子烙有后现代的印记,但并未彻底保留那份极端和破坏性。不同于传统文学“摆在面前”的严肃,网络文学是游戏“体验场”中无意识流露的严肃,陷入游戏的主体难以自我察觉。因此,网络文学游戏的深层意指内涵通常不在文本文字的表达里,而在文学文本为读者而表现中,与读者生存体验紧密相关,需定点于游戏的本体性和主体性去挖掘存在之思。无论网络文学与游戏存在何种关系,也无论网络文学的游戏性指向何处,我们都必须明确一点,游戏,尤其是文学艺术性游戏,是“由游戏者和观赏者所组成的整体”[3]141。加达默尔的游戏理论虽然有偏颇之处,但他的思考给我们留下了一条厘清研究思路的辅助线。他从本体论角度对游戏概述,不仅把观赏者、观看者、读者纳入游戏系统,还指出“游戏是为观赏者而存在的”[3]142。网络文学读者中心导向与加达默尔这一观点的契合,为网络文学游戏研究提供了新的有效性视角。从游戏者和观赏者共同构成的游戏系统出发,网络文学并非仅限于创作者的游戏经验与文本的简单交互,而是具有双层游戏关系构造的复杂体。网络文学文本中由游戏经验和逻辑植入构成的,只是相对于人物而言的第一层游戏,或者说,是小说人物充当游戏者的网络文学“文本游戏”。现有研究聚焦的正是这一“文本游戏”。读者在这里扮演观看者、观赏者角色,与小说人物游戏者共同参与游戏。除此之外,网络文学爱好者与游戏者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上瘾式”反复阅读行为和全身心忘我阅读状态,这表明阅读网络文学本身就是读者的游戏。“文本游戏”被包含在以读者为游戏者的阅读游戏之中,是阅读游戏在读者的游戏者、观赏者身份融为一体时转化而成的封闭构成物。“游戏者的行为与游戏本身应有区别。”[3]130阅读游戏首先是读者发起的主体性行为,一种与读者生存经验息息相关的伪装、扮演行为。其次,就阅读游戏本身而言,其意指内涵存在于转化而成的“文本游戏封闭构成物”中,始终为读者而表现。尤其需要关注的是,阅读游戏的观赏者指意不明,这一位置的空缺,促使阅读游戏在伪装游戏和“文本游戏”的转化进程中,将读者的爱欲想象延伸至现实,呈现向后人类、新未来敞开的可能性开放姿态。
一 作为游戏者行为的阅读游戏
“游戏者的行为是与主体性的方式相关联的”[3]130,作为游戏者行为的阅读游戏关涉读者主体,与主体性紧密相连。依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已经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的界限逐渐被销蚀,网民的生存体验和心理感受在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中实现共享。基于此,网络文学阅读行为经过反复发生,演化成读者的日常行为,以“拟游戏”形式连接起读者的阅读体验与现实生存经验,发挥其生活功能和文化功能。
相对于读者主体而言,阅读游戏发挥生活功能,“是一般生活所需的一部分,它装饰生活,扩充生活的范围”[4]10。网络文学阅读游戏以暂时性娱乐活动的形式打断了日常生活进程,将阅读游戏的体验纳入读者的日常生活,推进日常生活。阅读游戏与日常生活的交融由当代消费社会语境决定,受到消费逻辑控制。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者受制于享受和满足的约束,“越来越少地将自己的生命用于劳动中的生产,而是越来越多地用于对自己需求及福利进行生产和持续的革新”[5]71,通过开发一切潜在享受来实现存在最大化。加之学习、工作的苦闷压抑和日常生活的枯燥无聊,读者找到了网络世界的虚拟娱乐——电子游戏、社交媒体、互动直播等,网络文学阅读正是其中之一。随着网络文学文化产业的崛起和成型,网络文学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兴消费热点,游戏者发起的阅读行为被纳入消费行为,承载消费功能。让·鲍德里亚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消费的益处并不是作为工作或生产过程的结合,而是作为奇迹来体验的。”[5]8同时,作为阅读消费对象的网络文学作品,大量地围绕“逆袭”展开叙事,“通过英雄的制造、史诗的书写促成生活的奇迹”[2]。因此,在阅读行为的消费性质和网络文学作品游戏经验植入的双重交织下,网络文学阅读游戏给读者传递了一种有别于日常经验的游戏体验、奇迹体验。借助阅读快感的持续输出,阅读游戏为读者的日常生活制造了强烈的欣狂感觉,“其强烈的期盼使得日常生活的平庸得以延续”[5]8。阅读游戏对日常生活欣狂感和奇迹感的补充不断吸引读者,甚至孵化出一批“上瘾者”。在微博、豆瓣、知乎、简书等大型社交平台,诸如“如何戒掉网络小说瘾?”“网络小说上瘾怎么办?”标题类的帖子层出不穷。虽然其中有些属于精神障碍层面的极端情况,但网络文学爱好者确实普遍存在“上瘾”心理。面对喜爱的网络文学作品,他们或多或少地流露了难以自控的阅读冲动,表现出不受控的反复阅读行为。
阅读游戏的生活功能并非单纯的主体阅读行为、消费行为的产物,它拥有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包含在文化功能之中。对读者阅读游戏表现出的行为症候的探析必须回归现实文化环境,寻找触发读者阅读行为的现实心理动机。其中,阅读游戏中读者的反复阅读行为与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中的“Fort Da(去/来)游戏”在重复行为特征上的相通之处成为研究的切入点。一位18 个月的儿童,面对母亲的离开并没有哭泣,而是把所有能拿到的小东西扔在角落和床底,并发出意味“走开”的“哦”“嗬”声。基于这一发现,弗洛伊德以木线轴为实验工具,发现小男孩不断重复地将木线轴抛出去又拉回来,并将其视作一种游戏。木线轴经由儿童动作的消失与再现,是对母亲离开与再现的戏拟与重演。母亲的离开是儿童发出“抛出”动作的游戏动机,母亲回归则是游戏的根本目的,儿童成功地将分离经验转化成一种重复性的游戏体验。总体来看,儿童重复性的“Fort Da 游戏”包含两方面内涵:一是压制分离的痛苦,满足报复冲动;二是获得控制环境的能力,由经验的被动者转变为体验的主导者。在阅读游戏中,读者反复“进入阅读”和“退出阅读”,同样构成了与网络文学世界的分离与重现,同样遵循了现实经验与即时体验相转化的行为模式。从这一角度来看,阅读游戏与“Fort Da 游戏”同属一类游戏,这类游戏的核心在于将痛苦的、乏味的、虚无的生存经验转化为快乐体验。因此,在阅读游戏的两端也分别有压制和主导两股势力。结合前文关于生活功能的论述,阅读游戏的主导一端指向网络文学奇迹叙事提供的欢愉体验;压制一端作为其对立面,指向读者主体身处现实文化场域遭受的创伤经验。伴随技术而生,人类的愿望性冲动(wishful impulses)始终受到现代文明的管控。在文明进程中,个体超我与文化超我相融合,内部压抑和外部压抑相交织,将人从快乐原则的母体中剥离出去,并将其驱逐进用现实原则捍卫的父系社会。人们屡屡遭受的分离体验成为根植于全人类记忆中的文化创伤经验,现代人即使身处丰盛的消费社会,仍深陷丧失和缺乏爱的恐惧之中,于网络文学阅读中无意识地流露出母体失落感。“只有当游戏是一项被确认的文化功能时……它才被置于责任和义务的领域。”[4]9面对压抑性现代文明的坚不可摧,读者改变了满足目标,通过阅读游戏将创伤经验转变为爱欲体验,移情式地把爱欲要求和本能满足转移到网络文学阅读中。在阅读游戏中,读者反复进入网络文学世界的阅读行为,是对爱欲回归的模拟,承载了读者对获取主体性控制权的渴望。
“作为盛载个人单元体的一个外壳,主体的功能在于把壳中所载的内容表现出来,投射于外。”[6]448阅读游戏的生活功能和文化功能以读者主体为基点和前提,无论是对娱乐律令的高扬,还是对文化创伤的镇压,都是读者主体性向外投射的无意识流露。从游戏者行为角度观察阅读游戏,那么读者的游戏活动只是伪装,带给读者的游戏感受内含装假性(only pretending quality)。在这一游戏活动中,身为游戏者的读者能够意识到自己在游戏中(at play),他只是借助游戏活动扮演其他人。游戏者的行为看似切断了与日常自我的连续性,却意味着“他自为地把握了这种与自身的连续性”[3]144。读者投射至网络文学文本人物形象的他者欲望是其主体性的真正所在,他们沉迷于什么样的网络小说往往取决于他们的主体性在何种方面存在缺乏。例如,言情小说的受众通常是未收获爱情的女性读者。现实生活中爱情经验的匮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她们通过代入女主人公的角色来获得有关爱情的虚拟体验满足。通过自主选择,读者在阅读游戏中接触到与现实生活并不相同的生存模式。只有这样,读者才能成功地将自己从现实既定的具体时空架构中抽离出来,以心理代入的方式建构想象自我。换句话说,从读者行为出发,网络文学阅读游戏实质上是读者基于文字,借助想象,填充或弥补“主体性缺乏”的游戏活动,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颠覆现实自我的阿基米德支点。在颠覆和自我掌控的阅读游戏里,读者拥有选择和决定的自由,他们不再是背负沉重现实的苦行僧,而是当下愉悦的主导者、享乐者。读者在现实世界中失去和缺乏的事物——纯粹的爱情、真挚的友情、浓烈的热爱、一往无前的勇气……都在这里被找回,并得以接续。阅读游戏将读者于现实世界的断裂性生存体验重新接续起来,显示出个体心理在爱欲问题上的妥协与不甘。
二 向“构成物”转化的阅读游戏
加达默尔把“促使人类游戏真正完成其作为艺术的转化称之为向构成物的转化(verwandlung ins gebilde)”[3]142,从而衔接起游戏文化研究与艺术游戏研究,在双重视域下将游戏研究推向动态。转化不等同于变化,“是指某物一下子和整个地成了其他的东西”[3]143。阅读游戏向“构成物”的转化以读者心理状态为标志,具体表现为读者阅读感知中的“第四堵墙”被打破。读者阅读网络小说的行为动机,往往是打发时间、逃避现实。但随着读者沉浸式阅读体验的获得和加深,他将进入到游戏领域,把自己行为的目的转化到单纯的游戏任务中,获得表现自身的自由。阅读游戏本身就是一个在伪装游戏和“文本游戏”间发生转化的过程。研究对象从游戏者行为转移到游戏本身,研究视点从游戏主体性转移到游戏本体性,是伴随游戏状态转化的自然选择。
所谓“构成物”,是游戏者超脱现实、达到忘我的状态,进入到的“另一个自身封闭的世界”[3]144。在此世界里,“游戏就仿佛在自身中找到了它的尺度,并且不按照任何外在于它的东西去衡量自身”[3]144-145。这意味着游戏自身蕴含某种意义内容,可与游戏者的行为相脱离。直观来看,这个世界即“文本游戏”世界。不同于阅读游戏中观赏者的悬而不论,“文本游戏”的游戏者和观赏者十分明确,是一个封闭完整的游戏系统。小说人物是游戏者,读者是观赏者,读者与小说人物爱欲关系的建立,推倒了游戏世界封闭空间的“第四堵墙”。两者在沉浸式、代入式的阅读中合而为一,游戏者和观赏者的区别在构成物中被取消,游戏本身“以游戏的意义内容去意指(meinen)”[3]142。换句话说,在“文本游戏”中,游戏拥有自身的本体存在,而不是在游戏者的意识或行为中具有其存在。游戏是捕猎者,它为观赏者而表现,并吸引游戏者进入它的领域。以穿书类小说为例,主人公由于某种原因脱离原有时空,与穿书系统达成某种协定,从而携带任务进入另一时空,扮演其中的某个角色。在这一文本逻辑设定里,游戏系统先于游戏者存在,主人公/穿越者作为游戏者被传唤至故事世界,受游戏目的驱使,遵循游戏规则,推进故事发展。黎杨全认为:“这种由外部的玩家介入到故事世界并改变情节走向的写作模式,让中国网络文学具有了‘超叙事’(meta-narrative)特征。”[2]他指出,超叙事的自反意识根源于作者与小说故事间不同次元的融通,但并未点明这种融通背后存在为读者而表现的根本动机和前提。游戏唯有在观赏者那里,才能够被提升到它的理想性,超叙事结构才得以创造出奇迹体验,拥有对读者的召唤效力,并进而将作为观赏者的读者从“第四堵墙”外纳入游戏内部。由此,基于文学文本意义的承载性,游戏的意义内容在网络文学为读者而表现的过程中得到表现。
结合阅读游戏文化功能填补爱欲的现实动机背景,“文本游戏构成物”的意指即爱欲想象下人的非压抑性存在。赫伊津哈指出:“如果我们发现游戏是基于对特定形象的操作,或基于某一特定的有关现实的‘想象物’(即,进入想象的转换物),那么我们主要的旨趣就是抓住这些形象和现实‘想象物’的价值和意义。”[4]5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涵盖校园都市、无限流、科幻、玄幻、仙侠、历史等类型,在各种各样的世界中孵化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总括而言,网络文学文本为读者表现出一种可能性空间,创造了一类爱欲主体。
网络文学世界是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世界,它脱胎于现实,但又不同于现实。架空化是网络小说区别于传统小说的一个趋势,拥有这一特点的文本世界是“一种‘脱历史’和‘脱社会’的对于世界的再度编织和结构”[7],充满无限可能性。对历史和社会的脱离,归根结底,是对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始终的文明秩序的颠覆。现代人被驱逐出快乐原则的伊甸园,被迫接受现实、融入现实。爱欲渴望被现实原则镇压,心理空间爱欲日趋萎缩,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间的紧张对立状态始终潜伏在读者心中。“没有人可以摆脱‘想弄明白内在与外在现实关系’的紧张压力,只有在不受挑战的体验的中间区域(如艺术、宗教,等等)里,我们才能缓解这份紧张。这个中间区域跟‘沉迷’在游戏中的小孩的游戏区域有直接的连贯性。”[8]49“文本游戏构成物”重合了文学和游戏两个不受挑战的体验中间区,娱乐化、商业化创造的虚拟想象空间介于现实世界和自我心理世界之间,为读者提供了从现实通往内在心灵的过渡平台。现实世界压抑性操作原则在此失效,非压抑性爱欲文明得以确认,网络文学文本中的游戏时空摆脱了现实环境的约束,使主体多元发展获得多种可能。例如猫腻的架空历史小说《庆余年》中的穿越者叶轻眉,身为工科博士,她凭借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现代思想开展一系列改革,发行报纸、设立检察院等。她成功地以一人之力动摇穿越世界的封建君主专制,使抑制人类科技进步的神庙统治受到严重威胁,为人类文明和技术的新发展创造了可能,这在现实世界显然是天方夜谭。可以看出,网络小说的种种世界看似拥有自身严格的等级秩序,但根本不同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世界。这些小说世界的设定在极大程度上以为主体的能动性服务为宗旨,其等级体系为被主体打破而存在,充满着改变、突破、颠覆等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空间以人的主体满足为主导,以非压抑性爱欲文明推动表层秩序的设立和运行,因而得以容纳读者进入想象的转换物,并将其假想为爱欲主体。
与现代文明操作原则(或传统文学)的苦难英雄——普罗米修斯相对立,网络文学塑造的爱欲主体以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为英雄原型。首先,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的形象是快乐和自我实现,俄耳浦斯指向纯粹的他恋,那喀索斯指向纯粹的自恋,他们的结合象征完整的爱欲。俄耳浦斯深爱亡妻欧律狄刻,前往冥界复活妻子失败后,整日追逐欧律狄刻的幻影,不近女色,乃至发展出同性之爱。美少年那喀索斯拒绝所有示爱的神女,爱上自己水中的倒影。“文本游戏构成物”中的小说人物形象正是将读者从观赏者位置询唤至游戏者位置的“幻影”和“倒影”,是为读者而表现的爱欲主体。以读者与爱欲主体间爱欲关系的建立为前提,爱欲主体承载了读者对自我、对他者的想象,是读者欲望的投射。例如,桉柏《穿进赛博游戏后干掉boss 成功上位》中的女主人公“隗辛”。她穿梭于现实世界和赛博游戏世界,引导玩家和游戏土著团结。她强大清醒、杀伐果决,是阻止游戏世界摧毁现实世界的拯救者、保护者和决策者。正因隗辛承载了女性读者对自我性格、能力和身份完美想象的投射,她才能够获得大量女性读者的拥护,被亲切地称为“隗姐”。顾漫在《何以笙箫默》中塑造的何以琛频频入选网络言情小说最受欢迎男主角,被誉为“亿年修得何以琛”。从法院才子成长到律师界翘楚,他唯爱赵默笙一人,苦等七年,深情无悔,满足了女性读者对爱情、对伴侣的美好憧憬。无论是那喀索斯的自恋,还是俄耳浦斯的他恋,两者都是对性欲的超越以及对精神爱欲的追求,内含对压抑性秩序的抗拒。这一点在近些年女性受众阅读取向由“霸道总裁爱上我”向“纯爱文”的转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并且,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是“伟大的拒绝”的形象。俄耳浦斯拒绝色雷斯女子,追求亡妻幻影;那喀索斯拒绝神女,追求水中之影。两者形象的本质是不现实的,代表了一种“不可能”的态度和存在,他们共同拒绝了尘世生活的召唤,用爱欲态度完成拒绝后的重聚。网络小说中各路主人公的本质也是非现实的,他们往往拥有某种与市侩相悖的珍贵品质,在重要抉择的“黄树林”中走向“人迹更少的一条”。例如,《斗破苍穹》中逆境中不屈、顺境中不忘的萧炎,《11 处特工皇妃》中誓死守护燕北、与百姓共存亡的楚乔,《择天记》中心系天下苍生的陈长生,《魔道祖师》中秉持“是非在己,得失不论,毁誉由人”的魏无羡等主人公,面对重重坎坷和诱惑,他们始终坚守纯粹的本心,在艰难的选择和拒绝中实现自我。爱欲可能与现实不可能的强大张力,将读者牢牢吸纳进“文本游戏”。在阅读游戏的开端,读者就已经半只脚迈出现实世界、半只脚迈进自我心理世界。现实里的漠然、无力、随波逐流,随着阅读时空感知的改变而逐渐淡出读者内心。向“文本游戏构成物”的转化,更是如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一般受到非压抑性爱欲“幻影”的召唤,重回满足逻辑下的爱欲母体,或者说自我表现世界。琴声里的俄耳浦斯与自然相亲,“认识自己”的那喀索斯与水中影相融,阅读游戏中的读者与网络文学可能性空间相合,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游戏的此刻,“存在被看作是满足”[9]120,生命自有它的意义。
三 走向后人类的阅读游戏
“文本游戏构成物”为身为观赏者的读者而表现,那么以读者作为游戏者的阅读游戏为谁而表现?阅读游戏的观赏者何在?这关涉主体性、本体性,尚处悬置和空缺。这一“观赏者”角色姑且只能找到初具概念但尚未成型的后人类。阅读游戏以电子文学文本为载体,使得“文本游戏构成物”的意指不断渗入现实,逐渐消融读者认知机制中现实世界与网络文学虚拟世界的界线,传递出新媒介时代“人”向“后人类”状态过渡的讯号。
信息流的渗透和交互成为当前文化的某种关键性特征,表现在文学领域,即文本生产技术从印刷走向电子媒介,引发数字化阅读。新的文本世界与表现性代码相互作用,改变了读者阅读消费模式,激发了新的具身经验——游戏化阅读。信息网络社会带给读者的文学阅读感受极具致幻性和虚拟性,是“物质对象被信息模式贯穿的一种文化感知”[10]18。在网络文学阅读游戏的文化感知中,读者可以通过视觉方式直接无碍地触碰信息世界、进入虚拟情境,信息似乎变得比物质性更为本质。根本性地位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撼动了有关主体性的传统假定,显示出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后人类特征,即解构自由人本主义主体,创造新主体,探讨新的生存模式。后人类的主体是集合体、混合物,指向人与机器、科技与生命、物质与精神的无差别,它从各种异质异源的包围里“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10]5。读者阅读游戏中的想象自我与后人类主体并非全然一致,但都沿着“打破—重建”的路径,找寻人类的新自由,走向对压抑性文明的背离。正是这一重合点,致使文学、游戏与后人类在网络文学阅读中钩织起复杂的关系网。三者共同聚焦生存主体性,着眼于主客体关系,且如出一辙地提供了主客体界限模糊的中间区域。三者平面来看,是因共性而交互作用的,但从前后景来说,人机互动的后人类趋势应是时代大背景中网络文学阅读游戏作为后人类状态在特定领域过渡的前景而凸现。
这种凸现首先表现在网络文学阅读游戏认知视点(point of view)对身体的抛弃。在经典叙事学中,视点作为叙述焦点(focus of narration)的同义词,限定在叙事者和人物的感知之间,读者仅以提供场外固定视角的功能静态存在。这一情形在网络文学叙事研究视域彻底被扭转,读者的叙事理解和认知成为聚焦研究的重中之重。消费社会的主导逻辑渗透文艺创作,对读者阅读消费心理的迎合致使读者本体地位得到空前的确认,叙事回归到一种“感知中心”。正如曼弗雷德·雅恩所认为的:“与其说是一个叙述者在高高在上的窗户里面俯瞰,不如说我们是从故事人物的内心之窗(human scene)眺望。”[11]加之网络文学创作重情节、轻表达技巧和叙事手法,叙事视点难见创新,仍滞留在热奈特“内聚焦”“外聚焦”“零聚焦”的传统框架内,未提供深度挖掘的空间。因此,可进一步将叙事视点转向读者的认知视点,沿着读者的“聚焦之窗”(windows of focalization)打开。读者阅读游戏所在的网络空间不同于传统文学提供的文本载体,数字化阅读是视觉技术建构的一次飞跃。在主客体消融的阅读游戏中,读者意识与数据直接关联,“替代通过窗户看着场景的一个具身化的意识,意识穿过屏障变成pov,把身体甩在后面变成一具空壳”[10]50。视点不再是一种观看、感知的位置标记,而是直接替代角色,这构成读者的主体性,读者成为角色本身。跨越真实与虚构、现实与虚拟,读者进入到叙事世界,化身拉比诺维茨定义的“叙事的读者”,将意识具化成视点参与情节互动。肉体存在的现实当下性和局限性开始消失,主体性可以附身任何一个视点,从而呈现分布式的状态。以第十二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银奖作品《小蘑菇》为例,虽然小说全篇都定点于小蘑菇安折的视角,但当读者与审判者陆沨产生共鸣时,他将生出“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念头,坚信人类尚有未来。当读者悲悯于《玫瑰花宣言》对女性自由的束缚时,他将与伊甸园的陆夫人交感,陷入生殖厌弃和末世悲观,背弃集体人类,高扬个人自由意志。当读者身临其境般感受到末世废土的恐惧时,他会是诗人、安泽、肖老板等一众脆弱的生命。总而言之,不同的网络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同一部网络文学作品中的不同角色都有可能成为同一读者代入的视点实体,成为读者主体性投射的一部分。由此,电子文本数据被人格化,读者主体性被数据化,两者相联合。惰性身体在阅读游戏中被抛至身后,无形的主体性自由随性地栖居虚拟领域。
认知视点的变化进一步对读者思维结构和体验方式产生影响,显示出“人”向“后人类”状态过渡的第二个表征,即“在场/缺席”被“模式/随机”取代。身体的取消和意识的视点化,使得阅读游戏中的读者无所谓在场,亦无所谓缺席,传统意义上的“在场/缺席”已经无法解释这种人机交互的存在体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往往意味着新含义模型的建立,信息数据的渗透绝非仅是对文本呈现和储存方式的改变,它从根本上触及对能指和所指关系的革新。信息系统具有模式化和随机性特征,在信息数据的日常化进程中,这些特征穿透屏幕流动至读者的意识域,潜移默化地促成读者从“在场/缺席”到“模式/随机”的认知转换。网络文学阅读游戏是一种体验,读者认知最直接的来源无疑是网络文学文本。我们发现,当下大量的网络文学作品,无论是何种题材、何种类型,整体上都遵循着一种“模式化叙事框架+随机性情节”的叙事规则。小说叙事框架常常被限定在“复仇虐渣”“草根逆袭”“破镜重圆”“相互救赎”“打怪升级”等模式之中,同一类型文的情节走向大体一致。“随机性情节”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故事发生具有偶然性和随机性,这在穿越文、重生文中尤为明显。例如,《庆余年》中躺在病床上等死的范慎转眼间穿越成了襁褓里的婴儿范闲,《重生之贼行天下》中心怀怨恨和不甘的聂言意外重生回到十八岁,两部小说都以这种偶然性为故事开端,展开叙事。二是故事中途发生情节的随机性转变,这也正是网络小说同中存异的创新之道。例如,女频网文曾流行一类带有“强制爱”特点的斯德哥尔摩小说,但尸姐的《幽林》却与这一类型叙事背道而驰,别出心裁。她在添加恐怖悬疑元素的基础上突然转向反斯德哥尔摩,其创作出乎读者意料,获得好评。浸润于“模式化叙事框架+随机性情节”的阅读接受,读者无意识地形成“模式/随机”的自动化反应和思维方式,习惯性地以类型标签作为选择判断的根据,并逐渐将其拓展至生活的各个领域。不过,“信息的效力实际上源于物质性的存在基础”[10]38,读者认知的转换除信息技术和电子文本的影响外,必然存有现实根基。后现代的大众社会,人对物的使用权替代了所有权。使用权不要求对物的拥有,只是“访问”“进入”;它不要求物的定点存在,只是“路径”“通道”“轨迹”。物的实在让位于物的符号信息,“商品的实用的地位升华为‘氛围’游戏”[5]4。在现实消费社会和网络虚拟世界的双向互动和交叉渗透中,“模式/随机”以惊人的速度取代了“在场/缺席”的基本形态。
无论是认知视点对身体的抛弃,还是阅读游戏对“模式/随机”的确认,都不过是读者在现实中退缩,于感性延续的结果。它们产生的心理机制都建立在读者对现实的不适应、“不耐受”。追踪视点在叙事世界穿行的轨迹,我们会看到主体性的压抑、欲望和期许,并发现其终将指向创伤经验的无意识压制和对非压抑性生存的爱欲想象。深掘“模式/随机”认知系统的内涵,我们会觉察“这类系统朝着一个以偶然性和不可预知性为特点的开放的未来发展”[10]387,它表现出在既定参数中寻找意义可能性方案的努力。总之,在阅读游戏的后人类状态过渡中,它唤起了令人振奋的前景:摆脱压抑性文明的束缚,开拓爱欲方式,思考人类存在意义的多种可能性。
综上所述,着眼于读者,一种网络文学特有的阅读游戏凸现。在读者只“感”无“知”的游戏式阅读下,关涉主体性与本体性的深层意指浅露“尖尖角”。欢愉的奇迹体验与压制的创伤经验、可能性空间与爱欲主体、向后人类敞开的可能性……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阅读游戏与爱欲想象的交织中统一起来。网络文学运载的复杂性超乎我们意料,化用狄兰·托马斯的诗句,“不被真正了解”的网络文学或许正向我们发出这样一声忠告:“不要温和地走入那个网生幻象,要怒吼和思考;不要温顺地接受那份欣狂,要聆听沉默和无声。”
——读《图像与爱欲:马奈的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