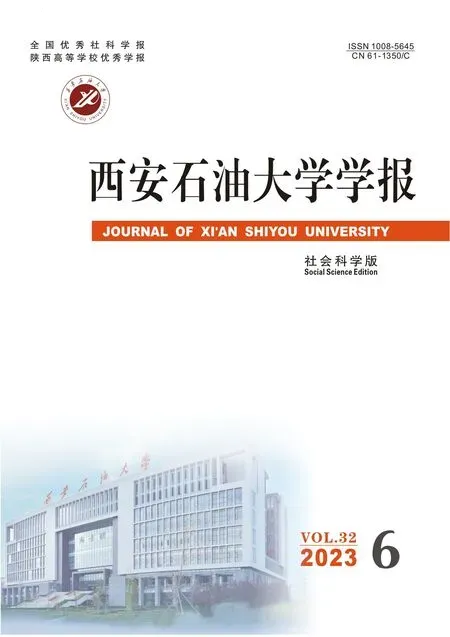日常叙事·人物形象·城乡关系
——论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的新书写
刘 虎
(山西大同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0 引 言
“乡下人进城”是一个关涉中国百余年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命题,在不同时段有着不同的历史内涵,但总与我国城乡关系变革的现实紧密相连。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进一步推进,数以万计的乡下人怀着改变自我命运的愿望来到城市,并期望在城市扎根,由此出现了我国人口规模最大的移民现象。这种社会现象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形成了“乡下人进城”小说的书写潮流(1)“乡下人进城”小说是学者徐德明提出的学术命题,他在研究专著《乡下人进城:城市化浪潮中的城乡迁移主题小说研究》和论文《“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乡下人进城”叙事与“城乡意识形态”》中详细阐释了这一概念命名,认为“乡下人”是一个比“农民”“民工”涵括性更强的学术概念。。作家关注乡下人在城市的生存境遇和精神漂泊,却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城乡间的对立与冲突,忽视了城乡融合的可能性和乡下人的自我主体性建构,他们常把进城乡下人的悲喜遭遇演化为简单的“受难”过程。无怪乎有评论家指出:“他们的审美理想中似乎隐含着这样一种叙述逻辑:作品要深刻,就必须让它体现出某种极端的情感冲击力;而要使叙事具备这种情感冲击力,就必须让人物呼天抢地、凄苦无边。这是一种典型的‘苦难焦虑症’式的写作。”[1]51
由于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和城乡资源配置的悬殊,乡下人确实在城市遭受过诸多的不公正待遇。然而,随着“统筹城乡发展”“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政策理念的提出,乡下人在城市的生存境遇逐渐向好,“乡下人进城”小说也呈现出新的书写面向。作家们在超越城乡对立的日常叙事中突出乡下人的精神品质,用理想化的笔触写出他们融入城市的精神成长与心灵蜕变,积极探索城乡融合的道路,从而丰富了这类小说的书写方式,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考。
1 淡化冲突的日常叙事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事进程中,城市和乡村不只是两个不同的地理区域,更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思想观念与价值诉求。城乡发展的差异和根深蒂固的“城乡意识形态”[2]48,造成了人们崇城抑乡的定势思维。作家们在创作“乡下人进城”小说时,常在故事情节发展中凸显城乡文化冲突给乡下人带来的磨难。徐德明认为,“叙述在事件层面上的辗转变化,除了具有用乡下人的眼光显示现代世界变幻的优长,更多的是因接踵而至的事件淹没了对进城的乡下人的心灵世界的感知与认识。”[2]53作家把进城乡下人的悲惨遭遇归因于城市环境的污浊黑暗,而并未深入探究他们的精神世界。当单调的“苦难叙事”不断刺激读者的阅读神经时,我们不禁要思考进城乡下人的出路到底在何方?除了在城市受苦受难,他们在城市何以立足?
新世纪以来,部分作家超越城乡二元的叙事模式,弱化外在事件的矛盾冲突,着力于在波澜不惊的日常叙事中探寻普遍存在的人性价值和道德尊严。王安忆在这方面的创作具有高度的自觉意识,彰显出其乡下人进城小说的独特价值。王安忆的小说大多不着意于对政治历史事件进行宏观言说,甚至有意回避跌宕起伏的故事叙述和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冲突,而是在庸常琐碎的衣食住行、邻里交往、聚会聊天中体察人生的意义。“我对历史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历史不是由事件组成的,我们现在总是特别强调事件,大的事件。我觉得事件总是从日常生活开始的,等它成为事件实际上已经从日常生活增值了,历史的变化都是日常生活里面的变化。”[3]233她立足于琐屑平淡的生活,并通过这种日常叙事反映时代变迁,寄寓人物的成长与蜕变。《骄傲的皮匠》中小皮匠来自江苏盐城乡下,两代皮匠在手艺传承中见证着城市的发展,他们不只是城市的外来者,更是城市建设的亲历者、参与者,城市不仅给予他们生存的资本,还增强了他们自我发展的信心。作家用细腻的语言描写岳父和小皮匠两代人在城市街道修鞋的生活画面:“皮匠摊前的小马扎上,常常坐着一个女孩子,脱了鞋的脚踩在另一只脚的脚背上,等待皮匠做完她的活计,这情景看起来挺温馨的”。[4]5-6除了做工的日常描写外,作家还细致描写了小皮匠家做饭时的讲究和饭菜的丰盛美味等生活细节:“小皮匠家的饭桌不是第一,也是第二。东西都是从乡下带来的,草鸡炖汤,六月蟹拦腰一剁两半,拖了面糊炸,蛏子炒蛋,卤水点的老豆腐,过年的腊肉或者风鹅,还有酒。”[4]13当然,小皮匠之所以能在城市立足,除了自己引以为傲的修鞋手艺,也离不开市民们对他的接纳与宽宥。城市女性根娣在屡次创业受挫的情况下结识了皮匠,主动帮他保管衣物,加热饭菜,并钦佩于他的高素质和有头脑。根娣的丈夫小弟失业后在城市开出租车营生,他并没有轻视农村出身的小皮匠,而是亲切地称呼他为“朋友”,底层市民的热情消弭了横亘于城乡间的隔膜。
《富萍》通过平凡而又不乏温情的生活叙事,展现进城乡下女性富萍在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命运沉浮。作家跳脱出“城市/农村”“城市人/乡下人”的二元叙事格局,转而深入到以富萍为中心的乡下人在城市的日常生活,观照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存命运,探究普遍存在的人性问题。虽然小说的叙事空间不断发生转换,从奶奶东家的淮海路弄堂,到舅舅家居住的棚户区,再到富萍最后生活的梅家桥,城市始终呈现出温暖的人情味与包容的胸襟。进城乡下人的自尊要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无不洋溢着浓厚的生活趣味。《上种红菱下种藕》以一个寄居于华舍镇的乡下小姑娘秧宝宝的视角,打量生活周遭的人物关系和世情变故。故事主人公年龄和生活环境的限制,使得小说可以脱离以往进城乡下女性所面临的生存焦虑等问题,也规避了大起大落的叙事方式。正是在这种平淡无奇而又充满摩擦的日常生活中,秧宝宝不断克服内心的敏感与恐惧,逐渐走向独立与成熟,确立了自我的主体意志,明确了人生的价值追求。
如果说王安忆侧重在生活叙事中表现进城乡下人的成长过程,其小说富有生活的温情色彩。那么范小青、迟子建、池莉等女作家在关注进城乡下人的生活境遇时,则带有一定的浪漫性想象。范小青《城乡简史》中城里人自清不小心将自己记录日常生活开销的账本误捐出去,西部农民王才出于对意外得来的账本上“香薰精油”的进一步了解,带着妻子和孩子搬往城市。一个小小的账本勾连起城市与乡村,但作家并不着意于描写城乡间的对立与不平等关系,而重在突出进城乡下人思想观念的转变。王才虽然仍生活在城市底层,物质生活窘迫,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满足于城市给他带来的生活新变:在城里可以捡拾电风扇、学着像城里人一样记账、明白了如何更好地与城里人打交道。范小青认为,“我写的农民工可能也有苏州人的心态,可能与你们碰到的农民工不一样,农民工也是各种各样的。很多的人写农民工是讲他在社会上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被歧视,找不到工作,要不就是写农民工的犯罪,我写的农民工就是我的农民工,就是一种无奈,一种默默地承受现实。”[5]178这与其说是作家怀着苏州人的心态描写农民工,毋宁说是她对新时代环境下农民工形象的展望与期待。
池莉《托尔斯泰围巾》中的老扁担在城市以捡拾破烂为生,因为房屋装修和搬运货物等原因与花桥苑的居民产生误会,但小区里的人并没有排斥老扁担,而是将他视为群体的一份子:在聚餐时主动叫上他,为他的不公正遭遇打抱不平,在他离世后对其念念不忘……城市居民与进城乡下人的交往充满了温情暖意,读来令人感动。迟子建在《踏着月光的行板》中虽然也以同情的笔触叙写了妻子林秀珊和丈夫王锐在城市打工的辛劳与奔波,但悲苦的生活和不公正待遇并没有压垮他们,反而更激发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彼此的关心。夫妻二人在两个城市打工,每个月才能相见一次,为了在中秋节这一天给对方惊喜,他们在互相赶往对方城市的列车上错过了彼此,两人没有享受到渴盼已久的中秋团圆日,最后只能在各自搭乘的列车交汇处挥手致意,但他们心中仍不乏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正如小说结尾所写:“这列车永远起始于黑夜,而它的终点,也永远都是黎明。”[6]80与以往的小说文本侧重事件的矛盾冲突不同的是,这篇小说以进城乡下人温暖细腻的内心情感打动人心,林秀珊和王锐作为情感主体的诗意建构给读者带来新的思考。
总之,以王安忆为代表的作家在创作“乡下人进城”小说时,能从日常生活的内部出发,淡化事件的戏剧性冲突,体察进城乡下人的成长经历和蜕变历程。这些乡下人虽然仍生活在城市底层,物质生活不尽如人意,但他们能理性地看待城乡文化的不平等性,并进行自我主体性调适,以期与城市更好地相融。
2 进城乡下人新形象的塑造
从叙事观念上来看,很多“乡下人进城”小说过于突出乡下人在城市的边缘地位,他们往往被贴上“肮脏”“愚昧”“落后”的标签,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进城乡下人形象的污名化、模式化与扁平化。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正如作家赵本夫所说:“过去我们写的农民工,只有两种面孔,一种是很卑微的,一种是善于阴谋和钻营的。两种面孔其实有着一样的内心,都在寻找与城市的认同感,他们对于城市是仰视的……这种仅仅把他们作为一个弱势阶层来写的视角并不全面。”[7]如果抛却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从人性的视角观察乡下人融入城市的过程,或许可以发掘出他们城市生活的劳动价值及其所蕴含的精神闪光点,以此建构进城乡下人的新形象。
乡下人新形象的塑造首先表现在作家对他们劳动价值的肯定上。乡下人常因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源的限制,只能在城市从事一些较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即便如此,他们的劳动价值还是常常不被认可,融入城市的愿望更是遥不可及。“20世纪中国文学中绝大多数进城乡下人的生活图景都是被放在城市生活外部展开的,他们远离市民群体……无法触摸到城市跳动的生活脉搏,身份认同自然无法确认。”[8]115与这类“过客”型的乡下人形象不同,王安忆在日常叙事中突出了乡下人身上所蕴含的劳动价值。《民工刘建华》刻画出一个手艺过硬而又有点自负、聪明干练而又有点狡黠的乡下人新形象。作家开篇就写出了刘建华干活时工具的齐全和技术的精湛,就连对他成见极深的老黄都忍不住夸赞他基本功的过硬。同样,《骄傲的皮匠》中在城市修鞋的小皮匠之所以“骄傲”,也是因为他高超的修鞋技术。小皮匠秉承“坚固总是第一位”的修鞋原则,就连轰动一时的“山姆大叔机器修鞋店”都无法与之媲美,表现了人的劳动价值的不可替代性。除此而外,小皮匠爱干净,上班从来都是穿戴整洁,一丝不苟,夏天穿衬衫,冬天穿滑雪衫。他不仅凭借精湛的修鞋技艺赢得了弄堂人们的信赖和支持,还以其忠厚善良的品性赢得了城市女性根娣的喜爱。刘建华和小皮匠是与之前进城乡下人迥然相异的崭新形象。王安忆在《富萍》中对梅家桥棚户区一带靠出苦力谋生的乡下人也表达了她的肯定性价值判断。“他们诚实地劳动,挣来衣食,没有一分钱不是用汗水换来的。所以,这些芜杂琐碎的营生下面,掩着一股踏实,健康,自尊自足的劲头。”[9]186王安忆笔下的进城乡下人或吃苦耐劳、或有高超的技术手艺,他们都凭自身的劳动潜入城市生活内部。作家能平等地看待不同劳动的价值属性,把劳动视为个人价值的重要体现形式,并对这些底层小人物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予以肯定,这也从侧面显示出现代城市包容开放的精神向度。
有学者指出:“对待劳动的姿态,在一定意义上也暗含了农民工对待城市的姿态。当他们仅仅将劳动作为谋生手段时,城市与他们无关,劳动的对象及其成果都是一种异质的存在;但当将劳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时,城市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劳动的对象及其成果都是一种同质性的存在。”[10]326由此可见,对待劳动的不同态度影响着乡下人对城市的认知,也决定着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城市。赵本夫《无土时代》中来自草儿洼的进城农民天柱热爱绿化事业,踏实肯干,工作突出,担任木城绿化队队长一职。与其他农民仅把进城务工当作谋生手段不同的是,天柱有更宏大的抱负,那就是把农村的麦田种遍城市的每个角落。他带领手下的农民工把苏子村大片的麦苗移植进城市的草坪,看似为了改善木城的自然环境,其实是想要用乡村自然文明对抗城市现代文明,以此唤醒城市人的土地记忆。“别人干活纯粹为挣钱,我干这活还觉得快活”[11]123,可见以天柱为代表的进城乡下人对自己的劳动价值有着清醒的认知,他们并未陷入对金钱和权力的肆意追逐中,而是将劳动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由此不断深入城市的内部肌理,进而实现身体和精神的全面进城。
乡下人新形象的塑造还表现在作家对进城乡下人精神品质的勘察上。“城市环境的最终产物表现为它所培养出的各种新型的人格。”[12]5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并没有回避乡下人城市生活的艰辛悲苦,而是呈现出生活本来如此的温情画面,发掘蕴藏于进城乡下人身上的精神力量,从而让他们“在面临选择的困惑和现实的困境时拥有超拔眼光、摆渡精神的力量”[13]294。《骄傲的皮匠》中小皮匠只身一人来上海打工,虽然也渴望妻子“绵软的身体”,但他能洁身自好。虽然小皮匠也一度迷失在与城里人根娣的婚外情旋涡中,但他能及时止损,把乡下老婆和两个孩子接到身边,表明了他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坚守。小皮匠爱读书、好思考,对不同年代的书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与理性认知,他不但没有盲目地崇拜城市消费文化,而且对城市人的膨胀物欲予以批判。无独有偶,池莉《托尔斯泰围巾》中收破烂的老扁担也爱好读书,在回收废弃的报纸杂志时,他不像其他收破烂的那样随意撕扯踩踏,而是对书本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在老扁担寒酸破旧的出租屋内,摆放着毛笔、墨水和成摞的文学杂志,表现出他对知识的渴求,这让身为作家的“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老扁担一开始靠出苦力挣钱,在装修队以次充好欺骗花桥区的居民后,他不但没有逃跑,反而向大家坦言自己的秤是七两秤,最终他以诚实坦率的品格赢得了小区居民的信赖,“围巾”成为他高尚人格的象征物。杨静龙的《遍地青菜》直面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空间的吞噬,菜农许小晴在拖拉机的轰鸣声中失去了土地,迫于无奈只能到城里当保姆。出于劳动的本能,她想在小区空地上栽种青菜,虽然遭遇了小区孩子们的破坏和痦子物管的阻挠,但许小晴凭借着乡下人吃苦耐劳的美德获得了城市雇主的尊重。最终,许小晴在杨大哥的帮助下把青菜种遍了C城的每个角落,实现了自己的“田园梦”,她也被评为“感动C城十大新闻人物”,意味着城市对乡下人的接纳与肯定。
作家们以平等的眼光审视乡下人融入城市过程的情感嬗变,并给予他们超越苦难的精神性力量。“乡下人进城”小说中的乡下人新形象,让我们看到这些人身上所蕴含的劳动价值及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优秀的小说不止于向人们简单描述和呈现生活的本来面貌,还以超拔的眼光和深邃的思想向人们揭示事物发展的新可能与新趋向。正如秘鲁作家略萨所言:“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表示用这样的拒绝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想象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代替现实世界的愿望。”[14]6
3 城乡关系的新表达
城乡关系书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不论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作家直面乡村的落后与凋敝,剖析国民灵魂深处的痼疾和劣根性,还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因不满于罪恶血腥的城市生活而回望原始淳朴的乡村田野,并把乡村视为真善美和人性之所在。“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乡土叙事中,城市及其文明始终扮演着双面的角色,一方面是先进与文明的代表,从而成为批判乡村愚昧落后的参照,另一方面又成为罪恶的渊薮,从而成为歌颂乡村田园牧歌及淳朴善良的人情美、人性美的参照。”[15]72这种对城市的暧昧态度表现在小说中,就是城市与乡村处于对立的局势,城市人与农村人也处于彼此隔绝的状态。在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中,这种城乡对立更成为普遍泛化的文学景观,这固然与当下以城市为中心而将农村农民边缘化的现实有关,但更与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城乡观念息息相关。贾平凹就曾坦言:“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好像农裔作家都是这样,有形无形中对城市有一种仇恨心理,有一种潜在的反感,虽然从理智上知道城市是代表着文明。”[16]62所以,与其说乡下人在城市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磨难,还不如说是作家在小说中宣泄他们对城市的憎恶和不满。“也许,真正熟于城市,才能不把人的境遇归结为诸如‘城市罪恶’一类的主题,而归结为人性与更为普遍的人类处境。”[17]200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积极探索城乡关系新的表达方式,从而拓宽了这类小说的书写向度。
城乡关系的新表达首先体现为城乡关系的平等性与城乡融合的趋势。在以往的“乡下人进城”小说中,城乡对峙一直是作家叙事的重心,表现了城乡二元体制的深远影响。然而,文学作品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如实照搬,作家们完全可以对现实进行提炼加工甚至再改造,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情感寄托。《遍地青菜》中的菜农许小晴来到城市当保姆,在和城市雇主杨大哥与赵姐的交往中,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尊重。许小晴在小区空地上种青菜遭到痦子物管的干预,意味着乡村伦理与城市文明的初次交锋,作家并未将两者处理为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最终,许小晴在杨大哥的帮助下把青菜种遍了C城的每个角落,实现了城市空间的乡村化建构。小说用“青菜”这一核心意象,连接了城市和农村这两个地理空间,预示着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正如城里人杨大哥所说:“其实,在多少年以前,并没有什么城市和农村之分。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他的名字就叫农民。所以,我们的血脉是相通的,那些血最后终究会汇流在一起。”[18]63这也体现了作家城乡同根同族、一体化发展的思维理念。《无土时代》中的天柱从草儿洼来到木城担任绿化队队长,他想要以乡村的方式改造现代城市,梦想着将乡下的庄稼种到城市来。在一次迎接上级的卫生检查活动中,天柱带领手下的农民工把苏子村周围的麦苗全部移栽到城市当草坪。这一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在木城引起了轰动,最后麦苗不但没有被清除,反而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绿化景观被保留下来。“麦收季节终于到了。一阵阵新麦的香味溢漫在每寸空间,闻着都让人舒坦。全城像过节一样,到处欢声笑语。”[11]358农作物被移植进城市,唤醒了人们对土地种植和四季流转的记忆。面对“无土”之城的现状和城市现代文明对人性的侵蚀,赵本夫在纸上建构起“有土”的乌托邦之城,寄寓着他对城市现代化的理性审视,也承载着城乡融合的发展新变。
其次,城乡关系的新表达还体现为作家用城里人的粗鄙衬托乡下人的理想人格。《托尔斯泰围巾》中的老扁担真心待人,靠自己的苦力吃饭,即使因房屋装修的事被花桥小区的居民误解,他也没有退缩逃避,而是坦荡地过着自己卑微平凡的生活,老扁担待人恭敬,对知识充满渴望,显示出其人格力量的伟大。相比之下,城里人王鸿图靠着剽窃自己老师饶庆德教授学术成果的不正当手段评上职称,分得住房,甚至和妻子聂文彦共同对付上门讨要工钱的老扁担。作家批判市民阶层的冷漠势利,以此彰显乡下人的高尚品质,同时,叙述者“我”也将批判的矛头对准自己。当“我”看到老扁担出租屋内摆放整齐的各种书籍和练习的大字时,震惊之余也感到羞愧难当:“我辈惭愧,虽有书房,毕竟掺杂了许多功利的因素;因要用书,故而有书?若讨饭食的本领完全无须用书,我是否还会有书?”[19]329《骄傲的皮匠》中的底层市民爷叔游手好闲、出言不逊,小皮匠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敢于和他动手打架。作家通过描写爷叔的自私颟顸,表现了小皮匠的现代人格。在小皮匠看来,城市人根娣说话幼稚,远比不上乡村女性的机警世故,连根娣的丈夫小弟也说:“乡下人是不可小瞧的,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大家都要为乡下人打工。”[4]40这样的评判可以说与之前“乡下人进城”小说的城乡叙事话语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固然暗含了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分野,但更体现了作家对城乡关系的进一步反思。
总之,作家们一方面看到城乡融合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又通过城里人的人格缺陷突出进城乡下人的精神品质。随着国家城乡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前辈相比,自我认知、城市认同和消费需求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作家理应看到这种趋势,及时书写城乡关系的新变化,积极探索城乡融合的道路,不断丰富“乡下人进城”小说的书写内涵。
4 结 语
在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中,作家超越了以往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在淡化冲突的日常叙事中塑造进城乡下人的新形象,积极探索城乡关系新的表达方式。也许会有学者质疑这些作家笔下的乡下人形象有失真实,小说人物一定程度上成为作家情感的主观投射。然而,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穿透现实的重重迷雾而直抵人心,能通过纷繁复杂的社会表象而揭示人性的光亮,进而给人提供精神的力量和向上的勇气。以王安忆为代表的作家摆脱了以往“乡下人进城”小说的苦难叙事主题和城乡对峙的思维模式,理性地审视进城乡下人的现实遭遇和精神困惑,凸显出他们的主体价值和人格尊严。这样的文学新书写丰富了小说的审美表达,给广大读者带来新的思想启示,应当引起批评家们的关注。
——根据课文《乡下人家》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