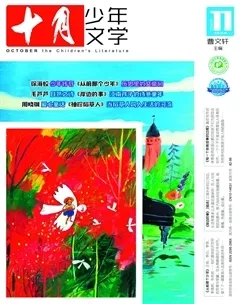[评论]鲜衣怒马少年时
世界的本质是叙事,向我们讲述它的未来,它的过去。历史不是孤立的平面,而是上下纵横多种关系的交织,从而提供了多重评说的可能性。历史人物则具有“原型性”,本身就蕴含了诸多解读的可能。当然,当历史进入文学,则进入了主体言说的当代语境,并经由作家主体个人体验而存在,是一种主观化的“自由叙事”。那么,《从前那个少年》,要和我们的当代读者述说什么呢?
五个片段,五位天才少年——王勃、李白、李贺、李清照和辛弃疾的少年人生剪影,以激情、诗意与美感,以带有个体生命情感的辉映,书写勃勃少年生机与意气。
少年意气,挥斥方遒。一切都还刚刚开始,一切都充满了美好与希望。所以,王勃篇写到他因戏做《檄英王鸡》被逐出长安,在名山大川游历间满怀对长安的希望就好,不必写他视宦海为畏途,更在去交趾县看望父亲归来的途中,溺水惊悸而死;所以,写到少年李白“仰天大笑”出川,自觉“我辈岂是蓬蒿人”就好,不必写中老年李白的罹难流离;所以,写到少年李贺行卷打动韩愈韩大学士,河南府试登榜即可,又何必管后来的迁调无望、功名无成,妻之病卒;所以,写到少女李清照的醉卧溪亭、误入藕花深处就好,又怎知后来的靖康事变,夫死国破;所以,写到少年辛弃疾文武双全,“抵燕山,谛观形势”,誓将收复这大好河山就好,又何必知晓后来的南宋偏安,辛弃疾屡遭劾奏,数次起落,最终退隐山居?
少年鲜衣怒马,对自我的天赋、才情确信不疑,对把握自我的命运与人生确信不疑。这是少年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时光流逝,当造化之手、时代洪流露出獠牙,将个体人生轻轻拨弄,英雄路短之际,才发现时间不可逆,命运不可敌。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所以,打住就好,半篇最妙。
少年意气汪洋恣肆,不仅形构了《从前那个少年》的故事细节,被赋予了重要的叙事功能,而且沉淀了作品的基本精神。这是一种包容的生命视野和悲悯的人性关怀。
历史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的虚构性,在根本上不能脱离想象;想象使历史得以完成。作为一篇历史题材的儿童小说,《从前那个少年》摒弃史实堆砌的纪事手法,转而关注历史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复活了耐人寻味的思想与细节,艺术再现了主人公的命运张力和生命活力。以基本历史事实作为构筑故事空间的依据,又运用小说的想象和散文化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构筑了作品诗性的意蕴空间。小说中史实是基础,但经作家诗意的眼光发掘、变换,作品鲜活起来,有识、有情、有意境,将情感与思想诗意再现,使该历史小说获得了一种充沛的审美体验。
对特定历史片段下人物际遇的感怀,饱含了文学感性光辉的烛照。作品并非政治视角对历史解释的垄断,而代之以个人史、心灵史,表达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和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叩问,形成了作品强烈的人文关怀。那就是,任命运千折百回,我少年志气干云。
康德曾言,美是自由的象征,自由就是乌托邦。人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自由,人生本是有限定性的。然而,少年儿童以内在心灵力量超越凡俗现实的生命力,形塑了童年精神之根本,也成为人类精神慰藉的落脚点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