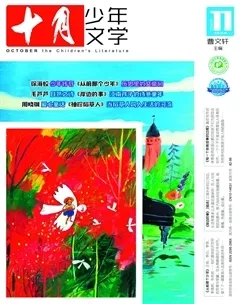把“少年之气”还给少年吧

女儿已经读高一了,她经历了初中三年的痛苦,现在还将经历新的痛苦。
大多数时间,只要不在学校,她都会将房门一关,躲进自己小房间里,坐在一张白色写字台旁刷题。除了睡觉,我见到她时,就是在刷题。以至于我常常会有困扰,有时想跟她沟通些什么,比如就某个问题探讨一下看法,即便这样简单的互动都会因为她要急着赶作业,而变得仓促潦草,阻碍重重。
初中三年结束,女儿将学校里搬回来的学习资料、习题集、各类试卷,加上房间里的学习资料全部理出来,装了满满12个手提袋。这12袋学习资料卖给了收废品的老汉,过了秤,足足130公斤。但她同学的学习资料似乎分量更足,有150公斤的,也有很多达到了200公斤。
这130公斤的习题,远远超过了女儿自身的体重,它承包了我女儿13岁到16岁的少女时光,这段时光,她本来还应该到田野里去放风筝,到湖畔去追逐落日,到剧院里去看戏;她本来还应该在书房里写她的隶书,在房间里弹她的钢琴,或者去森林里拥抱一棵百年的老树……她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了,但她错过了几乎所有关乎成长的事情。
那些类似于飞扬、无畏、率性、心比天高……这样的词语都已经在少年的心灵里渐渐枯萎了。
我想,这不光是我眼中的女儿,更是全中国99%的家长眼中的孩子。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我承认自己的心在这一刻被揪得紧紧的。应试教育的痛,间接地作用在我身上,就像狠狠地打了我两个耳光,生疼生疼的。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能做些什么呢?有一天,我突然想写写那些从前的少年,他们来自唐宋时代,之后都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璀璨的星辰。他们的文字穿越千年时光,即便在今天,依然照耀着我们的灵魂。他们之所以成为后来的他们,跟少年时代经历的种种绝对不会没有关系。我在故纸堆里拣择,又在纸页间以汉字重塑了从前那些少年,他们是王勃、李白、李贺、李清照和辛弃疾。当这五个少年站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了少年中国的蓬勃之气,也看到了中国少年的希望和抱负。
我不想定义少年,少年是无法被定义的,正因为没有边际,才有无限可能。但我想,世间真正的少年又是相似的。
我一直很喜欢一个词语,叫“少年之气”,什么是“少年之气”?那是一股虎虎生威的向上的朝气,是一股天真的率性之气,是一种永不言败的信念,也是一个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壮梦想。这些唐宋的少年,他们的心里还没有懦弱和退缩,他们有大把大把的勇气,他们或执剑天涯,或到广阔的山野里采集诗篇,或以初生之犊的无畏挑战威权,或背负着宏大的理想主义向前走去。他们心里装着一个阔大的世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他们有关。
我期待,这样的“少年之气”有一天能回到更多孩子身上。
徐海蛟,浙江宁波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散文学会副秘书长。曾获第四届《人民文学》新人奖、第十九届文津图书奖(提名奖)、三毛散文奖大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优秀作品奖、“小十月文学奖”散文组金奖等。在《人民文学》《十月》《作家》《山花》《青年文学》《散文选刊》《雨花》《芒种》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200多万字。著有《不朽的落魄》《山河都记得》《故人在纸一方》《亲爱的笨蛋》等15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