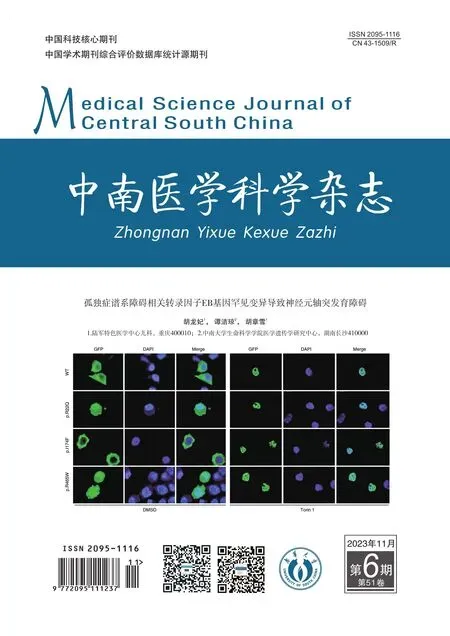巨噬细胞功能M1/M2极性化在心血管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张晓天, 任昊麟, 亢梦婕, 周明生
1.沈阳医学院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系,辽宁沈阳 110034;2.大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科,辽宁大连 116011;3.沈阳医学院科学实验中心 沈阳市血管生物学重点实验室,辽宁沈阳 110034
巨噬细胞(macrophage,Mac)是先天免疫系统的主要细胞,在器官发育、炎症、组织稳态和重塑中发挥重要作用[1]。巨噬细胞具有异质性和可塑性,通过极化改变其功能表型,根据其功能极性最少可分为经典激活M1(促炎性)和替代激活M2(抗炎性)2个功能亚型[2]。M1巨噬细胞参与启动先天性免疫反应和维持炎症反应,分泌促炎性细胞因子和活性氧自由基(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在宿主免疫防御和组织炎症反应中起重要作用;M2巨噬细胞通过吞噬和清理凋亡细胞,驱动胶原沉积和血管新生,释放抗炎介质起到抑制炎症和组织修复作用。巨噬细胞极化还伴随代谢途径的改变,引起代谢重编程,包括糖酵解、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和脂肪酸氧化以及氨基酸等变化[3]。巨噬细胞M1/M2功能亚型之间的平衡是维持生物体内环境稳定的一个重要机制,改变这一平衡可能引起各种疾病,包括炎症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等。现将巨噬细胞在心血管疾病中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巨噬细胞功能极性分类和调控
巨噬细胞是一种极具可塑性的细胞,能通过功能极化的方式迅速改变其细胞功能表型。M1巨噬细胞通常是在细胞介导的宿主免疫应答期间产生,被Toll样受体TLR4及其配体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或γ干扰素(interferon-γ,IFN-γ)激活,产生大量的促炎性细胞因子和ROS,介导宿主免疫防御反应和组织早期炎症反应[4]。M2巨噬细胞通常是受到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4、IL-10、IL-13和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刺激而启动,产生IL-10、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TGF-β抗炎性细胞因子,介导组织修复,促使干细胞增殖、血管生成及纤维化等过程[5]。巨噬细胞除M1和M2极性亚型外还可能还存在一系列中间过渡亚型,如M2a、M2b、M2c或Mox等亚型。
M1巨噬细胞常由微生物感染性抗原所诱导,这些外界抗原与巨噬细胞表面Toll样受体4(Toll-like receptor 4,TLR4)受体结合,通过经典先天性免疫通路激活核转录因子-κB(nuclear factor-kappa B,NF-κB)促进巨噬细胞激活,释放大量的细胞炎症因子,包括IL-1β、IL-6、IL-1、趋化因子配体9(C-X-C motif chemokine ligands 9,CXCL9)、CXCL10、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1,MCP-1)、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ible NOS,iNOS)和ROS,这些炎症因子可以杀死外来的细菌和微生物,以启动宿主的免疫防御反应。M2巨噬细胞受免疫细胞,如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或IL-2淋巴细胞调节,具有抗炎特性,表达高水平的甘露糖受体及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6、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PPARγ)、CD163、CD36和精氨酸酶-1(arginase-1,ARG-1)[4,6],产生促纤维化因子,如TGF-β、IL-10等,有助于炎症消退、组织修复和愈合[7]。
2 巨噬细胞能量代谢途径
正常情况下,巨噬细胞处于未激活状态,称为M0巨噬细胞或幼巨噬细胞,为非极化的免疫细胞。这些细胞需要经过代谢重编程来获得功能必需的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主要途径是葡萄糖和脂肪酸的氧化磷酸化,伴随氨基酸代谢,如精氨酸及谷氨酰胺代谢。在感染或抗原刺激下,巨噬细胞进行代谢重编程,能量代谢途径从氧化磷酸化转变为无氧糖酵解,其表型和功能也发生了极化。
2.1 葡萄糖代谢
葡萄糖代谢产生ATP主要通过两条途径,糖酵解:葡萄糖在细胞质内代谢为丙酮酸,同时生成ATP;线粒体三羧酸循环(TCA循环,也称克雷布斯循环或柠檬酸循环):丙酮酸在线粒体内还原为乙酰辅酶A[8],在TCA循环中还原反应产生的电子用于氧化磷酸化电子链,生成36个ATP。NADP与电子和H+作为底物生成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NADPH),并在NADPH氧化酶的作用下传输质膜上的电子,产生超氧化物和其他下游ROS[9]。虽然糖酵解产生的ATP量少于氧化磷酸化,但速率快,特别是炎症感染等引起巨噬细胞激活的微环境常常处于缺氧状态,糖酵解对低氧环境下维持M1巨噬细胞能量代谢水平和功能活性至关重要。癌细胞即使在氧充足条件下,也有能力进行糖酵解代谢,这有别于非癌细胞的能量代谢主要依赖氧化磷酸化,这一现象也被称为Warburg效应或有氧糖酵解,癌细胞所拥有这种特殊能力代谢功能可能是在各种环境中快速生长的一个重要机制[10]。巨噬细胞在受到LPS、抗原或其他细胞因子刺激后,诱导M1极化,通过代谢性重编程,从氧化磷酸化切换到糖酵解在缺氧环境中快速获得ATP,维持高水平的能量代谢,有助于维持线粒体膜电位。
在M1巨噬细胞中,由于TCA循环代谢过程中的几个关键点被中断,使一些具有信号分子调控功能的代谢物柠檬酸、琥珀酸等从线粒体逃脱并发挥信号调节作用,谷氨酰胺和精氨酸的消耗增加。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能阻止氧化磷酸化进程,而氧化磷酸化能阻止巨噬细胞从M1表型极化到M2表型[11]。琥珀酸可影响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1 α,HIF-1α)的稳定,HIF-1α是一个氧敏感的转录调控因子[12],通过促进低氧环境下的无氧糖酵解参与细胞能量代谢的重编程,调节糖酵解酶基因转录、1型葡萄糖转运蛋白及编码炎症的基因表达[13]。HIF-1α是巨噬细胞缺氧环境下无氧糖酵解的开关,促进M1巨噬细胞的极化,而HIF-2α通过激活PPARγ增加Arg-1的表达,有益于M2巨噬细胞的代谢重编程和巨噬细胞M2极性化。
2.2 脂肪酸代谢
巨噬细胞作为特化的吞噬细胞,能通过吞噬死亡细胞以及细胞表面清道夫受体CD36摄取各种脂质,如低密度脂蛋白、极低密度脂蛋白和血浆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oxidative low-density lipoprotein,ox-LDL)。巨噬细胞通过表面的CD36吞噬ox-LDL,内吞的ox-LDL可以向PPARγ提供特定的氧化脂质,上调CD36的表达[14]。CD36功能异常可引发脂肪酸代谢紊乱、炎症,并激活M1巨噬细胞。脂肪酸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u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已被证明可诱导肥胖脂肪细胞中M1巨噬细胞极化[15],葡萄糖、胰岛素和肥胖诱导的缺氧也会激活HIF-1α促进巨噬细胞M1极性化。脂质代谢还受到甾醇受体元件结合蛋白(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binding protein,SREBP)和肝脏X受体(liver X receptor,LXR)的转录调控。LPS通过激活NF-κB信号途径增加SREBP-1α活性,产生IL-1β,调节脂质代谢和炎症反应,而在SREBP-1α缺失的巨噬细胞中,LPS刺激不能产生IL-1β[16]。M2巨噬细胞以LXR激活为特征,LXR调节胆固醇稳态和脂质合成,还参与调节巨噬细胞的免疫和炎症反应,髓系LXR缺乏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剧增,并有泡沫细胞形成和斑块形成增加[17]。过表达或激活LXRα可以通过抑制NF-κB和衔接蛋白复合物(Adaptor protein complex 1,AP-1)的活性来抑制M1巨噬细胞炎症反应。
2.3 精氨酸代谢
精氨酸是iNOS的代谢底物,而iNOS是M1巨噬细胞的一个重要标志物,iNOS分解精氨酸产生瓜氨酸和NO。NO作为一种内源性血管舒张剂,引起血管扩张,增加炎症感染局部的血流量,此外,NO可与氧气或ROS反应,生成多种活性氮和活性氧自由基中间体,这些活性氮和活性氧自由基中间产物对微生物细菌等具有强烈地杀伤作用[18]。另一方面,精氨酸代谢中的另一个关键酶Arg-1是调控巨噬细胞M2极性化的一个重要因子。Arg-1将精氨酸代谢为鸟氨酸和尿素,用于产生多肽和脯氨酸,因此,Arg-1活性对诱导M2巨噬细胞极化至关重要。Arg-1在M2巨噬细胞中高表达,并通过调节巨噬细胞M2极化,加速炎症消退[19]。
2.4 谷氨酰胺代谢
谷氨酰胺代谢与巨噬细胞极化息息相关。M1巨噬细胞中谷氨酰胺代谢转化产生精氨酸,后者与NO生成相关。巨噬细胞暴露于高水平谷氨酰胺中,会抑制NF-κB通路的激活,降低TNF-α、IL-1α等炎症细胞因子产生,增加抗炎症因子IL-10产生,促进M2极化[20]。TCA循环中三分之一的碳元素分子来自谷氨酸,谷氨酸也是M2巨噬细胞氧化磷酸化的重要来源。谷氨酰胺分解产生的α-酮戊二酸对巨噬细胞极化有重要调控作用[21]。高α-酮戊二酸/琥珀酸比例增强M2极化表型,相反地,低α-酮戊二酸/琥珀酸比例增强M1极化表型。
3 巨噬细胞能量代谢重编程
巨噬细胞在改变功能极性的过程中常伴随着能量代谢的重编程,线粒体是细胞能量代谢和代谢重编程的主要场所,在维持细胞能量生成和免疫应答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心血管疾病常伴有脂质代谢紊乱,CD36是ox-LDL和脂肪酸摄取并发挥生物效应的重要受体。ox-LDL刺激巨噬细胞会加快脂肪酸摄取,而CD36敲减会减少脂肪酸摄取[22-23]。CD36与配体ox-LDL结合后,可引起线粒体能量代谢从氧化磷酸化转换到超氧化物产生,并增加巨噬细胞线粒体ROS生成,诱导NF-κB活化以及促炎基因的表达,抑制耗氧率,并滞后上调细胞外酸化率,增加葡萄糖摄取,上述变化被CD36敲减所抑制[24]。ox-LDL暴露不会明显改变细胞ATP、ADP和NAD水平、线粒体质量和线粒体膜电位,但会抑制ATP合酶α亚基半胱氨酸氧化修饰,抑制线粒体ATP产生,使细胞切换到无氧糖酵解,获得ATP维持细胞代谢活动,上调IL-1β、IL-2β、CXCL2等炎症基因表达。ox-LDL会重编程糖酵解代谢进程,上调糖酵解限速相关基因hk3、pfkl和pkm的表达,但大多数糖酵解相关基因表达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下调TCA循环中的大多数基因和脂肪酸合成酶基因的表达,而脂肪酸转化为脂肪酰辅酶A的基因大多上调。
4 巨噬细胞功能极化与心血管疾病
4.1 动脉粥样硬化
动脉粥样硬化被认为是一种由脂质代谢异常引起的慢性血管性炎症疾病。单核巨噬细胞激活机制在动脉粥样硬化中还不完全清楚,Chen等[25]提出,ox-LDL与巨噬细胞表面上的CD36结合可促进CD36与比邻的TLR4(LPS受体)/TLR6形成二聚体或三聚体,后者通过Myo88/NF-κB通路促进巨噬细胞激活。此外,一些胆固醇结晶体被巨噬细胞吞噬后,激活细胞内的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3(neutrophi alkaline phosphatase 3,NALP3)通路形成炎性小体而促进巨噬细胞激活。在人和ApoE-/-小鼠的动脉粥样斑块中M1巨噬细胞标志物表达增加[26-27],烟酸等治疗在促进斑块消退过程中常伴有M2巨噬细胞标志物表达增加。Zhang等[28]研究发现,ox-LDL显著增加M1细胞因子TNF-α和IL-1β的mRNA表达,上调TLR4,促进NF-κB激活,中药葛根素抑制ox-LDL诱导的巨噬细胞激活和促炎基因表达,下调CD36表达,抑制泡沫细胞形成和巨噬细胞凋亡。进展型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以M1巨噬细胞表型为主,有促炎症作用,而M2表型在稳定性斑块中的比例相对较高[29]。
4.2 高血压
高血压被认为是一种慢性血管性炎症疾病,伴有免疫系统功能异常和单核巨噬细胞功能极性变化[30],高血压引起单核巨噬细胞激活浸润的机制还不清楚。巨噬细胞释放的促炎性细胞因子如TNF-α,能增加血管内皮细胞ROS产生,并抑制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eNOS)磷酸化,引起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和血管炎症[31]。用化学药物或基因敲除等方法去除高血压小鼠的单核巨噬细胞可有效地降低血压和ROS,增加eNOS,改善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减轻心、肾结构和功能损伤[32]。高血压与巨噬细胞功能亚型有密切关系。Ndisang等[33]研究表明在自发性高血压大鼠中,使用血红素增强血红素加氧酶(heme oxygenases,HO)可减轻MCP-1、巨噬细胞炎症蛋白1α等M1表型的表达,增强巨噬细胞M2标志物ED2、CD2和CD206表达,而HO抑制剂阻断了上述效应。这些发现支持了巨噬细胞可能是高血压免疫治疗新靶点的观点。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在高血压发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不但增加血管张力和肾脏水盐重吸收,增加血压和ROS生成,还促进单核巨噬细胞浸润,氧化应激和血管炎症,引起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和血管损伤。血管紧张素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一型受体抑制剂和醛固酮受体阻断剂等通过抑制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过度激活阻断这些病理过程,降低血压并保护血管和靶器官功能。研究发现,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不但存在于血管、心脏、肾脏等高血压靶器官,而且参与单核巨噬细胞M1/M2极性化调节以及高血压的发病机制[34]。Usher等[35]研究发现,髓系特异性敲除盐皮质激素受体(mineralocorticoid receptor,MR),可以抑制高血压鼠的心脏和血管肥大、炎症及纤维化,并抑制巨噬细胞激活。研究发现,血管紧张素Ⅱ可直接诱导巨噬细胞激活,并通过ROS/HIF-1α激活TLR4/NF-κB信号通路[28]。髓系细胞特异性AT1R敲除可以改善盐敏感性高血压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降低巨噬细胞血管壁浸润、炎症和血管损伤,并减少腹腔巨噬细胞M1炎症细胞因子表达[36]。
4.3 吸烟诱发心血管疾病
吸烟是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ox-LDL通过增加CD36乙酰化激活CD36,增加巨噬细胞的脂质摄取,促进泡沫细胞形成[37]。慢性尼古丁暴露可增加巨噬细胞产生促炎细胞因子,从而促进动脉粥样硬化过程[38]。尼古丁通过烟碱受体选择性地增加CD36基因表达,但不影响巨噬细胞炎症因子的表达[39]。尼古丁与ox-LDL协同性增加巨噬细胞的CD36表达,并增强ox-LDL致炎效应和促进TNF-α、MCP-1、IL-6和CXCL9的表达,增加巨噬细胞脂质沉积和泡沫细胞形成,上述过程被沉默CD36基因所逆转。这些结果提示尼古丁或者吸烟可能通过上调巨噬细胞CD36介导的炎症和脂质代谢紊乱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吸烟可以增加肥胖患者心血管疾病的易感性,在高脂诱导的肥胖大鼠中,长期尼古丁(20周)治疗增加血压、血管ROS产生及血管舒张功能障碍,增加巨噬细胞M1炎症因子表达和血管炎症[40],提示尼古丁可能通过激活巨噬细胞加剧肥胖引起的血管损害。
4.4 COVID-19感染引起的心脏损害
COVID-19感染或新冠肺炎是由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感染引起的一种全球大流行性疾病,由于极高的传染性导致全球病例呈爆发性增长,对全球公共卫生系统和人类生命安全带来了挑战。COVID-19主要影响呼吸系统,但重症患者可引起全身各器官损伤,在心血管系统,引起心肌炎症、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2,ACE2)是COVID-19入侵人体发挥作用的一个主要受体,参与调控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功能,在心血管系统中广泛分布。小鼠模型和人类尸检结果提示,COVID-19下调肺部和心肌的ACE2表达,并伴有明显的心脏组织巨噬细胞浸润和心肌损伤,并上调CCL2促进单核细胞从循环血中向组织迁移,增加组织中巨噬细胞浸润[41]。ACE2降低可能增加NADPH酶活性和ROS产生,影响线粒体功能稳态,并可能抑制巨噬细胞线粒体氧化磷酸化转向糖酵解代谢[42]。COVID-19感染引起心血管损伤的另一个机制是巨噬细胞释放大量促炎性细胞因子而引发炎症风暴,有学者提出COVID-19感染可表现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表现为心肌损伤,冠状动脉血流量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和微血栓形成,促进病情恶化。重症COVID-19患者血浆中促炎性细胞因子IL-2β、IL-6、IL-7、IL-17、IL-19和TNF-α等显著增加,与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症状极为相似[43]。此外,通过抗炎症治疗来抑制炎症因子风暴可减轻COVID-19感染患者心血管和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症状及缓解病情[44],对一些重症COVID-19感染患者,应用抗IL-6、IL-1和TNF-α等抗炎性炎症因子治疗,可以明显缓解临床症状,也支持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参与COVID-19感染导致的心血管损伤。
5 小结和展望
巨噬细胞具有不同的功能表型和多样性,M1巨噬细胞具有致炎性,产生和分泌促炎性细胞因子。M2巨噬细胞具有抗炎特性,参与平息炎症和组织修复。吸烟、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危险因素或心血管疾病发病促进M1巨噬细胞极性化或改变M1/M2巨噬细胞比率参与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加强巨噬细胞极化在心血管疾病的分子和细胞机制的基础研究,研发对巨噬细胞功能亚型具有靶向诱导效应,并能控制各功能亚型的巨噬细胞在心血管疾病发生过程中的比率,利于心血管疾病康复的靶向药物可能为未来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带来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