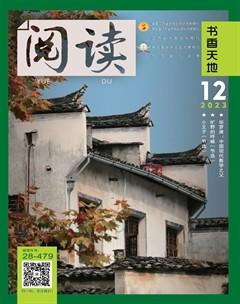我家的兔子
李娟

我家的兔子跟狗一样黏人,老围着人打转。
特别其中一只,整天简直寸步不离。
我妈去地里干活,那么远的路,那么大的一片地,它能跟着走到头。我妈劝它:“你还是回去吧,还有好远的路要走呢。”
兔子东张西望,拒绝沟通。
“你看你,鞋子也没有一双。走这么远,也不嫌脚疼。”
兔子若无其事抖抖耳朵。
我妈继续往前走,兔子左跳右跳,独立、蓬勃、骄矜。 红眼睛一闭,天地间就少了两颗珠宝。
我妈心中喜悦。被一只美丽的生命追随,活在世上的辛劳与悲哀暂时后退。
她忍不住模仿兔子的脚步。
兔子依恋我妈,源于生命之间最孤独的引力吧?
月球紧随地球在茫茫银河系间流浪,唯一的兔子和唯一的我妈在地球一隅的葵花海洋中漂流。谁也无法舍弃对方。
我家的狗赛虎也依恋我妈。但那种依恋是求取安全感的依恋。它无论何时何地都略微惊惶。
赛虎也依恋兔子。我妈把出生不久的小兔子捧给它看,它像触碰梦境中的事物一样,极其缓慢地、迷茫地探身向它,亲吻般触动着它,仿佛新生的事物不是对方而是自己。
仿佛那是它第一次出现在世上,第一次满心涨满柔情地接受活在世上的命运。
兔子的天性是打洞。若将它和鸡一样撒开养在荒野里的话,会不会另外安家立业,很快建立四通八达的地下兔子王国?
我担心我家的兔子会越养越少。可实际上,却越养越多。
一来因为我妈的伙食做得好——有榨葵花油剩下的油渣,还有碎麦子和玉米粒,偶尔还会把我们自己的蔬菜分两片叶子给它们。于是天色一暗,大家统统往家赶,等着吃大餐。
二来嘛,兔子生起娃来,一月一窝,那可是几何倍数增长啊。
而我妈则担心它们啃葵花苗。
结果人家可懂事了,碰都不碰一下。好像知道若是现在啃没了,将来就没有更好吃的花盘大餐。
葵花从播种到收获,共三个月的生命。三个月间,小兔子长成大兔子然后又生下小兔子。葵花对于兔子们来说几乎就是永恒的存在吧?
对我们来说,葵花地何尝不是永恒的存在?三个月结束后,它产生的财富滋养我们的命运,它的美景纠缠我们的记忆,与它有关的一切,将与我们漫长的余生息息相关。
我总是长时间凝视眼下这简陋的住处,门前的细细土路,土路拐弯处一丛芨芨草…… 极力地记住所有细节。我好像知道将来一定会反复回想此刻情景。好像在作最后的挽留,又好像贪得无厌。
兔子却心无挂念。它领我去向荒野深处,每跳三五下,回头看一眼。
我也想将兔子深深记在心里。可它左跳右跳,躲避一般。每当看向我时,眼睛绯红而冰冷。
在茂密的葵花地里迷路的兔子,整夜回不了家。这一夜,我妈辗转反侧,不时披衣走出蒙古包,遍野大喊:“兔兔啊!兔兔……”
这一夜额外漫长黑暗。葵花地像是黑暗中最黑的一条地下河,兔子皮毛的明亮和眼睛的明亮被深深淹没。
有人紧紧抱著兔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妈的呼喊声曾令他微微犹豫一下。
他穿过我们广阔的梦境,一直走到梦醒。
第二天,兔子独自回来,洁白,安静,崭新。
荒野的白天和夜晚肯定是不一样的。葵花地的光明与黑暗肯定相隔漫漫光年。唯有兔子自由穿梭两者之间,唯有兔子的路畅通无阻。
白天我们和它左右相随,一到夜里,它跳两下就不见了。
站在唯有兔子能通过的那扇门面前,我沮丧于自己庞大的身躯和沉重的心事。
我们决定离开这里。
我妈拆了蒙古包,把铁皮烟囱一节一节拆下来扔在空地上。兔子们不知离别在即,一个一个痴迷于生活中突然出现的新游戏——它们把烟囱当作洞穴,爬来钻去……
没一会儿,统统爬成了黑兔子……
真是一点也不爱惜白衣服!
还有一位老兄,屁股太大了,卡在里面出不来。也不知弄疼了哪里,在里面惨叫连连。
原来兔子居然也会叫啊!之前一直以为它们是哑巴。
我妈闻声而至,大笑。赶紧竖起烟囱“砰砰砰”一顿猛磕,好半天才把它磕出来。
(摘自花城出版社《遥远的向日葵地》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