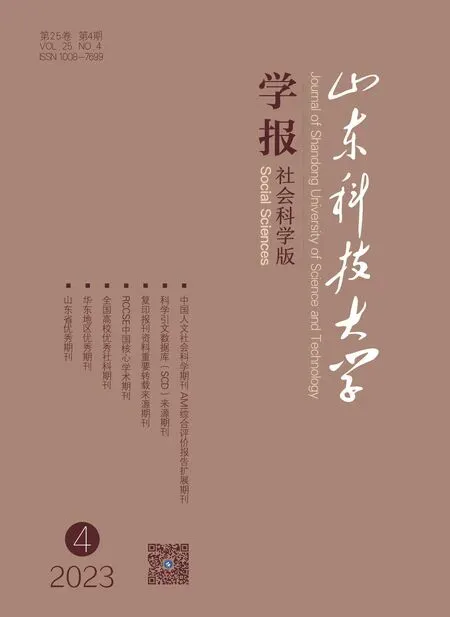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超越
肖雷波,王 秀
(1.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基地,江苏 南京 210044;2.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① 博斯科(Fernando J. Bosco)在《人文地理学中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网络和关系方法》中指出:“ANT是一种复杂的方法,可以处理地理学家在研究中通常关心的行动者、对象和过程之间的网络和关系,从经济地理到城市、政治和文化地理。”参见BOSCO F J. Actor-network theory, networks, and relational approaches in human geography[J]. Approaches to human geography, 2006: 136-146.
② 卡隆将ANT拓展到经济社会学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解读市场的建构过程,即“述行分析”。“述行分析”的主要观点是:经济学不是无用的经济理论,而是在构建经济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向人们展示经济理论的实际经济后果,利用人们提出的经济工具或经济理论,来创造他们想象的经济现象。参见CALLON M. The laws of the markets[M]. Oxford: Blackwell, 1998: 23.
③ 泰菲尔德(David Tyfield)在《科学经济学》中指出:“在ANT和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之间无疑存在相当多的概念重叠和联系点,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以ANT对分布式能动和权力等方面的关注来补充关系马克思主义。”参见TYFIELD D.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performativity turn[M]∥TYFIELD D. The economics of science: A critical realist overview. London: Routledge, 2011: 143-164.
④ 鲁迪(Alan P. Rudy)和加罗(Brian J. Gareau)在《行动者网络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学》一文中指出:“ANT已被许多政治生态学家广泛接受,其中许多人以前都接受过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形式。”参见RUDY A P, GAREAU B J. Actor-network theory, Marxist economics, and Marxist political ecology[J].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005(4): 85-90.
ANT(Actor-Network Theory)作为STS(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领域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方法论之一,其巨大的影响力已逐渐渗透至马克思主义领域。以沃特莫尔(Sarah Whatmore)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借鉴ANT的“行动者网络”①概念,重新考虑全球化、空间和规模等关键地理问题的新框架,以克服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之间的二分法。以麦肯齐(Donald MacKenzie)等为代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学派借鉴ANT的“述行分析”(performative analysis)方法,②从剖析市场建构扩展到了金融市场领域,并重点聚焦非人类行动者对经济和社会的作用。③以罗宾斯(Paul Robbins)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学学派借鉴ANT的“非人类行动者”概念,通过美国草坪文化的分析和水文社会周期分析等为切入点,将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杂合体和网络,吸收到一个深刻的政治生态框架之中。④正如德雷克(Phillip Drake)指出:“无论是谈到生态批评、动物研究、行动者网络理论、集合理论、与思辨实在论相关的理论,还是对物质形态的探索,这些分析视角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1]然而,“人类世挑战下,ANT与马克思主义在话题上多有重叠,在话语权的争夺上呈白热化……围绕ANT的三个论域……廓清该立场何以促成STS研究陷入反历史唯物主义和去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困境,从而揭示此一事实:在这个资本主义嵌入科技与网络的巨变时代,马克思主义仍是批判不公平权力结构、推动STS研究纲领守正创新的根基。”[2]59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如何批判和超越ANT这个问题便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1)就国外而言,2017年国际期刊《卓越》(Distinktion)刊出哈萨克斯坦塞耶斯(Edwin Sayes)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和ANT的契合与分歧”为要旨的《马克思与ANT批判:转义、转译与解释》。2019年出版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劳特利奇手册》刊出英国社会学家古根海姆(Michael Guggenheim)《如何以创造性的方式使用ANT使其批评不会失去动力》。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先后召开五届马克思主义STS学术论坛(2017年、2019年、2020年、2021年、2023年),主题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STS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STS研究”“技术批判理论的逻辑演进与理论实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科技与社会发展”“当代高新科技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变革”“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协同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与科技伦理治理”。这些学术论坛很好地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STS的深入发展,但对作为STS经典方法论之一的ANT却缺少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批判反思。笔者基于马克思主义视域,对ANT展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四维批判,并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自然交叉领域)和自然辩证法(自然领域)的三个层面,对ANT的反历史唯物主义、去政治经济学分析、激进经验主义立场所陷入的困境实现三重超越,从而回应这个学术论点,并为我国马克思主义STS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者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四维批判
尽管ANT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其局限性也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批判。正如塞耶斯(Edwin Sayes)指出:“为了正确考虑ANT的优缺点,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的角度来审视它。”[3]整体看来,笔者认为目前关于ANT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不同层面。
第一,在本体论层面,表现在对ANT非人类行动者能动性的本体论批判。拉图尔将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符号化等同,并赋予非人类行动者能动性,这点属于关系本体论的范畴。(2)关系本体论即“实体和物质被视为关系构成,并研究这些关系的形成和重建。所谓的关系性意味着基本的本体论概念(如技术、社会、人类或非人类)被视为效果,而不是解释的资源。”参见LAW J. After method[M]. London: Routledge, 2004: 157.虽然ANT对这一观点的探讨是深刻且富有启发的,但在威德(Henrik Rude Hvid)等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通过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商品拜物教概念能够看出,马克思主义含蓄地警告了ANT的支持者不要夸大事物和准事物的质量,从而犯下学术傲慢,教条地相信社会建构主义的优越性及其产生的批判,同时忽视了潜在的、规范的积极态度和情感的黑箱……这些态度和情感总是跟随和塑造人类的能动性。”[4]20-21因为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不能完全等同于人类行动者的意向性,例如人类行动者是有计划和目的,但非人类行动者则不具备计划性和目的性。因此,威德在《打开商品化的黑匣子:作为批判的行动网络理论的哲学批判》一文中指出:“ANT的定义是拟人化的(将人类的欲望和意图归因于事物),它的理论框架虽然与‘商品拜物教’类似,在原则上赋予无生命的物质与人同等程度的能动性,但是在评估商品化的后果时,ANT忽略了人的品质和意向性的特征。”[4]8同样,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沃特莫尔和索恩(Lorraine Thorne)通过理解食品商品链中的“代言人”(spokesman)力量,也批判性地探索了关于ANT的消极方面,即使用“地方”“全球”或“核心”“外围”等术语将全球进程指定为两极,消除了人类的能动性,与全球影响相关的力量应被理解为许多行动者的行动和能力的社会组合,而不是个人或组织的“代言人”属性。[5]由此可以看出,ANT并没有明确揭示非人类行动者本身存在的内在机制,也没有指明非人类行动者为什么具有能动性。
第二,在认识论层面,表现在对ANT非还原论的批判。非还原论是ANT的主要思想之一,它与ANT另一概念“转译”密切相关。(3)ANT由“行动者”“转译”“网络”三个核心概念构成,系统地描述出了一个行动者网络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行动者将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对称等同,并通过转译,将自己的利益与其他行动者的利益协调一致,最终形成一个消解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的行动者实践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各个行动者能够得以互动共生。“转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利益谈判过程,包括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利益化(interessment)、招募(enrolment)与动员(mobilization)四个环节,它的主要特征是对称性和不忠实性。马克思主义学者对ANT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两大特征上。一方面,转译概念的对称性特征忽略了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差别。所谓对称性,是指转译时对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符号化处理,并同等对待。例如,在“一个持枪的人杀了人”这个事件中,受害者死亡,是人与枪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枪变成了凶枪,人变成了杀人犯。[6]但是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的意向和责任不可能完全对称。虽然成功地转译将非人类行动者纳入了行动者网络并解释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看似消除了非人类和人类行动者之间的种种区别,但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往往是人类赋予的,因此本身不具备能动性。[7]同样以“一个持枪的人杀了人”这个事件为例说明,枪之所以成为凶枪是由人类,也就是凶手所赋予的。另一方面,转译概念的不忠实性特征会歪曲原始含义。不忠实性是指所有转译都不是完全的复制,而是可能会偏离原有的内涵。例如,巴斯德没有把整个农场带到实验室,所以炭疽转移到实验室是不完全和不忠实的。[8]同样,“忠实的转译者还是不忠的诽谤者?什么都不知道,只有通过代言人的审判才能实现。”[9]虽然ANT在自身机制中能够设定于操作审判另一对象,但是违背了忠实性。
第三,在方法论层面,表现在对ANT拒绝社会结构分析的批判。ANT认为社会是一个不存在的范畴,批判社会学中不存在“权力”的关键概念,并将“权力”“社会”“话语”等学术行为比作“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对众多批判者使用“资本主义”“权力”和“阶级”等概念的做法,不以为然。[10]拉图尔甚至将“社会”一词从其著作《实验室生活》的副标题中删除,并摒弃“权力”“资本主义”等概念,这遭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拉图尔坚持采用纯粹描述的方式描述“跟随行动者”之间的瞬时联系,而不是接受社会结构的因果效应,这是他从《实验室生活》的副标题中删除“社会”一词的主要原因之一。[11]国内学者鹿晓红也指出:ANT只是描述行动者网络,是“人和物”所有元素参与其中的“无缝之网”,以及不同种类的知识是如何确定地产生的。[12]而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是“完整版”行动者网络,人作为社会的现实能动行动者,离开社会具体结构形态就无法描述人,所以先描述社会后描述人。马克思早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有著名表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501可见,当拉图尔开始以ANT的人-物行动者“网络”视角重组“社会”时,马克思早就采取类似视角探讨过关于“社会”的重要性。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是由一切人力和物质要素组成的行动者网络的完整版本,并从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社会生产的确定性和积累中,来解释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标志的现实社会结构的确定性和发展性。因此,ANT强调只有“行动者网络”才能不确定性地“塑造”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而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理论作为“完整版”的行动者网络,不仅能够确定地生产不同的精神产品,如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和价值标准),而且可以确定性地生产不同的物质产品。
第四,在价值论层面,表现在对ANT本体论政治目标的批判。ANT的本体论政治目标为以“物的议会”(the parliament of things)方式实现生态正义的宇宙政治(4)宇宙政治概念是由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ēs)提出:政治边界和民族认同在道德上是任意的,所有人都应被视为道德价值的主要单位,就好像他们是普世政治共同体的平等公民一样。后来,斯唐热和拉图尔扩展了它的含义,将这种平等扩展到非人类,主张将人类与非人类融合成一个集体,构建民主政治的“万物议会”。参见BROWN G W, MCLEAN I, MCMILLAN A.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815.,对马克思以社会正义为目标的解放政治持忽略的态度。“物的议会”的主张源于ANT所坚持的广义对称性原则,强调对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对称态度,主张非人类也可作为代表参与政治协商,强调人与物之间的权力斗争可以有物的议会,物也有话语权。但是在这种主张中,集体的连续性将会被重新形构出来,再也不会有无遮蔽的真理,也不存在无遮蔽的公民,行动者占据了所有空间,自然而然地存在,但他们的代表(科学家等)只从他们的角度说话。这表明ANT期许颠覆人与自然二分的传统世界观,建构实现生态正义为目标的宇宙政治。但ANT这种给予非人类行动者能动性的做法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不同批评。一方面,针对ANT广义对称性原则所主张的“物的拟人化”,地理学研究者哈特威克(Elaine R Hartwick)批评说:“非人类行为(如传真机)与员工行为,具有相同的积极影响令人深感不安。这将产生什么‘激进’政治?因此,对称性原则根本没有本体论的政治意义”。[14]换言之,ANT主张的“拟人化”忽略了这点,即只有通过人类的代言和人类的社会安排才能发生政治变革。[15]另一方面,针对ANT广义对称性原则所制造的资本主义不平等假象,富勒(Steve William Fuller)批评说:“ANT重视将能动性从人延伸到物中所隐含的创新政治愿景……资本主义的形而上学,通过商品化过程,在生产力和效率等系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实现人力和机器劳动的交换。”[16]沃特莫尔和罗宾斯等学者也认为本体论上激进的ANT立场并不一定导致政治激进的立场。例如,即使承诺非人类行动者(如洋流)的本体论等同,显然也不支持被压迫人类的解放斗争。
总之,虽然ANT作为一股跨学科学术思潮越来越引人瞩目,但是其困顿与缺憾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敏锐审视下,也日渐浮现,主要表现在以上四维批判上。这凸显出了马克思主义仍是推动ANT乃至STS研究深入发展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接下来,笔者回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进行理论探赜,力图从马克思主义视域实现对ANT的三重超越,以期为正兴起的中国马克思主义STS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二、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实现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三重超越
常照强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后人类主义困境——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一文中指出:“围绕ANT的三个论域,即科技、经济、生态,全面呈现其后人类主义立场之症结,廓清该立场何以促成STS研究陷入反历史唯物主义和去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困境……”[2]59该文深刻指出了ANT的后人类主义立场所引致的反历史唯物主义和去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困顿,并试图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脉络下找寻化解STS研究困顿的契机,却未对ANT的反历史唯物主义困境和激进经验主义趋向提出纾困之道。笔者受此启发,以上述对ANT的四维批判为基础,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自然交叉领域)和自然辩证法(自然领域)三个层面,分别对ANT反历史唯物主义、去政治经济学分析、激进经验主义所陷入的困境实现三重超越,以达到彻底纾困的目标。
(一)从历史唯物主义层面对ANT的反历史唯物主义实现第一重超越
ANT“将技术(人工物)视为非历史性的、生产关系之外的东西”[17]361,走向了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趋势,同时拒斥总体性概念而主张多样性概念,是一种否定社会结构等范畴的纯粹描述方法。因此,笔者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和人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实现对ANT的超越。
首先,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超越ANT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摒弃。ANT不仅将“工具”与“工具使用”的范畴从劳动的辩证实践中抽离,还将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抽离;而且摒弃了生产方式的范畴,屏绝社会结构性的权力关系以实现对物质现实的概念化的观点。但对马克思而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至关重要,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18]591因此,以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超越ANT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摒弃,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坚持工具及其使用是劳动的辩证实践的前提,而不是ANT转译的随意概念。(5)ANT强调一切皆可见,认为没有必要将工具及其使用从具体劳动的辩证实践中抽象出来,也没有必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抽象出来,主张工具是随意的概念,是转译的效应,是对资本主义、权力的荒谬之谈。参见MILLS T. What has become of critique? Reassembling sociology after Latour[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8(2).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活劳动把工具和材料变成自己灵魂的躯体,从而使它们起死回生……而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却在资本中作为自为存在的东西存在着。”[19]因此,虽然自然供应了财富的来源,但若将自然资源转换为财富或使用价值,则需要通过工具及其使用的辩证劳动实践才能实现。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方式的范畴,超越了ANT对生产方式范畴的摒弃。ANT拒斥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对物质现实概念化的做法,提出“集合方式”的概念,即一种分散的、瞬时突现的、相互耦合的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的所谓“联合体”,从而逃避了剥削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20],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主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难以接受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3]532-533因此,讨论资本主义发展前景时,仍需回到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生产方式这个根本前提上来。
其次,以人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超越广义对称性原则的纯粹描述。ANT采用广义对称性原则,将人类与非人类符号化,无差别地纳入行动者的行列,对非人类行动者也赋予了能动性,是一种“怎样都行”的纯粹描述方法(6)“怎样都行”纯粹描述方法,即一切都是偶然实现东西,没有决定因素实现结构的走向,是描述性进路,不是规范性进路,但未考虑到人类与非人类的作用机制、参与方式以及利益取向不尽相同,这种强对称性从而是无法实现的。,走向了“天真客观主义的本体论”(ontology of naive objectivism),即崇拜纯粹描述的即时性(immediacy),忽略其所嵌入的背景。[17]365然而,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的,可从人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不断的互动首先始发于人类。人在劳动中彰显了能动性与创造性,劳动的具体性、普遍性与特异性表征着整个人类有别且超越于其他自然物种的本质内涵。[21]尽管不可避免地受到非人类力量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互动主要起源于人类。例如,红绿灯、路障和减速带的作用表现形式是“接近时及时减速”,食品包装袋的作用表现形式是“用完后扔进垃圾桶”等。这些互动之所以能够产生,都始发于司机和食客等人类。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3]524另一方面,从重视社会范畴的视角去考察人类及其活动。ANT主张追踪行动者之间的瞬时突现联系,拒斥“社会结构”“权力”等范畴的因果解释。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只有站在社会范畴去剖析人类及其实践,才能真正地领悟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正如卡斯特里(Noel Castree)指出:“如果我们放弃了识别多种社会自然网络所遵循的结构和结果模式的能力,我们怎么可能以更具生态和社会责任感的方式改变世界呢?”[22]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13]187
(二)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自然交叉领域)角度实现对ANT的去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第二重超越
“ANT具有很强的经验主义趋向,主要表现为一种反结构的研究取向,由此政治经济学在STS中相对缺乏。”[23]具体表现为ANT拒绝拜物教的批判,抛弃资本主义对生态危机的批判,走上了去政治经济学的岔路。因此,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脉络下,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对ANT实现超越。
首先,以拜物教批判超越技术拜物教。ANT排斥拜物教批判,将“社会”和“资本主义”等范畴斥之为错觉,对技术人工物的理解,与它们产生的特定社会关系脱离,从而陷入了霍恩伯格(Alf Hornborg)所说的“机器拜物教”(Machine Fetishism)[24]70,即技术拜物教(Technology Fetishism)(7)技术拜物教亦即技术崇拜,是指对技术(无生命的物或人工制品)的崇拜。。然而在马克思那里,拜物教有双重结构:社会存在与社会关系的物质化相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指代认知的错位,主张拜物教批判。一方面,将商品拜物教(8)商品拜物教概念是对商品神秘性质的形象化表达。例如,费尔巴哈从感性的人出发,认为人按照自己的形式创造了上帝,然后又把上帝当成独立的主体,顶礼膜拜,但上帝和商品其实都是人类的产物。批判扩展到技术人工物,而非赋予其能动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现在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即对象化劳动的,物的劳动条件(它们作为这种独立的要素,人格化为资本家,同活劳动相对立)的生产力和形式……我们在考察货币时,已经把这种关系颠倒的表现称为拜物教。”[25]而ANT以广义对称性原则来看待技术人工物,并赋予其能动性,是一种技术拜物教的主张。所以,需要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延伸到技术人工物上,而非赋予技术人工物能动性,因为技术人工物“是一种很简单而平凡的东西”[26]。另一方面,以拜物教批判超越技术拜物教下的不平等社会关系。恩格斯指出:“工厂制度、机器技术进步等带来的后果,在大陆上和在英国是完全一样的:对大多数人是受压迫和劳累,对极少数人是财富和享乐。”[27]将拜物教批判用来检视ANT主张的技术拜物教,洞察渗透在机器运作中事物之间关系之下的不平等、技术上不公正的社会关系,(9)例如,在感叹人类的创造力惊奇——曲折回环的万里长城、巧夺天工的埃及金字塔和奔腾澎湃的京杭大运河的同时,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出现了对技术人工物的崇拜,即在信徒眼中,人类的创造不再是人造的,而是被认为是外来的;这些膜拜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技术拜物教。从而揭示出技术拜物教的主张根本不可能认识到现代技术是不对称的全球交换关系的产物。[24]70正如霍恩伯格所言,“在马克思主义中,‘自主能动’属于无生命实体(如商品)的假设是一种资本主义幻觉,它使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变得模糊不清,是一种必须揭露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在ANT中,这种假设已经转化为必须在概念中承认的颠覆性让步。”[28]因此,只有将技术产物放在产生它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中,我们才能认识到它的本来面目。
其次,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态批判超越后人类主义政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蕴藏着潜在的生态观念,主要体现为生态经济观、适度消费观等,而在人类世(Anthropocene)叙事下,ANT对资本主义概念持拒绝态度,即放弃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态维度惯用方法:将资本主义作为理解生态破坏议题的综合框架。正如斋藤幸平(Kohei Saito)所指出的:“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下看待生态危机,如果不忽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生态维度,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貌。”[29]因此,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态维度对ANT的后人类主义政治生态学予以超越。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观,超越ANT后人类主义政治生态学对生态危机社会文化根源的忽略。ANT主张将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联合的集体聚集起来,以建构宇宙政治,实现自然与社会的协同演化。[30]61-62这种政治生态学,实际上从根本上忽略了生态危机的社会文化根源,结果无法廓清能源短缺、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无法理解气候问题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31]而生态经济观通过研究自然生产力在社会生产力中的作用,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破坏性影响,从而能够克服后人类主义政治生态学的困境。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适度消费观,超越ANT后人类政治生态学的消费叙事模式。ANT主张多物种纠缠,即为应对人类世的生态破坏,倡导以地球(人格化的盖娅)为界的政治[32],主张人类与非人类等同的广义对称性原则,从而无法看清人类对工具和语言的使用的消费特征与生态的紧密关系。而适度消费观注意到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影响,而且重视生态问题的人类维度,进而丰富人的本质力量并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正如《土地退化与恢复评估决策者摘要》所指出的:“土地退化的最终驱动因素是高昂的人均消费……刺激不可持续的农业扩张、自然资源和矿产开采以及城市化……这导致土地退化加剧。”[33]这一论断表明,当代生态问题源于人类的消费活动,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因此,需要从人类消费活动的视角来检视生态问题。
(三)从自然辩证法(自然领域)层面对ANT的激进经验主义实现第三重超越
ANT通过考察行动者、网络以及网络的组成方式(转译),建构了一种新的经验形而上学体系,具体表现为主张盖娅自然观、走上了“跟随行动者”纯粹描述分析的道路。因此,有必要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辩证法的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对ANT实现超越,从而为应对ANT陷入的激进经验主义困境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首先,以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超越盖娅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观点,是自然观的高级形态,具有批判性和发展性特征。而ANT主张的是纯粹描述现象的盖娅自然观,即盖娅是一种能包含多元自然维度的形象,自然(非人类行动者)与政治、文化(人类行动者)之间构成生命共同体[30]60,具有纯粹描述性和耦合性特征。一方面,在生态危机议题的探讨上,以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批判性特征超越ANT盖娅自然观的纯粹描述性特征。在ANT那里,拉图尔认为人类的现代性二元思维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采取广义对称性原则去描述人类与盖娅之间的互相缠绕,重点关注人类与非人类互动的地球表层“关键带”,这一做法实际上意味着ANT把复杂的生态危机问题纯粹描述为人类现代性二元思维作祟的结果。[34]1而批判性是指坚持通过劳动实践的总体视角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针对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方的生态问题,警告说“我们还是要再一次地特别是从工人健康状况方面把这些情况逐一加以考察。大城市人口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不良后果。”[13]409这意味着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除了当时流行的现代性二元思维外,还包括与人类劳动实践相关的多方面复杂因素,如工业革命、资本利润追逐、石化经济、消费经济、人口爆炸等。因此,面对生态危机根源问题的探讨,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批判性强调从劳动实践的总体视角出发考察,而盖娅自然观则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人类现代性的二元思维作祟,实际上摒弃了这种总体视角。另一方面,在目标导向的探讨上,以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发展性超越ANT盖娅自然观的耦合性。盖娅自然观在人与自然的未来发展上,主张“怎样都行”的耦合进路,目标导向具有瞬时突现性。然而,现实情况中的人类和非人类的作用发挥并不是同等的,ANT的这一做法显然是对二者在行动者网络中位置、能力与生态位的差异关注不够。[34]11而发展性是指人类在尊重自然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非生态型人工自然界转向生态型人工自然界,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35]由此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能作为积极的行动者,主动营造有利条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而动物则只是被动的行动者,缺少这种主动营造有利条件的能力。ANT盖娅自然观的耦合性恰恰是后者,无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其次,以唯物辩证法超越“跟随行动者”方法论。ANT采取“跟随行动者”的方法论,强调对人类和非人类的对称态度,并追踪描述他们的瞬时突现关系,走向了纯粹描述的歧路。因此,可从唯物辩证法进行考察。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10)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是反映和对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发展的辩证过程的思维,其特点是研究客体内部矛盾的运动和变化以及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以便从整体上和本质上理解客体,并用逻辑范畴及其体系来理解具体的真理。超越ANT“跟随行动者”方法论的瞬时突现性。拉图尔在《给我一个实验室,我将撬动地球》一文中写道:“通过实验室这个杠杆点,这个动态过程的瞬时点,农业系统就被置换了……每个人都发生了变化,用通常的术语来说,包括‘整个社会’都发生了改变。”[36]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中,对宇宙的演化规律进行了阐述,指出整个宇宙的演化规律,是人类在生存活动的时间短、空间小的条件下,用经验方法得出的,只能用辩证思维的方法,从宇宙银河系的特殊演化过程中,抽象概括出宇宙演化的一般规律。同样,在《反杜林论》中他也提到:“生物在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37],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的历史性和变化的辩证原则,一切事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行动者的实践来改变事物的状态,并具有相应的辩证范式,而不是在某个动态过程瞬时突现。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系统思维(11)马克思主义系统思维是指原则性与灵活性相互联动的方式,是人们应用系统视角,系统地认识对象的结构和功能的思维方式,总体性原则是这种系统思维方式的核心。超越ANT赋予能动性于非人类“物”的做法。ANT赋予了非人类“物”以能动性,在《重组社会》中反复强调非人类“物”也是行动者,倡导应该对物给予足够的关注。例如,餐厅“光盘行动,浪费可耻”“垃圾请扔进垃圾桶”的标识,当餐厅没有顾客和纸屑垃圾等时,标识仅仅是物,不具有能动性,但是当出现顾客、纸屑时,其能动性出现,人类行为会被影响,此时标识的能动性瞬时突现。这一观点遭到了弗里德伯格(Erhard Friedberg)等学者质疑,弗里德伯格批判ANT不划分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地位的做法,这意味着这种做法会使我们无法剖析人类主体能动性在实践过程中具有的特殊性。[38]因此,我们要超越ANT赋予能动性于非人类“物”的做法,最好的办法还是回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经典著作中,从马克思主义系统思维的角度寻找灵感。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39]这意味着ANT赋予非人类行动者能动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整个自然界是永恒的流动”的,应从系统思维的总体性原则去把握,ANT将标识看作是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显然略显牵强。
三、结语
作为STS研究的代表性方法论,ANT从建构性实践网络角度理解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这颠覆了传统实证主义科技观所秉承的自然与文化、科技与社会之间的传统二分法,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关系马克思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学派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益思想养分,如“行动者网络”概念、“述行分析”方法、“非人类行动者”概念。然而,面对这些吸收ANT养分而兴起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40]一方面,我们应具有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围”或“突破”理论困境的创新勇气,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ANT的反历史唯物主义、去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及激进经验主义等困境展开更多批判与超越;另一方面,我们应吸收ANT的理论优点如生态正义、过程性系统思维等,更好地服务科技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