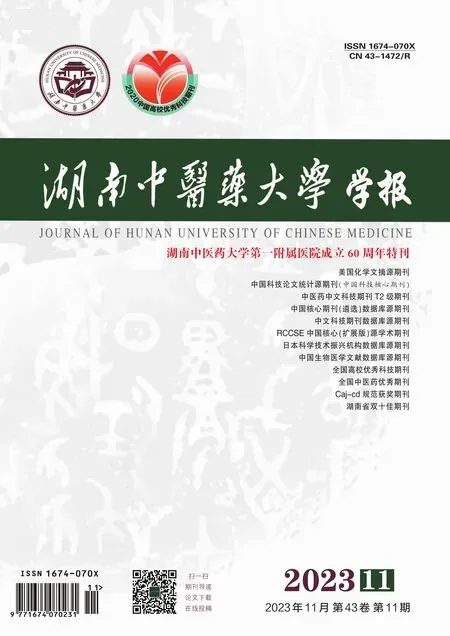历代医家对小儿便秘的认知探讨
陈月月,李瑞本,陆艳泓,蔡秋晗,郑子琦,胡思源*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300381
便秘是儿科临床常见的脾系疾病,主要表现为大便秘结不通,排便次数减少或间隔时间延长,或大便努挣难解[1]。 小儿便秘既可以是一种独立的疾病,也可以作为一个症状见于多种疾病。 本文主要讨论作为独立疾病的小儿便秘,其相当于西医的功能性便秘(functional constipation, FC)。 一项全球系统综述结果显示,儿童FC 的患病率为0.5%~32.2%,总患病率为9.5%[2]。 目前西医治疗FC 多以泻药为主,如乳果糖口服液、硫酸镁口服液等,长期应用此类药物容易产生依赖性,导致直肠反射敏感性降低[3]。中医学对小儿便秘的认识与治疗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诊治经验。 本文通过对古代文献中小儿便秘的渊源流变,总结并提炼历代医家对小儿便秘的病名、病因病机、辨证治疗与用药认识的规律和特点,以期为小儿便秘的现代中医药辨证治疗提供借鉴。
2 病因病机
1 病名
“便秘”一病的记载,最早可溯源至《黄帝内经·素问》,书中有“闭”“后不利”“不得前后”“大便难”等记载。 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对便秘进行了更详细地阐述,使用“不更衣”“阴结与阳结”“大便硬”“脾约”“不大便”等多种不同的称谓,在《金匮要略》中亦提到“大便必坚”的说法。便秘作为独立的儿科疾病,首见于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书中载有小儿“大便不通候”“大小便不利候”的叙述。嗣后,历代医家对便秘的命名多有不同。宋代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称之为“秘涩”“不通”,明代的《育婴秘诀》称之为“实秘”“虚秘”,清代的《幼幼集成》称之为“实闭”“虚闭”,清代的《麻科活人全书》称之为“大便秘”,最接近今天的“便秘”病名。 直至1919 年的《中华医学杂志》首次使用“小儿便秘”病名,并沿用至今。
2.1 隋唐时期——热壅气滞、食积内停
先秦两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虽未对小儿便秘做单独论述,但对后世小儿便秘的病因病机学说产生深刻影响。如《素问·举痛论》指出:“痛而闭不通者”,其机制在于“热气留于小肠”;《伤寒论》认为,便秘常见于“阳明病”,指出其病机为“燥屎”“宿食”内停。
小儿便秘的病因病机首论见于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候》,其谓:“小儿大便不通者,腑脏有热,乘于大肠故也。”指出小儿便秘病位在大肠,热邪与肠中糟粕相结致秘。亦云:“脾胃为水谷之海,水谷之精华,化为血气,其糟粕行于大肠。若三焦五脏不调和,热气归于大肠,热实,故大便燥涩不通也。 ”提出热气偏入大肠,可致肠中津液枯燥而成便秘[4]。 另曰:“时气病结热候热入腹内,与腑脏之气相结,谓之结热。 热则大小肠痞涩,大小便难而苦烦热是也。 ”“小儿大小便不利者,腑脏冷热不调,大小肠有游气,气壅在大小肠,不得宣散,故大小便涩。 ”大肠为传导之官,小肠受盛化物,负责传导糟粕和对津液的再吸收利用,结热、冷热实邪壅塞肠间,阻滞大肠气机,下焦不通,传导失司故成便秘。
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中言“小儿无异疾,惟饮食过度,不知自止,哺乳失节”,并自创紫双丸“治小儿身热头痛,饮食不消,腹中胀满,或小腹绞痛,大小便不利”。小儿乳食不知节制,脾胃损伤,停滞积久,化热伤津,大肠失润,可致便秘。 由此可见,隋唐医家认为小儿便秘的病机以脏腑热盛、下移大肠,或脏腑失调、气滞大肠,或饮食不消、积滞内停为主。
2.2 宋金元时期——三焦壅滞、热攻肠腑
宋金元时期,虽对小儿便秘的病因病机、症状和分类进一步细化,但对其病因病机的认识,以《诸病源候论》的学术认知为基础。 如宋代《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大小便论》云:“小儿大便有秘涩者,有不通者,皆由腑脏有热,乘于肠胃,胃热则津液少,少则粪燥结实而硬。 大便难下,则为秘涩;甚者则不能便,乃为不通也。 ”同时,也提出了腑脏挟热所致的三焦气机壅滞,是便秘的主要发病机制。 如宋代太医院编撰的《圣济总录·卷第一百七十九·小儿门》指出:“论曰水谷皆入于上焦,至中焦而腐熟,下焦而化出。 小儿腑脏挟热,三焦壅滞,津液枯少,不能传道,实热之气,归于大肠,故大便燥涩而不通也。 ”三焦为津液输布通道,为气运之道路,是人体枢纽。 脏腑热盛,致三焦气枢不畅,气机壅滞,津液输布失衡,肠道失润而致便秘[5]。 综上可知,宋金元时期的医家认为,小儿便秘主要病因病机为三焦脏腑有热,下攻大肠,伤津耗液,无以濡润,故见大便“秘涩”“不通”。
2.3 明清时期——气滞食停、热郁肠腑、津亏血虚
明清时期,中医儿科学发展进入兴盛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儿科医家、医著,对于小儿便秘病因病机的认识,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明代鲁伯嗣在《婴童百问·大便不通第七十三问》中云:“小儿大肠热,乃是肺家有热在里,流入大肠,以致秘结不通,乃实热也。 ”相较于前人,他提出小儿便秘与肺家有热的观点。 肺与大肠相表里,肺受风热,或化热入里,表里俱热,均可下移大肠,导致津液耗伤,肠道失于濡润,糟粕停滞不行,而致便秘[6]。 明代万全在《幼科发挥·慢惊有三因》中云:“肝有病,则大便难,泻青丸木通散主之。 ”指出小儿便秘与肝脏的密切关系。 清代黄元御在《素灵微蕴·噎膈解》中谓:“粪溺疏泄,其职在肝。 以肝性发扬,而渣滓盈满,碍其布舒之其,则冲决二阴,行其疏泄,催以风力,故传送无阻。 脾土湿陷,风木不达,疏泄之令弗行,则阴气凝塞,肠窍全闭。 ”后世医家据此推知小儿便秘发病或与肝有关,提出各种因素致肝气郁结,气滞不通,腑气不行,大肠传导失司,糟粕内停,不得下行,可致小儿便秘[7-8]。 清代冯兆张在《冯氏锦囊秘录·大便秘塞(儿科)》中言小儿:“有数日不便,腹胀闷痛,胸痞欲呕,咽燥秘塞,热气烦灼者,此热邪聚内,津液中干,大肠枯涩而气滞也。 ”指出气滞既可以是引起便秘的原因,也可以是便秘所产生的结果。
明代王肯堂在《证治准绳·幼科·大小便不通》中指出:“小儿大小便秘涩者为何?答曰乳食失度,使之四大不调,滋味有贪,遂乃五脏受病,甘甜聚食,咸酸滞涎,食滞留结于胃肠,风壅渍癖于心肺,气脉不顺,水谷不行,虽不逆于上焦,即秘结于下部。”清代秦昌愈在《幼科折衷·大便闭》中云:“宿食留滞则腹胀痛闷,胸痞欲呕,热气燔灼,则内受风热,坚燥闭塞。”清代周震在《幼科指南》中云:“小儿多因乳食停滞生热,结于肠胃,以致小儿便秘结。”清代王锡鑫在《幼科切要·大便门》中云:“小儿大便不利,多由饮食热物风热结于便。”小儿脾常不足,运化功能较弱,食滞积于胃肠,气脉不顺,日久伤脾,运化失司更甚,阴液不足,另食积易于化热,热灼津液,大肠干燥则致便秘[9]。
明代万全在《育婴秘诀·大小便病》中云:“如常便难者,血不足也,宜润肠丸主之。”指出小儿平素便秘者,为阴血不足,以致大肠失于濡养,传导失司,故大便秘结不通。 清代陈飞霞在《幼幼集成》中谓:“如平素便难者,血不足也,宜润肠丸、蜜导法。”此外,清代夏禹铸在《幼科铁镜》中也提出“血虚燥滞不通”的观点。 小儿便秘主要病位在大肠,大肠属金,金性肃降,阴血不足,通降功能失常;亦属阳明,为多气多血之腑,津亏血虚则易生内燥,大肠通降传导失司,故大便秘结不通[10]。 明清医家对小儿便秘病因病机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不仅丰富热移大肠、气机壅滞、食滞胃肠的内涵,还增加了血虚失润的便秘致病机制。
3 辨证治疗与方药
3.1 隋唐时期——荡涤肠腑、消积除满
隋唐时期的医家医著,虽对小儿便秘的病因有比较全面地认识,如“腑脏有热”“气壅”“哺乳失节”等,但缺少小儿便秘的治法及用药方面的论述。 仅有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论述紫双丸:“治小儿……饮食不消,腹中胀满,或小腹绞痛,大小便不利……惟此丸治之不瘥,更可重服。”方中含巴豆、蕤核仁、麦门冬、甘草、朱砂、甘遂、牡蛎和蜡等。小儿乳食不知自节,脾常不足,运化不及,食积于腑,郁而化热,气机失调,大肠传导失司而发为便秘[11]。 故用巴豆之辛散,兼甘遂之苦寒,以荡涤癖积;蕤核仁消心腹邪热结气,麦冬治肠中伤饱、羸瘦短气,牡蛎散内滞积热,蜂蜡清胃,甘草调中,朱砂安神,不使巴豆、甘遂侵犯正气也。
唐代王焘在《外台秘要·小儿大便不通方四首》中,亦提出“紫双丸”可治疗小儿食积便秘,与孙思邈所述所思不谋而合,且强调在鸡鸣时分服用此药疗效更佳,此外也有“灸口两吻各一壮”的记载,通过灸经外奇穴之法“疗小儿大便不通”[12]。
综上,隋唐时期医家对小儿便秘的论治较少,用药主在祛邪,多用攻散之品,亦提出使用外治法中的灸法,为后世医家治疗该病奠定实践基础。
3.2 宋金元时期——清热导滞、行气顾中
宋金元时期,对小儿便秘的治疗主要体现在北宋时期的《太平圣惠方·治小儿大便不通诸方》和《圣济总录·小儿门·小儿大便不通》中。 《太平圣惠方》为北宋初期医著,儿科疾病的记载非常丰富,治疗范围广泛,可谓集宋以前小儿医学之大成[13]。书中针对小儿便秘的伴随症状,分别提出不同方药及治法:(1)兼心神烦躁,以大黄散方清腑热、补阴血、安心神;(2)兼腹胁妨闷,以芎黄散方清热行气、通调二便;(3)兼心神烦热、卧忽多惊、腹胁妨闷,以丹砂丸方,清心火、安心神、攻积聚、祛腹满;(4)兼心腹疼闷、卧即烦喘,以通中丸方治之,此方峻猛,大寒大热之药共用,共奏寒热互制、逐痰消痞、荡涤肠胃之功;(5)兼小儿脏腑壅滞、腹胁妨闷,以犀角丸方清热除烦、行气导滞、疏通便秘;(6)兼心腹壅闷,以大黄丸方通便泄热、理气止痛;(7)兼脐腹妨闷,宜用桃叶汤方,需小儿液以坐浴,滓以帕裹,熨于脐下,另食地黄稀粥半盏,良久便通;(8)兼心中烦热,以牛黄丸方清心泻火、峻下通便、凉血解毒;(9)小儿卒大便不通,用蜂房散以清热软坚散结。 此外,《太平圣惠方》中还提出应用摩法治疗,如谓:“小儿大便五六日不通,心腹烦满,上取青颗盐末于脐中,以手摩良久即通。 ”
《太平圣惠方》所述治疗小儿便秘,内外兼顾,以内为主。 内治总以“峻下热结,清心除烦”之法,用药多属峻剂,意在逐邪,应用时需始终关注邪正关系、虚实状态。 《圣济总录》为继《太平圣惠方》后北宋官修的又一部大型方书,此籍除沿用《太平圣惠方》中的方药如“大黄丸”外,还提出:(1)治大便不通,妨闷,用丹参汤方;(2)治大便不通,调中,用二黄丸;(3)治大便不通,不能饮食,用鳖甲丸方。通用的方药包括:滑石汤方、橘皮汤方、木通汤方、黄连丸方、代赭丸方。
金元时期,寒凉派代表人物刘完素在《保童秘要·大小便》中提及:“大便不通诸方:大黄、枳壳、厚朴、朴消;又方:大黄、枳壳、栀子仁、郁李仁、麻仁。 ”未述具体方名,由方药可知刘完素治疗小儿便秘用药偏重寒凉,以泻下降火为主。 攻邪派张从正在《儒门事亲·大小便不利八十六》中云:“夫小儿大小便不通利者,《黄帝内经》曰:三焦约也。约者,不行也。可用长流水煎八正散,时时灌之,候大小便利即止也。”长流水性下行,八正散清热利湿,可治下焦积热,二便不通。 此外,南宋刘昉在《幼幼新书·凡十九门·大便不通第六》中总结了前人的成就,书中还可见“时人茅先生治小儿大便不通”方,即用朴硝、大黄,以蜜熟水调下;钱乙在《婴孺论》中也提到许多简易方,如半夏加蜜成丸,白花调葵子加或不加猪脂煎服,用羊胆汁灌肠以及《孔氏家传》的硝风散“治小儿大便不通,中入鹰条一二寸遂通”等。
综上,对于小儿便秘,宋金元时期仍以清热泻下药为主,但较北宋初期用药略微柔和,祛邪的同时亦注重扶正。 多用人参、甘草等健脾和中之品,同时加用陈皮、木香等理气药以调畅气机、下气除满,使用“仁类”多油多脂之品滑润肠道以增强导滞之力[14]。 在用药上,均强调剂量应随小儿年龄加减。
3.3 明清时期——泻下清热、顺气化积、养血润肠
明清时期的医家医著,对于小儿便秘的辨证、治疗与用药,日臻成熟,初步形成了小儿便秘的辨证治疗体系。明代鲁伯嗣在《婴童百问·大便不通》中将便秘分为实热、积热论治,谓:“小儿大肠热,乃是肺家有热在里,流入大肠,以致秘结不通,乃实热也。当以四顺清凉饮。”组方含赤芍、当归、甘草和大黄等。方以大黄通滞,当归活血,芍药养阴,甘草调中,通利之后,表里气血皆承顺矣。 “积热者,神芎丸尤妙”,组方含大黄、黄芩、滑石、黄连、薄荷和川芎等。 诸药合用,使火毒泻、湿热除、大便下而诸症悉除。清代秦昌愈在《幼科折衷·大便闭》中提出,小儿便结应急投煎剂并导法,热用三黄丸清热泻下,三黄即黄连、黄芩、大黄;积以消积丸健脾和胃,消食导滞,组方含白术、陈皮、青皮、益智仁、神曲、三棱、丁香和茴香八味药;此书亦云:“小儿便结哭声高,津液不润为火熬;急投煎剂并导法,免使儿遭日夜号。 ”“邪热入里,则内有燥粪,三焦伏暑则津液中干,此大肠之夹热也。 宿食留滞则腹胀痛闷,胸痞欲呕,热气燔灼,则内受风热,坚燥闭塞。 热宜疏利三黄丸,积宜消积丸,惟胸中活法治之。 ”对于食积大便秘、腹胀痛,清代周震在《幼科指南·杂证门》中指出以“神芎丸主之”。 清代王锡鑫在《幼科切要·大便门》中提出“以保和丸加枳壳、大黄微利之”。
明代万全在《育婴秘诀·治大便不通》中将便秘分为“实秘”“虚秘”论治,指出:“苟大便不通,宜急下之,使旧谷去而新谷得入也。然有实秘者,有虚秘者,临病之时,最宜详审。 ”对于实秘,主张凉膈散、承气汤、八正散、三黄枳术丸、木香槟榔丸、丁香脾积丸择而用之,中病即止;对于虚秘,虽有可下之症,缓则救其本,主张保和丸、枳术丸、大黄丸微利之;对于常便难者,认为是血不足所致,提出宜润肠丸主之。 陈飞霞所著的《幼幼集成》谨遵万全之法,分“实闭”“虚闭”论治,唯对虚闭,主张“但用保和丸加枳实微利之”。 清代夏禹铸在《幼科铁镜·大便不通》中,将小儿便秘分为燥热和血虚论治,指出:“肺与大肠有热,热则津液少而便闭,治用四顺清凉饮。 血虚燥滞不通者,治用四物汤加柏子仁、松子仁、胡桃仁等分服之。 ”大便不通证候,有虚亦有实,虚实夹杂,相互转化,最终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失常,阴血津液化生无源,肠道失于濡养,无水舟停,腑气不通,糟粕结聚肠内而发便秘[15]。
综上,明清时期小儿便秘的治疗方法可谓百家争鸣,其中内治法临床分证较多,但不外虚实两类。实证有热结、气滞和食积,虚证以血虚为主,总由大肠传导失职而成。 属热结者,以泻热通腑,气滞者以理气调中,食积者宜健脾消食,血虚者宜养血润燥。临证时应慎审其因,权衡轻重主次,灵活变通治疗。
此外,该时期各医家对于小儿便秘外治法的认识愈加深刻和全面。 如《婴童百问·大小便不通》书中记载的“掩脐法”:“用连根葱一根,不洗带泥,生姜一片,豆豉二十一粒,盐二匙,同研烂捏饼,烘热掩脐中,以绵扎定,良久气透自通,不然另换一剂。 ”《育婴秘诀·治大便不通》 提出的家秘之法,“急则治其肠,使其通利,猪胆汁导法,神效”。 《幼幼集成·二便证治·二便不通简便方》记载了治疗大小便不通的多种导法,如“皂角于桶内烧烟,令儿坐桶上熏之,即通”;“用草乌一个,削去皮,略以麝香搽上,抹以香油,轻插谷道内,名霹雳箭,至捷”;“以小竹筒抹以葱涎,插入谷道;以芒硝五钱研细,香油半盏,皂角末少许,令人口含,灌入谷道中,少时即通”;以及“平素便难者,血不足”应用“蜜导法”等。
4 结语
纵观中医儿科学古典医籍对于小儿便秘的认识及治疗,起自隋唐时期,即有“大便不通”的病证名称,“热实”“气壅”“哺乳失节”的病因病机认识,以及食积便秘方剂“紫双丸”的创立。历经宋金元时期,细化“腑热致秘”的病因病机,言其过程多呈现为“三焦气机壅滞、津枯液少,终致大便难下”;同时拓展了许多治法及方药,治疗谨守病机,随证治之,重视祛邪同时不忘扶正。延至明清时期,基本形成了以虚实辨证为纲,以热、积、气滞、血不足为主的病理机制和常见证候的小儿便秘总体认识格局,并创立了一大批经验方剂与治法。内治法治疗实证多以泻热通腑、消积除满为主,虚证以养血润肠为主,丰富了灸法、坐浴、按摩和贴敷等外治法内容。以内为重,内外结合,为现代小儿便秘的中医药认识和治疗提供诸多借鉴。此外,通过梳理隋唐时期以来中医诊治小儿便秘病证,笔者发现:历代医家医籍治疗此病多用大黄、巴豆、牵牛子、甘遂、续随子(千金子)和朱砂等峻下、药性猛烈之品,易伤脾胃且多有毒性。 其中巴豆、甘遂、千金子等大戟科植物具有一定的细胞毒性,并且对皮肤黏膜及胃肠道有刺激性,易引起皮疹、腹痛、腹泻和呕吐等症状;牵牛子内服可刺激胃肠道引起相关的症状[16-19]。 朱砂若使用不当则易产生肝毒性、肾毒性和神经毒性[20]。此类药品,用之不当则易致肠腑津液损伤,且易伤正气,不可轻投,故应少用、慎用,尤其是小儿这类特殊群体。 小儿为稚阴稚阳之体,形体与生理功能方面,都处于稚嫩之状。 脾弱尤甚,脾失健运,津血化生无源,肠道失润,大便难下。且小儿体质虽稚阴稚阳,但其阴阳平衡是以阳气占主导地位,阴津相对不足,发病易从热从火[21]。 热盛则伤津耗血,肠腑濡润乏源,肠道失用,故生内燥;加之燥热内结,气机升降不畅,腑气不通,致大便秘结。综上,治疗小儿便秘勿过用攻伐,以免伤正。 用药应以清热润下、缓下为主,同时注意顾护脾胃与调理气机,如此方使燥热清、津液充、肠道润、气机调、标本兼治而大便自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