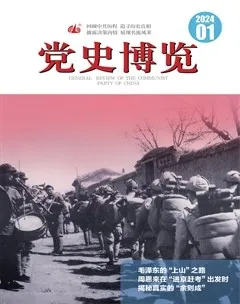歼教-1: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问世前后
罗元生
《航空工业科研发展史》中对歼教-1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歼教-1飞机研制成功,是中国航空工业由飞机修理、仿制进入自行设计喷气式飞机的开端,它标志着中国航空科研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顾诵芬院士作为当年歼教-1设计的亲历者,对此感触尤其深刻。他说:“歼教-1是新中国飞机设计制造史上零的突破,更是一种心理上的突破,是一个民族在历经百年屈辱之后重塑的信心。”
1958年7月26日,沈阳北陵机场。
随着一颗绿色的信号弹划破天际,一架银色的教练机呼啸着向跑道滑去,尾喷流卷起一片热浪,轻盈地飞向蓝天。
这架飞机两翼进气的整体设计、锋利的机头、棱角分明的机身,让人眼前一亮。
这架被命名为“歼教-1”的飞机,是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飞机,也是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从1956年10月开始设计到1958年7月首飞成功,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举世瞩目。
更令人敬佩的是歼教-1背后的设计者们。时年28岁的顾诵芬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亲历者,顾诵芬深知新中国自主设计飞机的艰辛与坎坷。
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分别在瑞士与芬兰举办。在这两次会议上,爱好和平的力量和声浪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遭到爱好和平人民的谴责。毛泽东审时度势,对世界形势作出科学判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阵营都面临休养生息的问题,世界性大规模战争在10~12年内打不起来。立足于这样的判断,毛泽东就中共八大的准备工作提议,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与国际和平时期,提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

顾诵芬
1955年12月5日,中国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充分利用这个休战期,加紧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思考,中国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但在此时,中苏关系经历了一段不平常的时期,两国关系由友好走向破裂。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老大哥”对中国很友好,派出大量专家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振兴科技、发展经济,也提供了不少用于飞机制造的资料,指导中国制造飞机。
1951年5月23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中国航空工业局聘请20名苏联顾问和100名技術专家的合同。到1952年底,航空工业聘请的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共369人,而且苏联还援助了大批设备、器材和资料。
中国航空工业的广大职工,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虚心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循序渐进,大大缩短了掌握技术的进程,为此后赢得了时间。
但是,后来中苏关系发生变化,苏联对中国的态度急转直下。他们援助中国的原则也很明确,只教中国制造飞机,不教中国人设计飞机。对此,中国的高层领导与科技工作者感触最深。
为了全面了解国外军工产品的真实状况,党中央决定让二机部部长赵尔陆带队前往苏联,航空工业局(四局)派出一个分组随行。
1956年7月,赵尔陆率代表团赴苏,就我国国防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问题,与苏联进行谈判。
赵尔陆是毛泽东亲自点将的新中国首任将军部长之一。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正激烈进行,志愿军武器装备的保障任务急迫而繁重。6月,赵尔陆应召赶到北京,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同他谈话,让他负责组建第二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原来分散管理的军事工业。
新中国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被战争破坏殆尽,这样的一个烂摊子,谁看了都不愿意接手。但是赵尔陆没有一句怨言,挑起了重担,成为共和国首任管军工的部长。这次派赵尔陆赴苏,党中央、毛泽东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这次谈判中,除工厂建设项目外,着重谈了空气动力、航空发动机、飞机设备等3个研究院的建设问题,以及导弹生产与航空工业结合,包括工厂和科研机构的结合问题。代表团曾3次提出参观苏联航空工厂和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苏方未同意。
这一趟走下来,赵尔陆感触颇多。除看到装备上的巨大差距之外,更意识到,求人不如求己,中国国防工业一日不发展起来,一日就不会得到别人的尊敬。从苏联回来后,赵尔陆下定决心,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发展中国的现代军工业,落后只会被蔑视,只会被欺凌!
新中国建立强大的空军,需要创建强大的航空工业,更需要培育独立自主的航空科研和飞机、发动机研究设计及制造能力。
1957年9月7日至10月16日,以聂荣臻副总理为团长,副总参谋长陈赓和三机部部长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工业代表团赴苏考察,四局又派出分组随行。此次主要谈判购买飞机及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空气动力、发动机、风洞等科研机构问题。苏方表示,要把中国航空研究院作为苏联研究院的分院处理,给予援助,但不同意中方参观米格-19、图-16飞机及发动机工厂的请求。
1958年,中苏关系开始走向不和。当时,中国虽有飞机工厂,但实质上只是苏联原厂的复制厂,无权在设计上进行任何改动,更不用说设计一款新机型。
对于苏联专家,在一线工作的顾诵芬多次与他们打交道。他认为,应该说大部分专家都是勤勤恳恳、实实在在地工作。他们对自己的责任比较明确,也是尽职尽责地完成任务。他们大都能做到把中国同志带出来、培养出来。但是,他们心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就是在关键技术上要留一手。
“他们给我们制造的飞机呢,基本上是他们要退役的飞机,没有新的东西。另外一点,他们比较霸道,给我们制造的飞机,我们觉得不合适要改,他们也不同意。”
“他们让我们生产雅克-18初级教练机和米格-15高亚声速喷气式歼击机(又称战斗机)等机型,给我们的图纸中,只有强度计算报告和静力试验任务书等,而没有设计飞机所必需的强度规范和气动力设计手册等资料。我们曾多次向苏方提出要《设计员指南》和《强度规范》,结果人家说,‘没有义务教你们中国人设计飞机’。”
顾诵芬说:“有一次,南昌320厂在修理苏联的拉-9型飞机时,自行制造了机翼。但因为没有气动载荷数据,不能做静力试验考核强度,我们就向苏联要数据。大概拖了一年多,他们才给了一张机翼静力试验的加载图。当时,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中国建立设计室可以,但必须跟飞机工厂、制造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那个设计室必须建在沈阳。这个时期苏联航空工业的管理体制是,设计局掌握着设计权,主生产厂不能更改设计,扩散生产厂就更没有更改设计的权力了。”
曾任航空工业部副部长的徐昌裕,晚年在谈到苏联对我国的援助时说:“从苏联政府的政策上分析,一方面苏联是想让我们强大起来,让中国能够承担一部分军事上的任务,帮助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又要限制我们,不希望我们太强大,认为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这就是他们的基本政策。”
每一种飞机的诞生,都必须经过概念设计和总体技术方案论证。中国人要想有自己的飞机,第一步就要过设计关,这也是我国建飞机设计室的初心。
新成立的飞机设计室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设计一架自己的飞机。顾诵芬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自主设计飞机?对于这个问题,在具体技术岗位工作的我们更是深有体会。仿制而不自主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中国人必须有中国人自己的飞机设计。”
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首先发展重工业及国防工业的指示,航空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完成空军飞机的修理与配件任务,并相应地建成修理厂;同时,积极地培养航空工业建设人才,有计划地与各有关工业部门协作,达到主要器材在本国生产,从而逐步地由修理过渡到制造,为建设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打下基础,为空军的发展创造条件。
为完成这一任务,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开始,党和政府就把航空工业摆在了重要地位,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给予了重点照顾。
1956年8月,《关于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以下简称《命令》)发布,决定从1956年8月15日起,在112厂、410厂分别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任命徐舜寿为飞机设计室主任设计师,叶正大、黄志千为副主任设计师。
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厂飞机设计室由此横空出世,开创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发动机的历史。
成立飞机设计室的命令一下,四局首先调徐舜寿、黄志千、顾诵芬和程不时4人到设计室工作。
1956年10月10日,顾诵芬与黄志千、程不时3人离开北京,北上沈阳,去实现他们的理想——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作为首批核心成员,26岁的顾诵芬担任气动组组长,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新征程。
顾诵芬回忆说:“我到设计室以后,住进了112厂设计科技术骨干的宿舍。房间不大,已经安排了4个人,我的床位被安置在靠窗口暖气的地方。宿舍中间有一张大桌子,我们航模组的人就在这个桌子上把这套遥控模型飞机组装了起来。但后来工作忙了,遥控飞行就没有进行。”
一天晚饭后,徐舜寿与工作人员散步时,无意间发现厂区的一排小红房,门前遍地落叶,墙上布满青苔,显然已弃置多年。在他们眼中,这无疑是一块“风水宝地”。徐舜寿当即决定将这里改造成办公室。
新中国航空工业的第一代设计师就在这里摆开了“战场”。
可是,刚刚组建的设计室,一开始什么东西也没有,资料奇缺,真的是“白手起家”。徐舜寿给了一些钱,让大家上街去采购资料。
不久,在徐舜寿的倡议下,设计室订购了1945年以后的英国《航空工程》《皇家航空学会志》及《美国航空航天学会学报》等出版物。通过收集大量文献资料,飞机设计室很快成为国内航空科技资料收藏最多的地方。
尽管办公条件简陋,但徐舜寿仍然按照他心目中的飞机设计室的要求设计办公室。他要求把小间的屋子打通,变成大办公室,所有的制图桌都集中在一间大屋子里。他的位置在屋子的一角,整个办公环境一览无余,有什么问题马上就可以协调解决。早年在美国麦克唐纳飞行器公司实习时,那里设计室的环境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徐舜寿对试验设备和办公设施也毫不含糊。比如绘图桌,就不是到外面选购现成的产品,而是由他和几个设计人员一起精心设计定制的。绘图桌有好几个抽屉,这样可以多放一些图书、资料,还配有可放铅笔、橡皮、三角板的专用板,另外还有可存放描图纸的空间。图板可以在上面平放,也可以竖起来。这种绘图桌的设计形式,一直沿用了幾十年。徐舜寿很重视模线间和模型间,挤出原来小平房里的过道,建了模型间,还买了些手摇计算机。
第一飞机设计室成立后,在航空工业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志于飞机设计事业的技术人员慕名而来,纷纷加入到新中国第一支飞机设计的队伍之中。
顾诵芬回忆说,当时航空工业规划设计院有一位1951年从国外回来的技术人员,得知飞机设计室成立后,坚持要求到设计室来工作。他学的是飞机强度计算,把从国外带回来的图书资料满满地装了好几箱,一起从北京运到沈阳。
管德比顾诵芬小两岁,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后在四局机关工作。设计室成立后,他坐不住了。叶锡琳、陈钟禄、高锡康、李永明等一批毕业于各大学航空工程专业的大学生也坐不住了。他们不愿继续在局机关做管理工作,而是希望在自己所学的技术专业道路上做更多的工作。在向上级提出申请并获得支持和批准后,他们来到了飞机设计室工作。
顾诵芬钦佩徐舜寿选人用人的独到眼光和远见卓识。设计室对于进入设计队伍的人要求很严格。当时,对于南京航空学院(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南航”)来的毕业生的要求是,毕业考试成绩必须全是5分。徐舜寿还指示去挑选的工作人员,要挑数学或力学成绩好的。徐舜寿曾经归纳出选拔人才的标准,主要有三条:成绩、爱好、进取心。而这三条标准,在徐舜寿眼里,顾诵芬都满足。
南航第一届毕业生黄德森回忆说:“徐舜寿是一位爱才、用才的人。他在组建飞机设计室时,抽调的大多数是技术骨干和优等毕业生。当时,他重用的技术骨干有‘才子派’之称。其中有‘四大才子’的传言,即气动组组长顾诵芬、总体组组长程不时、强度组组长冯钟越和机身组组长屠基达,而以顾诵芬的名声最高,他从四局调来时即有‘土专家’(未出国留学)之称誉。”
冯家斌是从北京221厂调到沈阳飞机设计室的。回忆起当年在设计室工作生活的情景,他激动不已,难以忘怀:“当时设计室人员大部分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根本谈不上飞机设计经验,面临歼教-1飞机设计,大家都在努力学习……有一次,顾诵芬给我一本图册,里面是古代造船用的船形模线的画法,以及船形表面光顺的检查方法。虽然船形与飞机外形不一样,但是造型方法以及表面光顺的检查方法都是一样的。当时,我是刚刚接触外形设计工作的新同志,这本图册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参考书,对我尽快掌握外形设计技巧起到很大作用。在我三四十年的工作中,这本图册一直保留在我身边,直到退休多年以后,我才将这本图册完璧归赵地还给顾诵芬。他说这本图册是他1952年在上海的西文书店买来的”。
“当时的设计室是一个非常团结、友好、和谐的集体,大家群策群力、互相帮助,这在当时已成为非常使人感动、使人振奋、使人敬仰的一种风气。设计室主任徐舜寿把他在美国画模线用的三条大形曲线板给我们用,黄志千把从英国带回来的《航空工程》杂志中的二次曲线资料送给我们,等等。那时新老同志在技术上互相帮助,在生活上互相关心。这种风气是那样自然、坦诚、和谐,至今想起来,确实使人感动不已。”

徐舜寿
飞机设计室成立之初,徐舜寿还想方设法为年轻设计师创造好的学习条件。每位来沈阳的航空领域专家,他都登门拜访,请他们来设计室授课。几位中专毕业的设计师对如何学习有困惑,徐舜寿甚至为他们请来苏联顾问、著名航空设计师斯米尔诺夫谈工作和学习方法。
不久,设计室又从南航招来毕业生12人,从沈阳航空工业学校(今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简称“沈航”)招来毕业生25人。1956年11月底,人员基本到齐,设计室总共有72人。
1957年初,设计室又从各厂调来了十几名技术人员,从北京航空俄语专科学校分配来11名毕业生,由112厂调来7名描图员、4名行政与会计人员。到1957年8月底,设计室总共108人,其中技术人员92人(本科及以上毕业生34人,大专毕业生33人,中专毕业生25人),平均年龄22岁。
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理想——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走到了一起。有的刚大学毕业,有的才下战场,有的离开了工厂,有的从国外辗转归国不久……
新中国的飞机设计就这样迎来了群星闪耀的年代。
在顾诵芬赴沈阳前的一个月,1956年9月10日,徐昌裕组织召集112厂开展飞机、发动机设计座谈会。在这次会上,徐舜寿作了关于设计室筹备工作的发言。
“经过我们较长时间的酝酿并和专家们多次讨论,我们认为飞机设计室成立以后的工作可分两个阶段来进行: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主要任务是配备人员,组织力量学习、消化已有的苏联飞机资料,编写有关设计的原始资料,并与国内各有关院校和科学院有关研究机构联系,寻求技术支持;第二阶段才是设计飞机。”
徐舜寿决定,飞机设计室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架亚声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
经过几次讨论,航空工业局领导及决策部门批准了这个方案。
飞机动力设计是项全新的创造性工作。徐舜寿、黄志千在国外留学时学习过,他们有些基础和经验。顾诵芬与这个年轻的设计团队,靠着翻译外文著作,研究他国机型,一步步地“涉险滩、闯难关”。
顾诵芬回忆:“徐舜寿同志领导飞机设计室是胸有成竹的,他以前在国民党航空研究院和美国的飞机公司都参加过设计。他热爱航空,也向往革命,1948年曾去解放区,1949年在上海入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向中央提过要自行设计飞机。”
关于设计一架什么样的飞机,顾诵芬跟徐舜寿一起讨论过。徐舜寿当时的主导思想是“需要与可能相结合”,“在实践中培养、锻炼队伍”。由此,他提出设计室成立后设计的第一种机型,应是一种喷气式歼击教练机。这里的“教练”有双层含义。这不仅是培养新飞行員的需要,而且新中国的飞机设计队伍本身也需要一个“教练”的过程,应当通过这架教练机的设计使我们自己的设计队伍成长起来。另外,我们已经具备制造喷气式歼击机的工业基础,设计一架亚声速喷气式教练机是完全可能的。
徐舜寿的思路是,必须尽快组建设计队伍,通过几个型号的设计和试制,既能部分提供给空军使用,又可以培养设计队伍和工厂的制造能力。
顾诵芬完全理解徐舜寿的设计思路和理念。他认为,这个方案既大胆又超前,完全是站在世界先进行列的起点设计。“在(设计)室成立前后,我和志千两人曾经在局里和去航院访问,请的都是教授专家,几次酝酿,大家的意见基本上是相同的,即要一开始就搞设计。至于设计什么,那要从空军现有的机种去分析,看哪里有缺门,自己能不能设计,也要看世界上的情况,是不是合乎发展趋势。就这样,我们就找出了这么一条歼击教练机的路来,认为当时日本、捷克斯洛伐克都在设计同类型飞机,英国也在试验全喷气教练程序,所以是合乎发展趋势的。而且经过和410厂发动机设计室协调,认为飞机、发动机都有原准机可行,所以是有可能设计的。”
新中国第一次设计的飞机,就是一架喷气式飞机,这个起点不低,赶上了世界航空技术发展的脚步。同时,新设计的飞机并不是对国外某种现成飞机“照葫芦画瓢”的模仿,也不是做一些“小修小改”,而是根据飞行任务的需要,从世界航空技术总库中挑选合适的手段,进行新的“工程综合”去形成自己的设计。这是新中国从设计第一架飞机开始就建立起来的设计路线,也是世界航空发展所遵循的主要设计路线。
设计前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征求使用者对新机的设计意见。
徐舜寿带着黄志千和程不时,到另一个城市的一所训练飞行员的航空学校去调查研究。
在调研中,徐舜寿组织了多次座谈,介绍了设计意图。飞行员知道中国要开始设计自己的飞机,非常兴奋,特别是对航校设计喷气式教练机更感亲切。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想法,徐舜寿向他们请教了设计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在草图设计过程中,为了使新设计的飞机得到空军领导机关的认可,使设计方案更加符合部队的训练需要,徐舜寿先后14次专程带着设计方案,带领设计人员,请空、海军领导机关,空军有关部队、航校及苏联专家进行审查,广泛征求意见,也请工厂试飞员评审设计方案。
这是一种“从实践中来”“从实践出发”的设计路线,在工作之初,徐舜寿便为设计室建立起这样的优良传统。
新型喷气式教练机最后被命名为歼教-1,即“歼击教练机1型”。
当时,工厂刚刚仿制成功苏联米格-17喷气式歼击机,工厂的设计人员对米格飞机非常熟悉。为了不让我国自己设计的飞机变成苏联米格飞机的仿制品,在开始设计歼教-1飞机时,顾诵芬就详细了解了几种米格飞机和雅克飞机的结构。
顾诵芬的这种想法,正是徐舜寿的设计初心。徐舜寿要求,搞襟翼的就要看这几种飞机襟翼的图纸,搞座舱布置的就要看这几种飞机座舱布置的图纸。大家在研究了几种相同部件的结构之后,对全系统进行集成,独立做出了“工程综合”的设计路线。
设计室里绝大多数人是第一次设计飞机,许多工作不知如何下手,包括打样设计、画模线等。
徐舜寿倡导“综合设计”的方法。他形象地对新的设计人员说,“熟读唐诗三百首”,意思是要熟悉许多不同的飞机,从中舍旧取新,创新设计工程措施,不要“唯米格论”。
徐舜寿对设计提出了明确而大胆的要求:每名设计人员对自己的设计依据和想法都必须作出说明,并与有关方面协调论证,各个局部在总体布局上必须是合理的,不允许各行其是;对大部件和大系统的设计总图,采取集体审查的办法,设计者张贴图纸,请有关人员参加,讲解自己的设计依据、思路、意图、数据、问题等,并进行答辩。答辩一旦获得通过,所有参与者当场签字;如答辩通不过,修改后再来。
在方案评审阶段,了解到飞行员反映苏联飞机座舱盖低、操纵手柄偏大,设计人员去部队收集了1400名飞行员的身材数据,根据中国人的身材特点设计了歼教-1的座舱和驾驶杆手柄;然后,再根据部队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修改原设计方案。
在最后确定的总体设计方案中,歼教-1多处体现了创新的特点。首先是打破米格歼击机的传统框框,采用了两侧进气、全金属、前三点起落架、双座、平直翼的总体方案。其中,抛弃米格机头进气布局,采用两侧进气布局,这对后来国产歼击机、强击机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气动力是飞机设计的灵魂,空气动力学的发展推动了飞机的跨代发展。然而,我国开始飞机设计时,气动力设计方法和手段完全是空白。顾诵芬任气动组组长,负责整架飞机的气动力设计。同时,确定整架飞机总体参数的任务也落在了他的肩上。
徐舜寿与顾诵芬等人前往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向张桂联教授求教。张桂联与徐舜寿在美国麦克唐纳公司一起实习过,之后又与黄志千在英国格洛斯特飞机制造公司一起工作过。当时,黄志千是机身設计组组长,张桂联是气动组组长,他们相互很熟悉。飞机设计室刚成立,徐舜寿就到北航找张桂联教授,请他讲授飞机设计的基本知识。
从北京返回沈阳,顾诵芬向徐舜寿作了详细汇报。徐舜寿很重视,听得很仔细,而且不断提出问题。顾诵芬又从沈阳奔回北京,去找资料。
1957年冬天,天气很冷,黄志千、顾诵芬在哈尔滨做了两个月的进气道方案试验。为模拟发动机抽气,黄志千与马明德商量,决定用鼓风机抽的方法。但需要的鼓风机外面买不到,顾诵芬也从没接触过鼓风机。顾诵芬决定自己动手设计鼓风机。通过参考国外资料,他最终完成了这项任务。
在一次试验中,设计室需要一排很细的管子用作梳状测压探头,这样的设备国内没有生产,只能自己设计。怎么办呢?顾诵芬与年轻同事想出一个法子:用针头改造。连续几天晚上,他都和同事跑到医院去捡废针头,拿回设计室将针头焊上铜管,再用白铁皮包起来,就这样做成了符合要求的梳状排管,再送到哈军工的低速风洞里进行试验……
随着风洞试验中一个个问题被解决,歼教-1飞机的气动力设计一步步走向成熟。
根据国外设计飞机的经验,大家决定在打样设计结束后制造全尺寸木质样机。但中国过去没有自行设计过飞机,更没有制造过木质样机。
接受这项任务的是木工车间一位从上海来的八级木工——陈明生。他只有30多岁,但技术过硬。设计员向陈明生介绍了木质样机的作用和一般要求,又给他看了国外样机的模糊照片,他就领着一个木工组按歼教-1的图纸干了起来。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木工活,他们居然用了100天就完成了,而且质量优异。
1957年8月5日,距离顾诵芬到达沈阳不到10个月,让他长期以来苦思冥想、夜不能寐的歼教-1的样机就呈现在眼前。
9月,空军机关派人对歼教-1进行木质样机审查。专家们经过对木质样机的认真审查,提出改进意见,设计室又指导木工车间对木质样机作了修改。
经过技术审查、审批等一系列的程序后,1958年3月底,歼教-1的圖纸下达车间,试制工作开始了。
鉴于这架飞机在我国航空史上的特殊地位,航空工业局局长王西萍从北京赶到沈阳,在工厂进行了试制动员。工厂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局面,车间日夜赶制,设计人员到试制现场与工艺人员、生产工人一同工作。为了保障各车间工人更好地参加“大会战”,后勤部门派人到生产现场发放日常生活用品。为了节省时间,他们还经常把盒饭送到生产一线。
为了及时处理生产中遇到的问题,顾诵芬与设计人员带着行李,吃住在车间。他们夜以继日地在车间跟产,有的人几天几夜没合眼。
经过几个昼夜的奋战,终于完成了歼教-1飞机的总装任务。
试飞,首先要制定一个大纲,依据大纲要求,细化到每一个架次的飞机任务单,确认每次起落要完成什么任务,明确任务分配和要求。试飞员按照任务单飞行。所以,好的设计还必须有好的试飞员。
歼教-1试飞前两周,才定了空军试飞员于振武,空军三航校派了教员敖厚德,还有112厂的吴克明参加试飞。
于振武是试飞站推荐的,那时是军队里的技术检查主任。在接米格-17时,他的飞行技术给试飞站同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于振武是歼教-1飞机首席试飞员。设计室向他详细介绍了飞机设计时考虑到的各种问题。面对一大堆空气动力的计算数据,于振武说:“真没想到这架飞机的设计做了这么详细周密的技术准备。”
顾诵芬还给他们三位提出了试飞时应注意的事项。
1958年7月26日,歼教-1完成了试飞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距离王西萍到工厂动员正好100天。
那天,全体机务人员检查完飞机之后,在飞机旁列队立正。组长跑步到试飞员面前,举手敬礼,报告:“准备完毕,飞机良好。”飞机的表面喷着银白色的罩光漆,成为一架名副其实的银燕。于振武走到登机梯前,看着这架崭新的从来没有人飞过的飞机,不自觉地用脚在地上擦了擦靴底下的土,才攀梯登上飞机。
指挥台升起一颗绿色的信号弹,这是对歼教-1放飞的信号。人们注视着歼教-1。歼教-1轻盈地飞上了蓝天。只见它逐渐爬高,迅速变小,像一只银色的燕子,灵巧地转了一个弯,保持在人们的视线内。

1958年8月4日,叶剑英元帅(左一)、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左二)观看歼教-1试飞
飞机设计团队和生产飞机的工人都在机场跑道边观看,紧张的心情转化为激动的喜悦,爆发出一片掌声和欢笑声。
歼教-1顺利完成首飞。
步出机舱,于振武汇报了试飞体会:“歼教-1座舱宽敞,前后舱视界比米格-15好,座舱安排合适,部分电门仪表安排有些不适,应加以改进;起落架减震好、刹车灵活、转弯容易;放襟翼时飞机低头,力矩变化较大……”
大家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歼教-1首飞几天后,迎来了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这一天,为庆祝建军节,在沈阳市于洪机场做了一次歼教-1飞行表演。
于振武提出,由于歼教-1很多课目还没有飞,飞行表演时很难飞什么动作,于是就设计了一个高速通场,他与敖厚德一起飞。当时也有朝鲜的武官在场。
8月4日,歼教-1在沈阳又进行了一次飞行表演。这一次,叶正大请来了叶剑英元帅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于振武飞得很低,而且做了盘旋。刘亚楼一看就急了,赶忙喊停。结果,于振武又飞了一圈。
按照初次试飞规定,于振武驾驶飞机在机场上空绕场一周,便进入了着陆航线。当飞机安全着陆后,徐舜寿走上前去同于振武热情握手,紧紧拥抱……
新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制造的喷气式飞机胜利试飞的消息,随后被报告给周恩来总理。
当时,有人建议国庆节时驾驶歼教-1飞过天安门,后从当时的政治、外交等多方面通盘考虑,感觉还不宜公开。曾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并发表首次讲话的伍修权,在《忆新中国第一代航空工业专家徐舜寿》一文中写道:“徐舜寿等同志在航空工业上的贡献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早在‘101号’(歼教-1又被称作‘101号’机)试制时,周恩来总理鉴于当时还不宜公开宣传这一成就,请人转告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先做‘无名英雄’。”新华社为这架飞机首飞发了一条内部消息。
歼教-1首飞,让中国人自主研制飞机的梦想第一次张开了翅膀。而甘做“无名英雄”“一切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已成为国防科技工业战线每一个人自觉遵守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