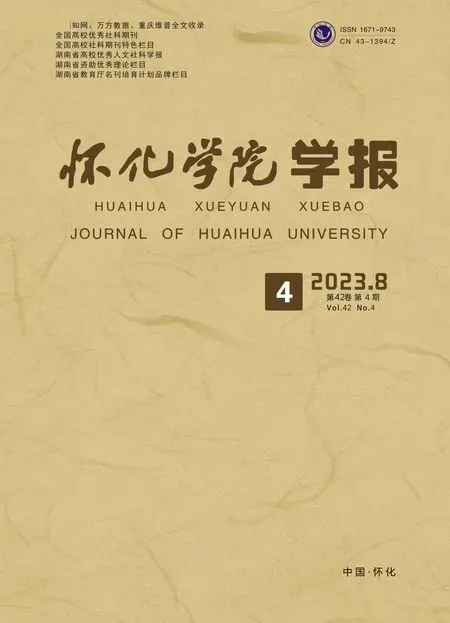窗户·三棱镜·渐近线·画框:电影与现实的四种形态关系
谭志勇
(怀化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8)
电影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经典电影理论家研究的重点内容,在这一问题上,经典电影理论家于果·明斯特伯格和写实主义理论大师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都提出了电影是“窗户”的观点;鲁道夫·爱因汉姆则认为电影是现实折射的“三棱镜”;安德烈·巴赞在物质本体论基础上提出电影与现实“渐近线”关系;让·米特里强调画面关注点的自由选择,进而提出了“画框论”。这些论说引起了美国电影理论家达德利·安德鲁的关注,他分析了经典电影理论家对电影与现实形态关系理解的异同。在达德利·安德鲁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以“窗户”“三棱镜”“渐近线”和“画框”四个形态论说为基础,分析论说形成的理论基础和心理机制,归纳和对比不同论说之间的关系,从而探究电影与现实的关系,揭示电影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一、“窗户”论:心智素材和物质现实的复制
在探索电影真实艺术本质上,传统形式主义大师明斯特伯格和写实主义大师克拉考尔都提出了“窗户论”,但是视点各有不同:一个是从形而上的角度诠释电影是照进观众心理“窗户”的审美艺术,是心智的素材,而非机械复制的工具;一个从现实主义笔触审视电影映照属性,即物质现实复原的“窗户”。两者在辨析电影与现实的形态关系时,存在统一的论说,却有着不同的视点,从而形成了形态论说一致,但是观点内核悖反的关系。
(一)心智素材“窗户”论的理论依据
明斯特伯格在《电影:一次心理学研究》一书中肯定了电影作为一种心理动机艺术,即“电影是对人心理机制的模拟,是信息的加工过程”[1],并运用威廉·冯特的结构主义解析电影在观众心理的过程:纵深感和运动、注意力、记忆和想象、情感,即人通过对光影纵深、运动的感知,以及注意力的改变,获得二维画面的三维真实感,再通过大脑的记忆和想象,产生意义、冲突和个人旨趣,最后,这些内容通过“情感”在主体心理得以呈现。电影的审美过程成为明斯特伯格认为的不同层次的心理活动,电影通过人类的心智素材的重组、冲突而产生意义,是纯粹的心理活动。他着重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的心理活动中智力、经验感知的主动性参与,指出电影以无生命的虚幻画面唤起观众生活中感知的具体物像,这些心智素材的组合是一种非现实、意识流和光影的游戏,观众透过电影银幕这扇“窗”了解人的精神活动。他指出“电影不存在于银幕,只存在于观众的头脑里”[2],并提出电影是展现人类心灵“窗户”的论说。
(二)“物质复制”与“心智素材”的辩证关系
克拉考尔和巴赞一样享有“现实主义”的标签,在《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世界的复原》中,他十分强调摄影在电影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电影的真实性与摄影密切相关、不可分割,这种近亲性必须受到尊重,并把对现实的复原作为首要任务和核心。克拉考尔认为观众看电影就像透过一扇窗,观看窗外随机的、客观的视觉真实的世界。
和明斯特伯格一样,克拉考尔也受到了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沿用了格式塔心理学中对物象心理感知的观点,他的电影“窗户论”类似康德的“先验”即对映照的现实进行整体感知的观点、韦特海默主张的直接经验的观点、胡塞尔现象学中如实描述再本质认知的观点、契合考夫卡关于“环境场”“心理场”“行为场”等“场”论的观点,以及马赫的物象可以独立于物质属性被个体经验感知的观点。
区别于明斯特伯格纯粹心理感知的“窗户论”,克拉考尔强调“窗户”映照现实物质外部表征的特点,认为电影作为“窗户”具有复制物质外在形象的属性,观众对“窗户”内的外在物质产生经验感知,经验感知是建立在自然物象和事件产生大量的“心理—物理”的基础上。[3]为此他对电影作为“窗”在洞察外在物质的形态时提出了具有心理感知效应的要求,即物质现实应具备偶然性、不确定性、多义性和模糊性的感知特点才能够被观众感知到经验的真实,并尊重观众“窗户”内关注点的自由选择。在创作主体层面,他指出创作者对物质存在的心理顿悟,可以通过摄影复制展现出来,观众在开放、经验式的想象中发掘超越素材本身的意义。
总体上,双方侧重的视点不一样,明斯特伯格“窗户论”重点在作为心智素材层面;克拉考尔的“窗户论”则把电影“窗户”作为媒介,重点关注媒介内物像映照后的心理感知。不同的侧重点,使得电影作为“窗户”的观点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延伸。
二、“三棱镜”论:折射艺术和“局部幻想”
爱因汉姆是深受明斯特伯格和格式塔心理学影响的电影理论家,他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明斯特伯格形而上的心理学研究,并开始专注于视知觉、审美艺术和经验心理、审美知觉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他把电影当作“三棱镜”,重点指出了电影作为“三棱镜”具有的“形象偏离”折射性和局部幻想性特征。
(一)延续:视知觉认知心理和艺术独立性
鲁道夫·爱因汉姆认为视知觉具有和思维一样的功能,他主要从格式塔心理学的“张力”“场”“异质同构”等理论来研究视知觉在直觉基础上的审美情感,认为意象是视知觉在物质表象上抽象的结构,是视知觉整体本质结构上的感知,而非完全复制。[4]爱因汉姆认为电影是人类视知觉感性认知基础上的理性活动,视知觉可以通过抽象的逻辑判断达成对事物本质的理性认知。
爱因汉姆延续了明斯特伯格强调的艺术表现形式与现实之间的区别,认为艺术不是对现实简单的模仿,电影是一门独立的艺术,是现实的抽象和剥离,要求电影区别于戏剧,与现实保持距离,从而保持电影的本真和艺术的独立性。为强调电影与现实之间的区别,爱因汉姆提出电影区别于现实的“六因素”:平面上的投影、纵深减弱、无色彩和人工光、画框限制、时空不连续、视知觉外其他感觉失去作用。他坚定有声电影给电影带来的破坏,认为技术应该为艺术服务,主张承认差别,反对写实,倡导电影作为独立的艺术化,反对电影是现实的复制观点,认为电影是技术性的视域产物而非人类真正的视觉,以及电影具有画框限制的重大“缺陷”。
(二)区别:强调“形象偏离”和“折射”的艺术
相对于明斯特伯格的心灵映照的“窗户论”和克拉考尔外在物质形象复制的“窗户论”,爱因汉姆关注于存在人与“窗户”之间的“折射”现象,他形象地把主观性的折射比喻为“三棱镜”,即通过技术转换、主观性创造,使现实“改头换面”成为新的艺术形式,他强调了电影与现实“形象的偏离”,以及对现实的主观“折射”性,并指出:与其说电影是“窗户”,不如说是“三棱镜”更恰当。
爱因汉姆的观点中强调的物象映照,并不是镜子直接的镜像,不是对现实“直线”的复制,因为他发现电影与现实之间存在“鸿沟”,比如演员夸张、程式化的表演,这些区别于现实的形态呈现更加容易刺激观众感应,从而形成电影独有的区别于现实的心理效应,以及观众对电影约定俗成的理解方式。在对电影动作的认知中,他指出电影动作是对自然动作的简单模仿,这种“仿造”的进一步演进,使得电影动作更加区别于现实动作而存在,电影进一步“仪式化”“电影化”“独立化”。在这些区别基础上,他坚持认为对象和事件作为电影的心理素材,需要透过“三棱镜”脱离现实才能成为一种创造性的艺术,这也成就了他著名的电影“三棱镜论”。
(三)延伸:电影是现实的“局部幻想”
爱因汉姆在格式塔心理学主张的“心理的结构能力说”的基础上提出“局部幻想论”。[5]观众通过局部的物质形象,想象并结构成一个整体,从而获得一个高度集中的、具有强烈艺术性的完整印象。[6]
“局部幻想论”认为只要电影出现与现实相符的关键部分,观众就能建构一个整体形象,产生幻想印象,而无需对现实进行完整地再现。“局部幻想论”是爱因汉姆“三棱镜”论的进一步发展。“三棱镜论”侧重于折射和“形象偏离”,“局部幻想论”极力要求承认电影与现实之间存在的不完整对称,并认为电影的“残缺”反而成为创造艺术的可能。爱因汉姆指出“只有在现实与表现手段不一致时,艺术家才有发挥创造力的余地”,于是,他极力维护“无声电影”的合理性,反对技术的运用,指出蒙太奇在对时空割裂的同时,间接创造了更多可能。“局部幻想论”强调了画框的限制产生艺术的创作可能性,这与米特里的“画框论”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区别于“窗户论”,爱因汉姆的“局部幻想”观点把电影与现实的关系描绘得更像是半掩盖的“窗户”,观众只看到窗户内的一部分再通过幻想获取完整的形象。这种“半边窗”局部幻想观点,在后来间接得到丰富,现代电影创作者力求突破画框的限制而创造更大范围的空间,往往主观的“局部残缺”化,局部的画面外存放看不见的“残缺”内容,观众通过想象拓展画面内部空间,产生延伸效果,形成独有的电影空间艺术。爱因汉姆的“局部幻想”观点,使得电影作为“窗户”的观点得到新的延伸。
总体上,爱因汉姆延续了明斯特伯格的“心灵窗户”论,但是否定电影仅仅是纯粹的心理、视觉认知,更加重视电影形式技巧表达和艺术功能,强调了电影与现实之间“三棱镜”折射关系,以及电影与现实非完整复制的“局部幻想”特征,承认了电影与现实的区别,将电影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所以,如果电影是明斯特伯格和克拉考尔所说的“窗户”,那么爱因汉姆则认为电影是被窗户上的玻璃折射到外面的光扭曲现实的景而成的艺术。同时,他进一步强调这种折射的不对称性,即电影和现实之间存在局部限制性,观众通过局部想象补充完整,完成对电影与现实之间的高度“仿真”效应。爱因汉姆在《电影的艺术》中开始探索从意识层面发展到形式艺术层面,从关注电影的意识内容,到关注电影作为艺术本身具有的特征,并主张利用形式和技巧的变化拓展电影艺术的张力。“三棱镜”和“局部幻想”论成为爱因汉姆看待电影与现实关系的重要观点。
三、“渐近线”论:无限靠近,永不相交
巴赞认为:影像是“光的模型”(A mould in light),它捕捉物体的“印象”(Impression)。它不是真实的物体,而是真实的、可追寻的“痕迹”(Tracing),电影素材就是事物留在胶片上的痕迹,影像高度接近实物,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Asymptote of reality)[7]。
(一)“渐近线”论的形态特征
第一,同一性的“渐近线”。巴赞深受萨特的存在主义、梅洛·庞蒂现象哲学、柏格森直觉主义等思想的影响,“电影的存在先于本质”“摄影本体论”源于萨特的“存在早于本质”的观点。[8]在存在主义的影响下,巴赞首先强调了“影像本体”的论断,摄影机“照相”属性和物质现实的复原属性是摄影的本质属性,摄影机存在意义和价值符合人类的“木乃伊”情节中“长生不老”心理,人类保存“像”的完整性和延续性心理欲望是先于摄影机存在的,这是摄影机复制“像”功能存在的价值和电影心理动机的基础,观众通过摄影机复制的“像”完成移情、共情和自我认识。其次,巴赞极力尊重“像”和现实之间复制同一的关系,认为蒙太奇组接方式主观地将时间、空间割断,违背现实时空该具备的连续性,长镜头则弥补了缺陷并尊重了现实的客观性。他赞扬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并不屈从“心智素材”“视知觉经验”“先验”等形而上观点,而从物质外在纯表象去推断存在的含义。所以,巴赞一直强调电影的纪实性、客观性和摄影机的“冷眼旁观”视角,并进一步认为现实主义电影需要放弃戏剧性、逻辑性、剧情结构和对人物的心理表现,关注现实本身,保持现实的多义性、模糊性和偶然性。[8]这种偶然性、多义性进一步强调了对现实素材攫取的非主观性原则,力求做到极致的客观创作,多义性则强调尊重观众对现实素材复制的“像”的自由理解。巴赞前期的观点着重于电影和现实同一关系,如同两条“渐近线”,在物质外在形象真实上高度一致。但是巴赞同样认可电影不可能实现对客观现实的完整摹写,尤其是摄影复制不能挖掘物质外在形象的内心真实,这让巴赞在后期更加重视对精神维度真实的探讨。
第二,精神真实的“渐近线”。在巴赞后期的电影研究中,他发现了更多自我矛盾的地方,现实真实具有摄影无法描摹的复杂性,比如摄影机无法解读演员脸部复杂的情绪以及物象之间存在微妙的规律和关系。与爱因汉姆的固执己见不同,巴赞果断地跳出唯实主义,提出真实也是观众心理感知的真实,电影的感觉真实是建立在摄影机所展现的真实空间基础上的。与把费里尼当作新现实主义的“叛徒”不同,巴赞认可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所传达的从“现实真实”到“精神真实”的观念,接受了费里尼“在想象和现实之间,我看不到明确的界限”的观点,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电影的革新和延伸,提出了“人之新现实”(Neo-realism of the person)的概念[9]。这些观点使得“渐近线”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延伸,并使得现实主义电影走向“形而上的现实”即精神层面的真实,探寻透过物象背后的内容、规律和潜在意义,寻找精神纬度的真实,开始了客观真实向内心真实的深入。此外,巴赞赋予了现实主义电影人文情怀、人道主义视角的表达,这在一定层面上与他前期强调的偶然性复制互相矛盾。于是,巴赞在“总体现实主义”基础上,开始丰富对“渐近线”的理解,并指出电影与现实之间是无限靠近,永不相交的“渐近线”关系,即电影真实和现实真实无限靠近,但是永不相同。
(二)从形式主义到写实主义演变
相对于明斯特伯格的“窗户”和爱因汉姆“三棱镜”论形而上研究,巴赞的“渐近线”论从传统的形式主义转到写实主义研究,这与克拉考尔的“窗户论”保持一致。同样作为写实主义的电影理论家,巴赞肯定和继承了克拉考尔的大部分观点,否定了作为电影剪辑的蒙太奇对时空的破坏作用,提出尊重摄影机的复制属性,现实是电影的基本素材,强化表现的真实、时空的真实和叙事结构的真实。反对形而上的论说,反对非理性、纯视觉的叙事方式,强调电影与现实的一种对应关系,认为电影的本性是纪实性的再现。巴赞不同于克拉考尔的是克拉考尔强调的现实是哲学基础上的、大自然的、存在的、物理属性的“物质现实复制”,是排斥内心、幻想等精神层面的绝对的物质真实,而巴赞表达的是摄影机对现实完整的“临摹”,是指一种“完整的真实”,包括精神层面存在的真实。与巴赞相比,克拉考尔的“现实观”显得规定性更强,在他那里“现实”只等同于“物质现实”,而绝对排斥“精神世界”真实观主观真实与客观真实。[10]
区别于传统的形式主义理论,巴赞从单个空间的映照,发展到形而上层面的真实性面貌,基于精神世界对现实的真实反馈,而不是重新的组合、反应,是一种透过外在现象看本质的艺术思考。“渐近真实”的提出使得巴赞区别于传统形式主义形而上的理解而又进一步,他的美学思想和电影评论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创办的《电影手册》成为法国新浪潮电影宣传的阵地,长镜头理论被热捧至今。随着3D、4D 等新技术的出现,电影与现实之间愈加无限接近,但是电影虚幻、画框限制等特征的存在使得电影同样无法等同于现实,因而无法相交。巴赞的“渐近线”理论将在长时间内被奉为电影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圭臬。
四、“画框”论:画框限制
“画框论”是建立在蒙太奇理论之上,爱森斯坦把镜头取景形容为“对象与人们观察它的角度和从周围事物中截取它的画框之间的相遇”。[11]基于西方电影理论中的“摹仿论”,爱因汉姆、明斯特伯格、爱森斯坦和巴赞等电影理论家把电影作为画框讨论过,重点在电影画面与绘画之间形态关系的类似,米特里则针对“画框论”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一)强调画框的存在
米特里赞同巴赞的“渐近线论”,但是着重探索“渐近线”的原因,即为什么现实和影像无法交织。他认为电影影像不同于心像,影像是对现实的复制,心像是建立在观众经验上的映照,但同时,电影影像与现实的区别是不能反映原物的在场。此外,电影影像是窗户还是画框,米特里认为两者皆是。当影像只是反映被纪录的现实事物时,就如同窗户;当影片影像作为再现形式承担起表意功能时,则构成了表意系统的一部分,如同画框那样,成为构图的一部分。[12]
米特里强调了画框的存在,并指出了画框存在的限制性,这是区别现实的重要特点。荧幕上有框现实却没有,人们只能通过想象边框外的世界的存在以达到真实的体验。绘画也是在有框的基础上产生更宽广的想象,才具备了更大的艺术魅力。因此,米特里从画框限制出发,指出电影更像是“画框”。同时,米特里也指出电影和绘画一样,观众承认画框外的世界是存在的,并相信画框外的世界也是真实的,这是观众审美认同的一种约定和诉求,也是观众的一种经验“预设”,并通过现实中的逻辑结构画框内和画框外的世界,使之产生整体意义。
(二)“类似物”:“中庸”路线产物
米特里综合爱因汉姆和巴赞的理论,走出一条“中庸”路线,以阐述影像是写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综合。电影被他认为是摄影机创造出来的“类似物”,电影只是与现实具备同质的视觉形式,这一特征如同绘画一样,同样是“类似物”的视觉形式,也同样有画框限制。画框限制是米特里认为巴赞的“渐近线”永不相交的重要原因,“画框”论成为米特里区别于形式主义和写实主义的重要论点。与明斯特伯格和爱因汉姆相同的是,米特里同样受到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并试图从心理学的视角去解读电影的景深、运动、色彩、音乐等元素,他充满着辩证精神,试图调和蒙太奇和长镜头之间的矛盾,证明两者能够和谐共存。他并没有严格区分自己的理论派系,而是兼容并包、博采众长,并认为这才是现代电影理论的研究方法。
“窗户”论、“三棱镜”论、“渐近线”论和“画框”论是经典电影理论家对电影与现实关系的比喻体,经典电影理论家在不同程度上相互渗透、借鉴、补充和讨论,或有共同的理论基础,比如一定程度上受到格式塔心理学和西方理论中的“游戏说”“摹仿说”的影响,巴赞的“完整现实神话”就涉及画框和窗户形态论说,米特里探讨过其他三个观点,这些论说的观点并非划清界限,更多的是理论基础和视点的不同。随着电影理论的发展,在探究电影与现实本质关系上,作为开端的经典电影理论侧重电影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探讨,现代电影理论中出现的“镜像”“符号”“媒介”等论点侧重研究电影与观众的关系,后现代认知符号学理论侧重于跨学科符号研究人类意义的生成。总体来说,经典电影理论的不同形态论说,像打开了一扇“窗”,推动电影理论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