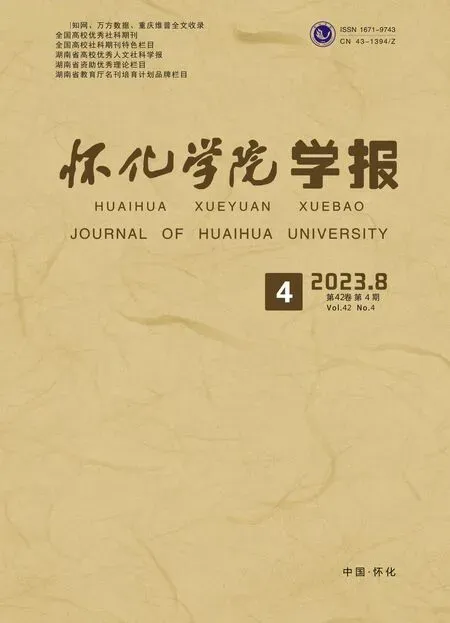舞龙活动中的文化交融与流变
张迎波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马克思曾指出:“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如果我们跨越经济场域的交换,社会交往以各种纷繁的形式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在社会文化的场域中,体育以其广泛参与性的特点,能让我们窥见更鲜活的社会交往表达。如果我们把民族体育理解为不同民族在漫长历史创造中对所积淀的传统文化的一种表达,它展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是与其社会特征、经济生活、宗教仪式、风俗习惯息息相关的传统文化现象。那么,通过对不同民族漫长历史过程中体育文化的构建过程进行观察,我们或许能够看到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交往与流变的内在动力。龙作为华夏民族的古老图腾和神灵崇拜,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其影响力渗透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各个民族的祭祀或祈福活动中,以龙为符号标识与表达形式的舞龙、赛龙舟等活动,向我们展示着不同民族、地域间的文化交往、交流、融合,以及龙文化的沉淀与流变是如何产生并持续发展的。此外,龙舟是一种以龙为文化背景的水上运动形式,虽然从直观上来看,与舞龙在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但从龙文化的深层内涵来看,龙舟显然是华夏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龙舟活动的演进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舞龙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是怎样交融与流变的,更进一步,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其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模式。
一、祭祀之龙中的多元民族文化融合
舞龙是以祭祀而滥觞的。据资料考证,最早具有传统龙特征的龙形象出现在旧石器时代[2],龙之所以成为传说神话中所建构起来的一个图腾形象,其深厚的基础在于农耕社会对于水的根本性依赖与需求。龙与水的密切关联,反映了东亚农耕社会对这一根本性需求的焦虑。在早期的甲骨文《殷契遗珠》中,就有“龙司雷雨”的描述[3],进而生成了“龙生于水”“川枯则龙鱼去之”的河海水神之演化。龙由此被视为超越一切、统摄万物的神秘力量,拥有绝对权力,主宰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决定着人世的命运及祸福,从而使人对这一神秘事物产生敬畏和崇拜的思想感情,祭祀因此而生发。舞龙祭祀大体可分为两类:祈福之龙与搏魔之龙。
(一)祈福之龙——视龙为祥瑞
祈福之祭通常在备耕之际与丰收之时举行,民间俗称农历二月二为“龙抬头”,是舞龙祭祀最为盛行的时节。在此备耕之际所举行的舞龙祭祀,意在表达开春农耕播种之前把春龙从冬天的沉睡蛰伏中唤醒,祈求司水之龙神赐福、赐风调雨顺,以求年丰岁稔。舞龙祭祀另一个盛行的时段则集中于中秋时节,表达的是对神灵庇护和自然馈赠的感恩。
然而,在文化变迁所发生的现实世界中,任何一种文化成分都可能是影响龙文化发展变化的潜在因素。比如,不同族群、地域和多样化的生计与生存环境,都会使舞龙祭祀的举行时间呈现差异化的特征。《吕氏春秋·仲夏纪》载:“五月祈龙降雨,以祈谷实。”[4]另如四川绵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耍蚕龙”活动就有“正月初八蚕过年,九月十五酬蚕节”的说法。又如浙江省东南部的仙居县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土地非常宝贵。传说有一年大旱,当地许多民众夜里梦见天空有长龙降雨,第二天便组织大家扮龙求雨,大雨如期而至保证了庄稼的收成,于是遇旱则舞龙祭祀沉淀为当地之民俗。[5]
虽然舞龙祭祀中的“请”“敬”“祀”“谢”龙王等环节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沉淀为该仪式的过程要素,但在多民族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具体的舞龙活动又呈现出各式各样的本地化形式。例如,在云南省石屏县北部的哨冲、龙武、龙朋三个乡镇,居住着全世界仅有的三万多花腰彝人。因为地处山区,肥沃土地甚少,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村民对雨水资源极为需求,所以以求雨为目的的祭祀活动应运而生。彝族崇龙,认为龙王是主水之神,作为彝族支系尼苏下的一个分支,花腰彝人每年都要着盛装举行祭龙仪式来求雨以保丰收,尤其是逢每十二年一次的马年马月马日,更是要举行祭大龙活动。位于云南西部边陲山地峡谷的施甸县布朗族,作为古哀牢国土著民族“百濮”后裔,每年大年初二都要组织隆重的舞龙祭龙活动。[6]
(二)搏魔之龙——视龙为不详
在舞龙祭祀的神圣礼仪中,正如范热内普所言:“神圣性之特质亦非绝对。”[7]神性的背面就是魔性的存在。因此,舞龙祭祀并非单面向的、一成不变的祈福之举,同时存在着与魔相搏的祭祀形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习惯、价值观念等文化属性,然而在长期多民族的历史交往中,文化的浸润使他们不断地吸收着新的文化要素,并对已经存在的文化形式加入了自己新的理解与新的要素。这些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的加入,使得龙图腾的形象丰富饱满起来。更重要的是让人们看到了龙的神圣不可侵、高贵不可辱的另一面是魔性的存在。这种与魔相搏的祭祀形式,在藏、苗等民族中得到了最典型的表达。
藏族早期认可的龙神与自然崇拜的山神、天神等不同,他们认为龙神的职能多与疾病相关,其中显著的特点是它并不是通过某种神力去撼动自然界,以此来对人类施加危害(当然也有这样的个别情况),而是能够直接对人类存在产生威胁。藏族先人多是把龙神当作恶神看待。他们认为龙是四百二十种疾病之源,这些疾病统称为“龙病”,严重威胁着藏族人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命。[8]
贵州苗族的独木龙舟活动也突出了龙文化神圣性特征的流变。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五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施秉县和台江县清水江流域两岸以及与巴拉河支流交界处的30 多个苗族村寨中开展独木龙舟活动,为其奠基的就是有关“恶龙”的传说,清水江边各个苗族村寨普遍都传诵着一个版本大同小异的杀恶龙、分食龙肉的传说故事。作为苗族文化重要传承方式的苗族古歌也有《斩恶龙》《划龙船史歌:杀龙草朗墟》等内容。[9]以苗族独木龙舟的形式而举行的舞龙祭祀,把神话传说与当地苗族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抗击洪水的事情紧密地结为一体。
在四川安仁,这一祭祀则是以板凳龙的形式进行的。安仁镇的居民大部分是第二次“湖广填川”中湖南人的后裔,相传安仁镇曾遭大旱,作物人畜极度缺水,为表达对司水龙神的不满,人们就把稻草用篾条绑在长条木板凳上,编成龙形,一人背负龙身在地上爬行,周围的人则拿锄头、扁担、铁锹等农具追打,龙则四面逃窜,人们就进行围堵,并用碗、盆、瓢等泼水在龙身上。一番追打过后,竟然马上下了一场大雨。更有传闻,板凳龙是龙神在凡间的私生子,为免于儿子挨打,便满足人们的要求尽责下雨。[10]应该指出的是,祈福与搏魔的两类祭祀,并非截然分离,而是相互交错的。如在清水江流域的苗族中,在以龙舟形式呈现搏魔祭祀的同时,也有对龙的敬畏感恩的祈福祭祀。芷江侗族孽龙原来也被称为“劣龙”,传说是兴水为害、作恶造孽的龙。名字足以说明当地先人对于孽龙的不满情绪,但还是要扎龙、舞龙、化龙来感化所敬畏之神灵,祈福纳瑞。[11]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多年的皇权社会中,“龙”无所不能的“天威”形象被寓为皇权的最高象征。但事实的真相是,龙这一文化存在,是在中国多民族的历史交往与合力过程中才得以构建起来的。
二、表演之龙中的文化沉淀与流变
(一)表演之龙寄托着美好愿景
正如韶乐歌舞一样,舞龙也逐渐从祭祀场域向表演空间拓展、从宫廷节目流变为民间的娱乐。这样的转变为舞龙这一文化现象打下了更为深厚的民众基础和广泛的社会交融空间。龙作为祥瑞的灵物形象,演化出悦神与娱人的双重功能。《汉书·西域传》就记汉武帝“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以“百戏”与域外之客共娱,其中的漫衍鱼龙之戏,就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12]
从祭祀之龙向展演之龙的转变使舞龙成为节庆之中最为耀眼的承载物。元宵节赏花灯,福建、山东等地便将花灯和舞龙相结合出现了舞龙灯的表演。夜晚花灯引龙四处游走,鞭炮齐鸣,烟花四溅,使人们沉浸在太平盛世的欢愉之中;河南焦作龙台村,每年正月十五、十六都要舞火龙,在锣鼓鞭炮的伴奏中,火龙左右腾跃还不时地喷火,气氛十分热烈;四川东部也有正月舞火龙的习俗,在伴奏的乐器中融入了川剧特有的锣鼓,极具地方特色;板凳龙因其制作和表演都很简单,在山区为主的地域极为流行,如陕西省南部秦巴山区的汉中和安康等地在春节和正月十五都会组织盛大的板凳龙表演,共同娱乐欢度佳节;[13]为突出舞龙活动的娱乐性,许多地方又将其称为龙舞。广东湛江和雷州地区,每年八月中秋节期间都会进行人龙舞表演,居民依海为生,以渔为业,龙舞表演大都在海滩进行,表演过程融入了祭海、敬龙等风俗,以人扮龙,成人扛起带上饰物的孩童扮演龙头和龙尾,老少齐上阵,齐心协力,独具海洋特色;[14]五月端阳节,古人又把农历五月称为“毒月”“恶月”。但几乎所有地方龙舟活动都在农历五月间,明末的《东莞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五月初一日,饮菖蒲酒,食角黍,观竞渡。”[15]广东地区从农历五月初一至初五举办龙舟竞渡的表演来表达民众驱邪逐疫的心愿。清乾隆《镇远府志·风俗》又载:“端午日作舟戏,结手两岸,观者如堵,以祈岁稔。”[16]贵州的苗族也用热闹非凡的龙舟表演场面表达作物丰收的情感。这样看来,虽然不同地域的人群生活习俗不尽相同,但对通过舞龙或龙舟表演的形式,普天同乐、悦人娱神以祝岁稔年丰的价值观念却有着共同的文化沉淀。可以说,正是诸如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节庆的表演之龙,为龙这一文化符号的沉淀铺垫了深厚的土壤。
(二)表演之龙承载着多元表达
表演之龙所传达的文化意义并不止于娱乐。如果说最初与祭祀密不可分的舞龙,其目标指向是对已确立的社会生活整合模式的确认与再造,是对以往在历史过程中沉淀下来的信仰、习惯和价值标准等文化内容的重申。那么表演之龙所完成的,不过是把原来受外在之力支配与规约的庄严和被动的形式,转化为自娱自乐的主动形式。它既可以是国家意志的纲纪传达,也可以是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地缘、血缘等多重关系依赖与维系的表述,以便再度确认沉淀为传统的基本原则,为日常生活的运行提供秩序的保证。因此,表演之龙浸满了社会教化的内容,具有多层的文化意义。也正是在国家意志与民众之欲的双重需求中,舞龙活动遍及中华,却又在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之中,在与当地文化要素的相互磨合中,生成出与之相适应的习俗礼仪。也正是基于此,舞龙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观察与理解文化流变与沉淀的一个窗口,抑或说是探析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中介点。
作为表演之龙,既以娱乐形式获得了更广泛的受众,也传达着大到族群、地域与国家对凝聚力的诉求,小到村寨、宗族甚至家族对地方原则的规训与实力的展示。舞龙灯的“灯”与“丁”谐音,就有旺丁兴族之意。舞龙就在这种社会教化的影响与代代相传中,不断地强化着社会整合的功能:它宣讲着合法的行为标准,以信仰的灌输来促进社会凝聚力。[17]
江西省南昌县向塘镇涂村舞龙需要10 名壮年男性;涂村供奉的神仙有三个,都需要用轿子抬,至少需要12 名青少年;再加上锣鼓等配套的打击乐器,至少需要30 名男性才可以比较顺利地开展舞龙活动,这对外可以显示涂村的人丁兴旺,年富力强。更重要的是,舞龙是一个动员全村力量的集体性的行为,它可以把平时分立的家户和村民联合起来,强调村落的内部团结和认同,造成一种村落共同体的意识,显示涂村人们的精诚团结。[18]
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舞龙文化逐渐发生了流变,不仅可以展示家族实力,它的表演形式还被赋予了“孝”的多元文化内涵。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木塔乡的方氏家族每年八月十五都会组织发起舞草龙祭天、祭祖活动。相传方氏家族由河南禹州迁往安徽木塔乡,在当地繁衍生息,为感谢祖德庇荫和上天福佑,通过舞龙教育下一代报恩先祖不忘本,增强家族凝聚力。[19]
徽州是一个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社会,有着严格的尊卑长幼的社会秩序。在徽州一带盛行“万世家风惟孝悌”,舞龙也被赋予“孝”的伦理内涵,在舞龙前需要在宗祠或社屋举行祭祀仪式,祭天地、社公、祖宗,以表对天地、社公的敬畏,突出对祖先的孝悌之心。如历溪村舞的就是孝龙,孝龙是用麻衣扎成的,舞龙伴以“十番锣鼓”调,并在用纸扎成的青狮、白象等五兽簇拥下,由村头舞至村尾,家家户户都要开门接龙,村民们说:“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教育下一代要孝顺长辈、孝顺父母。”如歙县的一些村落的接龙仪式需要按照房头辈分依次组接;在晔岔村舞草龙之时,每到一家门前,族人听到“龙来,龙来,四季大发财”后即放爆竹迎接,焚香拜龙后把香插入龙身,龙身上的香火越插越多,龙越舞越重,而香火多在一定程度上则表达出宗族的兴旺发达。[20]
苗族是一个社会组织比较严密的民族,内部的管理全靠理老、寨老、乡规民约等共同完成。贵州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多居住在江边,农田也在河道两侧,洪水冲毁庄稼和房屋时有发生,他们便认为是水龙王司职不力,便要将其降服以求安稳。与大部分民族对龙的认可不同,苗族人认为龙只是一种较为凶悍的生物。[21]于是苗族人民便在水上进行龙舟比赛来表现苗族坚韧顽强的民族品质。明弘治修《贵州图经新志·镇远府志·风俗》载:“苗人于五月二十五日亦作龙舟戏……是日男妇极其粉饰,女人富者盛装锦衣、项圈、大耳环,与男子好看者答话,唱歌酬和。已而同语,语至深处,即由此订婚,甚至有当时背去者。”[22]龙舟作为一项集体活动,自然需要本村寨齐心协力,因此划龙舟这项活动对于团结本族支系,展示村寨实力,扩展婚姻圈等,都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不仅如此,在台江县施洞地区,苗族基本上是一个家族一个龙舟,外宗族人不得参与。清水江流域的苗族还会在龙舟活动中划船到自己亲友所在的村落“接龙”(亲友前来祝贺,鞭炮齐鸣,龙舟头上挂满鸡、鸭、鹅,更有送来猪、羊等家畜的),“接龙”过程中家禽的叫声、鞭炮声、欢歌笑语声、江水拍岸声,异常喧闹,更平添节日的气氛。亲友之间通过送礼也达到了走亲访友维持社会关系的目的,而这些社会关系也是苗族人以为的立足之本。在相对封闭的文化圈内苗族利用龙舟竞渡活动年复一年地复制和再生产这种礼俗文化、血缘关系、姻亲关系。[23]苗族的龙舟之舞既是文化交融沉淀下来的产物,也是其社会动员力、民族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展现。
(三)表演之龙凸显地域特色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在长期的民族交往过程中,相互增进了解的同时,一定会有本民族特有的文化随之沉淀下来。据相关研究者统计,截止2016 年在全国25 个省份中,以舞龙为项目的各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187 项。[24]有诸如草龙、布龙、板凳龙、荷叶龙、断头龙、香火龙、湛江人龙舞等多种舞龙形式。舞龙的形式与龙之制作的材质和形象,也充分展现出地方性和民族性极具差异性的丰富表达。在江河之畔,舞龙大多以龙舟形式呈现;在山地平原,则以龙形游走来体现。在平原,男耕女织生活传统的深厚沉淀,舞龙大多以布疋彩缎制成一体长龙,在山地,则以板凳等制成灵活多变的分体之龙。如广泛流传于浙江、广西、四川等地的草龙,就取材于田间地头的稻草;江苏省锡山洛社“凤羽龙”,由无数的鸡毛缀成;广东江门的荷塘纱龙由竹篾和纱布制成,表面再绘上各种色彩;广西宾阳的炮龙,龙头龙尾用毛竹、稻草、黄麻、纱纸编织而成,龙身握把处则用毛竹编织,其余部位用印有鳞片的黄布、麻绳连接,黄布及麻绳用盐水浸泡,防止燃烧;重庆的铜梁火龙、湖南的芷江侗族的孽龙、广西仡佬族的草龙等,都突显了浓重的山地农耕文化的色彩。
又如,广西、四川、云南等地兴盛于不同民族中的板凳龙,就取材于农民居家生活的板凳。相较于宽阔的农田和山地,在狭小的谷场或者家庭院落,在长条凳上刻画出龙的形状,再以竹箍和棉布、稻草等谷物为原料制作出来,其形状质朴,工艺简单,舞龙者手握板凳腿进行舞动。[25]
湘西地区的苗族还给我们展现了舞龙文化独特民族特性。过去各地的祭祀活动被视为男性的特权,舞龙等祭祀活动均要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在湘西南绥宁县关峡乡大园苗寨的“草龙舞”和湘西地区苗族的“接龙舞”的祭祀活动中,是重视女性的参与的。[26]花腰彝族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有雌雄之分,汉族的龙也一样,因此在花腰彝族村落中,男子舞黄龙即雄龙,女子舞青龙即雌龙。重大节庆表演中便会呈现出男女共舞、雌雄同戏的特有民族文化现象。
三、竞技之龙中的文化交融与社会交往
文化的演进历程要求所有的文化现象都要具备社会化适应能力以满足其本身的生存发展之道。舞龙活动除了满足人们的祭祀和表演需求,其本身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的再生产机制还要求其更突显体育活动的娱乐性、趣味性和竞技性,同时也赋予了它诸如通过竞技形式来处理社会关系、整合社会资源等重要功能。在人的社会性存在中,趣斗一直作为一个基本的要素,“正是通过游戏,人类社会表达出它对生命和世界的阐释”[27],竞技由此生发。而竞技也有着多重的表达,它既可以是具体的、直接的行为项目的优劣比拼,也包含着隐喻村寨实力、建构社会关系,拓展婚姻圈等多重的社会诉求。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中的传统竞技之龙,大都体现出这种多重功能交织的文化现象。
例如,20 世纪50 年代以前,江西南昌县向塘镇涂村与邻村邓村为争夺两村接壤的湖而经常发生斗殴。涂村通过舞龙表演向邓村显示了涂村的人丁兴旺,村落内部的精诚团结。涂村舞龙不仅培育和再生产了涂村内外部良好的社会关系,同时,它也维持强化了竞争对抗的社会关系,由此,我们能通过冲突来理解社会秩序。两村都是以种植水稻为主,而水稻种植对水资源的依赖程度非常高。自古以来,涂村和村北面的邓村为了争夺两村接壤的两个湖而经常发生宗族斗殴,所以,这两个村落也就一直都是处于紧张的敌对关系中。自然,涂村不会去邓村表演舞龙,更不用说彼此之间有通婚关系。涂村舞龙期间,村民按照祖上的规矩去这两个湖边进行舞龙展演,既是向邓村表明涂村对这两个湖的所有权,也向邓村展示涂村的人丁兴旺和精诚团结,这又无形之中又强化了两村的紧张和敌对的关系。[28]如果说“要占有事物,所以会产生所有权制,其间的真正动机是竞赛,”[29]那么涂村这种通过舞龙活动来处理社会关系和彰显地域所属权无疑是舞龙竞技性的突出体现。
明弘治修《贵州图经新志·镇远府志·风俗》载:“是日男妇极其粉饰,女人富者盛装锦衣、项圈、大耳环,……即由订婚,甚至有当时背去者。”表面看来满足了个人对美感的追求,增加对男青年的吸引力扩展婚姻圈来壮大家族。细想一下,在这样一个各女子争奇斗艳的竞争场面,通过衣饰着装来展现本族财力,依靠财富博取敬意和家族荣誉也不失为这种场面出现的原因之一。
《苗疆闻见录》中有记载:“(苗族)好斗龙舟,岁以五月二十日为端节,竞渡于清江宽深之处……”[30]每年的农历五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清水江流域的30多个苗族村寨便会举行盛大隆重的龙舟竞渡。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龙舟比赛不一样,他们比的不是速度不是名次,而是通过龙舟活动比拼本族的社会关系。在清水江独木龙舟竞渡期间,两岸数万同族讨论最多的不是谁家的船速度快,哪个村子的船是最先到达的,而是哪条龙舟的龙头雕得好看,哪条龙舟上的鼓头(施洞苗族称“该略”,即龙舟头、船首、鼓主)收的礼物最多,谁收的礼物多谁就有面子,面子大的人在地方上才有威望。鼓头和寨老是龙舟活动的实际组织者。不论当年谁当上鼓头都必须全力以赴,不能懈怠,调动人脉关系,通知自家四面八方的亲友船到的时间,提前准备好礼物,给自己“崩面子”。预期达到的效果是活动那天鼓头带领团队划船一靠岸,亲朋好友便提前到来等候“接龙”(送礼)。以龙舟竞速比赛来说,龙舟上收到的礼越多肯定会加重船身不利于竞速取胜,但是他们依然乐此不疲地到处靠岸“收礼”,这也恰恰说明,各条龙船的鼓头不是为了竞速,而是比实力、资源和社会关系,这些人脉资源和社会关系是他们立足的主要依托。[23]这种竞技的代价无疑巨大的,作为社会交往的回赠,鼓头一定会有同样或更多的礼要送出去,但是鼓头身份所带来的荣誉感会在依靠社会关系立足的社会给氏族带来最终的受益,这也是对马塞尔·莫斯提出的“竞技式的总体呈现”的一种解读。[31]
现代体育发展之初只是英国作为贵族的业余娱乐消遣项目,在他们看来,体育运动不仅能健体强身、突破自我的个人素质,还具有等级维护、人际交往等方面的社会关系功能。传统舞龙活动一直被视为特定的地域的民族文化传播,作为多民族共同构建、融合的产物,其影响力非常有限。如果我们认可“全新的或是虽然陈旧但也已发生显著转变的社会团体、环境和社会背景呼唤新的发明,以确保或是表达社会凝聚力和认同,并建构社会关系”[32]这种说法的话,那么全球商业化的社会背景,必然赋予舞龙这种传统文化新的融合要素。
19 世纪中后期,作为现代竞技体育的主要推动者,英国公学融合了许多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制定了诸如足球、网球、赛马等体育活动的竞赛规则。当下,中国大部分地方的舞龙比赛,尤其是官方举办的赛事,多是以这种现代竞技比赛的规则为标准。以英国公学为代表的现代竞技体育之初是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与的,资本运营的商业市场开拓了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商业化是资本控制的体现,资本的运行成为社会普遍原则,利益成为了最终追求目标。正是这种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才促成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大规模资本渗入,对奥运会商业价值的开发给投资方带来的丰厚收益,正式开启了各种项目职业运动员允许参加奥运会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资本运作中,传统体育活动的规则也在不断改变,传统文化也在不同时代的政治、历史、经济变迁中,与其他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中相互交融。美国职业篮球的全球选秀让我们感受到资本力量强大的同时,更是实现了让全人类最优秀的篮球技能得以为全世界共享。
既然“文化不是单一的、统一的或自成一体的”[33],那么它就需要被更广泛的群体认可,甚至为全人类所共享。如果我们在静态的点上来看,商业原则的浸入或许会让人感到不安,但是文化变迁机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永远存在,我们可以把文化比喻成一条流变的河,它总要不断地吸收新的元素,而新的文化因子会不断进入而后慢慢消融。在舞龙这些传统文化积极改变的时候,我们会更平和、更欣然地去接受这些改变,突破传统文化的地方性、民族性等局限思维,我们认识到文化应是作为多元构建的共同财富为全人类共享。
我们对舞龙活动从祭祀、表演与竞技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是为了更好地呈现舞龙所蕴含的多重文化意义。应该指出,在现实中尤其在当下,这三者并非截然分离,而是相互交错,甚至是融为一体的。上述分析把我们引向人类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在对文化的诸多差异性理解中,对文化的根本性特点的认识至关重要,文化到底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还是一个不断缓慢流变的过程?囿于前者的窠臼,会误导人们把某一文化事项归属于某一具体民族;而在后者的基点上,我们就会清晰地看到,不同的文化事项在历史的长河中,会有沉淀、会有添加、也会有自然而然的遗弃。如以服装为例,汉服早在唐宋就已大变,而当下流行的旗袍实际是满族人的贡献。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的流变与融合,都是在多民族的社会交往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