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国的理想*
——从新发现佚文重探早期李叔同的图画观
陈晶晶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李叔同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系统地掌握了欧洲近代文艺的真精神:源自罗斯金的自然主义美术观,源自马修·阿诺德的现代文学批评立场,源自佩特和西蒙斯各自的文艺复兴研究的人文主义立场。日本学者坂元弘子认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毋宁说呈现出一种追随李叔同的情形”[1]210。早期李叔同与新文化运动的紧密关系已经为学界所留意,尽管李叔同在新文化运动开展后的第二年(1918年)即剃度出家。研究界认为,李叔同(弘一法师)早年留学日本,在西方美术、现代音乐、欧式话剧等多个领域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人”[2]62,是近代中国美术的先驱。王鹏杰将李叔同视为“晚清最后十年的画坛”的代表,认为他“几乎是最早将西方近代绘画原理和西画技巧系统搬到中国课堂上的人”。[3]13也有研究者对早年李叔同(别名李岸)留学日本学习西洋画的经历关注甚多。[4]86可以说,早期李叔同身体力行地从现代文艺的根基上把握住日本明治时期的美术现代性——李叔同在留日时期系统学习了西洋画法,并留下一些颇具分量的画论文章,为近代中国知识界引入了日本明治时期的“图画”观念。
据笔者新发现的李叔同早期的两篇画论佚文——《图画概论》(署名LK生,刊于《学报》1907年第1卷第1期)和《西洋画科》(署名LK生,连载于《学报》1907年第1卷第2至4期)——可论定,李叔同虽并非最早引入图画概念的近代知识分子,但他的佚稿《图画概论》(1907年)是汉语出版物中首次介绍三原色(赤黄青)、四间色(绿黄紫绀),并引申出西洋画调色、配色原理的画论文章。这些文章冲破传统国画的审美秩序,完整建构起现代图画的画法秩序,并将现代图画观在日本明治时期的兴起溯源到万国博览会所带来的美术竞争的背景。在这一宏阔的图画学视野中,李叔同于1890年代(日本明治二十年代)将“风景的发现”这一绘画命题引入了近代中国,由此彰显其对近代中国“图画”自觉的先驱意义。
一、佚文的判定:从《图画修得法》到《图画概论》《西洋画科》
学界一般认为,1905年李叔同25岁时赴日留学,当年所发表的《图画修得法》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对‘图画’的定义”[5]98。不过,在李叔同赴日的前一年(1904年),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所刊佚名《图画教授法》已翻译引入了现代“图画”概念,文章将图画分为“用器图”和“自在画”两大类,明显受到了日本明治时期美术思潮的影响。[6]佚名《图画教授法》(1904)可能是第一次对现代“图画”概念的定义,它与次年李叔同的《图画修得法》在内容上也有大致相近之处。这两篇将“图画”概念引入汉语知识界的早期文献初步说明,近代中国“图画”概念的自觉与明治时期的日本渊源匪浅。
“图画”概念在近代中国的自觉,与其所隶属的“美术”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一样,都经由明治时期的日本这一中介。早期李叔同作为倡导图画教育的先驱,可以代表近代“图画”自觉的关键一路。李叔同虽然不是近代最早从日本译介现代图画概念者,但其在系统学习西洋画法、引入图画概念、主张裸体画训练、表演新剧、引入现代音乐等多个方面都是身体力行的先驱者。早年作为“才子”的李叔同,其图画方面的修养不仅有绘画作品(包括水彩画、油画、炭笔画、漫画等),而且留下了诸多文章,诸如《图画修得法》(1905)、《水彩画法说略》(1905)、《石膏模型用法》(1905)、《艺术谈》(1910—1911)、《释美术(来函)》(1911)、《西洋画法》(1912)、《西洋画特别教授法》(1913)等,以上文章都已经收入《弘一大师全集(修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判断1907年两篇文章《图画概论》(署名LK生,刊于《学报》1907年第1卷第1期)和《西洋画科》(署名LK生,连载于《学报》1907年第1卷第2至4期)属于李叔同佚文的依据,主要是它们的行文与此前文章(《图画概论》与此前的《图画修得法》,《西洋画科》与此前的《水彩画法说略》)高度重合并呈现演进关系,且未见《弘一大师全集(修订本)》收录。刊载佚文的《学报》印刷厂在东京,同时期在东京美术学校进修的李叔同在《学报》创刊号上刊发美术文章是很有可能的。结合其同时期画作(1905年的《沼津风景》、1906年的《少女像》)上有“A.Li.”的字母署名习惯推断,“LK生”是笔者新发现的一个李叔同早年笔名。(李叔同早年曾使用李广平之名翻译公法著作,K可能代表广字。)从佚文内容上看,第一,《图画概论》(1907年)复述了《图画修得法》(1905年)对图画之效力的“实质上”“形式上”的二分法,对图画之种类也都采用了“用器图”“自在画”的二分法,行文方式也多延续旧文;此前《图画修得法》仅论及精神法、位置法、轮廓法三种,《图画概论》又增补至七种,并增加了“图画之用具及适用法”一节以及三原色四间色的配色说明。第二,《西洋画科》(1907年)是对此前《水彩画法说略》(1905年)的扩写,两篇内容都主要是谈水彩画;《西洋画科》的大部分内容后来又被重组到更完备的《西洋画法》(1912年)之中。《水彩画法说略》仅初略介绍了水彩画所用的材料四种(颜料盒、笔、纸、画板)以及临本十种(推荐了英国伦敦出版的水彩画帖);佚文《西洋画科》对画具的介绍更加完备,尤其侧重户外写生所用的画具,除了模写之外还介绍了写生的方法,并不厌其详地讨论天空、植物、动物、景物等诸多物态的写生经验。这说明1907年的李叔同相比两年前已经积累了更多写生经验,更加强调脱离临本的户外写生。笔者根据文章写作背景、文章互文内证多方面审视后认为,1907年《学报》所刊《图画概论》《西洋画科》二文是李叔同佚文。这些文献将丰富对早期李叔同以及近代中国图画自觉的认知。
如《图画概论》一文认为图画作为一种表达人类思想与感情的符号,能传达语言文字之外的“使人一望了然”的内容。图画的效力分为实质和形式两种。第一,在实质上的效力上,分普通与专门两类:在普通之技能上,可以“代语言文字而发表完全的思想感情之记录机关”;在专门的技能上,“于美术工艺上最要的基础,成一种独立的美术品”。第二,在形式上的效力上,分智识和德性两类:智识上可以“养成确实的知识、着实的想像、精密的注意、强健的记忆、健全的判断、敏捷的视察力、高尚的审美心”;德性上可以“养成高尚的嗜好、优美的人格,矫正一般卑恶陋劣的欲望,以成高洁之风气”。李叔同对图画作为符号之一种的表述,其实沿袭了日本教科书的惯常说法,这一说法早在1904年佚名的《图画教授法》(见王国维主编《教育世界》)中就已经引入汉语知识界。
《图画概论》收尾于对“画法上之顺序”的讨论,这也是李叔同重视形而下的图画教育的焦点:第一,精神法;第二,位置法;第三,轮廓法;第四,骨格(骼)法;第五,远近法;第六,运笔法;第七,浓淡法;第八,彩色法。转化为今天的术语则是:第一,先在精神上把握对象的审美感受;第二,在平面上布局画面关系、比例、位置;第三,用某种几何形相来勾勒轮廓;第四,确定这个几何形象的骨格(比如圆形的直径,植物的枝干);第五,除了轮廓法和骨格法,还需要远近法;第六,运笔法是对轮廓法的具体描述;第七,浓淡法,又分平涂法和渲晕法两种;第八,彩色法,考虑三原色、四间色的搭配运用。因此,这篇佚文也是汉语知识界较早讨论三原色、四间色光学原理在绘画中应用的画论。
二、美术的功用:李叔同图画观的万国博览会起源
李叔同刊于1907年《学报》发表的《图画修得法》《图画概论》这两篇佚文,将图画教育在日本的兴起溯源到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万国博览会——这是一个以往研究近代中国美术史所缺失的视角。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今称世博会),提供了国家实力的展示和竞争的新平台。其后,日本参加了1867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1873年的维也纳万国博览会,这些工艺品参展活动也为日本带来了一个新概念——“美术”,此词是日本明治初期参与万国博览会过程中从德语schöne Kunst翻译而来的。[7]298为配合万国博览会的参展,日本在国内还多次举办内国博览会。万国博览会和内国博览会作为现代国家组织本国美术工艺及工商产品的展览平台,在20世纪初引起晚清舆论界的较多关注。晚清舆论界在介绍万国博览会时,侧重指出本国工商业的落伍和世界各国的工商业实力。虽然也有《清议报》《教育世界》等报纸提及万国博览会中工艺美术方面的意义,但万国博览会在20世纪之初维新改良的舆论中,并没有被深入到一种新的认知方法或教育方式层面来理解。
1908年,《政艺通报》刊《留学日本高等商业学校学生谈茘生等上农工商部书》,介绍了博览会这一现代制度对于提振国家工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留学生们督促清政府慎选产品赴万国博览会,并组织内国博览会作为走出国门的预备。文章介绍说:“博览会之设,始于西历千七百九十八年,……究其宗旨,要以资观摩、图进取,培养国家富厚之基。然内国博览会为外国赛会之豫备,尤为亟图。日本以三岛之国,自明治维新以来,其开内国博览会者,前后已数次。”[8]这篇由留日学生所写的文章,颇能代表当时国内舆论对博览会制度的一般理解,他们侧重博览会这一现代体制对工商实业的直接效用,而对博览会提振美术的间接效用缺乏关注。
由于缺乏与博览会相匹配的现代美术观,国人并没有将万国博览会作为一种新兴起的认知秩序来对待。而此前1900年法国巴黎举办万国博览会时,《清议报》的报道反而对美术工艺方面有所留意——所刊《地球大事记:万国博览会开会演说》(1900年)提及,法国开万国博览会不仅能增加国民智识、推动“研究理学”(即科学技术),“使美术工艺,日有进步”,还符合20世纪世界之和平与公利,故而,工艺家、美术家在博览会中具有尊崇地位,万国博览会成为西方世界期许文明进步的平台:“以新奇知识、高尚学问,开导众人、启迪来者,一洗人类之逆境。”[9]相比于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首次列出教育类展区,1904年美国圣路易万国博览会更赋予了美术教育以较高的地位。对此,《教育世界》特别留意到,“此次博览会中,尤放特别之异彩者,美术之陈列品也”。[10]
维新改良语境中的近代中国舆论界,还重视日本人对西洋博览会的看法。日本博览会会长金子坚太郎《万国博览会之效果》一文(杨志洵翻译)指出,万国博览会具有提振美术、美化建筑的效用:“自博览会豫派专门之人赴先开之巴黎博览会,考究其建筑及装饰之法,归而应用之。美国国民之美术观念,因而大启,由是各地方竞相仿效。凡一切私家之住宅,公共之建造,无不机轴一新。现华盛顿之国会图书馆、卜斯登之图书馆,其式皆仿诸博览会者也。”[11]留日学生李叔同所处的明治晚期的日本社会,已经认识到万国博览会之于美术的重要意义。
由于重视美术的功用,李叔同对万博会的认知超出了洋务派和维新派的视野。1905年,李叔同《图画修得法》认为,万国博览会的举办将有力推动国民的图画教育,从而使国家进化为美术国。这为晚清“美术”概念的建构提供了一条十分新颖的思路:图画、美术之于国家、国民的意义,已经体现于近代英美法日等国通过举办万国博览会而上升为“世界一大美术国”的历史经验之中。1907年的佚文《图画概论》,重述万国博览会的举办作为近代国家重视美术的直接的社会推力这一观点,并且强调图画教育、奖励美术,乃是进化为“世界一大美术国”的关键,日本奖励美术、尊重图画的举措值得清政府效仿:
然征诸泰西各国,于教育上尊重图画,亦不过始于挽近来之二三十年间,然其动机则实发轫于英国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开设万国大博览会之时。盖此时博览会之出品,以英国之工艺品,成绩为最劣。夫英国固以商工两业立国,则此问题,固其死活之所歧也。于是不得不竭力调查、锐意改革,知所制品,墨守古风,不能立足于世界竞争之列,乃大奖励美术,置图画科为国民教育之必修科。果不数年,而英国工艺品之外观大非昔比,仍于竞争场中,复占优胜之地位。法国亦然,自万国大博览会以来,其苦心经营,费几许时间、几许财币,以谋图画之发达,殆非吾人所能憶度。然但就其关系于学校教育上言之,彼大美术家ユーゼエスギョーム氏,此时于图画教育,热心鼓吹,终得推为美术局长,又同时文部省下令,专置一图画教育视学官,以奖励美术。其于一方面也已如此,则其他方面可知。今也其美术品之进步,日异月新,几成为世界一大美术国。其结果固何如耶。此我国今日欲改良教育,不可不亟亟于留意于图画一道也。[12]
李叔同通过《图画修得法》(1905年)、《图画概论》(1907年)两篇文章,为晚清知识界的“图画”概念建构引入了世界博览会的起源这一因素。由此,19、20世纪之交“万国竞争”的时代语境,在万国博览会这一载体中呈现为美术品、工艺品的文明竞争,乃至图画教育、美术教育的国民竞争。这一视野直接受到日本明治时期奖励美术的社会氛围的影响。因此,相比于国内知识界介绍“美术”概念侧重形而上观念,认为“万国博览会”侧重工商经济的形而下层面,李叔同对“美术”和“万国博览会”可以改良国民教育的认知是别具一格的。李叔同的“图画”观注重实际应用,不循规蹈矩,但其用心又直指“改良教育”,并期待中国也能进化为像日本一样的“世界一大美术国”。可以说,留日时期的李叔同对“图画”教育的重视,映射了一种崭新的现代性秩序——这一以“图画”为中心的认知秩序,将会对本国旧有绘画秩序造成冲击,甚至后来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美术”自觉意识,也并没有超出李叔同早年在图画中寄托的文明抱负。
三、风景的发现:《沼津风景》画中的写实意识
李叔同于1905年8月赴日留学,在东京一边学习日语,一边准备东京美术学校的入学考试,他还与留学生朋友商议创办美术杂志,但计划最终失败。赴日四个月(1905年12月)后,他将与美术相关的稿件投至留学生杂志《醒狮》上,杂志连载刊出《图画修得法》《水彩画法说略》二文。翌年7月,李叔同考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9月入学接受专业学习,受到以西洋画闻名的黑田清辉的影响(黑田清辉作为日本西洋画之父,在1896年从法国带回日本早期印象派的画风)。该年,他还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音乐类专业杂志《音乐小杂志》,不过仅出了创刊号一期便告失败。1907年,他还在音乐学校学习西洋音乐,参与春柳社新剧公演活动。佚文《图画概论》《西洋画科》就写于这一文艺活动活跃的时期。1911年3月,李叔同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为母校留下了一幅油画自画像。
1905年冬,李叔同在日本沼津写生,画了一张写实风格的明信片水彩画《沼津风景》(图1)(今藏于天津李叔同纪念馆)。因此,李叔同也成为近代中国水彩写生画的先驱者。画面分成黄绿色的稻田近景、黑色松柏构成的中景(中间有一线白色,乃是海景)、淡蓝色构成的远山和云雾的远景。画作整体上朦胧、透亮,呈现雨后海边稻田将熟、雾霭未散的自然风景。在明信片背面,有李叔同拿浅绿色颜料题写的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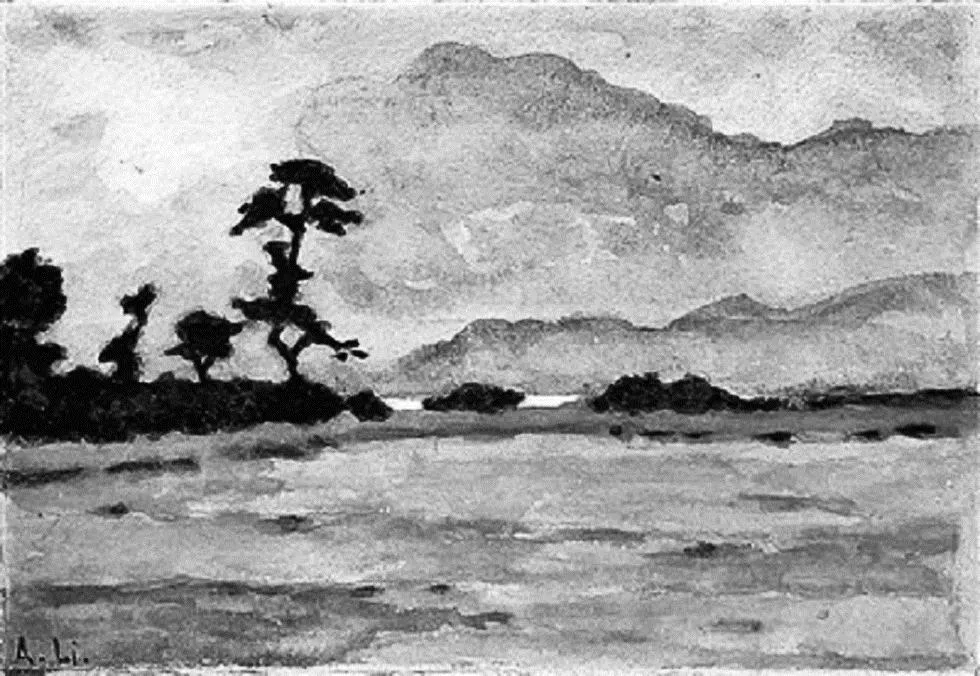
图1 李叔同《沼津风景》,明信片,1905年
沼津,日本东海道之名胜地。郊外多松柏,因名其地曰“千本松原”,有山耸于前,曰爱鹰。山冈中黄绿色为稻田之将熟者,田与山之间有白光一线,即海之一部分也。乙巳年十一月,用西洋水彩画法写生,奉月亭老哥大画伯一笑。弟哀,时客日本。[13]111
1912年4月《西洋画法》连载于上海《太平洋报》副刊《太平洋文艺》上。李叔同认为:“西洋画纯属于技术,非实地练习不可。是编所载之画法,虽属理论,亦大半自实地练习得来。故研究西洋画者,当以实地练习为主。”[14]19这也是李叔同对自己七年前在日本沼津实地水彩写生的经验之谈。在这篇画法中,他谈及“风景画”的地方,与其画作《沼津风景》的经验呼应颇多。他说:“学画风景画,宜择其简单者,地平线不宜高,因画前景最不易。初学者画阴天较易。初学者不可回家修补,因此最易染恶习,且有背自然之研究。”[14]3
确实,《沼津风景》的画幅中,地平线不高,前景是稻田,远景是山峦,阴天,且注重对自然的准确把握,不事后期修补。这种注重室外水彩写生而非室内临摹的观点,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美术家罗斯金那里,表现为一种由绘画作品带来的“真实的意识”:“模仿只能来自于某个实物,而真实则既与实物的品质相关,又与情感、印象以及思维相联系。真实既有精神上的,也有物质上的;既有印象上的,也有形式上的;既有抽象上的,也有实体上的。”[15]17这种绘画的“真实的意识”并非如同照相一样刻板地复制现实物,因此李叔同采用黑色来捕捉沼津松柏的真实感。在《图画修得法》和《图画概论》中,李叔同将画家对物体的主观把握视为画法的第一步——“精神法”。杨冰将李叔同“精神法”之论所取材的日本小学图画教育法教材《普通教育之图画教授法》(1903年)翻译了出来:“取一幅画仔细端详之,此时观者必会兴发出一种灵感,灵感即画之精神。或起极谨严之感,或生极崇高之感,或熏染蔼然之和气,或被壮烈之和气所动,有滑稽者,亦有清洒者,诸般皆为画者精神之出现,而画者精神即是描绘物体之心。描绘物体之心即是物体之性质、常习及活动。”[5]99这种绘画的写实观与李叔同对19世纪中期以降欧洲文学史的认知相互呼应。李叔同在《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1913年)中概述了其近代文学史观,从古典派到浪漫派(他表述为“传奇派”),再到19世纪后半期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最近的文艺思潮则是新理想派对写实的反动。[16]
根据《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展现的宏阔史观来看,李叔同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系统掌握了欧洲近代文艺的真精神——从约翰·罗斯金、马修·阿诺德到沃尔特·佩特、西蒙斯。这些经由日本习得的源自欧洲(主要是英国)的近代文艺思想,构成了李叔同早年的审美意识。李叔同十分认可罗斯金所倡导的自然主义美术观以及阿诺德《批评论集》所倡导的现代批评观。阿诺德的现代批评观是富有整体性人文诉求的。他指出:“一位现代诗人的艺术创作背后往往隐含着一种强烈的批评冲动,否则,其创作一定是内容贫乏、空洞且短命的。”[17]16李叔同认为阿诺德“思想雄大高峻,且富于雅趣”,与美术评论家罗斯金同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批评坛之代表”。[16]这种批评观综合了自然主义的美术鉴赏和文学批评的独立鉴赏眼光,显示出李叔同对19世纪中叶至后期美术和文学演进中的同步性认知。
《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除了提及19世纪中叶的英国美术评论家罗斯金及其代表作《近世画家论》、阿诺德及其代表作《批评论集》,还涉及文艺复兴研究学者佩特(代表作为《文艺复兴史之研究》)和西蒙斯(代表作为《伊大利文艺复兴论》)。这其实都游离于“文学之概观”这一文题之外,这种游离反而说明李叔同对自然主义审美意识、独立的文学批评意识、文艺复兴文化等文艺领域的丰富认知。这种认知的统一性可以用早期李叔同所引的英国思想家斯宾塞的话来表述:“文学美术者,文明之花。”[18]
西洋风景画的兴起,同步伴随着西方文学写实主义的兴起。这一文化现象较早地被保罗·瓦莱里看到。他说:“所谓描写对文学的侵犯,与风景画对于绘画的侵犯几乎是同时进行的,采取同一方向,产生同样结果的。”[19]20后来,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明治二十年代(1887—1896年)的日本文艺中发现了同样的运行逻辑,于是将其命名为“风景的发现”——他认为,风景的发现和写实的兴起,背后都是“符号论式的认识装置的颠倒”。[19]21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东方思维中,由于超越论式的外在秩序统治了我们观察外物和描绘自然的思维,所以在“内面”的现代自我尚未出现时,并不存在以这一现代意识为认知前提的“风景”。“风景”和“写实”的现代审美观,不可能在信奉超越论或天理观的个体视野中出现,而只能出现在具有现代审美意识的主体眼中。
1905年李叔同的水彩画受日本明治时期美术风尚的影响,另外他的水彩画也与传统画法相近。1905年《水彩画法说略》一文提及:“西洋画凡十数种,与吾国旧画法稍近者,唯水彩画。”[20]此时的李叔同在介绍水彩画法时,推荐国人使用临本而非直接写生,在画法介绍上也侧重对轮廓法的把握,也就是用几何形状来描绘物体。同年还有《石膏模型用法》一文,强调的也是轮廓法:“实物写生,取日常所用简单之器具为范本,固属有益。但初学者联系画线,以单纯之直线曲线之物体为宜。又练习阴影,以纯白之物体为宜。石膏模型,仿实物之形状,以美妙之直线与曲线构成,其色纯白,阴影处无色彩错乱之虞。阴影浓淡之程度,容易判别。故学图画者,当确信石膏模型为实物写生第一完全之范本。”[21]在两年后所写的佚文《图画概论》《西洋画科》中,李叔同的图画论述已经侧重写生,不再强调临本或石膏模型了。《图画概论》强调色彩的搭配,强调“专注眼于用色之巧拙”。[22]《西洋画科》也侧重户外实景写生:“虽然万事皆从联系得来,且实境实物之写生,万事万物皆在目前,则着色较有所凭,藉非若记忆画万事万物皆属相像也。兹将各写生家历来所经验者,分列于后,以便知所从事焉。”[22]这个微小的转变暗示着,李叔同面对外部“风景”的现代画家主体意识终于树立起来了。
留日学生李叔同在向国人介绍西洋水彩画法时,直面东方超越论和天理人文观的绘画秩序与现代水彩画秩序的冲突。这一秩序冲突具体到《水彩画法说略》(1905年)一文,则是中国人学习现代水彩画先临摹还是先写生的矛盾。[20]若按欧美教授法应先由写生入手,但由于中国传统绘画秩序影响根深蒂固,中国人面对水彩画时首先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画法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审美和认知秩序的置换问题。而临摹西洋画本,首先要直面由色彩、结构、调子等水彩画元素带来的直接冲击,从而培养现代审美意识的主体。此后,李叔同对户外写生和室内实景写生的图画教育方式愈加重视,才逐渐取代赴日初期对临本的关注。
四、图画的兴起:《图画概论》对绘画秩序的重构
李叔同在沼津水彩写生时,其绘画秩序受到了透视法则的支配。1907年,李叔同为《图画概论》(图2)文前配图做了远近法的解读,这是近代中国人对图画透视法的较早描述:

图2 李叔同《图画概论·远近法之一例》,载于《学报》1907年第1卷第1期
吾人于乘汽车之时试在最后之列车窗中以观延长之路线,及路旁挺立之电柱,由最近处,以及最远处,一带之景色,几无远近,恍若聚于一处焉。及路线终时,则电柱自电柱,而天空自天空,地面自地面,逈不相侔也。此远近法之通例固如是也。[12]
远近法(透视法)乃是一种现代经验。传统文人画、山水画并不呈现透视秩序,而透视法则是一种可以在列车上体验到的真实的远近感受。现代生活经验和传统绘画秩序之间存在冲突,这一冲突引导我们接纳写实的现代“图画”概念。1904年,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刊发佚名《图画教授法》,其中将图画概念分“用器图”和“自在画”两种,图画具有美育功能,这种理解不同于当时社会侧重的洋务制图的实用理解。[6]根据《图画教授法》中提及英国女学者休杜对日本画的考察这一案例,我们可以推断这篇《图画教授法》的出处,很可能是1903年东京三省堂出版的柿上蕃雄与松田茂合著的《普通教育における圖畫教授法》(《普通教育之图画教授法》)。此类日文图画教授法著作,早在1904年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中就得到了译介(译稿名《图画教授法》,也基本对应日文著题),1905年李叔同赴日时根据柿上蕃雄与松田茂合著版将之译介、改编为《图画修得法》并刊于留学生刊物《醒狮》上,1907年李叔同重写了此稿并增加了大量文字,文章名为《图画概论》。
这三篇近代中国早期画论(佚名的《图画教授法》、李叔同的《图画修得法》《图画概论》),都源自日本明治时期的美术思潮,而且开篇都谈及图画是一种不同于语言的符号。佚名《图画教授法》指出,图画与时间性的言语文章或音乐不同,它是空间性的,它是无声的言语、万国之通邮。图画具有美育的效用:“吾人取径于图画,以研究自然、知其理法,则情操高洁,得以美的、伦理的、论理的而保持之,至心灵之修养完全无缺,则我心与自然界融化为一。”[6]李叔同《图画修得法》开篇也认同图画的符号效用,并覆盖以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意图。他写道:“顾秩序杂沓,教授鲜良法,浅学之士,靡自窥测;又其涉想所及,狃于故常,匪所加意,言之可为于邑。”[23]他一方面谈及本国图画术发源于黄帝,具有辉煌的历史,另一方面痛心于近代图画秩序混乱、拘泥旧俗。
李叔同对“秩序杂沓”“狃于故常”图画的改良办法是,为国民教育引入日本的图画秩序。李叔同认为图画秩序乃是对文字秩序的辅助,因此其论证起点与同时期的刘师培、严复等人相距不远,比如李叔同认为图画乃是可以弥补语言文字缺憾的一种辅助符号,此论点在刘师培那里表述为“盖以图画辅文字之穷”[24]4904。但对于重视写生、写实的理解,二人则存在论证思路的分歧:李叔同重视的是西洋画的审美秩序以及训练方法的引入,图画与文字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图画之进步是推动国家成为美术国的关键,文字效用在近代反而不及图画;而刘师培则通过小学家对字画同源于征实精神的理解,从源头的统一性来论证图画征实的必要性,因而近代图画循规蹈矩的临摹之弊可以通过古代图画的征实精神来克服:“是以古人之画,与儒术相辅,所绘之图,咸视其肖物与否,以定工拙;后世之画,列美术之中,所绘之图,咸视其运笔若何,以定工拙。”[24]4907-4908刘师培对图画征实的诉求,乃是导向恢复国粹主义,将本国文明的古今之争作为批判近代图画的立足点;而李叔同对图画写实的诉求乃是导向文明进化论,通过图画教育参与美术竞争,实现“世界大美术国”的文明理想。
刘师培基于字学的图画理解,也符合李叔同所坚信的中国画的书法性特征。在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前后,李叔同写了短文《中西画法之比较》。他认为:“西人之画,以照像片为蓝本,专求形似。中国画以作字为先河,但取神似,而兼言笔法。尝见宋画真迹,无不精妙绝伦。”[25]由于中国画创作需要书法基础,因此日本人作中国画成家难度很大;反过来说,有中国画基础而去探索西画,则有一些便利。同一篇文中,李叔同还提供了一个奇妙的论点:“中国画亦分远近。惟当其作画之点,必删除目前一段境界,专写远景耳;西画则不同,但将目之所见者,无论远近,一齐画出,聊代一幅风景照片而已。”[18]这大概是受到日本画与西洋画相互融合一派的影响:“大抵日本画则以线为要点,而西洋画则以浓淡之彩色为要点。自近日日本,极力欲将两派画融合之,由是舍此所短,采彼所长,于西洋画亦多用强线,将两派画风,打成一团,是则于画界上,别开一新面目者也。”[12]在谈及刺绣时,他又批判国人“不知普通光学,于是阴阳反侧,光线不能辨别,无论圆柱、椭圆、浑圆等物,往往无向背明晦之差,阴阳浅深之别”[25]。李叔同的中西画法比较始终在画法层面,并不执着于本体层面的对立,而侧重画法的专业化。有学者从本土绘画观的写生观演变出发认为:“由于明清之际理学的逆转,传统山水画取舍景象的观想之法流变为对景写生,而正是此时西洋绘画开始传入中国。西洋绘画基本把人与外物立为对象关系,一为认知主体,一为认知对象,而主体对对象的认知是通过经验来完成的,因此它便与中国直接对应对象的写生方式一拍即合,二者合流而成为我们今天‘写生’观念的由来。在这一个转变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传统山水画的蜕变与衰微,这背后实际上是宋明理学的天理世界的崩塌与主敬功夫的衰落。”[26]142而李叔同的图画观推动了传统美术秩序迈入以日本明治时期为范本的近代社会。
李叔同引入“图画”观的意图是纯正、专业而严肃的,不是娱乐、简陋的。留日学生李叔同身处文化民族主义的氛围,对于新名词和旧国粹采取一种折中的态度——既认可现代文艺,又不忘本国故典。其《呜呼!词章》刊于1906年2月《音乐小杂志》第1期,其中认为:“挽近西学输入,风靡一时,词章之名辞,几有消灭之势。不学之徒,习为薮冒,诋讥故典,废弃雅言。迨见日本唱歌,反啧啧称其理想之奇妙。”[27]在批判留学生不学故典之余,他又在《昨非录》一文中反思中国乐界的恶劣:“我国近出唱歌集,皆不注强弱缓急等记号。而教员复因陋就简,信口开合[河],致使原曲所有之精神趣味皆失。”[28]在李叔同看来,“吾国学琴者,大半皆娱乐的思想,无音乐的思想”。[27]李叔同这种对待艺术的严肃态度,背后的隐忧乃是日本明治时期已经建立了成熟的音乐、美术学科体制,而近代中国的学科教育体制还远未成形。明治二十年代是日本“现代国家的诸种制度初步确立起来的时期”[19]34,而李叔同深处明治晚期的东京,现代体制的进化压力使他侧重基础的图画、音乐修习方法。
相比于王国维同时期的形而上建构所侧重的美术无功利性,以及严复所译《美术通诠》在娱心的美术与应用的实艺之间的区分,李叔同针对的是国人娱乐的思想,揭示图画和音乐教育中严肃的、艺术的思想,目的是在国民艺术教育体制下实现学科化。因此,王国维侧重形而上的哲学,而李叔同侧重形而下的技法;严复侧重美术娱心的性质,而李叔同侧重艺术专业的精神。在绘画观念上,李叔同针对的是国人“薄视自然”“杜撰”的非严肃态度,强调“作画者首重视力,辨别宜精细,对于自然物宜确实观察,不可杜撰”,强调“西洋画为一种专门技术”的专业性。[14]20另外,李叔同强调裸体画的必要性,超出了当时国人的道德认知。[14]20由于坚持写生训练、观察自然,必然要反对因袭临摹的传统教育模式,李叔同注重在知觉的层面从头学起。
具体到其佚稿《图画概论》,李叔同完整构建起图画教育的秩序,从图画分类到图画用具、图画画法一应俱全。文章认为,图画的效用,既可以作为语言文字之外记录感情思想的辅助符号,又可以发挥专门美术品的效用;在形式上对个人而言还具有德性和智识两方面的效用。图画的分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器图,一种是自在画;后者在日本学科体制之中又分为西洋画科和日本画科两大类。图画之用具包括画笔(六种)、羽箒、砚、纸、笔洗、画碟、绘具(即颜料)、胶。文章最重要的部分在“画法上之顺序”一节,分为精神法、位置法、轮廓法、骨格法、远近法、运笔法、浓淡法、彩色法八步。这是对此前《图画修得法》一文的完善,后者在“自在画概说”中仅提及三种画法:第一,精神法即画家对物体性质、常习、动作的主观捕捉;第二,位置法处理画面内部位置关系,尤其是留白;第三,轮廓法即通过抽象为轮廓来描绘物体(轮廓法包括竿状体、正方体、球、方柱、方锥、圆柱、圆锥)。而《图画概说》在此基础上补充了:第四,骨格法抓住轮廓下构造物体之枢轴;第五,通过远近法勾勒画面的透视秩序;第六,通过运笔法来表现主辅、明暗、远近关系;第七,倚赖浓淡法显出物体之远近、浅深、阴影、凹凸;第八,通过三原色、四间色的配合来运用彩色法。从画家对物体的主观捕捉,到画家对位置、轮廓、骨格的把握,再到画面远近和浓淡的处理,最后收尾于色彩的搭配。在此,李叔同系统地抛开了以谢赫“六法”为代表的、注重笔墨气韵的传统水墨画法。
图画用色奠基于光学这一见解的最初表达,便是李叔同1907年佚文《图画概论》中对三原色、四间色的阐释。色彩,是光学和图画学的中介。与这一“色彩”观念相关的,乃是西洋画通过颜色深浅、透视远近、明暗凹凸来表现的审美秩序。图画自觉的背后,涉及现代诸学科体制的建立。鲁迅1907年所作《科学史教篇》提及,美术和科学各有偏至,需要相互平衡来追求人性之全[29]35。而鲁迅个人更侧重的是《摩罗诗力说》所谓“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的方面。[30]73-74早期李叔同的图画观,并不具有这种“文化偏至论”的视角,毋宁说图画的兴起奠基于诸多现代知识,比如,绘画的写生训练与“自然之研究”是紧密相关的。他谈到:“各科学非图画不明,故教育家宜通图画。学图画尤当知其种种之方法。如画人体,当知其筋骨构造之理,则解剖学不可不研究。如画房屋与器具,当知其远近距离之理,则远近法不可不研究。又,图画与太阳有最切之关系,太阳光线有七色,图画之用色即从此七色而生,故光学不可不研究。此外又有美术史、风俗史、考古学等,亦宜知其大略。”[18]所以,李叔同的“写生”观、“图画”观,实际上与现代光学、“色彩”法则、透视法的支配,乃至也与解剖学、主客体论等紧密相关。早期李叔同图画观念的自觉,背后隐含他对国民教育建立起完整的现代学科体制的呼唤。而这个现代学科体制,正是基于20世纪之初留日学生在日本明治晚期已经观察到的现实经验。
五、余论
将《图画概论》与《西洋画科》两篇1907年佚文放回早期李叔同的图画论述之中,我们方能建构起李叔同图画观的整体构成,并揭示其中的文明抱负。首先,《图画概论》乃基于李叔同此前《图画修得法》一文改写而成,二文都追溯了东亚“图画/美术”教育兴起的万国博览会渊源,这意味着图画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作用于国家间的美术竞争,将推动国家上升为“美术国”。其次,李叔同的图画观背后隐藏了现代画家主体意识的形成,他对水彩写生训练的关注折射出“风景的发现”这一明治二十年代的绘画命题在近代中国的延续,他在1905年的美术文章中侧重的仍然是临本画和石膏画的训练,而1907年两篇佚文则已经侧重户外水彩写生的训练。最后,《图画概论》弥补了此前《图画修得法》(1905年)所缺失的色彩部分,提供了此前《水彩画法说略》(1905年)所暗含的对色彩原理的说明,并建构起一个系统的绘画自我秩序。这意味着李叔同的《图画概论》是汉语出版物中首次介绍三原色(赤黄青)、四间色(绿黄紫绀),以及由此出发的调色、配色原理的美术文章。由此,从赴日留学到剃度出家期间(1905—1918年)的早期李叔同图画观,蕴含近代中国图画自觉的关键信息。
可以说,李叔同在1905至1913年的画论文章以注重水彩写生的绘画创作,为近代中国“图画/美术”概念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新思路。这个思路侧重的是从认知秩序层面重构美术秩序,在实物写生中培养轮廓、骨格、调子、远近、色彩等审美眼光,图画教育既有形而下的技法训练,又有塑造具有现代审美人格的美育诉求。留日时期的鲁迅在《摩罗诗力说》(1907年)中接受了阿诺德的“诗为人生评骘”[30]73-74的观点;早期李叔同也接触过阿诺德,不过其服膺的方面侧重罗斯金“美的教育”的宗旨,通过图画教育(尤其是水彩画写生、油画色彩)提升国民的美术品格。相比于王国维,李叔同并不侧重形而上的美学观念,而注目于图画画法的基础训练。
正如“明治二十年代”的美育观念顺应于近代日本的现代国家体制建设一样,李叔同的图画观也具有晚清民族主义的色彩,其纯正的图画画法召唤的是现代美育体制乃至现代文明国家体制。“日本明治时期立足德国哲学,改造性地确立‘美’的三位一体结构,即美术的物质生产、美学的精神感召与美育的主体规训。”[32]56美术竞争作为国家竞争的一环的时代氛围,使得早期李叔同倡导文艺活动具有一种“明治—晚清”语境的错位感:一方面,其文艺活动具有日本明治时期朝向世界文明国家的色彩,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背负起尚未完成现代国家转型的晚清帝国的改良主义宿命。在他看来,通过国民图画教育确立现代学科体制,从而作用于文明国家之间的美术竞争,这是图画(或美术)的间接效用。现代国家之间“互以美术相争竞。美者胜,恶者败,胜败起伏,而文明以是进步”[33]19。早期李叔同推动近代中国图画的自觉,其背后是日本明治时期的美育体制以及欧美国家在万国博览会中美术竞争的世界潮流,这种外部压力使得“图画”概念所关注的“风景”和“写生”议题势必冲击本土图画传统,呼唤现代体制的移植。图画的自觉,也折射近代中国参与文明竞争的现代化诉求。
——《李叔同—弘一大师年谱长编》评介
——《李叔同——弘一大师影像》简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