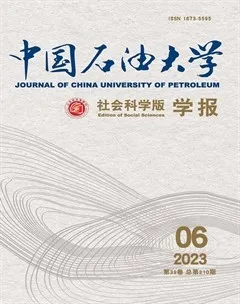翟理斯《聊斋志异》译本的中国形象建构
周若雯 周德波
摘要:翟理斯寓华20余年,一直致力于汉学研究和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的传播,其所译《聊斋志异》是英译本中的经典之作。翟理斯译本对《聊斋志异》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有着重要意义,为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通过研究分析他对原文的选取、译介语言的使用、注释的使用,能够看到翟理斯译本呈现出较为客观与真实的中国形象;但受其身份、所处时代和思想所限,其中仍不免带有译者主观的想象与对中国文化的曲解。
关键词:翟理斯;《聊斋志异》;译介语言;中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I2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3)06-0106-08
一、引言
法国学者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认为,“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这是从史学家们那里借用来的词)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représentation)”[1]121。这对于探知异质文化书写中国乃至域外译介中国文学文本里的中国形象成因,极具指导意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门被打开,中国逐渐被西方人所认识。然而,东西方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文化上的冲突,加之西方对东方固有的偏见,导致西方对中国逐渐形成了负面的刻板印象。西方人认为中国专制、落后,中国人愚昧、保守。翟理斯在华生活20多年,深入接触过中国社会和人民,阅读译介中国文学经典,在其著作和译作中突显了他对于中国的认知。这在他对《聊斋志异》的译介中表现得尤其充分。他从原版《聊斋志异》490余篇中精选164篇,对原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删增、改写和注释,其译作文本中展示出的中国形象既有社会集体想象物的特点,又有自我理性的把握,从而也使得这一译本具有考察的学理意义,绽放着别样光彩。
二、翟理斯译本中的中国形象
“就译者的主体性而言,塑造何种中国形象决定了译者对文本的选择,对翻译策略的制定甚至翻译的全过程;就翻译的形式而言,译本可以多种多样,以呈现立体多维的中国形象。”[2]1880年翟理斯译本《聊斋志异》在伦敦德纳罗公司(Thomas De la Rue)第一次出版,并在此后的一百年多年时间里多次再版,直到2014年宋贤德的全译本出版。翟译本一直是英译本中选篇最多的,其译本也是呈现中国形象的绝佳范例。
(一)中国人之性格
《聊斋志异》虽说记录的是狐仙鬼怪之事,但是这些传奇故事无一不是现实社会的反映,故事内容大多是以普通百姓的生活为基础,因而其中所塑造的人物能充分显示当时中国人的性格。
1.知恩图报的美德
翟理斯在《中国之文明》中提到,“中国人所拥有的美德是一种相当罕见的感恩美德。一个中国人,善举不忘,更重要的是,他对恩人从不会失去责任感”[3]213-235。他还特意提到了中国人对医生的感恩,《医术》讲的就是太守感谢其医生的小故事;展现普通人感恩之情的有《王六郎》,六郎作为淹死的水鬼受打鱼人洒酒祭奠的恩情,所以暗中送鱼报答他;《酒友》讲述的是酒友间的故事,表达了主人公对酒友的感激之情;有一些故事虽然以男女爱情为主,但中间也穿插着报恩的情节,如《鲁公女》和《西湖主》,两篇主题都是颂扬男女之间的美好爱情,但在其感情基础上加入了报恩的前提。这些平凡的普通人的报恩故事,都展现了中国人质朴善良的品格。
2.迷信的鬼魂复仇精神
“作为感恩美德的一种抵消,复仇精神推动所有的阶级,这是根深蒂固的。”[3]213-235翟理斯指出中国人无论男女都会选择以一种自杀变成鬼魂的方式去报复仇人。于是作翻译文本选择时他选取了一些类似鬼魂复仇的小故事,例如,《李司鉴》中的李司鉴打死了自己的妻子李氏,后被阴司诛杀;《三生》中兴考生投胎后将前世仇人斩首;《向杲》中主人公变成老虎咬掉了杀兄仇人的脑袋。这些复仇故事其实在蒲松龄那里更多展示的是当时社会的黑暗,揭露在家庭、科举考试、官场等地方的不合理现象,肉体凡胎难以实现正义的伸张,从而只能寄希望于鬼魂,如孔子所言“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中国人更多追求的是一种公平,一种社会正义,而非翟理斯所说的有仇必报,尤其是借助鬼魂复仇,更是塑造了中国人迷信的一种刻板形象。
3.对动物的喜爱
卡内蒂曾说:“以小动物为主角的故事在中国流传很广,特别多的是讲蟋蟀、蚂蚁、蜜蜂怎样把一个人接纳到他们当中,像人那样对待他的故事。”[4]西方人对中国人固有的印象中就有对动物的喜爱,而《聊斋志异》恰好又是一部精彩的关于各种动物的故事集。《放蝶》是一则警告人们不能虐待蝴蝶的小故事;抨击官僚制度腐败、朝廷横征暴敛的《促织》,译名为“The Fighting Cricket”,变相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斗蟋蟀的游戏;《义犬》讲的是人和一条忠诚小黑狗的故事,译为“The Faithful Dog”,重点在于忠诚的小狗;《王成》里的主人公王成是个懒惰的人,却通过斗鹌鹑不劳而获,翟理斯译为“The Fighting Quails”,也是更突出动物而非人。其实与卡内蒂一样,翟理斯认为中国人喜爱动物也是从西方视角对于东方审视的结果,然而《聊斋志异》故事中的动物只有少数是纯粹的对动物的赞美和喜爱,更多的则是对人类社会的反映,借由动物向不公世道发出强烈的呐喊。
(二)中国人之信仰
翟理斯曾专门出版过《中国古代宗教》(Religions of Ancient China)一书,他认为中国人虽然不是有信仰的民族,但是却非常迷信。由此翟理斯译本《聊斋志异》中选取了诸多有关佛道和民间信仰的故事,且这些故事在译本中占比很大,有些也并非名篇,译者在翻译时带有一定向西方读者传递中国人信仰的目的。
1.对道教的认识
翟理斯翻译了诸多有关道教的篇章,如《道士》《济南道人》《崂山道士》《单道士》《颠道人》等。他在《中国之文明》中介绍了道教研究如何增加人的寿命以及具体的办法;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中也介绍,中国“重视长寿,以及相信死是一种绝对的罪恶。因为照理说来,一个真正完美的人應该是可以避开死亡的”[5]266。可见,在西方人固有的印象中道教和增寿延年是无法分开的。《成仙》中的周生与成生对人间失望,后相继醒悟并成仙,翟理斯这里将“仙”译为“immortal”,是指长生不朽的人,其含义正好对应了西方人观念里追求长生不老的中国道士。而许多选篇中的道士扶弱济贫、行侠仗义,展现了中国人美好的品德,如《钟生》和《画皮》。翟理斯认为,中国人是受儒道释三家共同影响的,但是儒家更多的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规范,而佛教又是由外部传入中国的,只有道教是衍生于本土又是真正的宗教,所以对道教介绍较多。这种对道教的重视其实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即使儒教不被认为是宗教,却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从宗教的角度来说佛教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总体影响要大过道教。
2.受歧视的僧人
在古代中国,很多情况下佛道是相互影响的,翟理斯《聊斋志异》选篇中涉及佛教或僧人的篇幅也不在少数,如《长青僧》《僧孽》《西僧》《番僧》等,其中的僧人形象可大致分为两类。正面的僧人形象,例如,《长青僧》中的老和尚,在死后魂魄飘到官宦人家的儿子身上,虽然只有30多岁,行为举止俨然一个80多岁的得道高僧;《续黄粱》中的老和尚也是如此,文中对他着墨不多,但是展现了一个世外高人形象,相比主角曾举人,两者形成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强烈对比;同样《画壁》中的朱举人也是靠老和尚点醒才走出的幻境。但在翟理斯的译本中,选取的更多的则是堕落、贪婪、势利的和尚形象,例如,《僧孽》中在地狱里因到处募金、奸淫赌博受到残酷刑罚的和尚;《死僧》《珠儿》中的和尚贪婪无度,虽是出家之人,但对金钱却有着强烈的欲望。翟理斯说过,“中国的和尚会因为他们的光头遭受嘲笑,并且他们信仰的真诚性和生活的纯真性也会受到质疑”[3]55-79。韦伯也提到过佛教在中国受到了严重的迫害。可以看出西方人并不认同僧人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但这与中国僧人在不同朝代所受待遇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3.迷信的中国人
翟理斯认为中国人研究的风水、占卜等都为迷信,“一般而言,在中国,古来的种种经验知识与技术的理性化都朝向一个巫术的世界图像发展”[5]273。他在《聊斋志异》中也找到了各种奇异的小故事证明中国人是一个“迷信的民族”。《跳神》讲民间有人得了病就去请巫医占卜,并进行“跳神”的活动;《果报》里的书生通晓求签问卜之事,却品行不端,最后遭致惩罚;《镜听》中还记载了一种在大年三十用镜子偷偷地占卜的奇特方法;《醫术》中的道士很会相面。在这些故事中占卜方法毫无科学依据,很好地证明了中国人“迷信”的观点。
此外,“中国人坚信灵魂的存在,并且将其区分为好和坏,他们不怎么在乎前者,而非常惧怕后者”[3]55-79。在《聊斋志异》中,“坏的灵魂”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凶神恶煞的鬼怪。《画皮》中披着人皮的恶鬼,形象丑陋又十分残忍;《尸变》中的女尸,脸色蜡黄,头上裹着白绢,在半夜当旅客都已熟睡后谋害性命。中国民间文化受佛道影响,认为人死后变成鬼魂的观念十分流行,而在翟理斯看来,恶鬼索命之事是无稽之谈。这是中西文化的不同之处,翟理斯在此问题上有意把中国放在愚昧迷信的位置上,而认为西方是科学进步的代表。
(三)中国妇女形象与地位
“一国女性地位或可视为衡量该国文明程度的标准。”[6]翟理斯在多部有关中国的论著中都曾论述过中国妇女的相关问题,其中涉及妇女地位、教育、婚姻、缠足等。《聊斋志异》中有着丰富的中国女性人物,正是展现中国女性形象的生动范本。
1.落后的妻妾制
中国自古以来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传统中国士人心中这是一种很完美的婚姻制度,辜鸿铭就曾在《中国人的精神》中极力向外国人解释,纳妾制“并非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是陈风陋俗”[7]。但翟理斯将中国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形容为“notorious”,即“声名狼藉,臭名昭著”的,对此制度展现出强烈的不满。
《聊斋志异》中的很多家庭体现了这种妻妾制。例如,《聂小倩》中聂小倩与宁采臣感情和睦,家庭幸福,但是在故事结尾宁采臣又纳了一个妾,由此看出,即使夫妻感情很好,正常家庭还是会纳妾;《莲香》中即使是贫穷的桑晓也娶了莲香和燕儿,可见纳妾在中国之普遍甚至不仅只存在于富贵之家。翟理斯也有意选译了一些因一妻多妾制导致恶果的故事。《大男》中,家庭一开始破碎的根源就在于这“一妻一妾”。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很多关于家庭和睦的小故事,但是这些都没有被翟理斯选中,由此可见,作者与译者对于婚姻制度的看法有很大分歧,在婚姻问题上翟理斯一定程度上有意规避了中国的现实。
2.无法自主的婚姻
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妇女的婚姻不能由自己做主,尤其在婚后要完全服从夫家。《中国之文明》第5章中提及中国妇女是不能主动与丈夫离婚的,也很少能够离开夫家回到娘家。《珊瑚》中的珊瑚受婆婆刁难,又被丈夫送回娘家,说道:“为女子不能作妇,归何以见双亲?不如死!”[8]887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女子被丈夫赶回娘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对于女子来说是奇耻大辱,甚至比失去生命更严重。《中国与中国人》第6章中介绍,中国妇女如果成为寡妇,正常是不应该再嫁的(实际上很多人经常再嫁),如果守寡超过30年,会受到一定形式上的嘉奖。《土偶》中,王氏死了丈夫,她的母亲和婆婆都劝她改嫁,“汝志良佳;然齿太幼,儿又无出。每见有勉强于初,而贻羞于后者,固不如早嫁,犹恒情也”[8]405,从王氏母亲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妇女为过逝的丈夫守节是被鼓励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允许再嫁的。这些故事都比较真实地呈现出中国妇女当时的一种婚姻状态。
三、译介语言的使用
巴柔认为,“一切形象都源自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极其微弱的”[9]155。“他者”这个形象是对异国文化的反映,也是“自我”即译者基于自我的感受、在本国文化环境影响下所塑造的新形象,在这个新形象背后蕴含着译者对于异国文化的认知,实际上是译者自身文化与所译国别文化的整合。翟理斯《聊斋志异》译本中展示出的中国形象,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对异国和本国文化的整合。
(一)异域中国——他者文化视角
1.形象上的描写
翟理斯对语言的运用延续了英国人一贯严谨的风格,他在很多地方都对原著进行了相对忠实的翻译。比如在外貌描写上,尤其是对女性“脚”的形容上,他的译文非常忠实原文,因为脚是衡量中国女性外貌的重要因素。在《毛狐》中狐狸说自己的相貌与大脚驼背的女人相比也算国色了,大脚被蒲松龄形容为“莲舡盈尺”[8]259,这里的细节被翟理斯准确地翻译成为“boat-shaped feet,full ten inches long”[10]432,虽然在度量单位上英国与中国并不一致,但是10英寸的表达也较为合理,翟理斯其实并不在意于逐字逐句的翻译,而在这里却进行了一字不差的翻译;《娇娜》中娇娜同阿松出场时,原文为“果见娇娜偕丽人来,画黛弯蛾,莲钩蹴凤,与娇娜相伯仲也”[8]36,翟理斯译为“and accordingly saw Miss Chiao-no come out with a lovely girl-her black eyebrows beautifully arched,and her tiny feet encased in phoenix-shaped shoes-as like one another as they well could be”[10]41,可见在对女子的外貌描写上翟理斯描述得非常具体,原文所有的细节都一一翻译出来,生动地呈现出一个穿着凤头鞋的三寸金莲的中国古典美人形象。
2.古诗的翻译
作为一个了解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汉学家,翟理斯深知诗在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中的地位,他把原文中有诗的地方都颇费心思地翻译出来,虽然在韵味和押韵方式上与原诗肯定会有较大出入,但这毕竟是诗歌翻译中无法避免的遗憾。例如,《香玉》中黄生看到美女香玉便十分迷恋,题诗:“无限相思苦,含情对短缸。恐归沙吒利,何处觅无双?”[8]977翟理斯将之译为:“The pangs of love my heart enthrall,As I stand opposite this wall.I dread some hateful tyrant’s power,With none to save you in that hour.”[10]286这一翻译中将“短缸”译为“this wall”,“何处觅无双”译为“With none to save you in that hour”并不准确,但是“enthrall”与“wall”、“power”与“hour”的押韵,有着诗歌独特的音韵上的美感;使用简短的句式,这与当时西方流行的维多利亚冗长的诗风并不相同,流露出东方诗歌的韵味。《香玉》一文中,翟理斯完整地翻译了四首古诗,让这篇译文带有浓厚的东方式含蓄的美感,显示出他对汉语文言深厚的理解力和对英语语言出神入化的运用,也展现了中国文人求偶时的浪漫与优雅。翟理斯对所选故事中的古诗,大多选用贴切的东方意象和一二句和韵、三四句和韵的方式翻译出来,这些古诗大多为青年男女恋爱之作,借此互相表达爱意,这也使得译本传递出含蓄、内敛的中国之美。
3.选择性保留評述性文字
蒲松龄喜爱在《聊斋志异》每篇故事的结尾,通过“异史氏曰”直抒胸臆,发表自己的看法,留下一段评述性的文字,但是这不符合当时西方人的写作习惯。18世纪时,菲尔丁所采用的第三人称叙述的写作模式是很流行的,他让叙述者在文中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到了19世纪这种写作手法遭到了许多作家和小说家的批评,开始被淘汰,所以一般情况下翟理斯对此会选择删去不译,尽管如此,他还是对一些评述性的文字进行了保留,在表达人与动物的情感、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情感时多作此处理。卷九篇《义犬》译为The Grateful Dog,贾商人看到有屠夫要杀一只狗,就以加倍的钱买下它,后来这只狗又救了买狗人一命。小说最后一句“呜呼!一犬也,而报恩如是。世无心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8]790这是蒲松龄对此犬的赞扬以及对世道人心堕落的慨叹,这段评述性的结语被翟理斯保留并无太多差异地翻译出来了。只讲动物间情感的《二鸿情深》是一则短小精悍的故事,一只猎人捕获了雌鹅,雄鹅来到猎人的家中哀嚎并吐出黄金,后猎人放了雌鹅,二鸿结伴飞走了。蒲松龄赞扬了动物间真挚的情感:“禽鸟何知,而钟情若此!悲莫于生别离,物亦然耶?”[8]666这段结尾的评述也被翟理斯保留了下来,可见他对于蒲松龄的这些观点的认可。
(二)主观中国——自身文化视角
翟理斯同样无法摆脱西方人的身份限制,在其译介中会悄无声息地将自身想法加入到作品中去。因为译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创造,所以,翟理斯笔下的中国形象必然与蒲松龄笔下的中国有所出入,更会与现实生活中的中国形象不同。
1.对性行为描写的删改
翟理斯对《聊斋志异》文本最大的改写就是对原文中涉及性的部分的删改。蒲松龄其实在许多故事中都加入了主人公的香艳事迹。首先,蒲松龄本人常年在富贵人家教书,不能与妻子相伴,所以便将自己的欲望诉诸笔下,比如书生夜深苦读之时多有美女红袖添香、自荐枕席之事;其次,社会风气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明代前期虽然有着一系列禁娼举措和严格的纳妾制度,但“大约在正统至成化年间,经济的恢复和财富的积聚使社会上逸乐风气开始抬头,兼之以阴阳心学的流行,士界思想受到极大震动,长期被压抑的欲望终于从沉闷中挣脱出来,造成了晚明社会上人欲横流的局面。士人嗜谈情性,以纵情逸乐为风流……在这个时期人欲受到极大的肯定,任何形式都得到宽容甚至纵容”[11]。蒲松龄生活在明末清初时期,自然会受到晚明这种纵欲风气的影响。而翟理斯成长于维多利亚时代,受清教主义的影响,他基本不会去翻译书中大量的性描写。例如,《夜叉国》中有非常暴露的描写男女性交时的场景,在翟理斯的译本中直接删去;《画壁》中“舍内寂无人,遽拥之,亦不甚拒,遂与狎好”[8]8,翟理斯对此处改动非常大,他译为“He accordingly entered and found nobody else within. Then they fell on their knees and worshiped heaven and earth together, and rose up as man and wife, after which the bride went away, bidding Mr Chu keep quiet until she came back”[10]10。这里本来朱孝廉的举动是十分轻浮的,看见四周没人就去抱那女子,并且两人“狎好”,“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犬可习也”,是从驯犬衍生出来的字,用在两人交好中是很不尊重对方的,可见与翟理斯的译文“两人虔诚地跪拜上苍,结为夫妻”实在相距甚远,这样的译文展现出的人物形象与蒲松龄笔下的中国书生是有所出入的。西方人一直以来都认为中国人非常保守、闭口不谈性,翟理斯的这些删减和改写在一定程度上又附和了西方人的固有认知,虽然他也曾在《婴宁》的注释中对此进行了驳斥,声称中国人对性爱的激情像疾病一样,不过在其大多数译文中他都选择对性避而不谈。
2.对纳妾制度的回避
因为对纳妾制的不满,翟理斯有时候在翻译时故意舍去“妾”的说法。《聂小倩》中,聂小倩想陪在宁采臣身边,对他说的是“媵妾无悔”,而翟理斯译为“Let me go home with you and wait upon your father and mother ; you will not repent it.”[10]130,这里原文是聂小倩表明自己的诚心,若能够侍奉在宁采臣身边,宁愿当妾自己也不后悔,但是翟理斯将其译为“你不会后悔的”,与原文的意思出入比较大。《金姑夫》中,梅姑对金秀才所言为“愿以身为姬侍”,翟理斯译为“I intend to repay you by becoming your humble handmaid”[10]257,原文中的“姬侍”应为妾的意思,而翟理斯却只取了其中“侍”的意思,将其译为女仆,有意地规避了梅姑“愿为妾”的意图。虽然翟理斯本人很想通过《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人的生活,但是他对于中国人纳妾这一传统,在很多情况下是规避不译或者改译的。
3.对标题的改写
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等解构主义翻译学者曾通过对英美文化归化翻译历史的追溯 ,指出“通顺可以看作是归化翻译理想的策略,它不仅可以进行民族中心主义的算改,并且,在透明的效果下掩盖了这种篡改,从而给译文读者一种幻觉,即他们在阅读的作品不是翻译,而是外国文本是外国作家活生生的思想”[12]。除了对内容进行自由化的处理,在标题上翟理斯同样进行了十分主觀化的改写,使其能够更加贴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因为《聊斋志异》中大部分的篇名都是以人物的名字来命名,这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只看篇名会一头雾水,所以有时翟理斯自己对故事内容进行总结并为之起一个适宜的名字。虽然也有一些篇章如《婴宁》,翟理斯将其直译为Miss Ying-ning或结合其性格译为The Laughing Girl;但相当一部分篇章名称都是对人物特征的总结或对主旨的提炼,例如,《褚生》被译为The Disembodied Friend,《柳氏子》被译为Dishonesty Punished。还有一些篇名并非故事的主旨,例如,《席方平》,翟理斯将其译为In the Infernal Regions,既与原标题的“席方平”这个人物无关,又不能凸显其为父申冤的主旨,只是对“在地狱”一个位置的强调;《聂小倩》被译为The Magic Sword,既没有呈现出原文中的经典形象聂小倩,也不能展现出她由恶转善的历程,更没有表现她与宁采臣两人的感情,而是以书中次要人物燕赤霞的宝剑作为标题。由此可见,翟理斯的译文标题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西方读者理解聊斋故事产生干扰。
四、注释的使用
在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译本中,他增添了大量的注释。由于中英的文化隔阂,即使是译文,《聊斋志异》中还是有许多内容对西方读者来说较难理解,所以翟理斯在译本中增添注释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够理解,尤其是那些从未接触过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同时也通过注释起到了介绍中国文化的作用。
(一)正面客观地介绍科普中国文化
1.客观的文化传递
“西方文化传统中,有两种‘东方主义’,一种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另一种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前者构建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道德权力,使其在西方扩张中相互渗透协调运作;后者却在拆解这种意识形态的权力结构,表现出西方文化传统中自我怀疑自我超越的侧面。”[13]作为在华生活20余年的外交人员,翟理斯对华具有深切的生活体验,而非同为英国人的曼德维尔创作的《曼德维尔游记》一般,是纯粹的西方人对东方的主观幻想。在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译本中,许多的注释都有着对西方人科普中国文化的作用,并且很多都可与他撰写的中国专著中的论述相互佐证。
《聊斋志异》一定程度可以称为展现中国各类文化习俗的宝库。《狐嫁女》中,殷天官为了回去给同学做见证,将狐狸老头敬酒的金杯子藏在袖筒中并装醉,翟理斯将“醉”译为“tipsy”,并解释了中国的饮酒文化,调侃了酷爱饮酒的苏格兰人,因为他们不会理解中国的这种饮酒文化——视“微醉”的状态为一种优雅举止;还有中国人不喜欢却不得不遵从在社交场合要“敬酒”的这一习惯,所以出现了“代饮”这一现象。翟理斯通过注释饶有趣味地介绍了许多中国人独有的文化习俗。
译本中的注释涉及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节气与节日、历史人物、礼仪、运动等,在涉及婚姻习俗时,翟理斯一般都会在书中加入大量的注解。《莲香》中当桑晓和燕儿大婚喝交杯酒时,翟理斯在下面作了注释,解释了这种新郎和新娘要一起喝下被红绳系着的两杯酒的习俗,还讲述了“月下老人”的传说。《婴宁》中王子服偶遇美女后相思成疾,他的朋友告诉他即使这个女子许配人了,多花点钱也能把她娶过来,翟理斯就在下面注释介绍了中国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这一传统;后来王子服的朋友告诉他这女子是他的姨表妹,但仍然可以通婚,翟理斯又在下面介绍说,中国同姓有血缘关系的亲属间不能结婚,而母系这一支有血缘关系的是可以通婚的,因为中国人认为只有父系这一支的血脉才能延续。这些关于婚姻的社会习俗与西方社会并不相同,翟理斯详细介绍中国人的婚嫁传统,能够让西方读者对此有所了解。
关于男女礼仪方面,翟理斯在译文中都标注了详细的注释。《香玉》中黄生见香玉会写诗便喜出望外地握住香玉的手,在这里翟理斯细致地解释了男女礼节,并引用《孟子·离娄上》中淳于髡问孟子关于嫂子掉进水里、小叔子是否应该救她的问题,孟子回道“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真实地介绍了中国自古以来男女相处有着严格的要求与规定,但也可灵活变通的情况。翟理斯在其专著《中国与中国人》第6章也谈及男女相处之道,从古至今男女相处有着严格的界限,两性之间不能传递东西以免手的触碰。由此可见,《聊斋志异》的译介确实比专著更生动地解读了中国的文化风俗,在这方面可以说翟理斯做到了巴柔所言的“友善”,“第三种态度:异国文化现实被视为正面的,它来到一个注视者文化中,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注视者文化是接受者文化,它自身也同样被视为正面的。这种相互的尊重,这种为双方所认可的正面增值有一个名称:友善。友善是唯一真正、双向的交流”[1]142。在这种观点下,翟理斯《聊斋志异》译本中呈现出相对真实的中国,而非有色眼镜下18世纪耶稣会描写的乌托邦世界,也绝非目空一切的殖民者笔下的“野蛮帝国”。
2.对中国社会的赞誉
19世纪旅华的外交官、传教士等都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对东方文化持鄙夷的态度,这让翟理斯十分不满,他在导言部分也明确地指出,希望通过译介文学作品来达到让西方了解中国文化从而消除对中国的误解的目的,“一方面我希望能引起比中国事务更深入的兴趣,另一方面无论如何要纠正那些无效率的和不诚实的人总是欺骗人的错误观点,而这些观点又很快地被接受为事实”[10]xiv-xv。所以翟理斯在注释中多有对中国不同方面的赞誉,试图动摇西方读者心中负面的、落后的中国形象。
《阿宝》中对“贵族制度”的注释,翟理斯认为“中国没有贵族继承制度,任何人都可以从底层升到上层;只要他和他的家族一直存在,他们就被认为是贵族。贵族无关于财富,而官阶或文学品位,或两者相结合则可决定一个人受尊重的头衔”[10]186。在翟理斯眼中,中国社会是公平的、文明的,然而他对于中国没有“贵族继承制度”的评价并不真实,中国在“一夫一妻多妾制”影响下形成的是“嫡长子继承制”,上至皇帝官员,下至黎民百姓,都在這一制度下生活,翟理斯的注释主观性地美化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成仙》中周生被“搒掠酷惨”[8]52,翟理斯将其译为“most unmercifully bambooed”[10]55,原文只是形容周生被残忍地拷打,并未提及刑具的问题,翟理斯认为他是被竹条所打,在注释中还细致地介绍了这种刑罚,更是赞扬了康熙皇帝仁慈的行为,废除了这一残忍的酷刑,可见他对这位中国帝王的认同与赞赏。19世纪的西方人来到中国后看到了民间溺死婴儿的现象,对此大加批判,这也是致使中国形象受损的重要原因,翟理斯在《夜叉国》的注释中为中国人辩护称“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孩子的喜爱,一个外国人想在中国安全旅行,带孩子要比带手枪有用得多”[10]402,溺婴事件在古代中国时有发生,但“多子多福”和对孩子的喜爱也实为中国的传统,翟理斯在此尽力地展示出友善的中国形象,试图削弱西方读者心中对中国的负面看法。
(二)自由化的文化阐释
1.过量且附会的解释
翟理斯译本中有一些注释,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虽然是介绍中国文化的生动实例,却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例如,翟理斯一贯重视并排斥的缠足文化,虽然满族妇女不缠足,但是在满人统治下的汉族妇女依然坚守着缠足的传统。翟理斯在《中国与中国人》第6章中介绍了中国妇女缠足的传统,他讲自己认识的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妇女,自己没有缠足但是却让女儿缠足,因为这样女孩才容易出嫁,可见在当时的社会中缠足对于中国妇女的重要性。《阿宝》中,孙子楚变成鹦鹉来到阿宝的身边,后来把阿宝的鞋叼走作定情信物,两人终成眷属,其中阿宝“束双弯”(即缠足),被翟理斯翻译出来并且作了注解,他解释道 ,“每天晚上和早上都要裹脚,不然绷带就会变松,走路的步伐就会不稳”[10]192 。《画皮》中原文为“遇一女郎,抱襆独奔,甚艰于步”[8]71,本来只是形容女子走路艰难,但是翟理斯却在注释里大做文章,想当然地认为女子步履维艰是因为裹脚,并大量地介绍了关于中国妇女缠足的这一习俗,然而这样对原文的理解实在是太过于主观,在不知觉中就塑造了一个小脚的中国女子的形象。
2.个人观点的表达
翟理斯认为风水是所有迷信中对中国人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在他看来“山的形状、水的有无、树木的位置、建筑物的高度,这些都是风水师要深入思考的问题,这些风水师就是靠着迷信群众的无知发展壮大”[3]55-79,所以中国人看风水的习惯,在翟理斯看来是非常愚昧的。《堪舆》中就是一家人过度讲究风水,却把需要埋葬的父亲晾在一边的故事,蒲松龄在“异史氏曰”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虽不否认风水有一定的道理,但痴迷到如此地步实在荒唐。按照翟理斯译文的习惯一般都会把“异史氏曰”删去,但这里蒲松龄的批判却被翟理斯放在了注释处,可见他赞同蒲松龄的看法,或者说借蒲松龄之笔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3.易造成阅读困惑的注释
《瞳人语》的故事是为了告诫人们要自律自重,主人公方栋由于行为轻佻受到惩罚,从而眼睛里长出了小人。故事本身带有传奇色彩,但翟理斯在注释中介绍了人类的眼睛里存在一个微小的人形生物在中国是一个普遍认识,并解释了这一看法的来源。这里的注释与故事主旨无关,而且翟理斯把这解释为中国人的一种普遍认识,混淆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聊斋志异》里的奇异怪事。《长青僧》中,翟理斯对“按鹰猎兔”展开了长达300多字的注释,主要就是介绍这一比较特殊的中国活动,对诸多细节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与原文褒奖老和尚道德高尚的主题毫无关系,尽管这也是一篇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僧人修行之道的较好素材,但是翟理斯在注释中显然把重点放在了“猎兔”这一活动上,对佛教中的禁欲部分只是在注释中用50字左右去讲解,这样的注释处理容易让读者对文章内容产生误读。
五、结语
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译本在很长时间内都是英语史上选篇最多且影响力最大的版本,他对当时欧洲人恣意妄为地对中国形象进行曲解持鄙夷态度,因不满于西方对中国和中国人介绍的书都是二手材料,所以他希望通过《聊斋志异》这样一本由中国人所著的一手材料让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正如他自己在序言中所说“应该允许中国人为自己说话”[10]xv。《聊斋志异》展现了明末清初广阔的社会现实,反映了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中普通人的生活,的确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的绝佳材料。翟理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译164篇故事,并进行了巧妙的艺术化翻译和注释,通过这些精彩绝伦的聊斋故事向西方呈现了相对“原汁原味”的中国,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客观的中国形象;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各异、写作习惯不同,翟理斯在翻译中对原文进行了不少的删增与改动,注释上做了诸多自由化的处理,让这个异国人笔下的中国形象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异国想象”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 [G]//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付瑛瑛,王宏.从典籍英译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译:王宏教授访谈录[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30-35.
[3] Herbert A Giles .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M].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1911.
[4] 叶廷芳.论卡夫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12.
[5] 馬克思·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M]// 马克思·韦伯.韦伯作品集:V.康乐, 简惠美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 Joh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M].London :T.Cadell and W.Davies ,1804:138.
[7]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何叶,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111.
[8] 蒲松龄.聊斋志异[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
[9]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 [G]//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5.
[10] Herbert A Gile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lI[M].London: Thos De La Rue & Co,1880.
[11] 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
[12] 郭建中.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J].中国翻译,2000(1): 49-52.
[13]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98.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Image in Giles’s Translation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ZHOU Ruowen1,2, ZHOU Debo1,2
(1.Institute of Japa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0, Liaoning, China;
2.School of Liberal Art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0,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Herbert Allen Giles,living in China for more than 20 years,had been committed to sinology and the spread of Chinese language,literature and culture. His translation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s a classic English version, which has been exerting influence on the spread of the Chinese novel in the western world and offering a feasible path for western read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Through analyses of Giles’s selec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usage of the translation language and annotations,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his version presents a relatively objective and true image of China.But constrained by his identity, the living era, and his ideology, the translation inevitably connotates his subjective imagination and mis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Herbert Allen Giles;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original text;Chinese 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