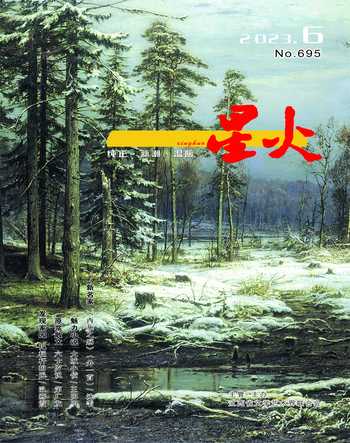六十岁说
第广龙
第廣龙,1963年出生于甘肃平凉。现居西安。中国作协会员。参加《诗刊》第九届“青春诗会”。已结集出版十部诗集,十部散文集,一部长篇小说。获中华铁人文学奖,敦煌文学奖,黄河文学奖,全国冰心散文奖。中国石油作协副主席,西安市作协副秘书长。
我六十岁了,按照北方民间的习俗,是要准备一副棺木的。意思也清楚,人到六十,在年龄上是一个界限,活到这么大,即便两腿一蹬,也算活够本钱了,到了阎王爷那里,不会被嫌弃。
棺材和死亡联系,有人觉得不吉利。其实,有生就有死,中国人的生死观,和天意是顺应的。过去的人,老了之后,制作棺木属于大事一件,大张旗鼓,唯恐别人不知道,棺材完工,要挂红放鞭炮,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
命只有一条,活得长久固然好,七老八十的说法,显然不仅仅是愿望。家里有一副棺材,出于应急的考虑倒是不假,没有后顾之忧的老人,反而安定下来,被死神遗忘了一样。我小时候在奶奶家的炕头一侧,就看到一副棺材,放了几十年,外表都发黑了,还不到派上用场的时候。我也不觉得害怕,奶奶在棺材里藏了好吃的呢。
在过去,到了六十岁,作为男人,也有了留胡子的资格。
是在下巴上留一撮胡子。这胡子,通常叫山羊胡。
人流露出某种情绪,会有辅助动作,也出现手脚不知道咋放的情景,如果下巴上有胡子,一下一下捏着,捻着,就显得镇定多了。
也显得威严。
要不,怎么会出现“都有一把胡子了”这个说法呢。
我六十岁了,就在这一年,生活在恢复,烟火气在弥漫,在升腾,我却要退休了。
六十岁的人,经历最多的,一个是疾病,一个是死亡。疾病害在自己身上,多是慢性病,有的得终身服药。我高血压,吃了七年麦丽平了。死亡发生在不认识的人那里,刺激不直接,发生在认识的人那里,容易联想,触动是真切的,心情是黯然的。常有隔些日子不见的人,提起说是走了都一月了,两月了,自然感叹一番生死之无常。这个无常,不是虚构的,不是想象出来的。一个活生生的名字,变成了讣告上的名字,墓碑上的名字。从今往后,世上就没有这个人了,这个人的存在,就风吹落叶一样被吹走了。这就叫死亡教育,谁都躲不开,却是愿意当旁听者,而不愿意成为当事人。平时,到医院只是做一个正常的体检项目,让签字的单子上,有责任的划分,也有可能出现意外状况的提示,知道发生医疗事故的概率很低,还是产生了不适感和轻微的恐惧;坐飞机买上一份保险,偏巧遇上气流,飞机剧烈颠簸,害怕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绝对不愿意灾难发生得到补偿而盼望的是平安落地。
我的一个朋友,打喷嚏引发脑溢血,躺床上五年,在这个冬天得到解脱。那天寒冷,河道结了厚冰,反射刺眼的光,早上的太阳也像是冰雕的。我去高陵殡仪馆祭奠,看到朋友睡在棺材里,头上戴一顶帽子,脸塌陷下去,都看不出本来的模样了。朋友刚过六十,虽然有五年是植物人,从整数上说,也算活了一个甲子。这个年纪,还是走得早了些。他再也起不来了,不可能给饭碗里调醋加油泼辣子,也无法去电影院看一场武打片了。他的老婆孩子,对他细致耐心地照顾,也没能让他苏醒。接下来的日子,他的家人是最难受的,一个大活人不见了,要接受这个现实,得有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对阴阳两隔有扎心的体验。
生死有命,这句话朝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一次性的,放到谁身上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如今的人,活七十普遍,活八十寻常,活九十的不在少数。有一个八十三了,和几个老朋友聊天,说这年头,活不过八十,连自己都觉得丢人得很。老朋友都不反驳,也无法插话,因为,老朋友的年龄,都不到八十,自然没有发言权。这种情况下,他拥有绝对真理。
这个绝对真理,谁长寿,谁就掌握。
生命只有一次,享受生命,让生命过得有意义,这个道理,再浅显不过了,不用细想都能明白。而生命必然有一个结果,对谁都不会例外,那就是死。死了啥都没有了,怎么能不怕死呢。活这么大,我见过太多的死,也知道这个死有一天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能正确对待吗?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有答案,又没有答案。这全是因为,一个人的死,是在场也是离场,而两边是不连通的呀。
我想过死,之前想,像是想一件遥远的事情,无关的事情,就像一句话所说,还没有准备好怎么活着,怎么会准备好面对死亡。大概过了四十岁,我就想过自己的身后事了。这确实过于提前了,不过我的情况特殊。那时候,我从事的职业,和野外多有关联,整天外出跑长途,工作的地点,属于高风险。包括易燃易爆,高空坠落,都近在身边;包括洪水暴发,山体坍塌,有过突然发生造成伤亡的案例。每次出行,安全须知里,都在反复提醒。家人担心,我自己也想到如果把命丢了该是多么倒霉和不幸。可是,既然身在这一行,我不能逃避,也自己进行了一定的心理建设,那就是风向不对,拿着命就跑。我还偷偷写了一份遗嘱,是写给妻子的,藏在书柜的一个盒子里,在里面写了一些安慰的话,也说了一些自己的期望。后来,经历多次搬家,这份遗嘱我自己都找不到了。跨过五十岁这个坎后,我的生活趋于平静,工作上也不那么辛苦了,对于死亡这个严肃的问题,倒变得坦然起来,没有再写什么文字性的东西。忙碌半生,已经不为吃喝发愁,我很是知足了。钱财不多余,住房有一间,我能有什么好交代的呢。可是,人生六十,这是一个重要节点,我有过许多思考,其中自然包括死这个问题。
在家乡的南山,有一片墓地。每年清明,上坟的人多了起来。许多都是从外地赶回来的。这片墓地,和那种统一规划的墓园不同,是沿着地坎一溜分布的。有的坟墓,墓碑高大,做工讲究。有的墓碑,矮小,简陋,还有些歪斜。人到了阴间,待遇都有差别,死和死,也给出了不一样的外在表现。不过,不论什么样的坟墓,墓前的亲人,都摆上了祭品,神情是肃穆的。有的还喃喃自语,在和地下的亲人说话。离开之前,还有一个步骤:清除坟头上的杂草。
有的墓前头,是空的。这个墓里的人,也许就等不来亲人的纸钱了。地不种会荒,坟墓不照管就剩下了孤魂。由于地坎前是庄稼地,隔上几年,要改土,地坎的位置就会发生改变。有的坟墓,甚至得迁移。村子里发通知,有截止时间。那些无主的坟,在开挖中暴露出来,一些遗骨散乱在外面,被人用铁锨铲走。
这样的场景,我多次目睹,曾有过感叹,与其落这样一个结局,还不如啥都不保留。都说人说不出三代以上的祖先的名讳,同样的,三代以上的祖先的坟墓,也是无处寻觅呀。
我由此树立了一个观点,既然不在这个人世了,就走得彻底,干净,这也是对自己负责,对家人体贴的表现。
我兄弟姊妹六个,父母操劳一辈子,没有清闲,没有享福。我们的成长,也是磕磕绊绊,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艰难,父母的不易。在我看来,大多数老百姓所谓的传宗接代,都是虚幻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我已经不可能儿孙满堂了,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遗憾的;别人人丁兴旺,我也不羡慕。我只有一个孩子,把孩子养大,是我的责任,所有付出都是应该的,不求回报的。我获得的生为人父的幸福,是孩子带来的,我也应该让孩子快乐成长。同理,孩子长大成人,走什么样的路,我没有能力安排,也不去强求,我的意见,都是参考意见,最终的决定权在孩子那里。在我和孩子的关系中,有一条重要的关系,是互相感谢的关系。这是我一开始就有的想法,也是我一直在行动上体现出来的。
过去日子艰苦,娃娃反而生得多,风吹着都长大了。这有那个时代的无奈和局限,道理在事后,似乎能成立,还原到当时又做不到。经济条件改善了,生育的愿望降低了。有各种投入,就有各种期待。拿自己实现不了的梦想,强加给孩子,这又是何苦呢。过去的娃娃,物质贫乏,得到的快乐,简单而长久,娃娃长大,各有各的不一样;如今的孩子,整天在补习班学习,天性被压制,充满成长的苦恼,走到外面,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也是奇怪,爱孩子都爱,但是给予得越多,孩子越和大人的期望相反;苦日子过来的,都特别孝顺。
那么,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不指望孩子养老,孩子也顾不上照应老人,就成了一个现实。一反一正,老人靠自己,来自儿女的约束减少,无形中也就放大了这个群体的形象,也带来了许多相互冲突的评价。
一种社会风气一旦形成,会产生累积效应,也会起到示范作用。有时候,即使介入强大的力量,也极难改变。老年社会的一些现象,争议中提倡包容,包容不下去了又都在指责。老人一会儿是个宝,一会儿又成了公害。
人老了,也和過去的老,有些不一样了。占马路健身呀,公交车上抢座呀,超市里偷鸡蛋呀,这就让人讨厌,这就不应该了。
老了也有老了的样子,起码的,懂得自尊,自制,自省;起码的,得承认自己老了。我老了,就按老了的样子活着。比如说,我是绝对不会再和人拼酒了,也不会直着腰大声划拳了。
翻过年我就六十岁了,可我把酒给戒了。
这对于我,是一件大事。知道我喝酒的,都很吃惊。即使我人在当场,也以为是假消息。我都亲口承认了,还充满疑惑看着我,还要再三确认,点头的少,摇头的多。
知道我喝酒的,都说,我是真的爱酒,自然的,也就离不开酒。怎么个离不开?远的不说,近十年,每天睡觉前,我都要抱着酒瓶子喝三两才睡觉,不然,总觉得缺个啥。疫情才开始那一年,我的小舅子,从重庆乡下给我快递来四十斤高粱酒,装在一个大塑料壶里,可重了,我单手提着,走几步就提不动了。城市静态管理,关在家里出不了门,饭馆全都关张了,酒友难相见,马路上都长草了,为了打发无聊,我每顿饭都喝,两个月就喝完了。这高粱酒味道冲,不过不上头,也没有后劲,正好适合我。问小舅子才知道,每年秋天,他那里会酿酒的师傅自带器具,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游走,有需求的,已经自备了高粱,师傅便留下酿酒,一道道工序下来,直到酿出成品,交付一些手工费,一桩买卖便得以完成。我喝的高粱酒,就出自这样的酿酒师傅之手。就图这酒喝着放心,我发信息给小舅子,又给我酿制了一百斤,我是预备这一年主要喝这个酒。我也算酒的行家了,喝过各种酒,我的舌头和肠胃能比较出来高低。经验告诉我,贵的不一定好,那是广告堆出来的。这个高粱酒我喜欢,喝着过瘾,关键是,不伤身体。到底是粮食酒,又没有任何添加剂,采取的是传统的酿制方法,绝对属于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粮食乃天地之精华,酒乃粮食之精华,以水,以火,吸纳天地之气,在时间的流逝中发生微妙变化,生成的物质,和人体最是对应啊。
可是,这高粱酒,才喝掉十多斤,我就戒酒了。
自然是有原因的。
在一次例行体检中,有一项是胃镜,针对的是我这样的老年人。我一天没有吃饭,第二天起来更不能喝水,空着肚子去了。结果发现我的胃部存在病变,虽然不严重,但发展下去,胃粘膜就会产生损伤,不光影响进食,还会深入到胃部肌理,进一步恶化,其后果将不可逆转。
不能喝酒了。
我以为我戒酒会很难。我有酒瘾是一定的,非一日之功,练不出来。喝进我肚子里的酒,光是白酒,拉一卡车只多不少。经常是才吃过午饭,我就寻思着晚上到哪里喝酒,和谁喝酒。约不上人,我一个人也要喝,舌头大了,走路摇晃了才算喝好。
我竟然说戒酒就真的戒酒了,没有难受,没有后悔。说不喝,一滴也不喝。算起来超过一年,我没有碰过酒,再好的酒,在我眼跟前,我也不动心。
这说明,我还是有毅力的。
有人说,一个人能把酒戒了,这个人是可疑的,要慎交。我琢磨了一下,没明白。我如果有什么可疑,一定与戒酒无关,与我这个人的人品无关。我庆幸我能戒酒,我思想斗争过多次,一直下不了决心,这一次总算落实了。喝酒有喝酒的好,戒酒有戒酒的好。这两个好,各有其好,两个好只能二选一,我如今属于后者。也只有喝酒,才有戒酒这一说。滴酒不沾的人,不存在好与不好。我这把年纪了,酒票用光了,我选戒酒。如果因为戒酒我会失去朋友,我觉得不惋惜。人老了,能交往的人,是做减法呢,最值得的才能留住。凡事不强求,这已经成为我的原则。连喝酒这件事都不理解我,不支持我,无论谁,继续相处下去,双方都别扭,那就各走各的路吧。
到了我这个岁数,一些病预备好了一样,等着我呢。无法预防和躲避,不能像在路上行车那样,遇见堵车绕过去,又是宽敞的大路。病来了,除了承受,我没有别的好办法。得上“五十肩”,我就遭了大罪。
有几次,我偶然发现,用过雨伞后收起雨伞,甩雨水时,我不能使劲,不然肩膀疼,是无法忍受的那种疼。我没有多想,过后也忘记了。毕竟,雨天不经常,用雨伞也不经常。再后来,我在后背抓痒,肩膀疼,手不敢过分伸展;往高处送东西,肩膀也疼,我就意识到,我的肩膀有病症了。不过,只要注意着,只要不把胳膊肘往后拐,做向上伸展动作,提垃圾袋呀,扛快递箱呀,肩膀不疼。再后来,我穿衣服脱衣服,肩膀疼;侧身取床头柜上的手机,肩膀疼;睡觉侧身,姿势稍微扭曲一下,也疼。在梦里疼醒来,以为是梦里疼,醒来怎么还疼,疼也能转移,来到梦外头了。疼得次数多,疼得剧烈,我有了心病了,就打算去红会医院瞧瞧,这可是西安治疗骨头伤病方面最有名气的医院。正计划时间呢,一次和朋友提起这件事,朋友说这叫五十肩,人过了五十,容易得上,就是疼,严重的疼得叫唤,疼得死去活来呢。不过,通常半年多,自己就好了。我就问要不要治疗,电烤呀,贴膏药呀什么的。朋友说,用了能缓解疼痛,一般不用。得了感冒,我都是硬扛,不愿意吃药,知道了五十肩在我这个年龄段常有发生,每次疼起来我都咬牙歪嘴的,依然没有进行任何治疗。这都快两年了,还不见好,疼痛有时候强烈,有时候稍稍轻微一点,我一一忍下来了,像是和疾病较量,看谁能赢过谁。其实呢,我可没这么厉害,我只是不愿意浪费药物,又担心产生副作用而已。
我多么希望肩膀上的疼痛哪一天突然消失啊。
按说一把年纪了,轻易不会冲动了,脾气再大,剧烈咳嗽的时候,怎么发火?有些病就是叫我这样想法多的人变老实的,这个我多有体验,也努力顺应着,变通着,愿意当一个性情平和的老头。
我在六十岁的时候,没有准备一副棺木,也没有留一撮山羊胡。习俗也在改变,除了一些偏远的地方,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们都不准备棺木了。
留山羊胡的,倒是一些搞艺术的年轻人。
我竟然理了个光头。这个对于我,也是稀罕的。
我十九岁正式参加工作,在一个厂矿企业谋生,虽然身处底层,见天劳累受罪,也算是吃公家饭的人。记得在野外队时,在工地上劳动,每人手头的工具,是不能丢失的,不然照价赔偿。有的找不见管鉗,有的找不见扳手,就拿起别人的辨认,看着像就说这是我的。老工人瞪着眼睛来了一句,什么你的你的,连你也是公家的。既然是公家的,那就有了规矩和约束,有些在纸面上,有些不成文。比如剃光头,就会引起议论,甚至带来麻烦:他是不是对领导有意见,他是不是得了大病了,他是不是和对象吹了……诸如此类。头发属于自己,但不得随意处置,头发也是公家的。想起上中学那阵子,留长发,被叫做长毛,那就和不良青年挂钩了。所以,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剃过光头,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产生过。有关头发的禁忌是一方面,主要的,有头发,尤其是一头黑发,人显得年轻。头发少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谁愿意一副老相出门啊。有人脱发严重,为了留住头发,用尽手段,越是在意,越是不如意。头发多少,说起来不影响吃饭睡觉,带来的烦恼,胜过丢钱,甚至比失恋严重。对象还可以再找,头发没有了长不出来。我也是头前面剩下一撮毛,往左梳,往右梳,都看着不顺眼。所以,当我退休,和单位的联系,也就结束了,我属于社区,我的身份变了,或者说,我没有啥身份了,一些行为,就不会被认为出格了。我剃了个光头,大夏天的,洗头方便,擦汗方便。我在路上遇见熟人,都不惊讶,也不奇怪;和朋友吃饭,我的光头也没有成为话题。这就对了。
通常的,人一辈子的光阴,有时候觉得慢,有时候觉得快。这都是心理感受造成的。年轻的时候,路长着呢,就着急,就觉得慢。老了,快到终点了,对自我的打量,侧重点不一样了,闲暇多,日子过得单调,快慢是交替着的。躺倒病床上,一定煎熬,出去旅游,十天八天没怎么度量就过去了。人老了有意思吗?没有意思,可是,多少老年人活成了妖怪,那是自己给自己长精神呢。所以啊,学会如何经营老年生活,也是一门学问。
人的寿命延长了,还觉得没活够。麻雀才活多久,天天快乐。乌龟长寿,满脊背都是金钱,没有生存压力,但压在一根石柱下面活着,愿意吗?老了偏爱怀旧,不由自主说过去,说往事,都是往后看,前面的路,再走,走不出什么景致,看不到啥新鲜。有的地方倒是没去过,那是奈何桥,谁都不会主动走上去的。稍稍留意就能发现,人老了,在脸面上能看出害怕和恐惧,行为也会显得古怪。忌讳去火葬场,到庙里烧香态度虔诚,花钱吝啬,却常常让贩卖养生产品的人得逞。
六十岁了,我挺高兴的。
人希望年轻,不愿意老去,这个能理解。可如果换一个角度,老去意味着已经走过了一段人生的长路,已经经历了生命历程中美好的时光,又何尝不是天赐的幸福呢。人要知足,总是停在一个年龄段,就体会不到变化,也失去了在不同年纪才有的乐趣。一个名人说,死亡对人类很重要,其本意很清楚,有生就有死,人类才能一代一代传承,不断走向进步。前面的人,不要挡住后面人的路,这条生命构成的大河,才能奔腾不息,活力充沛。我赞成这个观点,人的老去,虽说包含了烦恼,疾病,也自带着从容和安详。如果享受生命,老去的生命,也是有价值的,值得珍惜的。
有一句话,我不光年轻过,我还老过。这话是老年人说的,也是安慰自己的。不过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老,也属于一种资格,一份资历,不是人人可以拥有的。得活到这个年纪,才能获得这么一个认证。这个证书,是悠悠的时光颁发的。
我在一个矿区单位,忙碌了大半辈子,吃过苦,也见了世面,得到的是应得的,失去的说明不属于我。在这方面,我没有牢骚。几十年上班形成的习惯,倒让我调整了一阵子。以前,看时间就怕迟到,手里有个事情,没有完成总是心慌。自由了,不用早出晚归了,到特定的时间点,我还是本能地紧张一下。当我意识到我已经是一个闲人了,才轻松下来。多好啊,睡在床上就能拿钱,我也成了白吃饭的人了。曾经,对于别人的退休,我感叹过。有的嘴上不在乎,看得出很失落;有的竟然得了病,还一病不起;有的和家人闹矛盾,闹到了居委会。这都是有太多放不下,没有进行彻底有效的角色转化造成的啊。
轮到我了,我能适应吗?
我能。这是我的性格决定的。我认为,人在哪个阶段,就适应哪个阶段,让出力了,别窝工,让休息了,悄悄走人。有的场子,你上去他下来,是不断接替着的。下来就下来,都挤在里头,也装不下那么多。我是多出来的,这个我认得清楚,我没有意见。
我知足了。
我成为一个闲人,一个背着手走路,勾着身子看人下棋的人。我的失去就是得到,我够有福了。
我关心的范围,一再缩小。对于杂七杂八的是非,充耳不闻,谁跟我说人生,我就说菜价;谁跟我骂社会乱象,我就说我的脚气和痔疮。
我的在意,在乎,有变化是正常的,也是合乎我的价值观的。
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在疫情開始那一年,升格成为姥爷,有了外孙女。
我到了六十岁的时候,我的外孙女,已经三岁了。能说话,话可多了。能满房子跑,最怕磕碰一下。能发脾气,发脾气也可爱。能指挥我,叫我拿玩具我就给拿,叫我买狗熊糖我立马买。
每天听见外孙女的说话声,唱歌声,我的喜悦是在心上产生的,是糖果的味道一样绵延的。
给女儿带孩子,辛苦是肯定的。如今的娃娃金贵,吃什么不吃什么,吃药选择哪一种,还要掌握相关知识,不能用老办法老习惯,这个我愿意学习。老伴有时候也说,别的老人都出去旅游,看风景,等到外孙女长大了,咱们也走不动了。我就说,带孩子,获得的快乐和安慰,是不可替代的,也是最值得的。我看得出来,老伴也是嘴上说说而已,平日里,在网上购物,买得最多的,都是外孙女的衣服和玩具。手机里存照片,存得最多的,也是外孙女的照片。外孙女年前得病发烧,老伴也发烧,顾不上自己,给孩子喂药,量体温,眼睛都没有合一下。老伴把外孙女抱怀里,抱了三天,外孙女啥都正常了,人才轻松下来。老伴有这么大的能量,只有外孙女才能激发出来。一天里做事情最用心的,就是给外孙女做饭了。一天里最操心的,就是外孙女吃饭吃得好不好,吃饱了没有。
这叫隔代亲。
我有每天记录个人生活轨迹的习惯,而且,还喜欢公开到朋友圈。现在的人也是怪,一方面,注重隐私保护,存款多少不让人知道能理解,连得个病,连多大年纪都秘而不宣,谁如果问,那就是不懂事,严重的会惹上是非。可是,又把去了哪里,吃的什么放到网上,还希望点击率高。我发的信息,有人看也是高兴,遗憾看的人不多,点赞的主要是家人和亲戚。不过,这并不影响我按时按点公布消息的热情。
“早,4点57分出门,走路80分钟。”这句话,除了时间上略有前后,是我几十年不变的重复语,通常带有一张健步走的微信截图,每天一条,发布到微博上,对自己算是记录,也是激励。2022年12月22日,我又发出了这么一条。而这一天的这一条,有些不寻常。因为,这一天冬至。冬至是大节气,家家包饺子吃。在古代,皇帝要在这一天祭天。西安的圜丘,也就是天坛,在城南的会展路上,我去过。那里素朴,洁净,安宁,庄重,是古人和上苍的神灵离得最近的一个场所。我在乎这一天,还有一个原因,我的外孙女,就是在这一天出生的。
我对自己的生日,向来不重视。如果一个人在外面,想不起来过也是有的。六十岁的生日,就不能马虎了。不过,在我们这里,从五十岁生日开始,以十年为一个整数,都是提前一年过虚岁。我五十九那天,在外面订了一桌饭,一家人一起,过得挺热闹,挺正式。六十这一天,就成了一个正常生日,在家里吃一碗面就行了。我一个普通人,也是怕麻烦,讲究多了不自在。还是收到了祝福短信,银行发来的,社区发来的。记住我的生日的,除了家人,就是这些机构了。每年发来一次,我知道是仪器经过设置,自动发来的,我也知道,这里面有功利,我还是感受到了温暖。有总比没有强,可是,仪器知道我已经六十岁了吗?我估计不知道。这无所谓,我六十岁了,有一件事情,思谋过多次,这下可以动起来了,草滩南边的驾校,我已经联系了,报上名了,我要学开车,我要考驾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