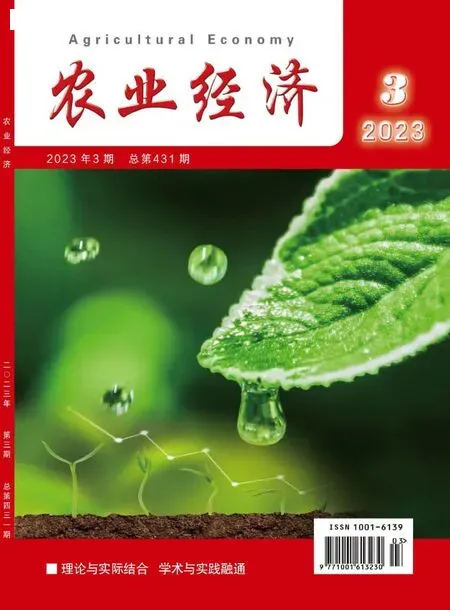行政化和自治性:村级治理中的两股力量的冲突与耦合*
◎刘香玲 马爱萍
一、引言
村级治理指的是多个主体基于一定的治理规则和治理逻辑对村庄场域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和文明等方面事务进行的协同行动过程。它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治理概念,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现代化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维度。由于村级治理赖以存在的实践场域是村庄土地这一公共资源,其上刻有社会主义集体公有制的印记,因此,村级治理离不开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这一核心命题。村级治理从某一层面来看,就是围绕集体土地所有权运行规律和内在特征的多元主体行动过程。正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天然的公私二重的属性,决定了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存在行政化和自治性两股权力的力量,且通常来讲,这两股力量处于一种分庭抗礼的状态之下,或是行政公权力“绑架”自治私权,成为主导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或是自治私权的呼声盖过行政公权力,声称要在乡村依靠自治行动实现自我管理。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时候行政化和自治性的这两股村级治理力量是冲突或是对立的,难以形成耦合协同的合力,为乡村治理提供规范化、秩序化的力量供给。为此,本文试图在对乡村治理中的这两股力量的特质进行解析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具有耦合协同的“行政化-自治性”的村级治理协同路径,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助力。
二、行政化的组织为村级治理提供稳定的公法秩序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体农村土地公有制的政治目的而设立的一种产权制度安排。它体现了国家层面的公权力意志,是国家公权力介入、深入甚至渗透到乡村社会对其进行控制的一种产权制度安排。尽管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完成了向地方政府的分权,尤其是对于农村基层社会还给予了一定的自治空间,但是只要集体土地上存在公有的性质,就必然少不了公权力的适度干预。因此,行政化的组织在农村社会得以存在并维持稳定的公法秩序也就有了正当性。具体来讲,行政化的组织从党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方针、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处理公共事务的纠纷等三个方面来维持乡村社会治理的公法秩序。
(一)党的组织在村上领导乡村治理
在乡村社会中,党的组织一直存在。无论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时期,发挥对乡村社会全面控制、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本就是一个具有强烈而浓厚政治色彩、体现党的意志的组织,还是在实行家庭承包的土地集体化时期,村民委员会和村级党支部都是实在的发挥党的宣传领导和工作部署的基层党组织。可以说,党的组织一直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的统筹领导作用。也正是因为它的存在,上级党组织有关乡村发展的指导方针都能够逐级传达到乡村社会,成为乡村治理的核心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新时期,国家更加重视乡村社会的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完善,明确了村级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地位,要求不断加强组织建设,特别是能够从返乡大学生、乡贤能人以及外出经商人士中选拔优秀的党组织队伍人员,完善党组织内部的领导力量的素质,发挥其集中力量做好乡村治理工作的人力资源队伍建设。可以说,党的组织建立在村上是一项要求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制度建设的政治任务,是乡村治理全面系统工作的重要保障。没有党的组织领导,也就无谓具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乡村治理。
(二)村民委员会或村级经济合作社为乡村治理提供基本服务
对于一些乡村来讲,由于集体经济相对不发达,在政社分离之后,只建立了村民委员会而并没有建立村级经济合作社。这一点也可以从法律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规定上得到证明。对于全部的乡村来讲,村民委员会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和发挥公法价值的基层自治组织,以全部具有农村户籍的村民作为其成员,发挥村民自治的民主功效。但它首先被定位为一个维护乡村社会稳定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村级行政组织。从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形成的那天起,农民不再是土地的私人所有者,他们被组织起来在一个特定的地域进行生产生活,交出去的私人土地所有权换回的是各自的村集体成员身份,能够凭借其成员身份资格享有在这个“小社会”中的基本服务。因此,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设计的初衷被理解为是为全体村民提供了一个以集体土地为基本资源,为其生产生活提供衣食住行等基本服务的“差序格局”的产权制度安排。
具体来讲,所有的农民被安排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地域范围内,由村民委员会或者村级经济组织为其提供承包地、宅基地以满足耕有其田、住有所居的生活,此外,还包括在集体内部的公共用地上建立科教文卫的生产生活设施,甚至包括来自政府补贴并有村民委员会或者村级经济合作社管理的各项用于生产生活的福利金等。这些资源的分配无不以村民的成员身份资格为前提。村民委员会或者村级经济合作社不过是一个将这些数量庞大的村民有机、有序地组织起来,便于生产生活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政治组织,对于这些资源的分配其并没有自主的决定权,相反是一种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和基本职责。
(三)乡政府为处理乡村自治行动中的公共事务纠纷提供纠正机制
村民自治是一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规范确立并长期发挥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价值的基层实践制度。可以说,乡村治理行动中关于村民共同利益的事项都是通过村民自治制度来实现全体村民在利益分配上的公平与效率。这是乡村治理实践中常见的一种民主决策和监督方式。然而,即便如此,依靠这种村民自治来对村民共同利益的事项进行决策和监督的私法手段,仍可能对部分村民的利益造成侵害。原因在于,每一位村民都是经济理性的自然人,都有趋利的天然内在追求,尤其是自治中采用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机制很可能以大多数人的赞成比例通过了一项对少数特定群体利益侵害的事项。在村民自治程序正当但决策内容违法的情况下,显然无法完全依靠少数利益受到侵害的群体的自力救济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时候就不得不倾向于从外部的行政力量中获得公力救济。具体来讲,这种纠正机制的发挥要求受到侵害的村民以正当合法的程序向乡政府提出为启动,原则上采取的是“不告不理”的模式。因为,乡政府作为外部公权力主体,原则上来讲没有义务也没有可能主动发现乡村治理实践中基层自治活动的展开情况。
三、自治性的村民集体民主决策和监督实现良性的集体行动
村民以民主决策和监督的方式,基于一定的自治规则对乡村内部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集体行动,是乡村治理活动中的主要力量。这种集体行动能够充分发挥村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关心乡村治理中的各项活动,形成主动性和自觉性。集体行动要求适格的村民能够以一定的自治规则即符合参与人数比例和表决通过比例对公共事务展开充分的意见表达,做到最大限度地统筹协调每一位村民的意见,以满足村民之间利益的均衡实现。
(一)确定进行村民自治的民主决策基本方案
所谓村民自治的民主决策基本方案指的是每一位村民参与决策的公共事务拥有一个基础框架,这个框架是法律为其设定的一种刚性边界。例如,关于农村承包地、宅基地的分配,无论是土地承包法还是土地管理法,都已经对此有了一些基本的规则的规定。所有的自治活动都应当按照法定的框架来形成民主决策,而法律已经给定的基础框架就是民主决策的基本方案,是不能为自治所突破的。通常来讲,这种民主决策的基本方案是由村民委员会或者是村级经济合作社的组成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按照法定框架形成的。这是交由村民自治的基本方案。全体村民能够最大限度地发表各自的意见,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都在这一法定的基本方案之内。
(二)一人一票的平等决策方式保证每一个村民参与
村级治理建立在农村集体土地之上,而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最根本的价值就在于平等性。但凡是集体的成员,每一位成员都基于平等的身份资格平等行使权利。这与资本自由结合形成的其他股份合作社有着明显的区别,后者完全是以资本的多寡来决定成员在合作社内部的决策的权重。每一位村民都是一票,平等地参与村民自治活动,这样就保证了集体行动中的每一位村民充分的参与权,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实践中集体土地征收程序前置的村民同意制度,只要有一位村民不同意政府的征收行为,后续程序就要按下暂停键。土地征收中的钉子户现象就是每一位村民平等参与自治的最好诠释。
(三)差异化的决策通过比例凸显决策事项的权重差别
对于关系到全体村民共同利益的公共事务,客观上也存在重要性程度的差异。例如,对于土地收益分配来讲,由于涉及的资金数额较为可观,自然受到村民的足够关注和重视,分配尤其需要谨慎。此时,对于土地收益分配方案来讲,原则上需要最大限度、最大可能地兼顾全部村民之间的利益,做到村民之间的利益的协调,自然也就需要占有村民人数更大比例的决策通过,才能形成最终的土地收益分配方案。相反,对于重要性程度不那么高的公共事务的决策,原则上表决通过的比例可以设定得低一点。但是,由于村民自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少数人服从多数的一种多数决定原则,因此,按照一般化的要求,只有超过半数的比例才能视为多数人同意。
在具体的决策通过比例上,一般存在过半数、三分之二以上、四分之三以上以及五分之四以上这几个通常的比例。对于重要性程度较高的公共事务的决策,显然应当选择四分之三以上甚至五分之四以上这样的表决通过比例,以体现绝大多数村民的利益诉求,反映绝大多数村民的共同意志。让绝大多数村民的共同意志代表全体村民的共同意志,至于少数村民的意见则自然被绝大多数村民的意见所吸收,最终也应当接受以绝大多数村民的意志而形成的决策方案。这就是多数决原则的体现。唯有如此,才能高效地形成最终的决策方案,否则,强行要求全部村民都作出完全一致的决策,期望达成全票通过的比例,既不现实又耗费成本,最终也必然使得自治活动难以持续下去。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差异化的决策通过比例的设计应当要考虑乡村社会的具体现实,例如,对于一些人口外流的城郊村或者城中村,由于在本村长期固定生活,以土地为基本保障的村民已经不多,对此则不应当设置过高的表决通过比例,否则很可能因为实际参与决策的村民基数较小而造成难以通过决策。
四、行政化和自治性的冲突表现及耦合路径
在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中,行政化组织提供稳定的公法秩序,而自治性的村民决策则以有效的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方案的形成,两者本来是相互融合和促进的。然而,在乡村治理中,时常发生村民委员会借着其作为乡镇一级政府代理人的身份对于乡村事务进行过度干涉,从而使得村民自治没有发挥的空间,村干部说了算就直接决定乡村公共资源和收益的分配,严重侵害了村民的合法权益。对此,在承认两者各自的重要价值的基础上,有必要寻求耦合的破解之道。
(一)合理划定行政介入乡村治理的边界
行政介入乡村治理提供稳定的公法秩序是必然的,但不得主动干预村民自治的合法空间。只有当村民自治中产生侵害村民利益的法律后果时,经过相关利益人的主动救济,行政力量才能够被动介入。因此,为了防止行政公权力对于私法自治的过度干预,应当为行政介入乡村治理划定合理的边界。这是一条刚性的边界,一经划定就具有法定的效力,不得任意变动。例如,在土地承包的事务中,行政公权力仅仅具有对村级经济合作社管理和维护农村土地承包的监督权力,要求村级经济合作社在职能范围内尽到相应的义务,对于内部的承包地分配办法则没有权力进行干预。这是村民自治自己的事情,理应交由自治进行民主决策。但同时,在村民自治中出现侵害部分村民合法权益的情形时,如在确定承包地面积时不将外村嫁入的妇女作为有效人口计算时,则显然使得这部分群体的合法承包权利排除在外,行政公权力又必须加以介入对此进行纠正。
总的来讲,行政介入乡村治理的边界是法定的、刚性的,需要由相关的立法加以明确,以规范行政权的适用和行使,保证行政权不会以其强势的地位超越乡村自治,成为独断专横的乡村治理手段。
(二)明确行政手段和私法自治的作用顺位
既然行政手段和私法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两股力量,均对乡村秩序的规范有序运行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两者在乡村社会场域发挥作用必然有其出场先后顺序。也即是说,两者有先后适用的严格规定。例如,对于农村土地征收问题,按照法定程序需要先经过村民的全体同意,尔后才能动用征收权这一行政公权力的工具,但凡是有一位村民不同意征收事项,都不得启动征收程序。因此,在土地征收事项上,以全体村民自治形成对征收事项的一致同意后,行政公权力才能介入乡村社会对具体的土地进行征收。行政手段和私法自治顺位的明确有利于保证乡村治理的良好秩序,程序法定才能保证每位村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对于两者作用顺位的规定应当在法律法规中予以明确,以体现乡村治理的程序正当性和严肃性。
(三)规范村民自治的法定程序和实质标准
村民自治作为最早在乡村社会自发形成并逐渐获得立法承认的一项基层实践制度,在解决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矛盾和冲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的背景下,村民自治的法程序和实质标准需要进一步规范,以防止私法领域内个别人凭借其先赋性的资源优势操控整个自治环节或被强势性的公权力侵害村民合法权益。在法定程序设计上,应当进一步明确村民自治适用的场景、时间、阶段等,确立村民自治形成的决策方案对于全部村民都具有法定的约束力,村民实现自身的合法权益均得依据村民自治形成的方案,任何村民不得寻求异于其他人的额外利益。而实质标准上,村民自治则应当聚焦对于具体决策的公共事务中资源和收益分配的具体规则设计,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设定相应的参考值,严格按照这一实质性标准为村民分配资源和收益,特别是当部分村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这一标准对于村民行使救济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