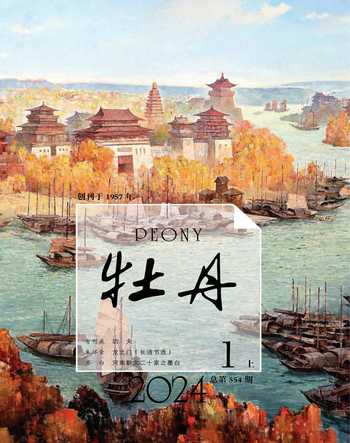我的散文观
墨白
我的第一篇散文《生命之体验》写于1992年,算来已经三十年。前些日子评论家刘宏志与我联系,说起散文观,仔细想来,我还真的没有作过这方面的文字。我写散文从来是松散的,就说最近刚刚完成的《真诚地帮助别人是一种幸福——纪念刘恪先生》,我断断续续写了10多年。要说,就以这篇为例吧。
形散神不散
2013年年底,我写了一篇《我所知道的刘恪先生》,写了我和刘恪的交往,写了我印象和感受之中的刘恪,写了那个时段以前刘恪的方方面面:他的生平,他的家乡,他的家庭、他的情感、他的性情、他的处世、他的阅读、他的视野、他的写作、他的事业,他的吃喝拉撒睡,他的油盐酱醋柴,总之,是写了有关他的事,大事或小事,各种各样的事。文章写好后,也没给他看,就放在抽屉里,没动。一直到2019年才发表在这年第3期的《莽原》上。
转眼到了2023年元月8日,一天早晨突然就传来了刘恪去世的消息,一天我都沉默不语,到了第二天我又写了一篇《真诚地帮助别人是一种幸福——纪念刘恪先生》,写了自2013年底以来10年间我们交往的点滴,其中包括从别人那里看到的关于刘恪的一些情况。到了元月11日的凌晨,我又在文章的后面作了一个《补记》,《补记》的内容是我从网络和朋友那里得到的有关刘恪的身后事,直到他入土为安。
我认为,这就是散文。有人说散文忌散,有人说散文贵散,文无定法。可是,散文不是小说,是以散为特征。但不是说散就没了章法,散文的最佳境界是形散神不散。
形散说是取材与记事。比如关于刘恪的这篇文章,取材不受空间与时间的限制,自由而广泛;神不散是说主题,文章所写事件驳杂,但始终不能跑题,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刘恪。这就像放风筝,你可以把风筝放得很高很远,但刘恪这条细细的线不能断,只要把刘恪这条线握在手中,最后才能把那只你从日出时分放出去的风筝在日落时分收回来。这其间,你可以看到天空飞过的燕子,也可以看天空里飘过的白云。天空中那只风筝的风笛声也可大可小,可远可近,你也可以海阔天空地想,也可以无边无际地念,但刘恪这根线所承载的主题始终都在。有这根线在,就能聚神,就能聚气,就可以前后有所照应。
这就叫形散神不散。但是,要做到神不散,光有这根线还不行,还要有内在结构。
散文的内在结构
不是因为散文不像小说那样依靠故事来做框架结构,就说散文没有结构。散文的内在结构,是散文的叙事语言。这就像我们人体。中医讲人体自成天地,里有五脏六腑,外有十二经脉,有奇经八脉,可谓“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身。”而语言,就是散文的心脏,主神明。神明就是精神,是散文的精气神。在这里,语言就是散文的心脏,要为全身的血液流动提供动力。我们说散文中的“神不散”那根线,是散文内容的主体,而语言的功力,则来自作者本身。你的语言有神性,血脉就畅通;你的语言有灵性,经络则发达。血脉畅通,整篇散文则鲜活,经络发达,情感才能饱满而感人。在这里,作者只有通过饱满丰富的语言,才能建构起浑然一体的叙事框架。“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是人生境界,作者的语言需要在漫长的人生修行中才能获得,没有对生活的切身的感悟,何谈“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富有人生情感的叙事语言才有质感。
叙事的质感
语言的质感就是语言的厚度,语言的厚度是由叙事语言的现场感来承担。不是说散文不写故事就会削弱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恰恰相反,散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散文的重中之重。之不过是小说对人物的塑造是虚构,是建立在艺术真实之上,而散文对人物的塑造,才是建立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常言说,画鬼容易画人难,难就难在你所写的那个人就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你怎样才能准确而形象地把生活中的那个大家熟悉的人用你的语言写活他?应该说,在散文中塑造人物不比在虚构的小说中塑造人物容易。你对人物的言行、举动、行为方式都要准确的觀察、领悟和感受,都要通过有质感的语言表达出来,他抽烟的动作、他喝茶端水杯的动作,他看人的眼神,他说话的语气都要有现场感。这样,人物才会在你的笔下活起来,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感受。
散文的信息量
其实,写好一篇好散文的难度还在于所传达出的信息量。仍以《真诚地帮助别人是一种幸福——纪念刘恪先生》为例。这篇散文共有《真诚地帮助别人是一种幸福》《我所知道的刘恪先生》和《补记》三部分结成,刘恪的出生成长与他的家乡与家族,他所走过的漫长人生路途与他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他的为人之道与处世哲学;他的思想与人生境界;他身染疾病的过程与他病中朋友们对他的牵挂;他的去世与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对他的悼念;社会对他的评价与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以及他身后所发生的与他的长眠之地,等等。这些内容虽然被分散在不同的章节里,却传达概括了刘恪的生前身后,呈现了他完整的一生。这些,必须要有准确而充足的信息量才能得以完成,而信息的传达又要自然。
以上几点,是我在漫长的散文写作过程中渐渐感悟所得,不知能不能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