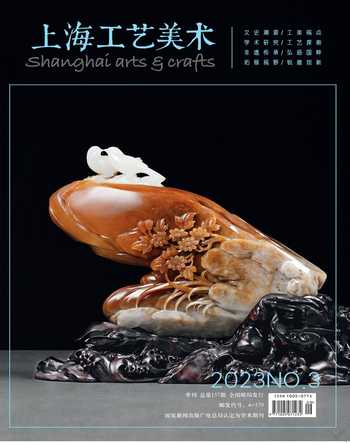月文化元素与现代日用陶瓷设计
孙梓钊



On the basis of re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moon culture elements,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are grasped. Efforts are made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hua White Porcelain, demonstrate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traditional moon culture, and achieve conversion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moon culture elements in design of modern ceramics for daily use.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新鲜的设计思潮及理念传到国内,历经四十年的探索,中国的现代陶艺立足于深厚的传统陶瓷根基,在文化愈加繁荣与多元的今日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从历史文化中挖掘设计灵感而创造更具有东方精神的作品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月文化是中国璀璨文化的一部分,从远古先民对月的膜拜到唐宋对月的描绘与歌颂,月文化的元素完成了具象到抽象再到意象的转化,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符号。在本设计案例中,笔者以月晕这一大气光学现象作为创作的主题,通过对月文化元素的重构与分析,把握内涵与外延,利用德化白瓷的特性体现月文化的意境,完成月文化元素在现代日用陶瓷设计中的转化与应用。
一、现代日用陶瓷的设计
1. 现代日用陶瓷发展阶段
陶瓷艺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我国最早对外输出文化的媒介之一。陶瓷在诞生之初便服务于人们物质生活的实用需要,而在机器化大生产中日用陶瓷的实用性已经达到高度水准的现在,人们对陶瓷的需求发生了转变。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现代陶艺应运而生。重视情感与观念表达的现代陶艺更多地被人们所需要,美观和实用不再是评判陶瓷艺术的唯一标准。因此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陶瓷扮演的角色发生了转向,日用陶瓷对于艺术性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现代陶艺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这个时期的陶艺家创作的主流方向是对于传统造型样式和形式法则的突破,陶瓷作品呈现抽象表现主义风格。同时针对借鉴西方创作的思潮,有一批艺术家开始逐渐意识到一味抛弃民族文化传统而追随西方的艺术形式,非但不利于实现个性的创作,反而只能拾人牙慧,附人骥尾,在世界艺术舞台失去自己的一席之位,于是强调自我“原创”和新的“东方式”的重要性。这与20世纪90年代后,陶艺家们开始回归传统,从传统陶瓷造型和装饰中“提取”并“组合”在一起,提出“东方方式”的创作思想也有所不同。
中西美学形式的多样性与矛盾性造成中国现、当代陶艺起步階段前二十年的“历史”错综复杂。经过四十年的探索,立足于深厚的传统陶瓷根基,近五年中国的陶瓷造型装饰设计重新焕发出活力。
2. 现代陶瓷造型装饰的审美方向
广义上,公共艺术陶瓷、装置陶瓷、雕塑陶瓷、实用陶瓷器皿、陶瓷绘画等艺术形式,凡是以陶瓷为主要材料,并依照现代艺术观念而创作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为现代陶艺。由于更加注重情感与思想观念表达,现代陶瓷的审美方向也呈现出更加多元的趋势,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向:
(1)个性美
在不同历史时期,传统陶艺在造型和装饰上呈现出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一部分陶瓷为满足平民百姓日常所需的民间陶瓷;另一部分服务于统治阶级,造型、功能都依照统治阶级的喜好来确立,大多没有个性化的展现。对于现代陶艺,封建主义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对艺术家个性的束缚,艺术家更加追求解放自我和情感表达,如由八木一夫组建的“走泥社”中的许多日本陶艺家,争相将花瓶的瓶口封闭,使实用器皿转化为“无用之物”。对于物中“用”的剥离,诉说着数千年以实用为目的的陶瓷传统被打破,以纯粹工艺水平优劣为标准的传统鉴赏标准被打破。现代陶艺作品呈现出千人千面、迥然有异的个性化风貌。
(2)材料美
材料即物质材料媒介,是艺术家宣泄情感,表达观念的物质载体。地域性的差异导致泥料与配方差异在唐朝便已经显现,早有“南青北白”的划分。而在交通物流发达的现代,材料的运输与流通的便利使得更多陶瓷艺术家选用不单一的泥料进行创作。材料的多样性使得艺术家可以依照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和情感根据光泽、色彩、肌理的需要拣选其宜,从创作之始便呈现出自身艺术特点,如广东的石湾陶塑便在现代陶艺传入中国后迎来鼎盛的时期。同时如金属、玻璃、纤维等材料与陶瓷的结合也展现出不同的风貌,拓展了陶艺的范畴。
(3)工巧美
《考工记》中有言:“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在作品的造型构建和装饰设计中,能与之相匹配的工艺技术和技巧十分重要。区别于传统陶瓷严格的成型范式,现代陶艺的创作更加自由,通过拍、捏、揉、压、刻、划、印、摔等各种手段可创造出千变万化的形态与无穷的肌理美感。加上釉料、泥料、材料、色料等装饰材料的丰富;烧造工艺的进步;气窑和电窑的普及;3D 打印技术的完善;以及柴烧的复兴;坑烧、乐烧、苏打烧等技术的引入,作者创作时可以自由地将多种新旧技术结合运用,从而使陶瓷作品展现出更加丰富的装饰语言和艺术表现力,为现代陶艺的发展繁荣创造了无限的空间。
一般来说,现代陶艺家为了在作品中展现思想观念和情感表达,自由运用各种材料和技术,最终呈现出个性美、材料美、工巧美相统一的状态。
二、中国传统月文化的概念
1. 中国月文化的演变及其历史背景
月亮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景物,也是中国一种传统的文化符号。从远古先民对月的膜拜到唐宋对月的描绘与歌颂,月完成了具象到抽象再到意象的转化,一代代文人以月寄情,赋予月亮独特的文化意蕴和哲学内涵,由此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月文化。
在上古时期,从事采集和狩猎的人们根据月的阴晴圆缺、循环往复认定其具有不死或再生的力量,是死而复生、主宰万物生长的象征。《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此始浴之月。”月也是人们生殖崇拜的精神图腾;同时也有着让万物生长的力量;智慧的先民对月观察掌握了月相的变化规律,创造了阴历,结合阳历为农种提供了节气指导依据。在远古时期的人们无法解释风雨雷电、地裂山崩,因而人们对月朝拜,认为“日月山川皆为神祇”,体现的是原始观测手段下对宇宙的感悟,这是先民最早对月的印象。
在山东大汶口遗址出土的陶樽上刻有“日月山”符号,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文字的雏形。在良渚遗址也有类似的发现。
从先秦《诗经》中的“月初皎兮”“如月之恒”,和《楚辞》多次出现描写月景的诗句可以看出人们在祭月同时也开始了对月的欣赏。两汉时期,月亮成为乐府诗和赋中的常见题材。西汉的公孙乘于《月赋》中写到“月出皦兮,君子之光。鹍鸡舞于兰渚,蟋蟀鸣于西堂。君有礼乐,我有衣裳。”将皎洁月光称为君子之光,将月光与君子的操守与品格挂钩。在这个阶段,月文化已经发展出丰富精彩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意蕴。到了唐宋时期,“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刚伐桂”“唐明皇游月宫”等神话故事开始被民间结合串联起来,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而唐诗宋词又将对月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意象推向了高峰。
2. 月文化意象与其符号的意义
意象一词的源出最早可追溯到《周易·系辞》。其述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像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表“观物取象”之意。子曰:“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圣人立象以尽意。”因此,意象:古义应“表意之象”,书与言不都能尽言尽意,而象可以尽意,形象思维,在实际上确立了中国传统审美偏重“意象”的思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最早以文艺视角提及意象,“意象”一词实际上已成审美活动之本体性范畴。随后是唐诗宋词将月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意象推向了高峰。诗人们对月亮有了素娥、玉轮、婵娟、玉钩、广寒等别称,也构造出“隔千里兮共明月”的对望月怀人的惆怅情境;“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希冀和渴盼;“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忧伤;“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对时光永恒的感慨。在诗词中蕴含的情感总能使人受到感动与共鸣。月亮已不再是纯客观的物象,当各种各样的情绪统统堆积在明月之上时,月已是不折不扣的符号。明月因作为物本身的特点和人们对其对认识与审美,呈现出多元的意象,形成形神兼具、虚实相生、变幻有序、损益互补的美学观念。因此月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情感符号和美学符号。
三、月文化元素的提取、转译与在设计中的运用
1. 对月文化元素的提取
月意象的所指,不仅是诗人文学思想的凝结,而且是形象本身的延伸、扩展和升华。《华严经》说“月印万川”;长屋王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天上一轮月,地上万人情。千百年来,月亮承载着人们内心深处诸多的情感,而其中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便是月文化中蕴含的思乡情感。最初与中秋团圆这一历史传统有关,与月本身的特性息息相关。明月能以同样伟大的宽容待普天之下的游子,不论是浪迹天涯、漂泊江湖,还是客居异乡、寄人篱下。在诗人以明月返照“乡思”成诗的过程,诗人与读者之间因生命背景各异、生活经验差异而产生的感情隔膜被打破,明月的照耀下,因为时间和空间所产生极具普遍性的思乡之情受到同样的慰藉。
中国千年的月文化积厚流光,每当人们在夜晚抬头望月,脑中便会翻涌起浓重的乡愁,不禁思量远方的亲人是否也在观赏着这同一轮明月。月光的美也牵动着人们的心神。身处异乡,对月的审美情趣和心神共鸣是笔者本次创作的缘由。
2. 月文化元素在造型和装饰的转译
当光透过高空卷积云,受冰晶折射作用,月亮周围会产生层层的光圈,这种光学现象被称为月晕。作品造型的灵感便来源于此。在造型上,抛弃日用瓷器的传统器型,以几何图形制作基本造型,用变形的圆来表现月亮和月光的形态,茶壶、公道杯、茶杯三个物体分别做出正圆、椭圆、半圆的变化。通过对月元素进行进一步的提炼,以扩散的圆形表现层层的月晕,装饰融入造型之中,呈现出有一定规则的凹凸面变化,表现明月的辉光。灯光下映射出如丝如纱、飘零婆娑的月影,营造情感和审美上的统一。
在茶壶和公道杯中,装饰被进行归纳与概括为层层向外扩散的圆弧,在视觉上呈现出扩张感;层层装饰最终在内圈的视觉中心彻底融入造型,以镂空处做为把手,又呈现内敛趋势,整体造型回归到凝练、稳重的状态。作品中的杯子两面有对称的层层圆弧,在烧制过程中借助拉力自然产生不影响使用的轻微形变。这种对随机性的追寻既是笔者试图对千篇一律的工业生产痕迹的干预和消弭,更是对月有阴晴圆缺的感悟。作品的三个单体都以圆为基本形态,其中壶倾向于正圆;公道杯倾向于椭圆;茶杯倾向于半圆,三者和而不同,在保证作品统一性的前提下展现更加丰富的视觉效果。同时作品左右呈对称状,体现“圆、稳、匀、正”的特点,与月亮圆润的形态相符。
在材料上笔者选用了家乡泉州的德化白瓷。德化白瓷选料精良,制作精美,釉质细腻,胎质紧密,光泽如绢,凝脂如玉,自然大气,一眼看去晶莹润泽。若置于强光照射之下,内部结构清晰可见。由此可见,德化陶瓷具有细致的美感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因其艺术特征和自身魅力突出,享有盛名,被赋予了“中国白”的美誉,是传统文化的优秀载体。德化白瓷拥有与月亮一样让人有同样清凉、柔软的体验。与笔者在案例中用来表现明月清晖的意图相得益彰,共同营造清静之感和给人带来主观的温暖感受。
四、结语
在此设计案例中,笔者从对月的情感着手,对中国月文化的来源和符號意义作了一定意义的探讨。在作品构思阶段,不仅将视野关注在陶瓷界的前辈们身上,对其他形式的美术作品和文学作品进行了学习和吸收,并最终在作品上将学习的成果进行了呈现,完成了一次月文化在现代日用陶瓷设计的运用。
参考文献:
[1]李正安.陶瓷设计[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2]杨永善.陶瓷造型基础[D].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80.
[3]徐海霞.我国现代日用陶瓷产品创意设计研究[J].景德镇陶瓷学院,2013.
[4]白明.关于中国现、当代陶艺的思考[J].文艺研究,2003(1):124-130.
[5]杭间.寄予希望的设计:超越日常性[J].装饰,2023(1):12-16.
[6]周虎.论月文化的意象之美在紫砂壶中的体现[J].江苏陶瓷,2020,53(5):64-65.
[7]张辉煌.论德化白瓷的艺术特色及影响[J].名家名作,2020(1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