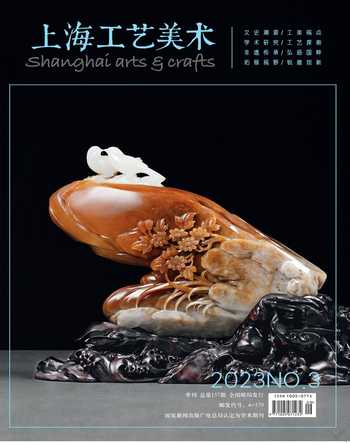从古江南到古中国
陈晴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n modern China, the ancient human groups, which scatter like sparks, gradually disperse and converge to form a number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al circles with different features and mutual influences,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current diversified and integrated Chinese culture. The early civilization, represented by the Songze-Liangzhu Culture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is period.
公元前六千年左右,人类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跋涉后终于跨入了文明的门槛,北纬30°附近亚洲和非洲大陆上的远古社会,纷纷进入了早期国家的阶段。由尼罗河三角洲、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一路向东,到达今天中国境内的黄河、长江流域,如星火散布的古人类族群逐渐由分散而集中,形成了多个面貌互异而又相互影响的考古学文化圈,奠定了今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基本面貌。而长江下游的崧泽—良渚文化所代表的早期文明,正是这一时期中国文明的杰出代表。
最早江南
追溯长江下游远古文化的源头,已发现的有距今10000~8000年左右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距今7000年前后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等,这些原始文化基本上独立发展,个性鲜明,各区域之间并无显著的联系,显然尚未形成统一的文化共同体。大约距今5800年左右,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继马家浜文化而起,并与长江下游的诸多其他古文化如北阴阳营、凌家滩、薛家岗等相互影响,构成了文化特质较为相似的“崧泽文化圈”,又称为“大崧泽文化”,其影响北越长江直抵江淮,南渡钱塘进入宁绍平原,向西则到达了今天的安徽境内,可以说,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古江南”此时悄然成型。
更令人瞩目的是,崧泽文化圈中的一些聚落中首次出现了超大面积的中心聚落,在人口数量、大型建筑、高等级墓葬、精细的手工艺品、原始宗教和艺术等诸多方面,处处体现出由财富到阶层乃至权力的分化,标志着社会已告别了田园牧歌式的早期阶段,向着文明的高阶发展,进入了古邦国时代。
在江苏张家港东山村的崧泽遗址中首次发现了高等级的大墓及大型房址,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而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的凌家滩遗址,则出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工祭坛、大型墓地、祭祀坑、积石圈、环壕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陶器、石器,显示出其卓然自立,作为区域性中心聚落的地位。在大型祭祀遗址中,不但出土了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石钺和玉璜以及造型奇特的龙首形玉器,还发现坑内大部分器物均经高温焚烧,表现出独特的制度性特征。在2007年发现的23号墓葬中,出土了多达330件的陪葬器物,其中200件玉器密集分布于墓中,是同时期考古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在该墓的填土上方更出现了一件长75厘米,高38厘米,重约88千克的大型圆雕石猪,周边布满回填的石块,反映出此类大墓的特殊葬俗,表明墓主与众不同的高贵身份。另外,1998年发现的29号墓中,发现了一件身上饰有象征太阳的八角星纹,双翼作猪形的玉鹰,融太阳崇拜、鸟崇拜、猪崇拜于一体,表现出原始宗教的神秘性。同墓出土的还有著名的凌家滩玉人,是新石器时期罕见的全形人像,冠带佩玉,状若祈祷,似可指向墓主身份与宗教的紧密联系。而上海青浦寺前村遗址出土的一件崧泽双层镂孔花瓣足陶壶,口沿与圈足皆呈花瓣形,腹部分内外两层,内层起实际承装功能,外层刻镂圆圈及三角纹,与足部镂孔相呼应,起纯装饰作用,说明崧泽先民在追求器物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已经开始了审美与艺术创作。
实证文明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长江下游各区域之间的文化联系愈趋紧密,距今5300年左右,以浙江余杭为中心的良渚文化强势崛起,势力范围更加扩张,而文明程度亦显著进步。世界考古学泰斗、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认为:“良渚遗址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
与崧泽时代相比,良渚文化的大型聚落数量更多,而且可以明显地区分为中心聚落、次级中心聚落并附着有众多散布的一般性聚落,形成了金字塔形的聚落级差,反映出良渚社会的复杂结构,印证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广域影响的区域性国家。
在浙江余杭良渚文化的遗址中,不但发现了拥有城郭、面积分别近800万和300万平方米的内外城,还在内城中发现了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和专门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在外城中发现了宏大的水利系统及用于天文观测和祭祀的大型祭坛。其规模之宏大,规划之完整,是世界早期城市文明的典范,被认为是良渚国家的“王城”。而远离浙江的上海福泉山、常州寺墩,则是拥有高等级墓葬和大型祭祀遗址的次级中心聚落,可视为良渚国家的“节点城市”。
支撑这些城市运转的,无疑是良渚国家发达的经济基础。在余杭和宁波的良渚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面积巨大的古稻田。这些稻田是世界上最早和最大的稻作文化遺址,它们规划整齐,被划成规整的“井”字形,并拥有河道、河堤、田埂、灌溉水渠等完整的配套设施,标志着良渚社会成熟的农业体系和生产组织能力,也反映了当时可能拥有的人口规模。而如此水平的生产力必然导致可观的粮食剩余——在良渚古城中曾发现大型的储粮遗迹,其残存稻谷量有20万千克之多。同时,这也使手工业分工得以更充分的发展。
良渚时代的手工业专业化程度已非常发达,生产的种类有石器、陶器、骨角器、漆木器、玉器和纺织品等,各门类器物又有丰富的应用类别如工具、日用器、装饰品、礼仪器等,而且制作精美,体现出高度的设计水平和工艺技术水平。比如良渚文化中典型器的玉琮,既有高达33.2厘米、分为十一节的多节型玉琮,也有上下两节,形态低而扁的矮琮,还有用作装饰品的琮型小玉管。它们一般都经过管钻,并在表面装饰有标准模式的神人兽面纹。这类纹饰不但各自具有适应自身体积的协调比例,且往往线割、细刻、浮雕兼施,造型和纹饰相得益彰,显得极为精致优美。此外,透雕玉器、嵌贝漆器、細刻黑陶、彩绘陶器,也堪称当时的“高科技”产品。
无论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还是精美绝伦的玉器的制作,都远非一人一时之力可达,必然要求具备十分细致规范的生产分工和系统的生产组织。在良渚遗址群及其周边发现了多处制玉作坊,发掘出大量玉料、制玉工具和半成品,表明了当时专业化手工业规模之大、程度之高,也显示出当时良渚社会存在着大量的非农业人口。这些人口居住于城市内外,主要为城中高阶层的统治人群提供专门的服务。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曾对世界上另外三个著名的古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文明进行研究,并于1950年发表《城市革命》一文,以城市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而良渚遗址高度发达的城市形态,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
作为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统治阶级及保障其特权的专门制度的出现也是一项重要指标。良渚文化中的用玉制度充分反映了良渚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复杂的礼仪规定。在各个遗址中,贵族墓地往往随葬有远多于普通人的玉器。余杭良渚古城中的王族墓地位于反山,随葬玉器级别之高、数量之多堪称“豪华”,其中仅12号墓就出土随葬品658件,包括重达6.5千克,迄今所见体量最大、雕琢最为精美的“良渚琮王”。琮一般被认为是用以沟通天地的法器,是良渚神权的象征。在高等级的贵族墓葬中普遍出现了装饰有复杂神徽的玉琮,神徽系由上半部头戴羽冠的神人和其下蹲踞的神兽组成的神人兽面纹,神兽的面部和双眼被突出地表现,具有神秘狞厉的美感。这种神徽广泛地装饰于各种类型的器物之上,体现出良渚社会统一的原始宗教信仰。而对装饰有神徽的玉琮的专有,则代表了良渚贵族对于神权的掌控。与神权相应的,还有贵族对于世俗权力的垄断。玉钺是一种专用的礼器,往往出现在高等级的贵族墓葬之中,最高等级的墓葬中还出现有装饰以豪华瑁镦的组合玉钺。而在福泉山和反山高级墓葬中出土的饰有神徽的象牙权杖及其残迹,更说明了当时王权的森严。
艺术的发展是人类精神文明演进的标尺。良渚时代的艺术装饰,较之崧泽时代简约概括的艺术风格,显然更为精致和细腻,无论是日常器物还是礼仪用品的装饰都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比如玉串饰是一种日常可见的装饰品,但良渚时代的作品不仅制作精细程度进步良多,在色彩和组件形式的配伍上也都显示出更为成熟的设计感。至于每每见于各种玉器上的良渚神徽,即便是在面积十分有限的配件如瑁、镦、玉管上进行装饰,也始终坚持在器物表面采用多层次的减地浮雕和细若游丝的繁复细刻相结合,形成纤细与突出的层次对比和丰富的节奏变化。而这种对规整和精细的追求在陶器的制作上也同样得到印证。
从经济到科技,从宗教到艺术,从习俗到制度,良渚文化用丰富而广泛的实物遗存向我们展示了5300年前江南大地上日新月异、生机勃发的社会大变革。恰如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年前所指出的那样:“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何以中国
距今大约4300年前,经历了一千余年发展,盛极一时的良渚文化不知何种原因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然而其高度发达的文明却已经在时空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当良渚文化兴盛之际,其“影响所及几乎达到半个中国”。向北,苏北鲁南的大汶口文化中经常可见良渚遗物,显示良渚文化的影响已深入该文化圈的中心地带;往西,良渚风格的遗物在安徽、湖北的同期遗址中多次出现,而在南面,良渚文化的身影甚至越过南岭到达了广东,在沿海的海丰地区出现了良渚式的玉琮。
在良渚文化消亡之后,其文明的余响仍久久地回荡在今日中国境内的各个区域。良渚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玉琮在各地都发现了仿制品,远及山东海岱地区,山西中原的陶寺文化,陕北的石峁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和长江中游两湖地区。直至商周,琮、璧等礼用玉器的基本形式仍在礼仪体系中得以保持,并被《周礼》固化为中国传统礼制的一部分流传数千年。而良渚神徽独特的构图方式和多层装饰的表现手法,也在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中获得了发展。同样被延续的文明因素还有江南地区至今不替的稻作农业技术,双层环护的城市营建传统和干栏式建筑及土木工程和水利系统的建造方式等等。这些我们日常随处可感知的文化元素早已深深地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永续而时新,并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图谱上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建构了历史、当下和未来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