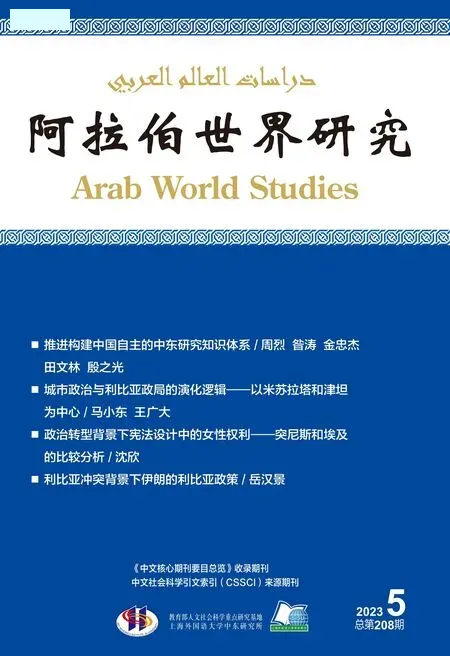城市政治与利比亚政局的演化逻辑
——以米苏拉塔和津坦为中心*
马小东 王广大
一、 引言
中东许多民族国家作为西方殖民体系瓦解后的历史继承物,国家构建并不完善,大量依托传统认同存在的超国家行为体(如阿盟等泛阿拉伯组织)、跨国家行为体(如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组织、“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和次国家行为体(国内以部落、教派和族群等为核心要素的团体)与民族国家争夺民众基础、治理空间乃至国家最高权力。中东民族国家处在各种次国家和超国家行为体的双重挤压之下异常脆弱,各种冲突频发。(1)刘中民:《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缘何紧张?——次国家行为体视角的分析》,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5期,第60页。次国家行为体不仅是影响本国治乱的重要势力,还具有较强的跨界渗透能力,可能对地区安全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因而成为观察地区局势的重要视角和研究对象。
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内部冲突频繁,派系斗争激烈,至今仍处于中央政府不统一、安全环境碎片化的“弱政府”状态,持续影响北非和欧洲地区安全。利比亚同样也存在次国家行为体影响国家构建的问题。利比亚问题专家拉谢尔认为,利比亚的家族、部落、非国家武装团体和城市(城镇)等各类地方行为体围绕国家权力和资源的竞争严重阻碍利比亚统一。(2)Wolfram Lacher, “Families, Tribes and Cities in the Libyan Revolution,”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VIII, No. 4, Winter 2011, p. 140.在诸多次国家行为体中,部落和武装团体是分析利比亚政局发展的两类重要地方行为体。部落和部落主义在利比亚根深蒂固,(3)参见王金岩:《利比亚部落问题的历史考察》,北京:北京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王金岩:《试析部落在利比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载《学术探索》2019年第8期,第51-58页;蒲瑶:《利比亚内乱的部落文化解读》,载《世界民族》2013年第1期,第21-28页;闫伟、韩志斌:《部落政治与利比亚民族国家重构》,载《西亚非洲》2013年第2期,第115-133页。部落、种族的差异矛盾是利比亚社会政治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利比亚地理上的三分(4)传统上利比亚分为三块地区:西部的黎波里塔尼亚、东部昔兰尼加和南部费赞。导致三个地区部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每个地区都有独特的部落组成。(5)Mohamed Ben Lamma, “The Tribal Structure in Libya: Factor for Fragmentation or Cohesion,” Fondation Pour La Recherche Stratégique, September 2017, https://www.frstrategie.org/web/documents/programmes/observatoire-du-monde-arabo-musulman-et-du-sahel/publications/en/14.pdf, 上网时间:2022年8月15日。三个地区的部落分别与突尼斯、埃及西部和乍得湖地区的跨国部落存在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部落差异性、部落政治和部落矛盾冲突严重阻碍利比亚形成团结统一的社会凝聚力和统一国家。(6)Ali Abdullatif Ahmida, The Making of Modern Libya: State Formation, Colonization, and Resistan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p.56.各类武装团体涌现是革命后利比亚政局十分突出的现象,学界对利比亚武装团体的兴起、类型、地域性差异、与中央政府的互动机制、互动模式及其非法经济活动等方面,已经展开了较为详尽的研究。(7)秦天:《利比亚民兵武装组织》,载《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10期,第28-31页。Brian McQuinn, “After the Fall Libya’s Evolving Armed Groups,” Small Arms Survey, Working Paper No. 12, 2012; Wolfram Lacher “Social Cleavages and Armed Group Consolidation: The Case of Khalifa Haftar’s Libyan Arab Armed Forces,” Studies in Conflict &Terrorism, 2021, DOI: 10.1080/1057610X.2021.2013757; Joelle Rizk: “Exploring the Nexus Between Armed Groups and the Trafficking and Smuggling of Human Beings in the Central Sahel and Libya,” Studies in Conflict &Terrorism, 2021,DOI: 10.1080/1057610X.2021.2002687; Buyisile Ntaka and Lszló Csicsmann, “Non-state Armed Groups and Statebuilding in the Arab Region: The Case of Post-Gaddafi Libya,”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8, No. 4, 2021, pp. 629-649; Tim Eaton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Libyan Armed Groups Since 2014,” Chatham House, March 2020,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CHHJ8001-Libya-RP-WEB-200316.pdf; Sara Merabti, “Ruling in the Name of the Revolution: The Local Grounding of Non-State Armed Groups in Western Libya,” Interdisciplinary Political Studies, Vol. 5, No.1, 2019, pp. 89-114; Emadeddin Badi, “Exploring Armed Groups in Libya: Perspectives on Security Sector Reform in a Hybrid Environment,” Geneva Centre for Security Sector Governance, 2020, https://www.dcaf.ch/ex ̄plo ̄ring-armed-groups-libya-perspectives-ssr-hybrid-environment, 上网时间:2022年8月14日。武装团体间的斗争引发社会撕裂、破坏公共安全秩序,严重阻碍国家统一。
尽管学界从部落和武装团体的角度对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政治局势已有深入研究,但已有文献仍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对城市这一次国家行为体关注不够,二是对城市和部落、武装团体间的区别与联系展现不够。事实上,城市行为体与部落和武装团体既紧密相连,也有其独特之处。相较于部落和武装团体,城市行为体的独特之处在于城市占有永久地理空间,能为其政治行为提供共同的政治身份想象和持续的物质保障。城市也总是和工商业紧密相连,工商业为城市带来丰厚的物质基础和高效的社会网络,城市中的业缘是形成城市凝聚力和身份认同的又一要素。
诚然,以部落和部落主义为纽带的社会网络依然是很多利比亚人赖以获得情感慰藉、安全保护、工作机会、物质财富的主要依托,部落长老等部落精英组成的各类委员会在基层民众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人际关系的调节作用,但部落更多是一种基层社会组织,部落的定居化和城市化促使部落血缘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凝聚力内嵌于城市之中,构成城市社会网络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城市身份认同的有机组成。城市不仅是社会共同体,还扮演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功能。城市在维持社会秩序与安全、推动经济发展、保障民生、提供政治参与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经历长期城市化发展的利比亚是北非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8)数据来源:“Urban Population (% of Total Population) — Libya,”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URB.TOTL.IN.ZS?locations=LY,上网时间:2022年8月18日。城市已成为该国最重要的一类政治和社会组织结构,以城市地缘为纽带的政治力量正成为重要的政治行为体。以城市为核心的地方认同,以城市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在利比亚政局发展中更为关键。利比亚动乱之后,国家权威暂时性丧失增强了城市等地方行为体的政治自主权,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度大大降低,城市开始承担传统上由中央政府承担的资源集中、权威价值分配的政治组织功能。后卡扎菲时代兴起的武装团体,尤其是大型武装团体往往依托于主要城市存在,同时服务于城市的政治目标。大部分有影响力的武装团体是城市的武装团体,城市为武装团体提供合法性和物质支撑,武装团体为保卫城市而战。
利比亚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活动集中在该国十几个主要城市。(9)John R. Allen et al., “Empowered Decentralization: A City Based Strategy for Rebuilding Libya,”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February 11, 2019,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9/02/Empowered-Decentralization.pdf. 上网时间:2022年8月20日。但米苏拉塔和津坦两座西部城市因其强大的武装力量和在中央政府机构中的影响力而表现出对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政治进程的特殊影响力。在中央政府无法垄断暴力的动荡环境中,武装力量的强弱是支撑城市进行政治角逐,左右政治议程和分配国家石油收入最重要的底层支撑。米苏拉塔和津坦在推翻卡扎菲的内战中形成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受米苏拉塔和津坦等城市控制的“革命旅”掌握着利比亚75%~85%经验丰富的战斗人员和武器。(10)Brian McQuinn, “After the Fall Libya’s Evolving Armed Groups,” p.13.在中央政府层面,来自两座城市的政治和军事精英也占有突出的地位。目前,东西两个政府总理(11)两个政府及其首脑分别是:位于首都的黎波里的民族统一政府(GNU)总理阿卜杜勒哈米德·德拜巴(Abdul Hamid Dbeibeh),2021年2月开始担任总理。利东部国民代表大会于2022年2月推选的法西·巴沙加(Fathi Bashagha)。都来自米苏拉塔,津坦军事领导人历来在西部政府内政部和国防部中担任要职,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在国家政治中突出的影响力。后卡扎菲时代国家经济收入依然依赖石油出口,米苏拉塔和津坦因其政治和军事影响力而对石油收入的分配享有较大话语权。甚至有学者将米苏拉塔和津坦等重要西部城市比作“城邦”(city-state)。(12)Christian Caryl, “Islands in the Desert, The Problem, and the Promise, of Libya’s New City-states,” Foreign Policy, August 14, 2013.
利比亚其它主要城市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并未体现出像米苏拉塔和津坦这样能够成为独立行为体的特点。首都的黎波里虽是利比亚首位城市,(13)首位城市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等级系中,规模最大且不成比例地大于其他城市的城市,该概念由地理学家马克·杰佛森于1939年首次提出。但更像是各类地方势力的聚合地和竞逐空间。的黎波里城市内也存在四五支具有影响力的武装团体(14)Jason Pack, Kingdom of Militias: Libya’s Second War of Post-Qadhafi Succession, ISPI Report, May 17, 2019.,但相互间的竞争远大于合作, 难以统一起来代表的黎波里在国家层面为城市自身争取利益,各类势力的复杂存在使该城市难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体。在东部,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和国民代表大会所在地托布鲁克在政治上也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两者都处于军事强人哈夫塔尔的控制之下。相比于西部,东部在哈夫塔尔的控制之下呈现出更为浓厚的“地区主义”,单个城市的角色反而并不突出。在南部,最重要的城市是塞卜哈,但该城市一方面因相互敌对的多种族、多部落共居一市而缺乏凝聚力,另一方面也因缺乏强大的武装力量而难以具有更广泛的政治影响力。因此,本文选取米苏拉塔和津坦这两座后卡扎菲时代最具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西部城市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城市行为体对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政局的影响。
二、 利比亚城市政治的观念和组织基础
分析米苏拉塔和津坦为代表的利比亚城市在利比亚社会政治中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先要考察它们能否作为独立的政治行为体。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行为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团,只要其显示出足够的行为内聚性,便可被看成是一个单一的实体。(15)李金祥:《国际体系变迁的动力: 一种非国家行为体的视角》,北京:时事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具有自身特殊的身份和利益、一定的内聚力及稳定的组织形式,构成了行为体的重要特征。(16)陈岳:《国际政治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6页。
(一) 利比亚城市的身份认同和利益
2011年利比亚政权更迭改变了城市的地位、角色和权力体制。第一次内战(17)本文中的利比亚第一次内战特指2011年卡扎菲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力量之间的暴力冲突,下文“战后”一词特指第一次内战后。相应地,第二次内战指2014~2015年以哈夫塔尔为中心的东部武装力量和以“利比亚黎明”为中心的西部武装力量间的系列暴力冲突。第三次内战指2019年4月哈夫塔尔利比亚国民军发起的旨在攻克首都的黎波里的战争。后城市的身份更加突出,城市的利益进一步扩展,城市权力(18)城市权力指一座城市对其它城市、中央政府等行为体的影响力,而非指城市内部的权力结构。不断扩张。实际上,利比亚始终存在着忠诚对象问题,国家不是唯一的忠诚对象,对城市、部落和家族的忠诚广泛存在于国家内部。在利比亚,对城市、部落和家族的忠诚甚至要强于对国家的忠诚,这严重削弱了国家认同。(19)Amal Obeidi, Political Culture in Liby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104.利比亚城市有着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文化,市民有着强烈的城市身份认同。国家这一概念及其背后包涵的统一和秩序理念在利比亚人的记忆中是短暂的,起码要短于城市的存在。伊德里斯王朝时期(1951~1969年),利比亚仍是一盘散沙,行政上依然延续着历史上东西南三部分各自为政的局面。卡扎菲统治的四十多年里,一个统一的利比亚国家概念才逐渐固定下来。因此,利比亚人想象一个城市共同体可能比想象一个国家共同体更为容易。对许多利比亚人来说,他们的身份和利益的视野往往只延伸到社区这一狭窄的范围内。上述特点在第一次内战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大多数武装团体都围绕一个部落或城市组成,大多数武装团体的活动范围都不超出自己特定的领土范围。
城市独特的身份认同和忠诚根植于市民独特的历史记忆。米苏拉塔、津坦和拜尼沃利德等城市都将本城市的“光辉历史”追溯到意大利殖民时期(1911~1933 年),将自己标榜为反抗殖民者的英雄,并产生独特的历史记忆和叙述。如被认为支持卡扎菲的拜尼沃利德人认为,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构成现代利比亚国家的领土一直被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沿海地区的“城邦”一直被来自地中海其他地方的征服者所统治。(20)Jonathan M. Winer, Origins of the Libyan Conflict and Options for Its Resolution, Middle East Institute Report, May 2019, https://www.mei.edu/sites/default/files/2019-05/Libya_Winer_May%202019%20update_0.pdf, 上网时间:2022年8月25日。作为内陆城市的拜尼沃利德视自己为抵抗惯于和外部势力勾结的沿海城市的内陆城市的桥头堡,第一次内战是沿海城市在外国势力的操纵下对内陆城市的又一次打压。第一次内战也赋予了利比亚城市新的身份——“革命城市”和“忠诚城市”。“革命城市”,如米苏拉塔、津坦、班加西、托布鲁克、扎维耶和柏柏尔城镇等是反对卡扎菲的城市;“忠诚城市”,如苏尔特、塔尔胡纳、拜尼沃利德等是忠诚于卡扎菲的城市。“革命城市”与“忠诚城市”之间的裂痕和冲突构成了内战后不久利比亚国内冲突的主要形式。在2014年后东西部的对峙中,苏尔特、塔尔胡纳和拜尼沃利德等不被西部信任的城市,成为哈夫塔尔联盟的对象和进攻西部时极力争取的对象。
城市共同的身份决定了第一次内战时期和战后政治进程中城市共同的政治目标和利益。第一次内战期间,城市最主要的目的是保卫本城市免遭卡扎菲政权的武力镇压,进而推翻卡扎菲政权。战后,在围绕国家最高权力斗争中,城市的最低目标是自己不被排除在新的国家权力核心之外,保障本城市在新政权、新国家秩序中有足够的代表和参与度。最高目标则是由本城市主导国家最高权力。这一点在第一次内战后历次政治和谈、新政府构成等方面体现得较为明显,无论是和谈代表还是新政府关键职位都是以城市和地区为基础进行分配。城市和地区代表在和谈及政府机构中尽力维护本城市和地区的利益。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城市内部也有政治派系分歧,但这些团体始终拥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即在政治和经济上保障本城市在国家重建中的地位。(21)Jason Pack, Kingdom of Militia’s: Libya’s Second War of Post-Qadhafi Succession, ISPI Report, May 2019, p. 27, https://www.ispionline.it/sites/default/files/pubblicazioni/ispi_analysis_libya_pack_may_2019_0.pdf, 上网时间:2022年8月25日。
(二) 利比亚城市的内聚力
较强的城市内聚力是维系城市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基本要素。据滕尼斯对共同体的研究,城市能否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共同体与其所处的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政治权力关系有关。(22)[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1页。在特定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下,城市可以成为拥有共同传统、共同利益、共同身份认同和共同政治目的内聚性实体。利比亚城市在2011年内战及战后政治进程中表现出较强的内聚力。这种内聚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该城市由传统价值观、城市内血缘、业缘关系网络等凝结成的固有社会联系;二是自2011年内战以来持续的暴力冲突进一步加强了城市固有内聚力。
利比亚西部城市固有内聚力首先来源于城市内部对部落等传统组织及其价值观的保留、由血缘、业缘等纽带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滕尼斯认为城市能否成为共同体与城市规模有关,认为共同体只能在小范围内自然形成,工业革命前的早期城市中还保留着一些共同体的生活方式的特征,而当城市发展为大城市时,这种特征就完全消失了。(23)同上,第92页。利比亚城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城市规模相对较小,除首都的黎波里和班加西是人口百万级别的城市外,其它城市主要是人口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中小型城市。这些中小城市基本上还是“熟人社会”,市民间有着较为紧密的社会联系。利比亚城市的部落血缘影响依然存在,血缘家庭关系依然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纽带,而且城市内部地缘和血缘相互捆绑,特定的部落生活在特定的区域内。个人对家庭组织、家族势力有很强的依附性。利比亚城市化虽然推进较快,但传统与现代的割裂并不十分严重,城市仍然保留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一个特定的共同体通常有共享的观念和文化,从而形成和支撑成员的行为规范。(24)褚松燕:《个体与共同体——公民资格的演变及其意义》,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如很多城市仍然设有由长者、智者、宗教人士和达官贵人等组成的非正式社会协商机构“调节委员会”,发挥着部落首领的作用。同时,人们也基于职业分工、行业利益等形成“工会”等特殊的业缘团体。滕尼斯认为因共同工作而产生的友谊也是形成共同体思想的来源之一,城市是这种纽带经常联合和维系的最佳空间。(25)[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第67页。市民能够通过家族、部落等传统关系网络联合成一个整体。2011年内战爆发之初,利比亚西部城市的革命武装几乎都是熟人相互联络建立起来的小团体,小的武装团体不断合并成较大的军事组织。
城市凝聚力不仅源于其固有特征,也是与外部力量进行集体斗争的结果。2011年以来的历次暴力冲突和对外斗争加强了城市的内聚力。市民因共同备战、共同作战而凝聚到一起,联合起来寻求胜利,获得安全,形成战斗共同体。2011年以来,大多数利比亚城市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暴力冲击。以米苏拉塔为例,2011年遭受了卡扎菲最血腥、最漫长的围攻,2014年与津坦武装爆发冲突,2016年打击崛起的“伊斯兰国”以及2019年抵御哈夫塔尔的攻击,其间还多次爆发小规模冲突。米苏拉塔人所遭受的共同创伤和胜利成为米苏拉塔个人和集体叙事的核心原则。(26)Brian McQuinn, “History’s Warriors: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Battalions in Misrata,” in Peter Cole and Brian McQuinn, eds., The Libyan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30.暴力冲突对社会结构、网络关系、边界和身份具有变革性影响。比如,暴力会激活社会边界,敌对双方用城市、部落等社会组织类别来定义对方,这种定义在互动过程中会不断自我加强甚至极化。(27)Collins, Randall, “C-Escalation and D-Escalation: A Theory of the Time-Dynamics of Conflic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7, No. 1, 2012, p. 5.持续的战争催生了由强大的集体认同所支撑、由强大的精英所领导、具有凝聚力、社会嵌入的力量,进一步增强对城市身份的认同、自豪感和内聚力,促使经历炮火洗礼的城市成为更有能力、更独立的政治行为体。战后,米苏拉塔等城市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价值观——革命价值观。战后历次冲突中,“保卫革命果实”是米苏拉塔和津坦等城市常用的政治宣传和动员口号。
(三) 利比亚城市的组织者和组织形式
城市的行为最终还是城市中人的行为。最能代表城市行为的是“城市精英”及他们组建的各类城市管理组织。利比亚城市精英既包括部落首领、宗教长老、望族家长、商人领袖和武装团体领导人等传统精英,也包括城市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如知名律师、教师、医生等行业精英。他们中的政治精英及其组成的政治组织往往代表着城市的施动者。
城市政治精英的行为代表城市的意志,而非仅仅个人的意志,他们寻求的是整个城市的利益,而非仅仅是个人利益。对于城市精英而言,他们追求个人政治目标,对外寻找联盟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内部分歧,但跨越政治的城市社会关系会对他们的行为形成强制约。(28)Wolfram Lacher, Libya’s Fragmentation: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Violent Conflict, New York: I.B. Tauris, 2020, p. 161.这是因为,城市精英的威望和权力基础来自于他们宣称代表城市的民众和利益。城市精英对城市利益的背叛意味着其群众基础的丢失和政治前途的覆灭。他们行为的底线是不能损害本城市的利益。城市精英机会主义倾向越明显,在本城市能够获得的支持就会越少,这显然不利于在国家层面的政治角逐。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精英网络。由精英们构成的城市管理组织是将不同网络连接在一起的组织保障。在米苏拉塔和津坦,一般有三类城市管理组织。一是基于民众选举和以“市议会”(municipal council)为核心的市政官僚体系,尽管市政部门许多官员的任命仍需中央层面授权,但由于当前利比亚中央政府过于软弱,地方官僚体系人员任命几乎在地方层面掌控中。二是由军事部门和安全部门组成的城市“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是第一次内战期间及战后混乱的安全秩序促成的特殊临时性组织。虽然在有些城市军事委员会的权力要远大于市政官员的权力,但随着国家重建进程加快,战争威胁减少,国家逐步正常化后,军事委员会的重要性也会逐步下降。三是城市长者和名人组成的协商和调解机构“智者委员会”。该机构通常是顾问机构,或为政治精英出谋划策,或承担着调解城市内部矛盾冲突的重任,在米苏拉塔和津坦当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独特的身份认同、共同的利益认知、强有力的城市内聚力以及明确的城市施动者,都是保障城市能够作为一类行为体的基础要素。这些要素在城市权力的加持下,赋予城市更高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三、 利比亚城市政治的现实权力基础
城市作为独立的政治行为体不仅需要身份认同和利益认知等观念层面的支撑,更需要一定的政治、安全和经济权力支撑。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强大的城市武装力量、依托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城市内聚力、对特定“领土”范围内经济和安全秩序的控制以及与外部势力的紧密联系是米苏拉塔和津坦等城市在革命后政治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地方权力中心的现实权力基础。(29)Ibid., p. 12.
(一) 地理因素是米苏拉塔和津坦崛起的有利因素
革命后米苏拉塔和津坦崛起成为有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城市,这与两座城市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不无关系。它们要么靠近边境、海岸,便于与外界联系,接受外界物资,要么所在地理环境复杂,易守难攻,便于保存实力。
米苏拉塔是利比亚第三大城市,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城市,利用作为港口城市的地理优势发展地中海贸易,积累了大量资本和深厚的国内外商业网络。米苏拉塔历来都是利比亚与海外贸易、沟通内地,连接东西南三部分的重镇,(30)Ronald Bruce St John,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Libya, Lanham: The Scarecrow Press, 2006, p. 168.以其商业活动而闻名。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国内外商业网络成为米苏拉塔在 2011年能够挺过卡扎菲政府围攻并进行反攻的重要因素。米苏拉塔的资本支持建立和维持了其主要武装力量。第一次内战后,米苏拉塔将这些优势以及在内战中获得的资本转换为政治力量,争夺国家最高权力和国家资源。一个突出的例证是,一批显赫的米苏拉塔商人兼政治家领袖在革命后的利比亚政坛崛起。(31)如在2016年4月至2021年3月担任过渡民族团结政府副总理的艾哈迈德·迈阿提克(Ahmed Maiteeq),自2021年3月开始担任过渡民族统一政府总理的德贝巴(Abdelhamid Dabaiba)和2022年2月单方面宣布代替德贝巴的位于利比亚东部的政府总理巴沙加(Fathi Bashagha)等。
位于纳福萨山地区的津坦是继米苏拉塔之后西部地区的第二大革命堡垒。(32)Emilie Combaz, Key Actors, Dynamics and Issues of Libyan Political Economy, Helpdesk Research Report, April 2014, p. 6.津坦因特殊的地理优势而在第一次内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里海拔较高、地形复杂,拥有天然地理屏障,周围还有其他小城镇拱卫。无论是2011年卡扎菲向纳福萨山地区推进,还是2014年米苏拉塔企图进攻津坦,都必须考虑津坦易守难攻的山地地形。津坦距离首都的黎波里和突尼斯边境都较近,这意味着战争中津坦更容易与外部保持陆地联系和货物转运,而且能够迅速抵达首都郊区。2011年政府军在纳福萨山地区举步维艰,山区成为革命者的大后方,来自东部以及外国的援助源源不断地从突尼斯边境进入利比亚,津坦成为战争物资的重要储存地,并在给西部前线分配物资方面拥有发言权。第一次内战后,津坦不断将其革命资本转化为争夺国家权力的武器,获得了超过其人口规模的政治影响力。
(二) 排他性“领土”占有是城市获得权力的基础因素
与利比亚部落相比,城市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控制特定的地理空间。20世纪70年代前,部落也曾占有特定土地。但1969年后,利比亚革命确定的发展农业目标之一是摧毁部落土地所有制,实现社会主义。部落深度参与社会治理,垄断着土地和水源,利比亚政府通过在沙漠地区建立村社和实施生产计划,打破部落垄断,实现地区间平衡发展。(33)韩志斌:《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2页。至1970年代后期,部落已经逐渐失去经济自主权,石油租金分配已取代畜牧业成为国家经济基础,国家也不再需要税收,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组织形式遭到严重侵蚀。部落声称对“领土”拥有“主权”已不再可能。
在战时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下,“领土”控制和国家机构接管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为积累权力和财富提供了机会。因此,第一次内战后城市对周边“领土”即机场、港口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是利比亚冲突逻辑的组成部分。各城市间,尤其是敌对城市间广设哨卡,居民穿越敌对城市领地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例如,2012年米苏拉塔对拜尼沃利德的战争起因之一,就是拜尼沃利德扣押了几个途径该城市的米苏拉塔人。机场和港口作为货物进出口的节点具有战略价值。2013年,津坦人控制了的黎波里唯一能运行的米蒂加机场后,津坦人的政治对手几乎无法通过机场旅行。(34)Wolfram Lacher and Alaa al-Idrissi, “Capital of Militias: Tripoli’s Armed Groups Capture the Libyan State,” Small Arms Survey Briefing Paper, June 2018.这是导致后来津坦人被驱逐出机场和首都的因素之一。第一次内战后,部分城市以武装力量为后盾,与周围城市爆发暴力冲突,夺取可耕种的农业用地等有价值的“领土”。(35)Wolfram Lacher and Ahmed Labnouj, “Factionalism Resurgent: The War in the Jabal Nafusa,” in Peter Cole and Brian McQuinn, eds., The Libyan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80.在纳福萨山地区尤为明显,津坦和柏柏尔城镇依靠在内战中积累起来的武装力量不断向南扩张。(36)Ibid., p. 278津坦的军事扩张主义是造成革命后纳福萨山地区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津坦部落和马莎夏(Mashasha)部落之间历史上存在分歧,革命后混乱的安全环境使更强大的津坦有机会控制马莎夏部落的土地和水资源。(37)“Barred from Their Homes: The Continued Displacement and Persecution of Tawarghas and Other Communities in Libya,”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3, https://reliefweb.int/report/libya/barred-their-homes-continued-displacement-and-persecution-tawarghas-and-other, 上网时间:2022年8月23日。同时,柏柏尔城镇的势力也在南移,与南方的城镇和部落结盟,党同伐异。部分柏柏尔城镇如哈瓦米德(Hawamid)、卡巴(Kabaw)和阿拉伯城镇希岸(Si’an)和巴德尔(Badr)等因争夺农业土地多次爆发冲突。(38)Abigail Corey and Esra Elbakoush, “Amid Libyan Crisis, Two Hostile Towns Build a Basis for Peace,” USIP, June 2020 , https://www.usip.org/blog/2020/06/amid-libyan-crisis-two-hos ̄tile-towns-build-basis-peace, 上网时间:2022年8月28日。因此,与战后利比亚中央权威衰落相对的是,城市等非国家行为体对“领土”的排他性占领、对边境的实质性管控,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各类资源的争夺。
(三) 武装独立是城市保持独立性最重要的保障
第一次内战后,利比亚非国家武装团体作用非常突出。城市以武装力量为后盾,对内控制“领土”内安全秩序,代替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对外与其它城市竞合,形塑利比亚国家安全形势。
战后城市武装力量的形成仍需追溯到第一次内战期间。随着反抗卡扎菲政府的起义在各城市爆发,米苏拉塔、津坦和班加西等城市迅速建立起所谓“军事委员会”来指挥反对现政权的战斗,确保必需品的供应。这种模式很快在全国城市中得到复制,(39)“Holding Libya Together: Security Challenges After Qadhafi,”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December 2011, https://www.crisisgroup.org/middle-east-north-africa/north-africa/libya/holding-lib ̄ya-together-security-challenges-after-qadhafi, 上网时间:2022年8月20日。短短数月内各类武装团体持续涌现,最多时达到数百个,在国家层面有影响力的武装团体不下数十个。游行示威者通过联络其他城镇革命力量,夺取政府军火库,积极对外联系取得外援等方式形成了本城镇的军事力量。大多数在昔兰尼加以外组建的革命武装力量的最初目标是保护当地社区的小股武装力量,最终发展成为成熟的武装团体。(40)Wolfram Lacher, “Fault Lines of the Revolution: Political Actors, Camps and Conflicts in the New Libya,” SWP Research Paper, May 2013, 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cations/products/research_papers/2013_RP04_lac.pdf, 上网时间:2022年8月25日。在的黎波里,卡扎菲部队撤退后的几天里,出现了几十个军事委员会。(41)“Holding Libya Together: Security Challenges After Qadhafi,”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December 2011, p. 17. https://www.crisisgroup.org/middle-east-north-africa/north-africa/libya/ho ̄ld ̄ing-libya-together-security-challenges-after-qadhafi, 上网时间:2022年8月20日。这些委员会很快成为“革命”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并成为当前分散权力结构的雏形。(42)Mattia Toaldo, “Decentralising Authoritarianism? The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the New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Involution of Post-Qadhafi Libya,” Small Wars &Insurgencies, Vol. 27, No. 1, 2016, p. 42.战后武装力量地方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国过渡委员会”(NTC)等历届中央政府都未能成功解散地方武装力量,重建国家安全机构。战后,大多数武装团体不愿放弃新获得的武器和独立性,(43)Roland Friedrich and Francesca Jannotti Pecci, “Libya: Unforeseen Complexities,” in Paul R. Williams and Rebecca I. Grazier,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Post-conflict State Building,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0, p. 125.武装团体都在尝试通过模仿正规军队的组织实现自我正规化和制度化。它们成为城市和地区内公共安全的提供者和秩序塑造者。
战后有影响力的武装团体突出的特征是具有城市性和地方性。大部分利比亚武装团体基于地理分布,与特定城镇或地区相联系,依靠城市存在,是城市政治力量的延伸,城市社区为武装力量提供至关重要的人力、财力和后勤支持。根据麦奎因(McQuinn)的分类,(44)将利比亚武装团体分为四类:一是根植于当地社会,受城市政权影响和支配的革命部队;二是游离于当地城市政权之外,不受节制的非正规革命部队;三是革命后兴起的不受城市政权控制的队伍;四是犯罪团伙、极端组织等构成的民兵。不受城市控制的“民兵”只占利比亚武装团体的2%左右。(45)Brian McQuinn, “After the Fall Libya’s Evolving Armed Groups,” p. 32.最重要的武装力量围绕六个主要城市或地区形成和活动,即的黎波里、津坦、米苏拉塔、利比亚中部(包括苏尔特和朱弗拉)、利比亚南部和利比亚东部(包括班加西、迈尔季、苏克纳、托布鲁克、艾季达比耶和德尔纳)。几乎每个武装团体领导都带有强烈的地方特色。革命部队指挥官往往表现出对家族、社区和城市领袖的忠诚。武装组织领导人无法仅仅依据自身的最大利益和风险得失来灵活反映和调整自己的政策,(46)Wolfram Lacher, “Social Cleavages and Armed Group Consolidation: The Case of Khalifa Haftar’s Libyan Arab Armed Forces,” Studies in Conflict &Terrorism, 2021, DOI: 10.1080/10576 ̄10X.2021.2013757.他们必须和当地政治领导、商业精英、家族长老等进行复杂、非正式的谈判和协商,共同作出决策。(47)Wolfram Lacher, Libya’s Fragmentation: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Violent Conflict, p. 104.基于城市的武装力量除了保护本城市的安全,捍卫本城市的利益外,很少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议程。因此,就权力和影响力而言,利比亚城市之间的互动更具决定性意义。就津坦和米苏拉塔而言,它们的武装力量是西部地区最强大的两支军事力量,为两座城市在国家层面争夺权力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四) 对经济的有力控制是城市长期保持独立性的关键因素
第一次内战后,城市等地方权力中心加强了对国家经济的控制。各类经济资源是地方权力中心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争夺的主要对象。战前利比亚主要依赖石油经济,石油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的90%。劳动力就业也主要在高度依赖石油收入的公共部门。目前,利比亚国家收入依然依赖石油出口。战后武装冲突和暴力犯罪使石油行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出现重大混乱,石油被高度武器化。(48)Richard Baltrop, “Oil and Gas in a New Libyan Era: Conflict and Continuity,”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February 2019, https://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9/02/Oil-and-Gas-in-a-New-Libyan-EraConflict-and-Continuity-MEP-22.pdf, 上网时间:2022年8月25日。缺乏经济来源而拥有武装部队的地方权力中心对石油基础设施、石油收入和石油经济的占领成为各派势力斗争的主线之一。对立派别之间争夺对石油设施和国家石油公司(NOC)的实际控制权。(49)Ibid.各城市都在尽可能多地抢占石油资源,通过财政划拨和为武装团体支付工资等形式瓜分石油收入。
石油收入并非地方权力中心唯一的经济来源。控制走私交易、经营黑市以及税收也是权力争夺的一部分。走私经济历来是利比亚某些区域非正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纳福萨山区—突尼斯边境走私、东部托布鲁克—埃及边境走私、萨布拉塔石油走私、南部边境走私等都是利比亚走私贸易发达的地方。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虽然也存在走私和人口贩运等犯罪活动,但整体可控。革命后,随着国家军队和安全部队的瓦解,燃料、毒品甚至是人口等走私经济在利比亚部分城市越发猖獗。城市为这些非法经济活动提供便利和庇护,甚至从中获益。如在突尼斯边境,革命前努瓦里(Nuwail)和希岸两个城镇控制着对突尼斯的走私。革命后,柏柏尔城镇纳鲁特利用他们对过境点的控制与努瓦里和希岸争夺走私贸易份额。日益猖獗的边境走私也引起了津坦人的兴趣。2012年8月,利比亚国防部长津坦人乌萨马将纳鲁特至加达梅斯边界的边境管辖权授予津坦部队。(50)Wolfram Lacher, Ahmed Labnouj, “Factionalism Resurgent: The War in the Jabal Nafusa,” in Peter Cole and Brian McQuinn, eds., The Libyan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81.费赞地区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与南部邻国的合法和非法贸易。跨撒哈拉走私路线已从合法商品的非正式贸易通道演变为武器、毒品、燃料、假冒香烟和人口走私的渠道。2016年,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到地中海的陆路为走私者和贩运者创造了高达15亿美元的收入。(51)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Global Study on Smuggling of Migrants, 2018.祖瓦拉、扎维亚和萨布拉塔等沿海城市,深度参与海上和陆上石油等多种形式在内的走私经济,每年从中赚取数亿美元收入。
税收是地方权力中心创收的另一种途径。战前的利比亚,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很少将税收作为财政来源途径。战后利比亚石油收入下降,城市财政更为拮据。税收作为一种“开源”的方法在地方层面开始实施。2014年以来,贝达市议会一直努力确保从地方税收、甚至市政警卫和交通警察的罚款中获得地方收入。兹利滕市是利比亚最大的两家国有水泥厂所在地,市政府对购买水泥者征税。在部分城市,当地武装团体向当地市场或企业“征税”以换取“安全”。在首都的黎波里的阿布斯利姆区,市议会对市场交易商和企业征税,“收益”被重新投资于公共工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保护已经常规化和制度化。部分城市从战时经济产生的可观收入中受益。战时经济中的激励制度已成为其持续存在的原因,阻碍了国家权力在地方和国家层面的重新确立。
总之,革命后利比亚的政治秩序不再是中央—地方的等级秩序,而是以多个主要城市为中心的平行秩序。城市等地方权力中心形成了倒置的等级秩序,从中央提取它们想要的东西。(52)Philippe Droz-Vincent, “Competitive Statehood in Libya: Governing Differently a Specific Setting or Deconstructing Its Weak Sovereign State with a Fateful Drift Toward Chaos?,” Small Wars &Insurgencies, Vol. 29, No. 3, 2018, p. 442.
四、 西部城市竞合与利比亚政局的演化逻辑
2011年第一次内战后,利比亚又爆发了两次内战,国家机构多次分裂。宏观上看,利比亚的分裂呈现出东部和西部两大地区间的巨大张力;但在地区内部,尤其在西部,既不受制于中央政府,也不相互统属的城市在战略条件不断变化的战后环境中争权夺利对利比亚政治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战后十多年利比亚政局的演变无不与米苏拉塔、津坦等城市力量的此消彼长、相互竞合有关。城市间关系直接影响到冲突爆发与否,中央政府统一与否。
(一) 西部城市间竞争是导致第二次内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2011年内战爆发后不久,反对派力量便于3月成立了主要由东部地区代表、前政府叛逃高官和流亡人士组成的临时中央权力机构——“全国过渡委员会”。该委员会并没有实质性的权力基础,其权威很大程度上只来自国际社会的承认。在地区内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米苏拉塔和津坦等地方武装力量才是利比亚的实权派。同为革命堡垒的米苏拉塔和津坦在战后并未携手重建利比亚,而是为各自城市利益发生摩擦乃至暴力冲突,成为2014年内战爆发的推动因素之一。
2011年8月至2014年2月这段相对稳定的过渡期内,利比亚逐渐发展出两组矛盾。一是米苏拉塔和津坦之间的矛盾。(53)第二次内战前较大的津坦武装有三支,卡阿卡旅(Qa’qa’ Brigade)、萨瓦克旅(Sawaeq Brigade)和乌萨马·朱瓦里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卡阿卡旅和萨瓦克旅与哈夫塔尔关系密切,哈夫塔尔还任命了一名津坦军官担任其利比亚西部指挥官。乌萨马领导的津塔武装和哈夫塔尔保持距离。2011年8月随着米苏拉塔和津坦等革命力量进入的黎波里,它们开始在国家机构内外拓展影响力。津坦寻求与其力量不相称的政治权力和地位遭到米苏拉塔的反对。二是来自米苏拉塔的革命强硬派(54)如米苏拉塔国民议会成员阿卜杜拉赫曼·苏维赫利(Abderrahman Sweihli)和萨拉赫·巴迪(Salah Badi)。联合其它城市的强硬派及伊斯兰主义者与围绕在哈夫塔尔周围的世俗主义者、前政府高官及东部地区自治运动者的矛盾。米苏拉塔最终和班加西地区哈夫塔尔的打击对象班加西革命者协商委员会(BRSC)等伊斯兰武装分子结成事实上的联盟,津坦则和哈夫塔尔领导的各派系结成战术联盟,由此形成了2014年内战中的两大松散联盟。米苏拉塔发动“利比亚黎明”行动打击津坦武装等“反革命力量”,保卫革命果实,哈夫塔尔发动“尊严行动”反击伊斯兰主义者和恐怖组织。
米苏拉塔革命强硬派主导的《政治隔离法》引发了国民议会内部的第一次严重分裂和政治格局的深远变化。《政治隔离法》的通过意味着前全国力量联盟(NFA)成员、部分津坦领导人和哈夫塔尔等人被边缘化甚至会被追究法律责任。津坦力量在国民议会中被削弱,津坦和米苏拉塔间的冲突开始螺旋式上升。(55)如2013年6月津塔部队袭击了位于的黎波里的爱国阵线总部。2013年10月,一个隶属于利比亚革命行动室(LROR)的米苏拉塔武装组织绑架了总理扎伊丹,导致扎伊丹在的黎波里不断升级的控制权斗争中站在津坦一边。与此同时,班加西局势也在不断恶化。2014年2月,哈夫塔尔宣布,不再承认国民议会和《宪法宣言》,并要求将权力移交给总统委员会,三个月后发动“尊严行动”,在班加西等东部城市清除他所称的以班加西革命者协商委员会为代表的极端分子。该组织许多领导人出身于与米苏拉塔有广泛社会联系的班加西家庭。班加西革命者协商委员会依靠米苏拉塔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西部的资金、武器甚至士兵。哈夫塔尔与班加西当地部落阿瓦齐尔(Awaqir)结盟,该部落公开宣称要将所有“米苏拉塔人”(56)班加西当地很多家庭与米苏拉塔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联系。班加西当地部落认为这些家庭并不是真正的班加西人。赶出班加西。同月,津坦武装卡阿卡旅(Qa’qa’ Brigade)和萨瓦克旅(Sawaeq Brigade)袭击了国民议会,促使米苏拉塔武装再次返回的黎波里,与津坦当地武装发生重大冲突。
2014年6月,国民议会再次举行选举,但选民参与率仅为2012年的三分之一。到选举前夕,双方零散的冲突发展为全国性对抗,暴力取代了国家政治进程。7月7日,选举结果公布,伊斯兰主义者和米苏拉塔势力在新议会中的议席占有率大幅下降,引发的黎波里西部又一轮大规模冲突。7月13日,以米苏拉塔为首的武装力量袭击了卡阿卡旅和苏瓦克旅在的黎波里的基地及其控制的战略要地米蒂加机场,这场战役迫使津坦人团结一致。津坦人认为,这并不是针对卡阿卡旅和苏瓦克旅的袭击,而是对整个城市的战争。随后,多数大型米苏拉塔部队加入打击津坦武装的“利比亚黎明”(57)大多数直接参与发动利比亚黎明的人物都是当地民兵领导人,而不是国家级的政治战略家——巴沙加除外。“利比亚黎明”行动的核心是一个主要由伊斯兰民兵组织领导人组成的网络,但组成此次行动军事重量级人物的米苏拉塔部队的领导层与该网络是分离的。行动,国家陷入全面内战。8月4日,新选举的国民代表大会(HoR)在东部托布鲁克召开首届会议,继续保留萨尼政府。米苏拉塔及西部其它有影响力的城市代表均抵制此次会议。8月底,米苏拉塔将津坦武装完全赶出米蒂加机场和的黎波里。同月,西部革命强硬派代表在的黎波里重新召开国民议会,委托奥马尔·哈西(Omar al-Hassi)组建政府,否认国民代表大会合法性。至此,利比亚国家机构第一次一分为二,出现两个平行的政府和议会。
(二) 西部城市力量缺席导致民族团结政府缺乏权力基础
2014年下半年,米苏拉塔武装一方面在纳福萨山区与津坦武装周旋,另一方面向东部推进。2015年2月开始,米苏拉塔内部温和派寻求与津坦武装及哈夫塔尔武装和谈。3月底,米苏拉塔武装撤出锡德拉湾(As Sidr)地区,停止向东推进。4月,米苏拉塔最大的两支武装海勒卜斯营(Halbus Battalion)和马赫朱卜营(Mahjub Battalion)公开主张全面停火。同时,联合国积极推动双方接触,最终于2015年12月组建民族团结政府(GNA),但该政府的缺陷在于缺乏权力基础,如同先前的“全国过渡委员会”一样,其最大的资本是国际社会的承认,但未获得两大正式机构国民议会和国民代表大会中任何一方的支持和批准。所谓《利比亚政治协议》(LibyanPoliticalAgreement) 只是两个议会中部分议员以个人身份签署,许多实权派机构如米苏拉塔军事委员会、津坦军事委员会等并未明确表示支持该政府。换言之,民族团结政府只是联合国议程强行拼凑的机构,缺乏统一全国的权力基础。对民族团结政府的承认与否又引发了东西部政治势力新的分裂,两方内部都出现了支持和反对该政府的派系。
民族团结政府组建后西部地区局势出现两个特点。其一,中央政府依旧软弱,受到部分的黎波里民兵组织保护才得以在的黎波里立足,但米苏拉塔、津坦和哈夫塔尔武装等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几乎都游离在民族团结政府之外。其二,西部城市内部分歧开始明显化。米苏拉塔内部分为,以巴沙加为代表的温和派主张与东部和民族团结政府接触,与以阿卜杜拉赫曼·苏维赫利和萨利赫·巴迪为代表的与伊斯兰主义者联系紧密的革命强硬派拒绝谈判。尽管在政治上分为温和派和强硬派,但这些团体在社会层面的联系依旧紧密,它们有共同的政治目标,即在政治和经济上保持米苏拉塔的地位。(58)Jason Pack, “Kingdom of Militia’s Libya’s Second War of Post-Qadhafi Succession,” ISPI, May 17, 2019, 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lication/kingdom-militias-libyas-second-war-post-qa ̄dhafi-succession-23121, 上网时间:2022年9月1日。津坦也是如此,尽管津坦也分为乌萨马领导的主张支持西部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一派和哈立德·阿米安尼(Khaled al-Amiani)领导的对米苏拉塔态度强硬的一派。尽管如此,津坦仍然是利比亚最统一、最有凝聚力的城市。(59)Buyisile Ntaka and Lszló Csicsmann, “Non-state Armed Groups and State Building in the Arab Region: The Case of Post-Gaddafi Liby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8, No. 4, 2021, p. 635.
(三) 西部城市力量相对弱化是第三次内战爆发的关键因素
自民族团结政府成立至第三次内战爆发,利比亚政治僵局持续了数年。其间,在预期无法用武力迫使对手屈服的情况下,各派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并从中受益,同时加强在中央层面对石油收入等国家资源的争夺。此间,东、西部力量消长发生变化。西部陷于派系斗争,东部哈夫塔尔从经济、安全和领土控制等领域全面加强实力。相对实力不断强化增加了哈夫塔尔以武力取胜的预期,最终导致哈夫塔尔发起了第三次内战。
民族团结政府入驻的黎波里后,西部陷于派系斗争。第二次内战后,的黎波里民兵组织不断壮大。2016年年中至2017年5月,它们将其它对手逐出首都,在国家机构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形成数个民兵卡特尔。(60)Wolfram Lacher and Alaa al-Idrissi, Capital of Militias: Tripoli’s Armed Groups Capture the Libyan State, Small Arms Survey Briefing Report, June 2018, p. 9.民兵组织将首都分割占领,对政府机构肆意敲诈勒索,严重阻碍民族团结政府正常运行。(61)2012年,首都的黎波里有多达30个有影响力的武装团体,经过数年的分化重组后,至2017年中,有四个主要民兵组织控制着的黎波里,即是黎波里革命旅(Tripoli Revolutionaries Brigade)、纳瓦西旅(Nawasi Brigade)、特种威慑部队(Special Deterrent Forces)以及阿布·斯利姆中央安全部队(Abu Slim Central Security Unit)。详见Wolfram Lacher and Alaa al-Idrissi, Capital of Militias: Tripoli’s Armed Groups Capture the Libyan State, p .9。此外,的黎波里还有少量米苏拉塔武装,如301旅。但一般认为,该旅的领导层来自米苏拉塔,士兵则来自其它地方,并不是真正的米苏拉塔武装。米苏拉塔和津坦大部分武装力量退回各自城市,在的黎波里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从2017年底开始,米苏拉塔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对的黎波里民兵组织对国家机构的控制感到不满,部分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联合其它城市力量多次企图攻入的黎波里,驱赶首都民兵。2018年8月,双方在首都南郊爆发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的大规模冲突。津坦军事领导人乌萨马趁机将部队部署到的黎波里西部近郊。利比亚西部和南部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变得更加支离破碎。
同时,哈夫塔尔从各方面加强实力,在东部建立了较为统一的中央集权权力架构。政治方面,哈夫塔尔与国民代表大会、当地部落、城市精英、萨拉菲派宗教精英结成联盟,尽可能扩大政治基础。安全方面,自2014年至2019年2月,哈夫塔尔完全控制德尔纳,逐步清除伊斯兰武装组织。经济方面,哈夫塔尔控制中东部地区油田和码头,获得与西部政府以及国家石油公司谈判的筹码,进而获得稳定的预算。此外,哈夫塔尔军队还通过“特许经营”垄断东部贸易,获得资金。(62)Tim Eaton, The Libyan Arab Armed Forces: A Network Analysis of Haftar’s Military Alliance, Chatham House Research Paper, June 2021, p. 20.社会治理方面,哈夫塔尔实施军事统治,深化与萨拉菲派的合作,加强对东部社会的控制。军事方面,哈夫塔尔的部队从米苏拉塔手中接管了塔曼汉特和朱夫拉空军基地,进一步巩固了战略地位。对外关系方面,哈夫塔尔不仅巩固了与俄罗斯、埃及和阿联酋等国的关系,在控制了中东部油田后,西方国家也在重新评估哈夫塔尔统一利比亚的可能性。西部持续分裂和东部哈夫塔尔综合实力提升极大地改变了第二次内战后形成的东西部力量平衡。2019年4月,哈夫塔尔对的黎波里发动突袭,第三次内战爆发。共同的威胁很快促使米苏拉塔、的黎波里民兵组织、津坦主要武装(63)部分有萨拉菲主义倾向的津坦武装支持哈夫塔尔对西部的进攻。、柏柏尔城镇、扎维耶等西部重要城市和武装力量迅速团结起来,共同御敌。(64)Wolfram Lacher, “Think Libya’s Warring Factions Are Only in It for the Money? Think Again,”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0,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19/04/10/think-libyas-warringfactions-are-only-it-money-think-again/?utm_term=.4a4f1caa72c2, 上网时间:2022年9月5日。
(四) 城市精英分化直接导致国家机构再次分裂
西部城镇的团结、国家石油收入的骤减和土耳其的支援使哈夫塔尔攻克的黎波里的目标落空,此次军事对抗在2020年6月后陷入僵局。在由双方军事领导人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65)又称“5+5委员会”,是东西部各出5名军事代表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最初是柏林进程三大框架之一,2020年10月负责监督停火协议的执行,现在仍然是利比亚东西方政治进程的沟通平台之一。的主导下,双方于10月达成停火协议。几周后,联合国推动各方在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LPDF)框架下谈判,最终于2021年2月由论坛选举出新一届政府机构——总统委员会和新总理,并在同年12月24日举行大选。3月,新总理德贝巴组建2014年8月以来第一个东西部统一的政府——民族统一政府(GNU)。新的国家机构依旧由地方代表按一定比例构成,三名总统委员会委员分别代表利比亚西部、东部和南部。德贝巴政府的关键职位则由不同城市代表瓜分。(66)Wolfram Lacher, Libya’s Flawed Unity Government: A Semblance of Compromise Obscures Old and New Rifts, SWP Comment, April 29, 2021, p. 3.
原定于2021年12月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由于缺乏足够的政治和解和信任以及各种内外力量的复杂矛盾最终流产。2022年2月,利比亚东部国民代表大会单方面宣布推举巴沙加为总理,要求西部民族统一政府总理德贝巴下台。德贝巴拒不让位,坚持继续执政,直到选出代表全体国民意愿的民选政府。东西方新的分裂再次出现,利比亚又一次出现两个平行政府竞争合法性的局面。
从整体上看,此次竞争虽仍在东西对峙的框架内,但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方面,米苏拉塔城市精英的角色更加突出。作为革命后最强大的地方权力中心,米苏拉塔城市精英在历次冲突和历任过渡中央政府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德贝巴和巴沙加在东西部政府中的地位凸显出米苏拉塔城市精英中的实权派在国家层面从幕后走到台前。德贝巴和巴沙加都是商人政治家,均在卡扎菲时期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在2011年革命中凭借雄厚的财力支持米苏拉塔武装力量。德贝巴的支持者包括一些较强大的米苏拉塔武装力量,以及来自的黎波里郊区获得土耳其支持的民兵组织,背后有其堂兄兼商业伙伴阿里·德贝巴作为后盾,后者是利比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67)“Who Are Libya’s New Leaders?,” Orientxxi, February 20, 2021, https://orientxxi.info/magazine/who-are-libya-s-new-leaders,4539, 上网时间:2022年9月10日。巴沙加的权力基础主要包括米苏拉塔武装希廷旅(Hiteen Brigade)、的黎波里及其周边地区当地武装(68)如的黎波里革命旅前指挥官海瑟姆·塔朱里(Haitham al-Tajouri)领导的777旅,穆斯塔法·卡杜里(Mustafa Kaddour)领导的纳瓦西旅(Nawasi Brigade)等。以及哈夫塔尔国民军的支持。
另一方面,巴沙加和德贝巴的斗争加剧了利比亚的冲突。被任命为总理后,巴沙加急于用武力进入米苏拉塔取代德贝巴。2022年春以来,因巴沙加强行进入的黎波里而爆发的武装冲突已发生数次,但均未成功。双方的暴力斗争无疑恶化了西部地区的安全局势,进一步分化了西部地区的政治力量。最后,德贝巴和巴沙加的斗争使得津坦及其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再次凸显,甚至有分析认为津坦可能决定利比亚的未来。(69)John A. Lechner, “Will Zintan Determine Libya’s Future?,” Foreign Policy, July 16,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7/16/zintan-libya-militias-tripoli-dbeibah-bashagha-haftar/, 上网时间:2022年9月10日。津坦的武装力量足以改变利比亚西部乃至整个利比亚脆弱的军事平衡。津坦,2014年是米苏拉塔的敌人,2019年是抵抗哈夫塔尔的合作者,现在又成为米苏拉塔派系争相拉拢的对象,其政治地位无疑在上升。
五、 余论
2023年以来,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以下简称“联利支助团”)推动下的利比亚政治进程并无实质性进展。利比亚各派仍无法就宪法草案、选举法和选举路线图等问题达成一致,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武装团体、部落、城市和地区等地方权力中心难以就利益分配达成一致。中央政府被严重“地方化”的背景下,政府领导人利用国家机构为各自“地方”谋取利益。在地方权力中心武装力量势均力敌,均无法用武力取胜的情况下,各派和解成为利比亚走向统一的唯一可能途径。
城市是利比亚政治进程中最活跃、最有凝聚力的行为体,可成为利比亚重建的积极因素。虽然城市间的权力斗争和资源争夺阻碍了利比亚国家重建进程,但利比亚安全和政治秩序的恢复还有赖于城市间的谈判、协商甚至最终和解。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利比亚国家重建扶助的关注点多放在中央政府层面,期望通过选举等方式首先建立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进而自上而下地推动国家进入有序状态。只关注地位和权威有限的中央政府而忽视地方权力中心间的相互博弈,很难理解利比亚国家重建进程走向。以联利支助团为代表的联合国调解固然重要,但利比亚革命后的国家权力分配更多还是掌握在拥有武装和财力的地方实权派手中。因此,利比亚国家建构既需要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从上到下推动建立有权威的国家机构和中央政权,也需要关注地方势力自下而上的竞合动态。
利比亚根深蒂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并非发端于2011年。后卡扎菲时代的政治过渡不仅要重塑国家机构,还要完成国家宣布独立60年以来未完成的国家建构任务。利比亚仍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之中,任何建立统一中央政府的努力都将是一场艰苦的斗争。武装团体、部落和城市等地方行为体共同构成了利比亚强大的地方社会,成为重建中央权威必须要考虑的关键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