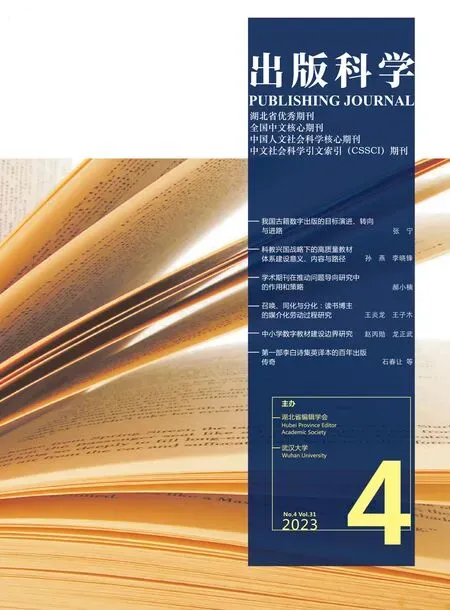中国古农书传播对日韩等东亚地区的多维影响研究
莫鹏燕 李 洁
(郑州师范学院传播学院,郑州,450053)(郑州师范学院文学院,郑州,450053)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重农抑商”的小农经济不断孕育出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相对先进的农耕文明通过对外贸易及外交活动,除输出至中国西部贸易线上的阿拉伯、印度等地区,更是东传至当今日本、韩国、朝鲜等邻近国家。不论是农作物、农具的使用与普及,还是《氾胜之书》《齐民要术》《陈旉农书》等可考农书书目的传入,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东亚国家的农业文明、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甚至政治变革。日本史学家藤间生大曾言:“日本民族从未开化的世界,进入到原子能时代,其间必须经过数千年的岁月,以及许多重要的发展。作为这种发展的第一步,是从中国输入水稻开始。”显而易见,中国农业成果的传入,对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的社会发展举足轻重。本文大致以中国古农书东传概况、东传影响及日韩农史学家对中国古农书的研究三方面为切入点,浅谈中国古农书在日韩等东亚地区的动态传播概况。
1 中国古农书的对外传播
中国古农书东传是“亲仁善邻”式的文化东渡,是东亚文化圈内自然的农学辐射。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依黄河、长江两水发育,农业文明起步较早。战国以降,铁犁牛耕的普及更是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有助于小农经济的迅速成长。在“重农抑商”的社会大环境下,在迅猛成长的农业实践中,一批批农学家展露锋芒,担任起理论总结的工作。自可考的战国《神农》《野老》始[1],西汉氾胜之有《氾胜之书》、东汉崔寔成《四民月令》、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唐朝李石作《司牧安骥集》……朝代更迭,历史变迁,长期稳定的小农经济社会的农书出版未曾间断。
中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引入着沿途国家的农作物品种和种植方式,也在东亚文化圈内充分发挥辐射作用,输出自己的农业技术、农业成果和农耕文明。隋唐—海上丝绸之路繁盛期,我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的交流愈加频繁。《行走的作物:丝绸之路中外农业交流研究》一文中写道:“中国古农书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至世界各国, 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2]尤其是造纸术、印刷术的应用和普及,使外来学者向本国输入中国古农书的载体由个人手抄本升级至官方刊印本,加快了中国古农书“走出去”的步伐。各朝代的中国古农书持续漂洋过海,被东亚文化圈内的日韩等地区广泛研习,并在其本土扎根成长。以日本为例,汉代《氾胜之书》传入后,与其本土农业实践相结合,迅速衍生出具有其本土特色的农书如岗岛秀夫、志田容子的《氾勝之書:中国最古の農書》;崔寔《四民月令》则有渡部武《汉时的岁时与农时》;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在日传播可考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唐李石《司牧安骥集》入日后指导成书平仲国的《仲国秘传集》及桥本道派的《假名安骥集》,同时代陆羽《茶经》则是荣西《吃茶养生记》的依托;宋楼璹《耕织图》是日本《四季辨作图》的前身,《陈旉农书》则为天野元之助《陈旉农书和水稻技术的开展》的蓝本;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可考在17 世纪末、18 世纪初传入日本,同时代日本还有借鉴徐光启《农政全书》的《农业全书》,参考喻氏兄弟《元亨疗马集》的《马经大全》。
中国古农书在东亚土地上的传播是因地制宜的,东亚各国家地区对中国古农书的学习是持续渐进的。中国古农书东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所载农作物种培技术及禽畜养殖方法等的实用性,而因农作物及禽畜物种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约束限制,故日韩等地对中国古农书的学习引入,就呈现出因地制宜的特点。首先,日韩国家国土面积及旱地资源有限,故其引入学习多为米稻等合适的高产农作物;其次,日韩等国区别于中国的气候特征—海洋性显著,决定着其引入学习的物种类型;最后,作为彼此长期交流互通的友邦,中华文化的魅力也决定着日韩等国学习的深入性与持久性。
以日本为例,就其引入的部分代表性书目,可看出学习的持续性和因地制宜性。以时间为线索,纵观其引入中国古农书,从被称作“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农业科学著作”[3]的《氾胜之书》,到被誉为“中国17 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天工开物》,贯通汉、唐、宋、元、明五代,易看出其学习的不间断性。再考其所习古农书的适用地域及内容概况:汉代讲黄河中游地区耕作原则、作物栽培技术和种子选育等农业生产知识的《氾胜之书》,记洛阳地区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发展状况的《四民月令》;北魏载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加工贮藏、野生植物利用及治荒方法的《齐民要术》;唐代适用于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等地,讲茶叶生长规律、品质优劣、加工烹煮、茶具制作等知识的《茶经》;南宋总结南方地区水田农事、养牛、桑蚕良方的《陈旉农书》;明载录许多江南湿润地带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的《农政全书》……多吸收中原地区黄河流域及以南地区的农耕文明成果,而对西北内陆亦或东北地域的农业成果收录难觅只言片字,可发现日韩农史学家对于生物地域适应性的考虑。
从中国古农书的传播背景到其入外壤的传播特点,这中间的传播途径是实践与理论并举,主动与被动共存的。实践与理论并举有两层含义。一为实践主导下的间接传播:日韩使者来华,亲身投入中国古农书指导下的农业生产实践,充分感悟中国古农书中相关知识,在切实掌握技术后,返乡二次总结普及。比较有代表性的属荣西与其所撰《吃茶养生记》:荣西作为来华修习佛法的日本僧侣,钻研佛法之余潜心研究中国的茶叶种植及饮茶之道,最终回国著成《吃茶养生记》[4];二为理论发力下的直接传播:中国古农书通过海上通道,直接被东渡华人或日韩回国使者引入,逐渐影响当地农业活动。如以手抄本形式在日本流传的《齐民要术》,有写于文永十一年 (1274 年)的名古屋市蓬左文库藏本,还有据北宋本过录的金泽文库本 (缺第三卷)—现存最早抄本[5]。这些书刊在很长一段时期的传播中,深深影响其农事活动。
主动与被动共存亦分为二说。笔者在此视日韩为接收主体,将“被动”释为中国官方贸易或私人东渡时对古农书的输出,而“主动”则为日韩使者对中国古农书的直接或间接引入。比如世人熟知的“鉴真东渡”,即日本对中国相关文化的“被动”接收,在此过程中鉴真为日本带去了众多书籍,其中不乏与农事相关书目,日本《本草医谈》所载木本药草种植知识,就与鉴真对《鉴上人秘方》的传播息息相关。“主动”则不可不谈朝鲜半岛地区,其对陆羽《茶经》精神—“俭”和“全真”的学习与本土化发展极具代表性。李崇仁、李行以及郑梦周等人不仅学习种茶制茶,更研究其中延展开来的茶文化,直至热爱茶道的大诗人李奎报时代,当今韩国的茶文化在那时渐成体系,发展至巅峰[6]。
2 中国古农书对日韩等东亚国家的影响
中国古农书东传,从微观处百姓的农业生活,到宏观上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它的影响是由点及面、多层渐进的。在农业方面增物种,拓领域;对文化陶染由表及里,潜移默化;就经济来说发展小农经济,催进商品经济;而以上生产力进步又律动着政治变革的必然性—社会变革。
就本土农业生活来说,随古农书一同入驻的生物丰富了物种,拓展着农业领域。以高丽为例,《世宗实录》载:“传旨户曹,各道移荞麦耕种,考《农桑辑要》《四时纂要》及本国经验之方,趁时勤耕”[7]这说明其荞麦种植领域出现之源为中国。另有高丽毅宗13 年(1159)所译北宋《孙氏蚕书》,向本土介绍普及了养蚕技术,开拓了桑蚕养殖领域。
对文化领域,从表层的图书编撰到深层的社会文化,再到更高一度的农耕文明,中国古农书在日韩等东亚地区的影响是“层林尽染”式的。
第一,影响着类似图书的编撰风格方式。最显著的属被日本誉为“人世间一日不可或缺之书”的《农业全书》,在编撰风格上,《农业全书》习《农政全书》的总论—分论的结构,效《农政全书》的“农本思想”,在首卷就点明阐述了农事的重要性;从编撰方式来看,中国《农政全书》采改前代所著而加作者评注阐释所成,日本《农业全书》则遴选徐书章节并附己所释而作。窥斑见豹,对比两书目录便可形象品悟:作者宫崎安贞大胆学习我国《农政全书》的体系和格局著成此书,可以说是对《农政全书》的本土化。
第二,促使其社会文化的多样化发展。《茶经》与《碧岩录》东传日本,其文化中从此多了“茶道”;《元亨疗马集》指导下《马经大全》的出现,见证着日本育马文化的成长;《农政全书》除对日本农业有指导性意义外,更促进了其国本草领域的学术研究工作,松岗玄达就在对此书“荒政”思想的研究下,于享保元年(1712)将书中的《野菜谱》《救荒本草》加“训点”并详注后刊行,1799 年,日本著名本草学家小野兰山又进一步刊行《正救荒本草、救荒谱》[8]。
第三,形成了类似于中国长期稳定的农耕文明。日本学术界普遍认为,日本稻作农业系中国传入。稻米种植传入日韩之前,其社会长期滞于渔猎采集时代。而水稻和中国古农书漂洋过海,使这些民族拥有了种植产物和日趋进步的生产技术,应运促进其社会文明的进步。渡部忠世在《稻米之路》中表示,比丝绸之路意义更重要,“稻米之路”是百姓之路,是人类大众生存繁衍的生命之路。这生动展露着中国稻米文化对日本社会的深刻影响。
在经济方面,中国古农书的传播促进着传入地生产力进步,带动了手工业发展,使小农经济活跃升级,也环环相扣地催进商品经济。
《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等书目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促使日本出现了像贝原益轩、宫崎安贞、佐藤信渊这些杰出的本土农学家,他们立足本国农业实际,对从中国传入的古农书或加以翻译总结、或作解读延伸,对本国的农业技术革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推动效应,增加了土地单位面积内产出,极大地提升了农业生产力[9]。以输入中国古农书为基础,日韩等国将书中理论深入应用到生产实践中,不仅渐形成本国的种植业、养殖业,还在这些日趋成熟的基础农业系统上发展出相关手工业,如上文提到的种茶烹茶、养蚕缫丝等。牵一发而动全身,生产力进步推动手工业衍生,小农经济的繁荣又悄然孕育着商品经济。长期较为稳定的小农经济社会在江户时代几近繁荣顶峰,和平的社会环境、繁荣的农业经济,此时人们手中的生产资料富足甚至盈余,再加上身份统制令[10]的催化,商品经济自然发育成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变革是生产力进步下政治进步的必然表征。日本学习中国谷物种植初期,先是由绳纹时代进入农耕社会。《〈农政全书〉在近世日本的影响和传播:中日农书的比较研究》一文还指出:“《农政全书》直接或间接地对日本近世农书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日本当时得到了广泛地普及和传播, 并对推动当时整个日本农业技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是促成日本当时展开‘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的一个远因。”[11]对于当时深受中国古农书影响的朝鲜半岛地区来说,亦如此理。
3 日韩农学家对中国古农书的研究
日韩农学家对中国古农书的研究聚焦于农书记载的农业概况及适用范围、成书体例及载录方式、中国古农书的本土化发展及本国农书的改进创新三方面,是秉持着因己制宜、创新发展的原则进行的。其研究大方向从未偏离因地制宜:他们研习中国古农书所载农业概况,又从中筛选适合本土自然及人文国情的部分引入。
韩国釜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崔德卿曾写道:“高丽后期曾两次再版(1349 年、1372 年;后者是庆南陕川本)元朝(1264 年)的《农桑辑要》,并且从中只挑选符合韩国现实的内容,之后又在14 世纪中期发行了《农书辑要》。”[12]日本亦如此,考虑到本国气候与土地资源限制,对中国古农书中水稻种植部分的学习便更浓墨重彩。如天野元之助的《陈旉农书与水稻技术之展开》与《火耕水耨之辩:中国古代江南稻作技术考》[13]。
《从几部农书的传承看中日两国人民间悠久的文化技术交流(下)》一文中说:“宫崎安贞编著《农业全书》,在体系、格局方面,大都仿照《农政全书》。”[14]的确如此,通过中国《农政全书》和日本《农业全书》目录比较,可以直观感受日本对中国古农书成书体例及记载方式的模仿学习。语言风格上,两书均节节平实凝练,字字恳切,既讲农业技术,又强调农业重要性;内容布局上两者都图文兼具,相互诠释;书目思想则都强调农本,唯一有区分的一小点是《农政全书》贯穿“以农为政”的线索,《农业全书》“贯彻”以农为业的观点。类似的模仿学习在日本借鉴中国成书的农业著作中均有体现。
中国《齐民要术》序讲,“今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号曰:《齐民要术》”“欲使天下之人皆知务农重榖之道。”而日本宽保四年(1744 年)荣堂本《齐民要术》的《新刻齐民要术序》写道:“民家之业,求之要术,验之行事,无不可者矣。”山田萝谷还在此提出,译注刊刻此书是“欲使本邦齐民有治生之要术,尚亦有利哉”。两者对比,不难发现日本对中国农业著作语言风格之效仿和对重农为业、劝民务农思想的贯彻。再比较日本宝历十三年(1763 年)平贺源内《物类品》与中国宋应星《天工开物》的轧蔗取浆图等[15],也易观察出日本对中国古农书内容布局方面的学习和精进。另载录方式上,若为书目,农学家便以文字记录的形式传抄;若为图画,农学家们便孜孜不倦地兼职画手,对其进行加工复刻,如以楼璹《耕织图》为蓝本的《四季辨作图》。
“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适当地借鉴有利于取长补短,一味地模仿只能滑向悲剧的深渊。作为自古以来对中国优秀文化虔诚见习的日韩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同样深知学习中国古农书的奥义。是故这些农史学家不只对中国古农书进行简单的翻译引入,更在传播过程中将其加以优化升级,进行本土化地创新发展。
就朝鲜半岛地区言,可考“茶”在陆羽《茶经》中称“嘉木”[16],而在草衣的《东茶颂》中谓“嘉树”[17],窥一斑而见全豹,这印证其对中国古代农书的学习借鉴。被誉为“茶学泰斗”的韩雄斌先生更是将陆羽《茶经》直接译为朝鲜文。在这些基础上,朝鲜半岛地区对中国种茶、制茶以及禅道与茶道的融合学习,从而产生的总结手册、礼仪典籍等,都可视为对种茶用茶的本土化衍生。
还有高丽对《农桑辑要》中元朝棉花种植的本土化适应。最初,高丽地区直接将《农桑辑要》直译为本土俚语刊行学习,但随着百姓将其适用到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李朝世宗王便要求三南各道访问有实践经验的老农并撰写勘察报告,命崔南善将这些报告汇集整理,于1429 年印出1000 册颁发各地[18]。亦有李朝后期为解决大规模饥荒问题,徐有榘将《农政全书》相关内容结合当时朝鲜实际,编撰成书《种薯谱》指导实践。
再如日本,中国北方旱地农业技术为中心的农书—《齐民要术》, 对日本湿地农业来说实际借鉴意义偏低,但为什么仍被国民传承发展呢?其承袭的,便是适合当时日本社会的“农本”思想。观日本“花道”,也是由中国佛教中关于花卉养殖及佛堂供花等书籍影响而萌芽成长的。拿早期中国流传的《妙法莲华经》来说,此书见证着花与佛的不解之缘,而日本也对诸如此类的经文积极学习引入,比较典型的有圣德太子和小野妹子,他们将中国佛前供花的文化渗透到了本民族文化中去。《由“佛前供花”到日本花道》一文中就有如此分析:“……《仙传抄》中有关‘唐样花(中国插花)’的记录,其中所记载的‘桥(阶梯)之花事’‘柱花瓶之事’‘横梁(梁柱)之花’等,与《清异录》中所记录的李后主在家中窗柱、阶梯等地方,以壹、简等插花装饰基本类似,这正是入宋求法的日本僧人将中国插花艺术传播回国的结果。”[19]再到宋明后世,由于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影响,佛教中的花文化也蒸蒸日上,我国农业著作中更是出现了育花的专题,譬如宋人温革所撰的《分门琐碎录》,详细载录了牡丹、芍药、荷花、水仙等多种花卉养育之法。作为中国花文化的学习者,日本当然毫不落下,相近时期日本的书籍中也出现了花朵专题板块,例如樱田绚的《花谱》。诸如此比,皆为东亚各国农史学家结合本土特色对中国古农书的衍生发展。
中国统一的历史相对较早,在长期中央集权制的稳定社会环境中,小农经济成长壮大,农业文明长期繁荣。作为农耕生活智慧结晶的各代古农书经久不衰,被不断东传至日韩等东亚地区,被当地劳动人民传诵借鉴,与其地农业实际融合发展。从华夏土壤到东洋岛屿,藕断丝连的农事生产经验,见证着中国古农书踏上的土地;从农业水稻种植到朝代政局革新,社会各维度以历史车轮的前进,讲述着自己在中国古农书影响下的升华;从汉代氾胜之的《氾胜之书》到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时代更迭中接续的传播节奏,诉说着历史长河里中国古农书的“川流不息”。中国古农书的传播是宽领域、长时期的,它似一石激起千层浪,由点及面,多维立体地作用于当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