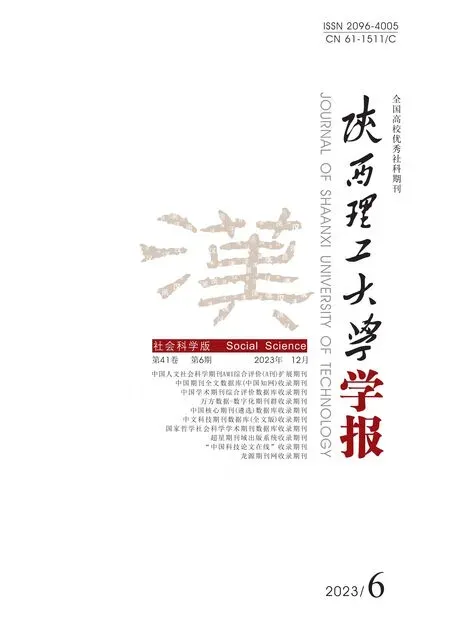赵之谦的“金石朋友圈”与石门名刻
杨 斌, 邵 华
(陕西理工大学, 陕西 汉中 723000)
在晚清时期,金石收藏之风大盛。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同治朝十三年间,为恢复秩序耗尽精力,所以文化方面无什么特色可说。光绪初年,一口气喘过来了,各种学问,都渐有向荣气象。……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1]33-34其实,早在咸丰、同治年间,金石学已经成为文人士子研究之滚滚洪流。可以从晚清文人士子所撰写之日记、信札、题跋甚至诗文中发现,在当时,金石碑刻搜访品鉴活动之繁密、参与人数之多,可以说令人叹为观止。作为汉中地域碑刻的杰作——石门石刻,自然成为这些金石家、书法家的收藏、临写、品评的重点对象(1)石门石刻之所以受到晚清学人的关注,主要不外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地理位置的原因。石门石刻所处之地理位置——连云栈道,在明清时期属于国家驿道,自然景观亦颇为状观;其二,艺术价值原因。石门石刻之名品《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石门铭》,书法苍古,充满着天然、放逸之艺术美。。在咸丰、同治年间,赵之谦与沈树镛、魏锡曾(2)有关魏锡曾的生平,参见杨斌《晚清金石学家魏锡曾年谱(上)》,《大学书法》,2023年第4期,第90-98页;杨斌《晚清金石学家魏锡曾年谱(下)》,《大学书法》,2023年第5期,第102-110页。、吴大澂等结成金石好友,他们大多博通经史、精擅书画,这些文人士子对金石的收藏、考证都抱有着极大的热忱。他们与常年居住于京师的潘祖荫、王懿荣等人,由相识至相交,群体合力,形成的以寻访金石、考证文字、刊刻著述为风尚的“京师金石文化圈”(3)当代学者程仲霖认为,同光时期京师金石文化群体主要包括如下几类成员:一是相对固定活动在北京地区的;二是在各地任职,致仕后寓居北京的;三是多次来京参加科考试,后到地方任职或归里的;四是科举成名后在各地流动任职的。显然,沈树镛、赵之谦属于第三类,吴大澂属第四类,而魏锡曾是因公事偶尔至京师的,无法归入此四类,但却是京师金石文化群体不可或缺的一类成员。详参《晚清金石文化研究——以潘祖荫为纽带的群体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0页。。而汉中地域的著名碑刻——《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石门铭》诸石刻,也成为他们重点搜访、考评以及在书法篆刻实践中追摹的对象。考察当前学界,有关晚清金石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实,但以专文来探讨赵之谦以及其友朋沈树镛、魏锡曾等对石门石刻拓本搜访、考评、研究的成果在学界还未有。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赵之谦、沈树镛等金石好友的题跋、信札、书法篆刻作品等为材料,结合其年谱、日记等著作,对赵之谦“金石朋友圈”的形成,赵氏及其金石好友对石门石刻的搜访和品鉴,他们在书法篆刻实践中对石门石刻的追摹进行考述,以期推进晚清金石文化史和石门石刻的研究。因笔者学力所囿,如有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斧正。
一、从江南至京师:赵之谦“金石朋友圈”的形成
发生在晚清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清政府与其展开的战争,对地方经济、政治统治、生活秩序的破坏相当严重,也对城市发展格局以及士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太平天国在当时信奉“夷教”,掀起反孔排孔的文化风暴,制造文化恐怖。“所过劫杀,恶经籍文字。见聚藏者火之,火不足秽之。且奉夷教,毁庙宇,得碑石皆仆之。不可仆,划之、击碎之。昔人竭金钱日力有之,以为大文奇宝者,顷刻灰烬。”[3]125沈树镛等江南士子,均遭受了此次浩劫。咸丰十年(1860)二月,太平军攻入魏锡曾的家乡杭州,在此次战乱中,魏锡曾“举家奔避,屋毁于火”(4)据赵之谦为魏锡曾所治“鉴古堂”印款:“自庚申二月,贼陷杭州,稼孙举家奔避,屋毁于火。”详参(清)赵之谦《钱君匋藏印谱赵之谦》,安徽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37页。。其时,赵之谦恩师缪梓战死,赖以生计的幕府亦已解散;四月,太平军攻破吴大澂的家乡苏州,四月初十日吴氏与家人“申刻,抵周庄”[4]4,之后其家宅被太平军占据;六月一日,周庄告急,吴氏一家于是前往上海避乱[5]8;十一月十五日前后,富阳又陷入战乱,魏锡曾则“避地黄岩”。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赵之谦接受好友傅以礼之劝,动身远赴温州[6];三月二十九日,沈树镛与在上海避难的吴大澂相约与翁文平、陶淇“同叙数日”[4]40;四月,赵之谦客居瑞安[7]73;九月,自瑞安返回温州;十二月,赵之谦由温州再入福州[7]80。大约在此际,太平军攻入沈树镛的家乡川沙,沈氏遂携家眷入京,这样既可以避太平起义之祸乱,又可以准备在京举行的会试[8]299。同治元年(1862)初,吴大澂奉母命,亦赴京应乡试,乡试失利后,馆于彭蕴章家[5]14-15;此年春,同在福州客居的魏锡曾和赵之谦始订交[7]83;十二月,客居温州的赵之谦与胡澍一起出发,于同治二年(1863)正月抵达京师;此年夏,魏锡曾则由训导改盐场大使,北上京师,入京师验放,于八月间亦抵达京师[9]。至此,这些来自江南,或因参加科举考试、或因公事的士子在京师聚首“奇赏疑析,晨夕无间”,共同探讨搜访金石、品鉴古物。
二、但恨金石南天贫:赵之谦的“金石朋友圈”对石门名刻的搜访和品鉴
受到太平天国战乱之影响,江南地区由豪门、贵族、士子收藏的古籍、碑帖、金石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和损毁。但在京师,由于帝都军事力量的拱卫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金石古籍的收藏仍然相当繁荣。“晚清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市场,无论是拓片的流通、集资椎拓或是影印出版,也渐趋发达,一般的拓片资料已不再需要层层人情的委托。”[10]234当时的京师琉璃厂,为金石文物的流通提供了便利条件,各地的藏书家、文物贩子皆汇集于此,成为晚清时期全国最大的书籍市场和文物集散中心。沈树镛与赵之谦等好友,在准备应会试的闲暇时间,常常出入于琉璃厂。作为晚清最杰出的书画家、鉴藏家、学者,沈树镛等人在碑学考证、著录方面的成果,皆受益于北京活跃的碑拓市场,晚清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就这样谈到:“欲网罗古刻非至都门终为坐井观天。”[11]26京师碑拓市场之繁荣可见一斑。
同治二年(1863)春,赵之谦与沈树镛、胡澍皆参加了此年会试,三人皆未得中。在会试不第之后,他们便将精力投入到金石碑帖的搜访和著述。其时,吴大澂、沈树镛、赵之谦、胡澍、王懿荣等青年才俊,均在潘祖荫门下走动,相互过从,游览厂肆,诗文雅集,以为常事。
在珍爱的碑帖拓本上,请名家考证、题跋,不但有助于金石碑帖在文人之间的流通,也可以使拓本身价大增。在同治二年(1863)期间,赵之谦与沈树镛、魏锡曾、胡澍来往极为频繁,除了为此三人刻制了大量印章,更为沈树镛等人所收藏的金石拓片多次题写跋文。在赵之谦此年所刻印章中,以九月九日所刻“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白文印章最具代表性,边款云:“余与荄莆以癸亥入都,沈均初先一年至。其年八月,稼孙复至闽中来,四人者,皆癖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12]23-24此印既记叙了四人由江南至京师的行迹、相识过程,也是几位金石好友密切交往的力证。而在此年,由于吴大澂既要在彭蕴章家坐馆授课,又要忙着准备应试,和沈树镛等人交往较疏。这些来自“南中”的“金石朋友圈”中,沈树镛是较为富裕的一位,他与魏锡曾对金石收藏有着近于狂热的喜爱,甚至为了买到心爱的碑刻拓片以至于“典衣缩食”,亦毫不顾虑。大约在此年八、九月间,沈树镛购得《石门颂》和《瘗鹤铭残字》,汇集《六朝造像》册,请赵之谦为其刻“汉石经室”青田石朱文印(见图1)。沈氏购得《石门颂》后,立刻请赵之谦校定并题写跋文。收到《石门颂》拓本后,赵之谦致信沈树镛:“《石门颂》已来,容校定而后书。……上均初同年仁兄大人。弟谦顿首。稼孙小印,昨夜已成,午后当携以与之。行灯一枚藉还,并及。”[13]292经赵之谦校定并书写题跋的《石门颂》有幸保存于世,跋文云:
此《杨孟文石门颂》旧拓本,闻为故家所藏,遭火毁阙十之四。均初从琉璃厂书肆得之,重裱成册,复经俗工傎(5)“傎”即“颠”的异体字。到二处。(“明”字重文,“奉魁承枃”误列“春宣圣恩”下。)计失首行下三十七字,后以“子午”下八字,“友”残下一字,“废”下三十二字,“弥光”下四字,“乾通”下八字,“纪纲”下八字,后凡百七十字。是刻真东汉人杰作,近来拓本漫漶,古意隐矣。此独字字秀发,乃剩者无几,劫灰久空,余烬自在,当何如宝之?同治癸丑十月,会稽弟赵之谦。
数日之后,赵之谦又为此拓题写跋文:
“后数日,均初又从破书中寻得首行‘躬’字以下二十九字,‘蓬路’以下八字,‘子由’以下三十二字,‘辅主’下八字,‘言必’下八字,遂补于后,示我,为之惊喜。神物当合,安得并前后缺失,一夕来归也?祷祀求之,以饱眼福。悲盦又识。”(计前后尚少一百八十字。)[8]173
从跋文可知,沈树镛所购之《石门颂》系前人所藏之旧拓本,且此本曾遭受过火灾,故残阙之文字达到十分之四。当时的拓本为了便于收藏、鉴定和临习,通常会请装裱师按原刻内容重新剪辑,再装裱成册。但由于许多装裱师文化学识较低,经常会将文字内容前后颠倒误装,使碑刻文句不可卒读。赵之谦则根据前人著述或别的拓本,仔细校勘缺漏、颠倒、多余之文字,并题写跋文于后。在校勘工作完成后,沈树镛又从别的残本中寻得缺失之文字,重新剪辑后再装裱,示于赵之谦。见到沈氏重新装裱的完整拓本后,赵之谦为之惊喜,并再次题写跋文一则。对于购来的金石拓本,沈氏经常亲自粘册装裱,以致“面糊满桌”,并求赵之谦、胡澍等人为之题跋,即使“被人耻笑,然不顾也”[14]。
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魏锡曾以编辑赵之谦印谱为由,返回福建,在京仅逗留三个月。同治三年(1864)春,沈树镛、赵之谦、吴大澂仍客居于京城。大约在年初,赵之谦致信远在福建的魏锡曾:
《西狭颂》有一旧拓本,甚佳。去冬得之陕西碑估董姓,渠有汉中全分(共两分)。索价每分八金。南中有人要否?弟则无力为之。[13]273
赵之谦在信中所称“汉中全分”可能指拓自陕西汉中的全份《石门十三品》,也有可能指以《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石门铭》《郙阁颂》(6)《郙阁颂》为汉代摩崖石刻,与《石门颂》《西狭颂》合称为“汉三颂”,原石在汉中略阳县析里(又名白崖)嘉陵江畔古栈道旁,现存汉中略阳县灵岩寺。《郙阁颂》虽为汉中石刻,却不属于石门石刻。为代表的汉中地方碑刻。据此,我们可以得知,在当时汉中石刻全份共“八金”,即八两白银。而在同治末年间,在上海制造局翻译馆任编纂的萧穆,月薪仅二十两白银(7)据萧穆癸酉年(1873)三月一日《敬孚日记》:“早杂检一切,后收到薪水银廿两。”详参(清)萧穆《敬孚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3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31页。。同治十三年(1874),赵之谦任职于江西书局期间“每月薪水银六十两,一切照知府式样。”[13]353可见,在同治末年,知府的薪水也仅六十两白银。在同光之际,旧本、孤本拓本价格比较高,因为旧拓本上多有名人题跋,为拓本增加了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新拓与其他时代的书画、古籍比较,价格也不便宜。赵之谦在信中所述,从“陕西碑估董姓”获得的“汉中全分”,虽然是新拓,但因为是全份,品类当然多,价格亦是不菲。对于赵之谦来说,在京师谋生本就不易,同时还要贴补远在家乡的儿女,用八两白银去购一全份汉中石刻,实属不易。但也可能是赵之谦故意虚报价格,以期从中获利,故询问好友魏锡曾或南方的藏家是否有人购买。“同光之际,拓本作为财富的意义进一步凸显,收藏家之间的竟争也日益加剧,即便是友朋之间的拓片交流,也需要银钱。”[10]248
同治三年(1864)八月,吴大澂与其弟大衡乘船南下,应江南乡试,以第六名中举[5]23。秋,赵之谦移居于永光寺中街南头路沈树镛宅[15]546,此地离琉璃厂较近,使他们寻访金石古物更加便利。同治四年(1865)三月,沈树镛、赵之谦、胡澍皆参加了此年会试,三人均未中。五月,胡澍准备南归,二十一日,潘祖荫与翁同龢为胡澍践行,沈树镛与赵之谦皆同座[16]428。八月,赵之谦亦离京南归。同治五年(1866)初,沈树镛因原配奚夫人已于前年在北京病逝,娶吴大澂之胞妹为继室[5]23,使得原本就互相倾慕的金石好友成为亲戚。此年五月,沈树镛返回家乡川沙。同治六年(1867)春,沈树镛客居于吴门(今苏州),购得《石门铭》旧拓一本,喜不自胜;此年夏,吴大澂再次进京,仍馆于彭蕴章家。同治七年(1868),沈氏仍赁居于苏州双林里,赵之谦、胡澍、吴大澂则客居于京师,准备应此年的京师春闱。赵、胡二人皆未得中,吴大澂则中蔡以常榜第三名会魁,朝考入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5]26,可谓春风得意。此次会试之后,赵之谦开始大力谋求纳赀捐官。
同治八年(1869)冬,仍客居于苏州的沈树镛将《石门铭》残本重新装裱,并题签、作跋:“《石门铭》旧拓残本,嘉兴张氏清仪阁旧藏,同治丁卯春得于吴门己巳冬装成记之。”[8]83跋文中所述“嘉兴张氏清仪阁”即嘉道年间著名金石学家张廷济之藏书楼。从此则跋文可知,沈氏所藏之《石门铭》为张廷济经藏之拓本。同治九年(1870)二月,寓居苏州的沈树镛,再次翻检自己所藏金石拓片,为《石门铭》作跋,跋文云:“此北朝人书,最疏宕有奇气者,溯原篆分,中与《瘗鹤铭》印证。庚午二月,均初书。”[8]83在作此跋后,沈树镛后来还为此拓本再次题写跋文:“此北朝人书,最疏宕流逸者,邓怀宁、包安吴多从此得力。郑斋。”[8]44沈树镛认为《石门铭》在北魏书法中,属于最疏宕有奇气者,与焦山《瘗鹤铭》可相抗衡。 并认写书法大家邓石如、包世臣之魏楷多得力于《石门铭》。赵之谦之魏碑书法亦多借鉴《石门铭》,他《章安杂说》中评“《石门铭》最纵宕”。认为此碑开启初唐书家欧阳询、褚遂良书风之先,赞美魏碑古刻“一波磔、一起落,皆天造地设,移易不得。”[13]1167其魏碑书风很好地将“碑”和“帖”完美地融合,形成雄放豪迈而不失研美之态的独特书风。可以说赵之谦、沈树镛对《石门铭》的收藏、考评,是《石门铭》“经典化”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通过沈树镛、赵之谦等人对石门石刻的收藏、题跋活动可以看出,他们在治学思想上的一些特点:一是崇拜汉魏古刻,有意标举汉魏之遗物,追求“古意”。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朴学考证精神,注重对碑刻原文本的还原。三是力图发掘碑刻的艺术气息。赵之谦盛赞《石门颂》为“东汉人杰作”“字字秀发”。将《石门颂》飘逸、疏宕的风格运用到书法、篆刻创作。
三、碑帖熔合,印外求印:赵之谦的“金石朋友圈”在书法篆刻实践中对石门名刻的追摹



图2 赵之谦刻“北平陶燮咸印信”(9)采自《赵之谦印谱》,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在同治年间寓居北京期间,随着赵之谦所见碑刻的增多,其书法、篆刻创作亦深受石门石刻的影响。大约在同治二年(1863)秋,沈树镛购到《石门颂》拓本后,赵之谦曾临摹《石门颂》并题写边款赠与友人,如赠与“芷汀世仁兄大人”的隶书条屏(见图3)。边款云:“《杨孟文石门颂》临似,芷汀世仁兄大人正,弟赵之谦。”此幅作品,书风奇纵豪迈,字形舒展。因为是赠友人的书作,赵之谦仅将后面四言句式的歌颂杨孟文之贤德的部分颂文临写。款文中交待此作以“临似”手法表现原刻,“临似”即现在所说“意临”,即临习碑帖者不拘泥于原碑、原帖的外在形似,力图发掘碑帖内在审美意趣的一种临摹方式,即所谓“不徒貌其形似,但就其心得之字,追取前人神韵,挥洒而出之”[17]135。历史上的书法大家董其昌、“八大山人”皆以此种方式学习古代经典。可以说“意临”式的书写,是艺术高手的再度创作。赵之谦此作更多地强化了《石门颂》舒展、飘逸的风韵,在线条的刚劲生辣方面略逊于原刻。

图3 赵之谦临《石门颂》(10)采自岩出贞夫编《覆刻悲庵賸墨》,日本东京堂,1976年。


图4 赵之谦为魏锡曾所刻“钜鹿魏氏”印(君匋艺术院藏)

图5 《开通褒斜道刻石》之“钜鹿”二字(11)原石现藏汉中博物馆。
同治三年(1864)秋,赵之谦移居于永兴寺中街沈树镛居所,在此居住将近一年。在此期间不但为沈氏治印多枚,还为多次其所藏拓本题写跋文。其中为沈树镛所刻“灵寿花馆”白文印,边款云:“法鄐君开褒余(12)采自《赵之谦印谱》,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道碑。为均初刻。悲盦记。”(见图6)结合印面可以看出,章法上赵之谦借用《开通褒斜道刻石》整体密实、浑为一体的布局,在字形结体方面则有意强化了此碑“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字形内部空间。印章很好的借鉴了此碑的疏与密、争与让的形体特征,将《开通褒斜道刻石》经历风雨侵蚀线条所具有的苍茫感,运用到篆刻作品中。

图6 赵之谦为沈树镛所刻“灵寿花馆”印(13)“余”读作“斜”。《石门颂》原拓“斜谷”即作“余谷”。宋欧阳修《集古录》云:“以余为斜,汉人皆尔。”
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在京任户部郎中的胡澍因病逝世。次年(1873)二月,沈树镛亦病殁于苏州双林里,其身后遗物,大多藏于吴大澂家。其后,赵之谦、吴大澂均到地方任职,曾经在京搜访金石的好友各自星散。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吴大澂被任命为陕甘学政,在公务之余,常常寻访古刻。此年秋,吴大澂视学陕南汉中,策马至汉中褒城,寻访石门石刻,并聘请汉中拓工张懋功为其拓石门诸碑刻,撰写《石门访碑记》。对于此次访碑活动,当代学者白谦慎《吴大澂和他的拓工》、蔡副全《吴大澂石门、西狭访碑始末》已多有论述。通过此次石门访碑之行,吴大澂更加对汉魏碑刻尊崇之极,认为“汉人书体,大者如《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及各碑题额,小者如仓颉庙碑阴、碑侧题名,更以款识字参之,无美不备矣……。”[19]50光绪元年(1875)正月二十六日,吴大澂出棚赴甘肃,先考庆阳,次泾州、平涼、固原各属[5]52。二月,吴氏至固原,途经魏光焘所修三关口大路,作《三关口修路碑记》,并摹勒上石,此碑原石现存于宁夏固原博物馆。关于此事,在此年九月吴大澂致李慎(1827—?)的书信中曾谈及:“勤伯仁兄大人阁下:……魏午庄观察属书《三关口开路记》,略仿鄐君碑书之。午翁属交邓榕墅太守购石摹勒,未知在省否?祈阅后转交为感。……弟大澂顿首,九月十四日灯下。”[20]18-19吴氏在函中指明此碑系略仿《开通褒斜道刻石》而成。细察吴大澂所书此碑,在整体布局上,纵有列、横无行,将《大开通》体兼篆隶、有横直而无波磔的书体特征表现了出来。吴氏此碑第六行之“开通”,第七行之“广”,第十三行之“万”等字,全仿自《大开通》。相较于《大开通》,吴氏所书《三关口修路碑记》,在浑穆苍劲、厚重拙朴、自然奔放等方面不足,而在气息淳雅、古朴端庄、整饬严谨等方面则有余。
碑拓的流通,是晚清书刻艺术传播的重要推动力。碑拓尤其是汉魏碑刻,成为晚清书法篆刻界的新宠、碑学风尚的取法资源。因石门石刻位于在当时比较偏远的西北汉中,赵之谦及其好友对于石门石刻的搜访,主要依托于京师琉璃厂,他们或亲自寻访,或向碑估定购。很少学者能像吴大澂那样,利用公务之便亲自访拓。但无论是通过古董市场购买,还是亲自访拓,皆可以有力地证明,他们对石门石刻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重视。正是通过赵之谦等人对石门石刻的签藏、题跋、考证、临摹、再创作,使得石门石刻日益受到晚清、民国以至当代学者、艺术家的关注,最后“强化”为碑刻艺术的经典。在对石门石刻倾注浓厚兴趣的赵之谦等人中,由于各自财力、学力、兴趣的不同,关注点亦自不同。沈树镛和魏锡曾偏重于鉴藏,赵之谦偏重于艺术,吴大澂则偏重于考据。但中国的学术向来注重综合,所以在晚清时期,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且诗书画印兼善的文人士子比比皆是,赵之谦等人就是这样的代表。他们对石门石刻鉴藏活动,除了资考经史之外,还力图发掘碑刻的艺术气息,并将其用之于书法篆刻艺术的创作活动中。如今,斯人已逝,仍然可以从赵之谦的“金石朋友圈”与石门石刻的金石古缘中,窥见当时金石收藏、考评风气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