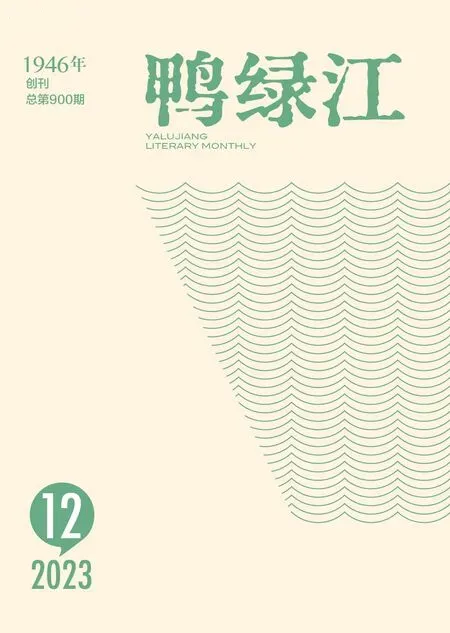冬夜未雪(组诗)
龚学明
苍茫大地
它愿意承受,也能够承受
而我在自己的呼吸里
天地太小,胸闷气短
延展的大地
从华东到华北:初冬
平原上的色彩后退
树木依旧向上,挺立
微弱的色彩,低调的时辰
你看不见湖泊的悲伤
这些眼睛学会克制,并
深沉,老练
远方是一片混沌
既是原始的,也是自然
努力的终结
借助它,人间得以
找到无数的借口延续:
“我们并不懂得,因此心安”
列车驰向北方
南方在干净而精致的车厢里
思考:世界到底多大
棉衣内的身体,何时是
大地的一个部分
云
这明明是个好天:阳光灿烂
寒露后的万物,表面宁静。
可是“感觉”就这样值得相信?
反应迟钝的物种一味独欢
你看天上的云朵,它们分明
正在扭曲和痉挛;它们并不
舒展,在风的轻推下,自由
自在,向着想要的方向而去
更多的云已奔向天边,互相
紧挨,形成高高的围墙状:
乌青的颜色,绷紧着紧张感
天象在云和阳光中——分裂
有没有受惊的生命,比如
必须在天空中生活的鸟类
有的殒命自绝,有的震撼难抑
而风继续流动,不顾左右
冬夜未雪故作
没有落下的心事仍是心事
打开白天的一道口子
晨起的自然依旧晦暗
我真的需要雪吗
它们早已走入记忆深处
雪的消息提前泄露
而我要把雪比作妈妈
妈妈,一想到您远去
我抑制不住花朵般地颤战
此刻的我却十分迟钝
雪不会回来,雪
终究要来;鹅黄的花瓣
像我脆弱的心又升高一寸
我甚至不敢进入回忆
过沧州
下午二时半,车过沧州
天色昏暗,天空压了下来
土地平坦,树木孤独
不见野猪林、草垛和大雪
草色枯黄,偶有的工厂闪过
高压电塔列队向远
沧州的温暖不容易到来
从小说到季节,一千年阻隔
不,当我的诗歌收尾
太阳光从云层钻出,击中我心
我得重新描述
所有已低调的生命获得好运
这些幸运的水一小片,一小片
看到的人,都已放心
从铜陵回南京高铁上
在繁昌,看到田里的稻茬
干枯的白色意味已远离收割
初冬,杂树低垂
芦花举着散漫的表情
因为阳光
山间零星的白墙有约略的反光
而山中雾霾正成功隐藏
那些很打动人的曲线
池塘啊,小小的池塘
装得下变化中繁复的情绪吗
我固执记起离开铜陵时
旅舍窗外的三只椋鸟
黑白相间的身体一闪,飞入
我敏感的记忆:列车在向
芜湖驰去,窗外看不到
一只飞动的鸟;水面,这
恍惚的美和痛,在增多
一切都在呈现之中
藏起的必是短暂之物
我们一直在构思生活,并不
如意:撤回既定的,只是
匆匆写就的诗句
——它们那么美而无用。
在虚拟中活得久了,想
换一种工具:将笔换成刀
温柔的刀比诗意真实
切开面包,让胃尝到甜
但我不知道用之还能做些什么
离开
离开人类聚居地:他们创造了
文明——房屋、市井、古老和
崭新的建筑,巷子——我
曾行走其间,没有一个熟人
还没有相识,没有温暖之感
他们的菜肴搭配得莫名其妙
不能体会这个城市里的
人是幸福的——他们持久地
活着,看不出是在忍受
我们出城,随着火车远离
像一种撤退——楼房,高压电塔,
快要干的小河,灰色的
草木,一闪而过
夕阳将部分景物镀亮
而天空以高远保持严肃和神秘
一个学文的人不能说出
现代文明:我们的多少感觉
和生活被其裹住;当荒芜
渐多,在原始的前方,我们
会否再次绕进都市的陌生
诗人的苦恼是深沉的,三个
诗人向三个家的方向远去
他们被时间和空间安置,唯有
诗和质疑统一了标志
时寒冷
喜鹊的叫声穿过槭树的
紫红;它背负着
一个名字的兴奋,并
不知道喜乐何在
而气温下移
不愿听命;不,也或许
受谁指使
而一群石头如故
圆圆的脸和表情依旧
干涸的溪床交出它们的子孙
我坐在十月时坐过的
石头上
愿意双方有友人之感
这一回,没有引来暖意
红色的小果子少了一些
喜欢在一条路上反复行走
只是要找回
最好一次的感觉
毯子
一块毯子覆在我的身上
我和冬夜都不拒绝
漆黑中的雨声
年关在轻轻召唤
薄薄的毛毯像提前的呼喊
抑或来自远方的无奈
我在眼前独自的空间里
犹疑要不要继续一则故事
一块彩色的毯子上
花朵朴素而真实
像消失的叮嘱幻化而成
在冬天,寒冷属于既成事实
毛毯也不是身外的多余
而我,年轻时不用毛毯
冬天不懂冬天的寒冷
在此刻的雨夜,大地
就要覆上白雪
我接受毯子的爱并非不必
失去是时间在隐身
我高兴我今天保留快乐
风干的玫瑰花
旅舍的桌上,一只
竹制的圆形盆里,浓烈的
香味已经浅幽,这经历过的
事物用淡红的眼神回避
诉说……
一次旅程其实不长
从期盼到惜别,一眼望见
而我们走过的湖深不可测
看到的季节,借着
淡黄的银杏,红褐的
水杉树悸动不安
这个世界愿意承接我们
而我们对之又了解多少
我们的快乐和悲伤
也都是真实的,只是
盲目而无助
暴躁,任性,甚至愤怒
饱满的感觉在裂开
时间之光在吸走
酒给予的酡红的部分,留下
干净、空洞、持久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