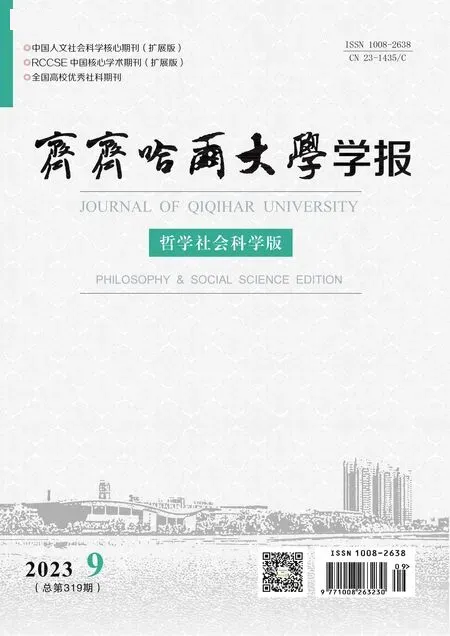《奇鸟行状录》中的隐喻和记忆象征
孟 辰
(辽宁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奇鸟行状录》是村上春树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创作的一部作品,村上春树在美国创作这部作品时正赶上海湾战争,虽然并未亲历战争,但是在随时有可能爆发战争的环境下起笔必定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村上春树也认为:“‘准战时体制’的紧张空气对自己写的小说有不少影响。”[1](第4卷“解题”)这部作品有很浓的历史印记,有关战争的描写也很多。主轴以“诺门坎战役”展开,通过日本军队和苏蒙联军在华的战斗开启了历史记忆,战争场面描写细致生动。但是,战争的反思和历史记忆文学化的部分并不是作者的临时起意,在《奇鸟行状录》创作之初,村上春树在图书馆中阅读了大量有关“诺门坎战役”的相关书籍,因此,从战争记忆的角度来创作作品不是偶然才有的想法,而是作者创作的初衷。这部作品也成为其转型之作,村上春树运用了很多隐喻手法,非常巧妙地书写出了战争记忆,这些意象将历史具像化。哈佛大学的杰·鲁宾教授称赞该作品是“村上春树创作的转折点,也许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2]
隐喻是村上春树小说中经常运用的写作手法,例如,《且听风吟》中“鼠”象征了孤单和寂寞,而“猫”则是作者的化身;《寻羊冒险记》中的“羊”象征了西方思想的引入;《海边的卡夫卡》中的“图书馆”象征了记忆存储;此外《第一人称单数》中的“奶油”、“深入地下室的酒吧”等都具有象征意义。这些文字在文章中如同“摩斯电码”一样,彼此关联,却不是非常明晰,引发人们的好奇心,读者只能从中揣测作者的本意。对此村上春树也并不想给出明确的解释,“当然,我不是在写推理小说,不会追求明快地解决所有的谜。”[1](2003:431)正如邹波所言,文学意象不是孤立的存在,在作家的创作中,一个意向往往由创作灵感所触发,然后在作品中逐渐增殖,形成彼此联系、意义丰富的意向群。[3]
《奇鸟行状录》中作者也运用了隐喻手法,不过这些隐喻之间并非是独立的,它们相互关联,与历史记忆的叙事有着密切关系。作者透过隐喻的象征描写了错位的历史记忆,并将集体记忆重构。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曾说过,“文字不仅是永生的媒介,而且是记忆的支撑。文字既是记忆的媒介又是它的隐喻”。[4]作为战后作家,村上春树在作品中不断尝试用隐喻来探究追忆过去,唤醒人们缺失的记忆,体现了其建构战争记忆的意愿。
一、“拧发条鸟”隐喻历史记忆追溯
《奇鸟行状录》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贼喜鹊篇》、《预言鸟篇》和《捕鸟人篇》。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冈田亨在寻找丢失的猫的过程中认识了少女笠原May、通灵加纳马耳他和其妹妹克里特,后来,冈田亨的妻子久美子不告而别,冈田亨发现久美子是被其哥哥绵谷升控制的,绵谷升是国会议员,邪恶的政治家。冈田亨最终潜入井底穿越时空并击杀绵谷升,救出久美子。
《奇鸟行状录》中的“奇鸟”指的是“拧发条鸟”,而“行状录”可解释为编年史或是年代记,也就是时间的象征。发条鸟的职责是拨动指针以此调节时间,每当故事情节发生巨大转折时,拧发条鸟都会拨动象征着时钟的发条并发出“吱吱吱”的叫声,拧发条的鸟是个时间驱动装置,用一个小发条来驱动世界,唤醒隐藏着的历史事件和集体记忆。
作品中的主人公冈田亨曾多次听到发条鸟的叫声,主人公更是被偶然认识的少女笠原May称作发条鸟君。这一称呼也暗示了主人公冈田亨的职责,即找到发条,开启时钟的开关,回溯历史记忆。另外,整篇小说都是以“我”这个第一人称描写的,因此,“我”对于历史记忆的追溯很有可能代表了村上春树本人的意愿。书中也借“我”的口吻提示读者“拧发条鸟”是溯及过去的倒叙写法,因此在小说中,每当记述一个故事时,都有一个编号,如<拧发条鸟年代记的#8>等等,对应了某一时段的历史故事。故事中总是充满了危险,拧发条的鸟也不断地用叫声发出提示。例如,小说中冈田亨结交了肉豆蔻与肉桂母子,肉桂的父亲被人杀害,他看到家中树下父亲的心脏,听到发条鸟的叫声,从此不再说话。母亲想尽办法都无济于事,医生认为是精神疾病,那肉桂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心灵创伤呢?在第29章“肉桂进化链中失却的一环的”中主人公冈田亨发现拧发条鸟年代记#8是肉桂写的故事,而且不只是这一个故事,整个年代记中的16个故事都与之相关,而拧发条鸟年代记中#8的故事正是“新京动物园事件”的延续,有着极高的关联性。那么由此可知,发条鸟拧动的正是肉桂头脑中的记忆拼图,这个拼图与肉桂母亲肉豆蔻所叙述的“新京动物园事件“可以拼在一起构成一个历史记忆。而这种记忆和父亲被害的记忆叠加在了一起,因此,在多重打击下肉桂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创伤。
此外,在“新京动物园事件”的描写中也有拧发条鸟的出现,间宫中尉参与战争时,一个被处决的中国人拉着兽医一起掉入坑中,间宫中尉补了一枪,与此同时间宫侧耳聆听到发条鸟的叫声,他看不到鸟的居所,只是有一种想吐的感觉。
“拧发条鸟”不时地在危险时刻出现,使得历史故事中惨烈的部分显得尤为突出,作者不断地通过“拧发条鸟”来追溯战争记忆,也强化了读者对于战争的感受。
虽然“拧发条鸟”会带我们回溯历史记忆,但对于历史记忆会不会消失,作者还是在小说中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文中有相关的描写,“拧发条鸟”发出的信息是通过文字、图像等方式传递于“我”的,每次传递都似乎拧紧了发条,不断提醒我不要忘记去追溯历史记忆。而当笠原May诉说着男朋友如何被她所害之时,发条又似乎松了,对于“我”的追问,笠原May很不想回答,好似想让记忆抹去。“拧发条鸟”随时能调节松紧,如,记忆可以反复提及也可以搁置不问。一根根发条也许会消失,记忆传递的危机便显露无疑。
二、“猫”隐喻个体记忆危机
除了“拧发条鸟”,“猫”同样也是一个有关记忆的隐喻。众所周知,作者村上本人对于猫是非常喜爱的,还专门为“猫”写过散文《大致若猫》。他认为,“猫”特立独行、高雅且安静,“猫”既有灵性又能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掌握分寸。研究村上春树的铃村和成也认为,“猫”就是村上作品主人公“我”的化身。于是,在村上春树的很多文章中都有“猫”的出现。如,村上春树的第一部作品《且听风吟》中就提及了“猫”,“猫”是哈特菲尔德最喜爱的东西之一,实际上,哈特菲尔德是作者喜爱的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化身,这种爱屋及乌的方式,也是作者对于“猫”喜爱的表现。在《弃猫》中,村上春树还描写了与“猫”相关的记忆。“猫”作为珍贵的东西,是村上成长的记忆,也是父亲的牵绊。“猫”失而复得时,“猫”的命运似乎与父亲的幼年遭遇一样,寄人篱下、流离失所。“猫”在其中不只是一个有着相同遭遇的命运象征也暗示了个人记忆。而在结尾处,作者对于“猫”命运的担忧,又将这种隐喻升华。“猫”可能在树上化成白骨,也可能消失不见了。“猫”象征了一代人的记忆,而这种记忆似乎游离于在与不在之间,耐人寻味。这段珍贵的记忆也似乎超越了单纯的个人记忆,而成为了一种历史记忆的书写。
在《奇鸟行状录》中,对于“猫”的这种象征意象的书写也是很明显的。“猫”是主人公冈田亨和妻子久美子的共有物,也是两人的共同喜好,最终促成了婚姻的结合。“猫”本是象征着冈田亨和妻子的美好记忆,但他却有个奇怪的名字叫“绵谷升”。“绵谷升”是久美子的哥哥,也是国会众议员,在小说中代表了权力意志的邪恶人物,这种邪恶属性暗示了个体记忆中不太美好的部分,随之而来的是“猫”的离奇失踪,美好记忆的代表物消失了,不久,冈田亨与妻子关系破裂。直到后来“猫”又返回家中,给两人的关系带来了转机。冈田亨决定将“猫”的名字修改,“将大凡与“绵谷·升”这一名称有关的记忆、影响和意味清除干净。”[3]文章在最后也提到了妻子给冈田亨写的信“请爱惜猫,猫能回来我真感到高兴。我觉得那只猫彷佛是我与你之间萌生的好的征兆。当时我们不该失去猫的”[5]712
“猫”的失而复得与《弃猫》中“猫”的遭遇很相似,作者多次借用“猫”来表达内涵,体现了这一象征意向的重要性,而《奇鸟行状录》中“猫”的经历暗示了个体记忆的缺失与个体记忆的复位过程。在“猫”回归以后,冈田亨将“猫”改名,竭力遗忘并清除“绵谷·升”的影响,象征了个体与过往经历的关联的决断,也展现了个体从恐惧、逃避到面对现实重塑自我的整个过程。
三、“井底之水”隐喻集体记忆的重构
《奇鸟行状录》延续了以往的写作风格,突出“后现代主义”色彩,时空自由转换,虚拟和现实相结合。其中不乏想象的内容,比如,关于“井”的描写。小说中“井”的意象起到了连接时空的作用,作者通过描写间宫中尉“井”中体验引出历史记忆中的战争感受。主人公冈田亨通过“井”下的延展穿越到虚拟世界,并最终击杀恶人绵谷升,救回妻子久美子。“井”这一意象连接了过去和现在,也连接了虚拟和现实,作者用隐喻传递了重要的内容,书中符号化的文字让人印象深刻。在小说中无论是“拧发条的鸟”、“猫”还是“井底之水”、“痣”都展现了其独特的语言风格。
“井”的隐喻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多次出现。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中就有对“井”的描述:“随着身体的下降,青年觉得井沿逐渐变得舒服起来,一股奇妙的力开始温柔地包笼他的全身。”[6]“井”似乎是个神秘之所;《挪威的森林》在第一章就长篇幅的描写了直子记忆中的“水井”,直子认为,一旦掉入井中便会摔伤或摔死、也没人发现,一个人孤零零苦苦挣扎,很显然,“井”在这里是一种孤独和恐惧的象征;《1973年的弹子球》也提到了,“我”的心被挖了几口井,井口有鸟掠过。透露着孤独和迷茫。“井”看起来是一个个的个体,被黑暗笼罩,充满了恐惧。但村上春树作品中的“井”并非是个死胡同,“井”的底部可以相互贯通,正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心底的沟通可以缓解内心的孤独。与这几部作品中“井”的意象不同,《奇鸟行状录》中的“井底之水”不再是单纯的“孤独”的意象,它是对前者的超越,有了更深刻的含义。在这里“井”暗含了对于集体记忆的追溯与重构。
小说的第五章作者以“柠檬糖中毒、不能飞的鸟与干涸的井”为题开启了对枯井的描述。在“我”与笠原May的对话中强调了这是一口“没有水的井”,“我”认为,其中必隐藏些缘故。而“井底之水”哪去了?又隐喻了什么呢?
在“间宫中尉的长话”中,“井”再次出现,间宫在执行任务时被捉住并被扔进一口干涸的深井中,甚至几近绝望,后来通过射进来的阳光和本田的援救才得以生还。这里的“井”是战争中用来处决战犯的工具,在“井”中的时光是间宫人生中的至暗时刻,间宫在深井中的痛苦体验加深了人们对于战争残酷性的认识,同时也将人们带回到那段历史记忆中。“井”是连接现实与历史的通道,但是“井”中没有水,在井中的记忆就很难传递给外面的人。
在小说的高潮部分,主人公冈田亨潜入井下,透过井壁抵达绵谷升的邪恶世界,最终用棒球棍击杀了绵谷升,救回了妻子久美子。与此同时,“井底之水”涌出,“井早已干涸早已死去,现在突如其来地重现生机,莫不是同我在那里做的有关系?有可能。”[5]695这里“我”所做的事情正是在井中发生的,“我”与井下试图控制思想、篡改记忆的绵谷升做了了断,保护了“我”的真实记忆。而井底物体变得支离破碎暗含了记忆的推到重启,关于“井底之水”的涌出,本田曾提示“我”:“最好注意水”。“作为话语我倒是没忘(毕竟那含义太奇妙了,很难忘掉)”[5]695
那么,“井底之水”到底意味着什么?村上拒绝对作品中的意象做出清晰的解释,他表示,符号本身既在文本语境中承担一定的意义功能,同时,又在不同读者群的阐释中生发出丰富的意义之链。[7]虽然村上没有对此进行明确的解释,但不难看出村上赋予了“井”丰富的含义。“井”从干涸到涌出水来的过程即是冈田亨直面战争记忆并将记忆带出的全过程,是有关于历史记忆失而复得的过程,也是将历史与现实相连接的过程。
四、“痣”隐喻战争记忆的传承与疗愈
“痣”在《奇鸟行状录》中也是一个重要的隐喻,出现在井下以及新京动物园的记忆书写中。主人公“我”在井下长出了一颗光鲜鲜的“痣”,“它是我的一部分,我必须接受它。”[5]463在井下“我”将注意力集中在“痣”上,通过意念穿越了井下的墙壁,深入到黑暗世界,展开了与绵谷升的对决。我凭借“痣”的力量穿越了墙壁,可以说“痣”是“我”找寻到暗黑世界的一把“钥匙”。而正是这颗“痣”带我穿越了时空隧道,追溯了历史记忆。
同样,脸上有“痣”的是赤坂肉豆蔻的父亲,他是一名兽医,曾和两名中国杂役随同射杀队行动。在新京动物园中首先射杀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满洲国”老虎。而后又杀害了豹、狼、熊等等。赤坂肉豆蔻在回忆父亲时说:“可我记忆中的动物园是否真的就是和我所记忆的一样的那个动物园,不知为什么我却没有把握。怎么说好呢,有时我觉得那实在过于鲜明了”[5]483。有关战争的记忆,虽然战后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战争记忆又是如此鲜明,作者透过文字表达了战争记忆留给后世的深远影响。小说的第十章的结尾处写道:“十五日正午,收音机播出‘天皇终战诏书’。七天前,长崎市区被一颗原子弹烧成废墟。几天后,‘满洲国’将作为虚幻的国家淹没于历史的流沙中。脸颊有痣的兽医将在旋转门的另一间隔与‘满洲国’共命运。”[5]491这段对于战争结局的描写,直观地反映了村上春树的战争观。村上认为战争的结果是惨烈的,无论是侵略者还是受害者都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痣”如同刻在脸上的印记,痛苦的战争记忆并不会因此而消亡,同样有“痣”的还有主人公“我”,这段记忆将由一代人传递给另一代人。
除了隐喻记忆的传承外,“痣”的出现到消失也象征了记忆创伤被治愈的过程。小说中描写“我”与绵谷升决斗的部分,体现了这一点。“痣”是“我”在井下寻找绵谷升时长出来的,“痣”一直是“我”的典型标志。小说第三十五章描写了一则电视的报道,特意强调了绵谷升议员被一个脸上有“痣”的三十岁男子用棒球棍打晕,而这个人酷似“我”。但在现实世界中这些事情并非“我”所为。这之后“我”在井下以同样的方式击杀绵谷升。因此无论在现实世界中还是在非现实世界中,“我”都使用同样的方式与试图控制“我”的思想、篡改“我”的记忆的绵谷升做了了断。当“我”解救了妻子久美子之后,脸上的“痣”也消失了。“痣”在这里象征
总之,村上春树在《奇鸟行状录》中展现了直面历史记忆的决心。正如刘研所诉,村上的小说“用物语重新叙述历史,发现历史深处潜藏着怎样的记忆,记忆的固化与忘却中又呈现着当代日本人怎样的心态”。[8]
在记忆书写与反思历史的过程中隐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架设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小说通过“拧发条鸟”、“猫”、“井中之水”以及“痣”的隐喻帮助人们回溯了这段历史记忆,以物语的形式将记忆传递并重构,力图唤醒更多人的共鸣,这在战后的日本文学中是不多见的,彰显了村上春树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担当。